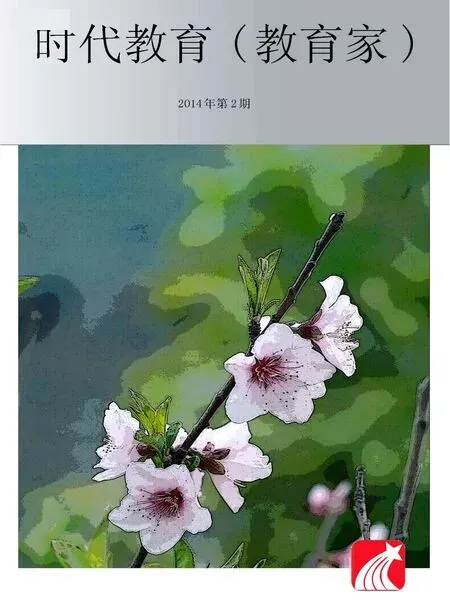“读碑说古”王家葵
本刊记者_庄真诚
“读碑说古”王家葵
本刊记者_庄真诚

在当代社会,一位研究古典文献的学者变得备受瞩目,听上去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王家葵做到了。
四年前,王家葵在南方都市报开辟了一个读碑专栏,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自己:“斋号玉吅,杂家者流。爱好偏多,见识偏浅,曾经不自量力,点将印坛,品藻书林。今又技痒,继续以论碑说帖文字,骚扰读者,贻笑方家。”
除了读碑说古,王家葵对《神农本草经》和道教也有着深刻的研究,而他本人却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医药学教授。
读碑即是读史,这需要深厚而广泛的文史知识和考据文献的能力,并不容易。看似简单的一块字碑,背后牵连是一整套的历史、书法理论、书法版本、史料故事的文献资料。在王家葵的随笔里,他旁征博引,字里行间贯穿许多历史趣闻、宗教和轶文掌故。
“我不是一个大家,我只是以业余身份进入几个领域,然后在这几个领域内,别人承认了我研究者的身份。”王家葵对本刊记者说。从这一句话里,可以听出两个信息,一是他同时涉及了几个领域,二是他成为了这几个领域的专业人士。
他承认,如果非要来总结他能同时成为几个领域的专业研究者的因素的话,那么对文献的考据能力,可能是让他能同时贯穿几个领域的关键。
考据又称考证,是中国古代正统学术里的一种方法,指的是对古籍的字音、字义以及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等问题进行考核和辨正。
“考证”这一概念在南宋时已有。但直到18世纪,才成为一种学术宗旨。
人们总是容易忽略18世纪在整个近代学术史上的承前启后作用。但是只要把眼光从社会关系转到社会思潮,就不难发现,知识阶层对中华帝国正统学术的批判早在18世纪就已达到高潮。而中国的知识阶层长期生活在宋明理学的古典阴影中,直到西方实证科学的涌入,才催生出中国传统学术在研究方法上的转变,最终导致了知识话语权的倾斜。
一
王家葵点了一杯素毛峰,开水入杯,杯中的茶叶被搅得上下翻动,抿了一口茶,他便开始娓娓道来:
“我是在文革期间成长的,在这十年里,整个教育都是十分散漫的,我们除了简单的语文、数学之外,没有其他的科目。不像现在提倡素质教育。更不要说那些书法啊,篆刻啊。我父母虽然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了解这些东西,但不精通。但可能是天性的原因,我喜欢‘舞文弄墨’,给我一支笔我就可以乱画,打发一段时间。直到上了大学后的一年冬天,大概是十一、十二月份,我跟平时一样,拿了一支毛笔,蘸了点墨水,就在本子上写字,无意间我写了个‘大’字,第一次觉得,我写的字还有点好看。”
王家葵把他的母亲叫过来看这个“大”字,母亲评价说:“这个字像是隶书的字体。”
“什么是隶书?”王家葵不懂。母亲于是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五体书正气歌》字帖给他看。在翻开字帖的一瞬间,王家葵跟触电了一样,觉得字体太美了。
从这以后,王家葵对书法完全入迷了,他以前做事基本只有三分钟热情,唯独书法,他彻底钻进去了。读大学时,空闲时间多,他便跑到图书馆去借与书法相关的书,没有老师教,他就按照书上写的入门步骤学习。首先要学会临帖,石鼓文的篆书,颜真卿《多宝塔》的楷书,他通通借来看,慢慢揣摩。几个月里,他就把《正气歌》写了很多遍。母亲没想到王家葵对于书法有如此高昂的兴趣,便将他推荐给自己在四川大学任教的一位对语言文字颇有研究的朱姓旧友认识。王家葵学术道路的转折,就是从与这位朱老先生的师徒关系开始的。
“当时的朱先生六十多岁,胡子全白了,留得很长,很仙风道骨的样子。他从里屋慢慢出来,和他见面的那一幕,我现在想来都很有戏剧性。他年长我48岁,为了表示尊敬,我就喊他朱爷爷。朱爷爷听我妈说了我的情况后,很有兴趣,就把我招到他的房间里去,跟我谈话。他让我写个字给他看,让我用篆书写我姓名里的‘葵’字。”正说着,王家葵拿起一支笔,在本子上写了个篆书的“葵”字,指着这个字说,“这个篆书的‘葵’,下面就像六把叉,写这个字是很考技术的,因为要写得很匀称。朱老先生考我也是考的这个字。我写完后,他看了看,觉得我写得还不错,就允许我每两个星期到他那去一次,同时我们也开始了书信的交往。”
朱老先生出生于20世纪初,行事作风严谨、讲究。他从不直呼王家葵的姓名,而是称王家葵的“表字”——曼石。
“朱爷爷拿到我的信就给我说:‘曼石,你称呼我太白是可以的,你这个信写得好。’然后,他再给我指出信里面语句不通和需要改正的地方。”
从此以后,王家葵便开始了和朱先生长达十五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朱先生从未刻意去教授王家葵什么知识,他酷爱看书,每当有一个见解或者体会,就写下来和王家葵讨论,话题广泛,“这完全是古代贵族式的教育,师生之间的谈论,没有主题,老师和学生都自己学习,遇到问题我们就不断的交流。他有时候也问我问题,但不是为了考倒我。我有问题也请教他。他读的是语言学,对文本和文字要求是很严谨的,他看到奇怪和生僻的字,就叫我去查阅。”
这些看起来有些碎片化的交流过程,给王家葵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收获,“可以说,朱爷爷言传身教带给我的东西,远远超过我从小学到博士这十几年所学习到的知识。不仅是我的学术行为,甚至我个人性格的形成,也是跟这位老师分不开的。在一定程度上,他性格的一部分已经传承到我身上来了。”
二
考据学者认为,有效的知识锤炼来自对外在事实不偏不倚的观察, 朱先生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格,很快在王家葵的学术研究上体现出来了。
不久之后,王家葵无意中看书帖《急就章》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急就章》是西汉元帝时命令黄门令史游为儿童识字编的识字课本,全文共1394字,内容涉及了当时社会的姓名、服饰、饮食、器物、人体、鸟兽、草木等各方面,如同一部小百科全书。作为一本儿童启蒙读物,从汉朝至唐代,《急就章》一直是流传于民间的主要识字教材。
《急就章》里面也有很多草药的名字。王家葵本身就是药理学出身,对药物的名字很敏感。
《急救章》第二十五篇,罗列了31种汉代药物:
灸刺和药逐去邪,黄芩伏苓礜茈胡。
牡蒙甘草菀藜芦,乌喙附子椒芫华。
半夏皂荚艾橐吾,芎藭厚朴桂栝楼。
款东贝母姜狼牙,远志续断参土瓜。
亭历桔梗龟骨枯,雷矢雚菌荩兔卢。

“汉代的药名和今天的药名,在字的写法和发音上,都是有些不一样的。具体是怎么不一样,名字的叫法发生了哪些变化?我的兴趣来了,这个跟我的专业有关系,我就想以此来做一番研究。我当时的愿望是为这些药名做一个鉴证,叫《鉴书》。”
王家葵的神情突然变得兴奋起来,声调开始有点高昂。他用手指在桌子上写着字,说:“比如黄芩的‘芩’字,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今’字,是指类似‘蒿’的一种植物。然而在《说文解字》里,这个‘芩’字写作‘菳’。‘今’和‘金’不是一回事,为什么这个字有这种不同的写法呢?”
在文本研究上,王家葵认为应该追根溯源弄明白,一件事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王家葵作品《张二刘鹊桥仙》
“做这个就不容易了,就要开始要找资料了,资料还很多。我就顺藤摸瓜,顺着思路走,既然涉及药名,那么就要去查阅《神农本草经》。问题就出来了,《神农本草经》上说的,怎么和我之前看到的、了解到的差别那么大呢?要么是我之前看到的描述错了,要么就是我手上这本书错了。《急就章》就被我搁置到一边了,我决心要弄清楚《神农本草经》相关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考证学里面的校勘方法,其目的是恢复古籍之笔下原貌,当然包括作者笔下的误字。
“我把关于《神农本草经》的问题研究透了,光论文就做了有十篇。实际上学界对于《神农本草经》的认识,是存在一些欠缺的,我的研究就是想把这个问题给弄清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又涉及其他相关问题,比如汉代的历史,汉代的学术文化,就挖掘了很多东西出来。这些都是环环相扣,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的。”
王家葵抿了一口茶,继续说:“中间有很多细节,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而以后的学术道路,也就这样自然而然展开了。”
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的学问总是围绕着思想上的演绎,却缺乏逻辑化、演绎化。而从18世纪开始的考据学提倡慎重求证、反对空泛粗放的论证方法,这正好弥补了哲学和传统人文科学治学方法的不足。
王家葵致力于的,也是这样一个辨伪的考证步骤。
三
“后来,我在《中国书法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又开启了我书法研究的道路。那篇文章写的是唐代书法家欧阳询,欧阳询的儿子叫欧阳通,这篇文章写欧阳通早孤。《旧唐书》上是这样写的: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书。每遗通钱,绐云:‘质汝父书迹之直。’说的是欧阳通父亲死得早,他妈妈徐氏让他学习父亲写的字,但欧阳通不喜欢学。那个时候欧阳通家里已经很穷了,母亲为了让他好好写字,就对他说,我们家现在的钱都是卖你父亲的字换来的,欧阳通听到他母亲这样说了以后,就开始勤奋学书了。
我看这一段时,老觉得有点不通,我想,首先欧阳询官及太常博士,怎么会缺钱?其次,欧阳询死的时候是八十五岁了,难道欧阳询六七十岁才有了欧阳通?也不太可能。所以,欧阳通怎么会‘早孤’呢?我就觉得这里面有文章,于是我就像当时研究《神农本草经》一样,开始追溯这个故事。”
说到关键点,王家葵突然将端着的水杯放在桌子上,直起身子来。
“原来这个故事是弄错了。我发现《新唐书》《旧唐书》里都有这个故事,最后我找到原因了:这个故事很可能是欧阳询和他父亲欧阳纥的故事。欧阳纥曾经担任南陈广州刺史和左卫将军的职务,在隋朝的时候因为举兵反陈失败,被杀了。欧阳询变成了孤儿,被他父亲的好友收养。这是在《陈书·欧阳纥》里面的一段记述。但是在《新唐书》里,就变成欧阳询和儿子欧阳通的故事了。所以,我为了考证这段故事写了篇文章,叫做《欧阳通早孤事迹考辨》。”
18世纪考据学兴起,一些倡导“实事求是”学风的学者开始采用“辨”体论述方式,把考辨形式视为建立务实、公正、客观学风的关键因素。考证成为了考证学知识理论产生的中心议题。文献真伪、著作时代的考辨是为其他目的引用史料必备的首要步骤。辨伪是运用一系列文体、文风鉴别方法考订古书真伪的精密学术方法。

王家葵是第一个发表关于《论书启》书信正确顺序文章的专家。发表后,又写成了一篇文章。
对于这段故事,他娓娓道来:“作为医药学家,陶弘景一直是我专业研究上一个重要人物,陶弘景除了是一位医药学家,同时是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他还有一个碑刻特别出名,叫做《瘗鹤铭》。梁武帝萧衍没称帝的时候,便与陶弘景认识了,萧衍非常敬佩陶弘景的才能,几次想请他出仕做官,都被他拒绝了。后来没有办法,萧衍就通过和陶弘景书信往来,进行一些探讨。其中有九封信便被编成了书,就是《与梁武帝论书启》。九封信里,梁武帝四封,陶弘景五封。这几封信感觉前言不搭后语。我认为这个顺序有点不对,我不轻易相信任何既定的东西,文献也好、实录也好,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合逻辑,我就要去考证它。哪个先?哪个后?我就根据当时的背景把它们重新串起来。一来一去,发现有很多可以勾连的,甚至有些书信还有遗漏,我就开始查漏补缺,又重新把九封信串了起来。”
四
提到碑刻,它和书法关系和渊源是最深的。碑刻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当时,人们出于官方或纪念的目的,把篆、隶体铭文镌刻于石碑上。到了汉代,书法家的主要名作都镌刻于石头上。考证学兴起之后,金石学自然又成为考据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时的金石学摒弃了前代看重的艺术鉴赏,转为对重要庙宇、陵墓、碑石及其他研究材料都作了十分全面的记录。字体学与碑刻学从古至今都是相互影响,考证学引入到金石学后,人们开始分析字体,关注和讨论字体在不同时期发生的变化。
王家葵把水杯放在一边,继续说:“汉代出的一个碑刻,叫做《肥致碑》。这个碑我以前就知道,重新开始看的时候,觉得这个书法字体有点另类。之前我已经看了很多碑帖,我一万本书里面有三四千本都是碑帖,所以我一看就觉得不太对。我就写了一篇《肥致碑考疑》,我怀疑这个碑是伪造的。”
在王家葵的《肥致碑考疑》中,原文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汉碑分行有一定之规,若以碑名列第1行,则正文首句若“君讳某字某”必居第2行首,以示醒目,如孔宙碑首行为标题“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铭”,其下曳白,“君讳宙字季将”句居次行首。肥致碑则连续书写。又碑中有两“诏”字,“诏闻梁枣树上有道人”句,提行示敬,而“诏以十一月中旬”句,不提行亦不空格,此又前后不统一 。
王家葵从格式上质疑,这不是属于汉朝应有的行文格式,文章还从字体、碑例中引证怀疑。
由于之前在文献梳理和考据学方面的积淀,王家葵慢慢走上研究书法的道路,常涉猎诸如碑帖、书法理论和书法历史方面的书籍。他说自己并不是想成为什么大学者,他能同时涉猎几个领域,完全是研究文献学时打下的功底。

“并不是说我有多么出色的天赋和能力,我只是在文科领域研究过程里,跳出了文科研究的局限性而已。”王家葵说。
话题转入到对学科的认知上来了,王家葵直言不讳地说:“当代文科学术方法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把感性当做证据来思考。”
他说,最近十年来,文科的研究陷入了困境,而就在不到一百年前,已有一批研究国学的大师把中国文科及文献研究提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而考据和考证,正是近代国学最核心的治学方法,国学大师钱穆、季羡林都是以考据学家自称。国学的考证方法吸收了西方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当时的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现在回顾中国各学科的学术成就,寻求有关中国学问的渊源,则不难发现,国学的兴起,正是由于考证在现代中国学术发展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考证,正是使传统学术转向现代学术的起点。
王家葵认为现在文科方法丢失了这样一种推演求证的能力,“现在的文科考证做到一定程度上就无法继续了,陷入了空想,如果是个错误的结论,那么在做形而上的推演的时候,就错得更远。我觉得这是传统思维带来的弊病,而西方的文科研究是严密的,先比较,然后由证据衍伸到结论,由结论再推演。虽然理科是属于在西方现代科学体系下构建起来的,它本身的思维,实际上有很多逻辑化的东西,要严谨得多。但是,追根溯源地说,这并不是理科和文科思维,而是跟我们本身的文科训练有关系。本身正派的文科训练是应该更严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