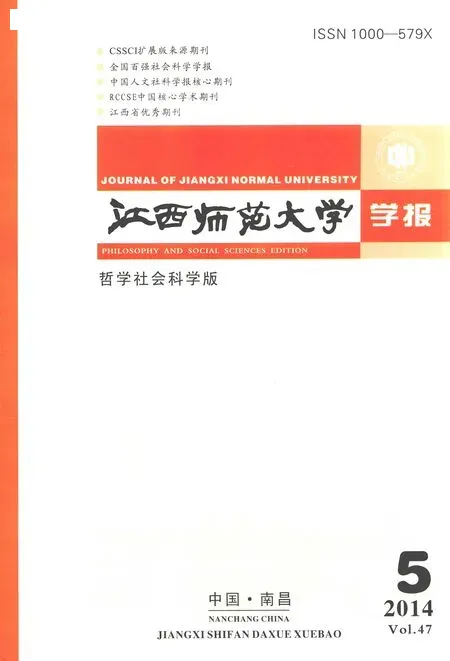《卖花女》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刘茂生,王 英
(江西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卖花女》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刘茂生,王 英
(江西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萧伯纳的戏剧《卖花女》讲述了卖花女伊莉莎意图通过语音矫正和文法学习成为上层社会优雅小姐的故事,生动地展现了伊莉莎在人生重大变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人际困境和自我身份的迷失。以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为基础,通过主人公伊莉莎做出身份选择的伦理环境,探讨伊莉莎改变自我的动机以及此后所面临的伦理身份困惑,揭示导致其伦理困境的根本原因。萧伯纳通过讲述伊莉莎的故事,集中展现了当时英国社会个体阶级身份与伦理诉求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并对该社会中个体寻求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寄予关注,从而传递出深刻的伦理意蕴。
萧伯纳;《卖花女》;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身份
《卖花女》(Pygmalion)(又被译作《皮格马利翁》)是爱尔兰著名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萧伯纳的代表作之一。该剧作讲述了英国皇家学会的语言学家希金斯(Higgins)和朋友匹克林上校(Pickering)打赌,在六个月的时间内将目不识丁、粗俗不堪的卖花女伊莉莎(Eliza)教导为一名“上等人”,一位举止优雅、谈吐不俗的上流社会小姐的故事。剧本诙谐幽默、妙语连珠,不仅展现了剧作家萧伯纳高超的语言写作能力,更展示了其对当时英国社会不同阶层的细致刻画和深入观察。该作品在1912年出版发行之后,立即获得成功,并于1956年改编为舞台剧在百老汇上演。1964年导演乔治·丘克将之改编为电影《窈窕淑女》,搬上荧幕。歌舞剧与电影的视觉推广使得萧伯纳的这部作品家喻户晓,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国内外学者大多已从神话原型批评、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批评以及比较文学的视角对该剧的社会主题、人物特征以及剧作影响进行了阐释。金柏莉·伯曼(Kimberly Bohman)认为“‘逝去’的叙述贯穿于这部作品”,[1](p110)探讨了剧作人物伊莉莎爱尔兰身份的消失与毁灭。萧伯纳的戏剧创作多以涉及社会问题见长。邓宁豪斯(Friedhelm Denninghaus)在对萧伯纳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进行了总体的对比后进一步探讨了该剧作的主题。[2]《卖花女》通过讲述卖花女伊莉莎试图通过语音矫正和文法学习成为上层社会优雅小姐的故事,生动地展现了伊莉莎在人生重大变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人际困境和自我身份的迷失。文学伦理学批评正是“从伦理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3](p13)然而,要真正深刻解读其面临的困境,则必须“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现场解读和阐释”。[4](p14)正是该剧所设定的特定伦理环境,使得伊莉莎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卖花女》讲述的是社会底层人物的悲惨遭遇,客观地展示了当时英国的社会面貌,同时更深入地揭示了当时英国的社会问题。因此,伊莉莎所处的伦理环境、对社会的伦理诉求及伦理身份的转变是萧伯纳关注社会问题的最佳注脚。立足伊莉莎做出身份选择的伦理环境,探讨伊莉莎改变自我的动机以及此后她所经历的伦理身份困惑,从而找寻导致其伦理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作为萧伯纳社会问题剧的伦理价值所在。
一、伦理环境
《卖花女》的前两幕细致刻画了伊莉莎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伊莉莎出身于伦敦丽松林区,那是一个“连猪圈都够不上”*文中所引原文皆出自萧伯纳的《卖花女》,杨益宪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不再一一注出。的穷人居住的地方,而家境富裕的有钱人就可以住在公园路这种富人聚居的地区。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指出地理空间“从来都不是中性的”,[5](p102)社会中只存在“阶层化的地理空间”。[6](p124)伊莉莎所处的地理空间清晰地表明她的下层阶级身份。伊莉莎的下层阶级身份不仅体现于她糟糕的居住环境,也体现在她与他人打交道的情形中。当这个贫穷的卖花女出现在街头时,几乎人人都对她嗤之以鼻。有一次伊莉莎和一群人一起躲在廊檐下避雨时,卖花女趁机向匹克林上校兜售自己的鲜花。然而她缠着上校买花的话全被希金斯记录下来,伊莉莎大惊失色,认为做记录的人是警察探子,而她将面临非法售花和坐地起价的起诉。她立即大哭大喊,发出各种难听的声音来替自己辩解,并请求匹克林上校和周围的人上前为自己作证。这不仅反映出伊莉莎极为糟糕的生存状况,更是其难以摆脱的下层阶级身份的最好体现。
糟糕的生存状况和下层阶级的身份迫使卖花女必须屈从当时的社会规范及道德准则。伊莉莎的父亲杜立特尔(Doolittle)对此颇为不满,为此他大胆地进行了控诉:“咱穷人是不配得一点好处的穷光蛋”,“绅士们认为我们不配”,并无所顾忌地质问希金斯和匹克林:“绅士们的道德是什么?还不是不给咱穷人钱的借口吗?”[7](p119)虽然杜立特尔是为了讹诈希金斯才说出这番话,但这种看似蛮不讲理的论调却不经意间道出了上层阶级在道德上对下等公民蛮横的压制。与此同时,主人公伊莉莎的口音被希金斯斥为“难听”和“粗俗”,她也因此不得不忍受希金斯对她颐指气使的态度。这一切都雄辩地说明,即使伊莉莎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上层阶级的说话方式,她也不可能真正消除其下层阶级身份的特征。正如剧中所揭示的,希金斯教授始终认为伊莉莎是他在大街上捡回来的“一块料”,一个试验品,根本谈不上伊莉莎是作为平等的个体而存在。伊莉莎永远也不可能摆脱其作为下等人的伦理环境。
二、伦理身份
人的社会存在必定赋予一定的社会身份。“社会身份指的是人在社会上拥有的身份,即一个人在社会上被认可或接受的身份,因此社会身份的性质是伦理的性质,社会身份也就是伦理身份。”[4](p264)伊莉莎对自己身份不平等的状况显然并不知情。她所看到的只是作为语言学家的希金斯如何通过人的口音辨别身份的本领,以及希金斯有能力教导有钱人改正口音,成为在上流社会言谈优雅的绅士或淑女。在这种情形下,伊莉莎自然会迫不及待地来到希金斯家里,向他表明自己如何不愿意在大街上当个贫贱的卖花女,希望他能够教导自己学习“有钱人讲的话”,从而成为一个“花店里的店员”。在她看来,成为花店的员工,她就有了份体面的工作,从此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卖花。她将再也不必担心因为在街头兜售花朵而受到警察的殴打和起诉。她觉得这一职业将彻底改变她街头卖花女的耻辱身份,甚至让她得以改变下层阶级的身份。伊莉莎希望自己能够以平等的姿态卖花,而成为花店店员是实现这种平等身份的关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社会等级差异的花店店员与买花的有钱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血脉相连的伦理关系仍有根本的区别。花店店员与顾客之间的联系是社会交往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关联。而对伊莉莎而言,这种伦理关系的构建是其对自身职业身份的选择与为此做出的努力而形成。店员与兜售者有着本质的不同,花店店员相对于街头兜售的卖花女来说,是被认可和接受的。伊莉莎对此的看法是,在卖花给上等人或有钱人时,店员是不需要言语就可以表明自己是一个“正经姑娘”。伊莉莎对自己身份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卖花本身。
《卖花女》的主人公伊莉莎不止一次强调自己是“正经人”、“正经闺女”。对这一身份的重视,从她身为卖花女咄咄逼人、看似粗鲁的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在伊莉莎以为自己遭受了监视可能受审的情况下,她用令路人难以忍受的口音和土话为自己辩白,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当听到希金斯要求別斯太太(Pearce)为伊莉莎买新衣服、并承诺会教导她成为男人喜欢的淑女时,伊莉莎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她“扬着头”坚决地说:“咱要走了。这家伙有神经病,咱可不要疯子教咱念书。”伊莉莎毫不怯懦地强调自己“不要新衣服,新衣服自己会买”。作为穷苦人家的女儿,女孩儿大了是要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伊莉莎正是在此情形下被迫走出家门,自食其力,而她谋生的途径就是街头卖花。伊莉莎当然明白不劳而获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会极大地伤害她的自尊心。伊莉莎作为下等人的身份与她渴望受到尊重的矛盾无时无刻不在折磨她,以致无法摆脱其内心的焦虑与困惑。
三、伦理困境
伊莉莎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这“不正经的女人”的耻辱身份,从而使自己陷入更大的伦理困境。当伊莉莎准备走出希金斯家时,匹克林提议,希金斯教授在六个月内将伊莉莎培养成一名谈吐举止优雅的女士,并与他打赌。这让希金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认为教导如此“低俗、粗俗不堪”的伊莉莎是个很大的挑战。因此,希金斯极力挽留伊莉莎参与此次实验。希金斯要求伊莉莎接受他六个月的培训,学习正确的发音,并告诉她六个月后她就可以像花店里店员那样讲话,可以像个上等人一样去参加宴会,别人再也认不出原本那个“不自量力的卖花女”;她将会实现做花店店员的梦想,“拿七个半先令”的工资。伊莉莎想象着可以穿漂亮的衣服,坐着汽车,举止言行优雅动人,她受到极大的诱惑,于是同意参与这场实验。然而,伊莉莎欣然接受此项任务时,她显然没有意识到她将面临的风险。剧中借別斯太太之口陈述了伊莉莎将来的困境,即实验结束后的伊莉莎又该去往何处?希金斯教授与匹克林当然可以满不在乎,作为接受实验的主角,年轻的卖花女只能沉浸于六个月的实验而处于虚幻的世界里,她从未考虑自己是否仍然能像从前那样自食其力。
伊莉莎此时面临的伦理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伊莉莎与希金斯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六个月后,伊莉莎获得了成功,正如希金斯所说的那样“创造发明新的伊莉莎”,她学会了装扮自己,也学会了优雅的文法、美妙的语音,学会了“上等人的礼貌和习惯”。但实验结束之后的伊莉莎愈加惶恐不安,当希金斯热烈地祷告着“谢天谢地,总算完了”的时候,伊莉莎猛然瑟缩了一下,她的美丽面容变得阴沉可怕,她“倒在地板上”,发疯似的扳扭着自己的手指。希金斯并不关心伊莉莎内心的感受与未来的生活困境。希金斯对伊莉莎的关注和帮助,只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实验成功后的希金斯与匹克林如同完成了一项巨大的任务,沉浸在自己的喜悦中。他们眼中的伊莉莎只是一个赌注,一个可雕琢的物件。拥有上等人礼貌和习惯的伊莉莎也意识到了实验结束后,希金斯对待她仍然像对待之前的卖花女一样,像对待“厨房里的小丫头”一样,像对待“脚底下的泥土”一样,对以全新姿态出现在眼前的伊莉莎视而不见。六个月前的伊莉莎只是浪迹街头的泼辣的卖花女,是大家眼中粗鄙的、毫无教养的但能够自食其力的大胆的丫头。但是在接受了六个月的教导之后,伊莉莎本人也承认跟上等人待过一段时间以后,“跟下等的普通人在一起是过不来的”,“也无法回到大街上去”。伊莉莎甚至把希金斯和匹克林上校当作自己真正的朋友。然而,让伊莉莎不能接受的是希金斯只把她当做自己的工作和仆人,态度粗暴,更无平等可言。她无法被上流社会所接纳,内心始终深处矛盾的焦虑之中。
二是伊莉莎伦理身份发生的转变加重了其面临的困难。事实上,真正让伊莉莎陷入困境的是她身份的转变。她由流浪街头的卖花女被教导成了上等人家的小姐,但却不能拥有上层阶级的财产,没能自力更生地生活,也不能“依靠任何其他的人”;她虽然穿着光鲜,谈吐优雅,但却“是一个奴隶”,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人。伊莉莎身份发生的变化未能改变她窘迫的生活,她虽然外表如同一位高贵的上等人家的小姐,衣着体面,谈吐优雅,却不能养活自己,只能依靠婚配或她意外获得一大笔遗产的父亲生活。这对个性独立的伊莉莎来说,当然是无法接受的严酷事实。同时,伊莉莎发现即使自己的身份发生了改变,希金斯仍然是以对待下等人的态度与她交往,她在希金斯教授面前仍是一个地位低贱的卖花姑娘。伊莉莎幡然醒悟,“一个上等人和一个卖花姑娘的区别不在于她怎么做,而在于别人怎么对待她”。伊莉莎试图学习上等人的礼节,获得新身份;然而当她真正习得了上等人的语言和习惯,这些习得的东西却成了束缚伊莉莎自由生活、积极向上的枷锁。伊莉莎从希金斯教授那里获得了优雅的仪容,却不能从他那里获得自由生活的途径。她不自由并不仅仅指生活上行为上或者言行的不自由,更是指对其伦理身份的束缚。之前的伊莉莎虽然是一个人人讨厌的卖花女,却能自力更生、自由自在地生活。换句话说,虽然她出身卑微、受人鄙视,却可以拥有独立的人格与尊严。当她习得了上层阶级的语言特征和习惯,反而不能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生活,只能做一个依附于他人的寄生虫,看似光鲜的身份变化让伊莉莎愈加显得卑微而遭人唾弃。
伊莉莎发现六个月后的自己成了任人摆布的玩具,她内心的挣扎、无助使她的自我意识再次爆发,最终选择逃离了希金斯教授的家。她竭力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而渴望回归真实的自我。希金斯自然也不会接受只是改变了语言习惯的伊莉莎,其所谓上层阶级的身份不过是虚伪的装饰,其本质仍然是下层阶级的卖花女。伊莉莎“除了我叫她想的说的以外”,根本没有属于她自己的思想。伊莉莎也终于在六个月之后认清了现实,逐步瓦解了当时的坚定。她痛恨自己的懦弱与无力,渴望实现全新的自我。
《卖花女》深刻揭示了当时的英国社会个体在自我重塑过程中遭遇的伦理困境。卖花女伊莉莎试图通过学习上层阶级的言谈举止来跻身上层社会,从而改变她卑微的身份。但是她并没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种愿望。在剧作结尾,伊莉莎仍然是借助意外获得大笔财产的父亲才摆脱她耻辱的下层阶级身份。伊莉莎最初看似美好的愿望让她失去了自食其力的力量,也迷失了真正的自我。伊莉莎虽然取得外表、谈吐等自我转变的成功,却同时陷入了更为糟糕的伦理困境。她在追逐所谓高贵社会身份的同时,更失去了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萧伯纳通过讲述伊莉莎的故事,集中再现了当时英国社会个体阶级身份与伦理诉求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对该社会中个体寻求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寄予了关注,从而传递出深刻的伦理意蕴。
[1]Bohman,Kimberly.Undoing Identities in Two Irish Shaw Plays:John Bull’s Other Island and Pygmation[J].The Annual of Bernard Shaw Studies.2010,Vol.30.
[2]Denninghaus,Friedhelm.Die dramatische Konzeption George Bernard Shaws:Untersuchungen zur Struktur der Bühnengesellschaft und zum Aufbau der Figuren in den Stücken Shaw[M].Verlag W.Kohlhammer,1971.
[3]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
[5]Bourdieu,Pierre.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责任编辑:张立荣)
AnInterpretationofLiteraryEthicsofPygmalion
LIU Maosheng,WANG 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Jina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George Bernard Shaw’sPygmaliontold a story about Eliza Doolittle,a flower girl who managed to turn herself into an upper-class lady by learning good pronunciation and proper grammar,and vividly displayed how she got trapped in ethical predicament and identity crisis in that process.By adop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thical environment in which Eliza made her choice of ethical identity,explored Eliza’s motivation to establish a new identity and the ethical identity confusion hereafter faced by her,and revealed the basic reason for her ethical predicament.Through this story,Bernard Shaw revealed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class identity and ethical complaints in British society at that time which was difficult to reconcile,and paid attention to the possibilities of individual seeking self realization in the society,thus conveying the profound ethical implications.
Bernard Shaw;Pygmalion;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ethical identity
2014-09-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与政治的伦理表达:萧伯纳戏剧研究”(编号:14BWW049);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世纪英国戏剧批评研究”(编号:12WX11)
刘茂生(1968-),男,江西吉安人,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首席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王 英(1989-),女,甘肃永昌人,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I106.3
A
1000-579(2014)05-007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