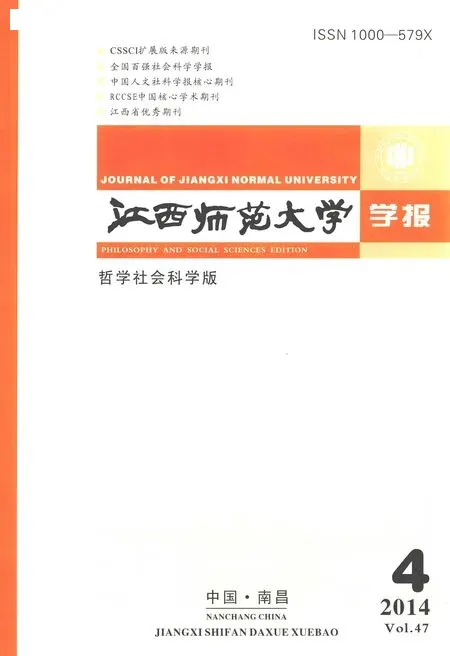“游戏江湖”的虚拟快感:从“再中心化”到主体间性
孙金燕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游戏江湖”的虚拟快感:从“再中心化”到主体间性
孙金燕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游戏玩家通过“再中心化”及主体间性,于武侠角色扮演中获得虚拟的快感。在人与媒介的“内部互动”中,角色扮演为玩家提供人物“视点”,使玩家从所处的现实世界,“再中心化”入由语词、形象和观念所构筑的属于所扮演角色的虚构世界“江湖”。与此同时,玩家沉浸于对另一主体的陌生体认,不断积累建构他我主体来理解“江湖”,并将其当作“有生命”世界逐步体验与认同,进行从现实世界撤退、摒弃,以及对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
角色扮演游戏;再中心化;主体间性
在超越的体验活动中获取自由的生存方式,是武侠游戏深入民间的关键因素。相比于小说、影视、动漫等体裁,游戏形式颠覆原有的武侠语境和接受方式,提供玩家“亲身”扮演武侠人物角色的虚拟快感。游戏文本的接受者即玩家通过在游戏角色扮演中的“再中心化”以及与武侠游戏文本的主体间性,在虚构的“逼真”江湖中,以极强的带入感消融玩家在现实世界的主体性,于虚构世界中重构另一个主体性,以此获得欲望的满足并且穿行其中而透明。
一、武侠角色扮演与世界“再中心化”
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assive Multiplayer Online Role Play Games),是目前武侠游戏的最主要形式。①最早的RPG是欧洲的桌上RPG游戏,大名鼎鼎的“龙与地下城”规则便是其中一例;后发展为欧美的奇幻RPG、日式RPG,在中国最为突出的是武侠RPG,如《仙剑奇侠传》系列,就被公认为华人世界经典角色扮演类武侠游戏。玩家扮演某个行为角色进入游戏,控制一名或多名角色组成的队伍行进,游戏路线依故事发展采取单线行进模式,并设有某些支线情节;玩家在其中需要遵循游戏虚拟“江湖”世界所规约的行为准则和行事方式。
武侠游戏逻辑同武侠小说叙事一样,都是一种心理建构,而非实体存在。武侠游戏活动的对象是游戏产品,在进入游戏文本的过程中,它由物质性的存在成为符号化的文本,在心理建构塑形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又有某些关联的虚拟世界。简单地说:游戏设计过程,就是编码一个虚构世界“江湖”作为现实世界的替代;玩家在游戏接受过程中,会依循心理建构进入这个虚构世界。而玩家在游戏过程中对游戏文本虚构世界的经验,将通过从现实世界向完全虚构世界投放而获得。
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将符号接受者对虚构世界的经验区分为三部分:其一,本源域,文本被读者处理的世界;其二,目标域,构成读者处理输出的虚构世界;其三,文本特征系统,引发各种世界知识,将读者从本源域投射到目标域。[1]由于虚构世界具有某些与现实世界类似的逻辑,可以“不须牺牲绝对存在的、独立于心灵的现实的思想,我们可以通过将个体关于现实的意象而不是现实本身放置在本体系统的中心而将本体系统相对化”。[2](p101)因此,玩家能够在他所处的“当下”世界做“角色扮演”向替代的世界位移,以致不由自主地沉浸入一个迥异于现实世界的“江湖”世界。
瑞恩(Marie Laure Ryan)将这个过程称为“再中心化”(recentering),用来解释接受者如何在符号接受过程中处理虚构世界。它的程序可表述为:当接受者沉浸在虚构世界里,可以以某个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为中心重新组织整个文本所表征的模态系统,可能性的领域围绕叙述者表现为现实世界的领域被重新中心化,人物所在的世界即文本现实世界暂时取代接受者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再中心化”过程与三个以不同的“现实世界”为中心的模态系统有关:“首先是我们的本土系统,其中心世界是实际的现实世界(或更简略地称,现实世界),我以下称AW。第二个系统是文本宇宙,文本所投射的世界的总和。位于该系统中心的是文本现实世界,简称TAW。作为文本提出的一个表征,文本宇宙必须同它所表征的系统区分开来,我们称其为指涉宇宙。正如文本宇宙是作为指涉宇宙的意象而提出的,文本现实世界TAW 是作为外在于它的一个实体的精确表征而提出的,即文本指涉世界,简称TRW。”[3](p23)在这三个模态系统中,文本现实世界可以与现实世界不对等,或者较为精确地呈现现实世界,如新闻文本等非虚构体裁;或者隐射性地呈现为某个可能世界意象,如传奇故事、武侠小说中构建的虚构世界。后者也反映了它所指涉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不对等,但可以通过“再中心化”,让接受者沉浸入文本中,再度成为“现实世界”。
武侠角色扮演游戏属于人与媒介的“内部互动”(Internal interativity),*瑞恩(Marie Laure Ryan)根据输入策略的不同,把人与媒介的互动分为两组四种:内部互动(Internal interativity)、外部互动(External interativity)、探索型互动(Exploratory interativity)、本体型互动(Ontological interativity)。其中,“内部互动”指使用者通过认同虚拟世界中的化身或是以第一人称视野来理解虚拟世界并把自已当成虚拟世界中的一员。参见Marie Laure Ryan.Beyond Myth and Metaphor:The Case of Narrative in Digital Media[J/OL].Game Studies 2001,01(01).(2001-01-01)[2012-10-03].http://www.game studies.org/0101/ryan/。由于提供人物“视点”(Perspective),则更易于将游戏提供的“世界”“再中心化”。游戏设计师克劳福德(Chris Crawford)称,电子游戏应具有扮演(Representation)、交互(Interaction)、冲突(Conflict)、安全(Safety)四项基本特征,[4](p17)其中“扮演”与“安全”将玩家与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的关系明晰化。因为游戏是一个正确或错误表征现实世界的封闭形式系统,所以玩家所进入的是一个非现实世界,他在这个封闭的形式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遭遇,不会反向影响入现实世界;与此相对,通过“扮演”,玩家可以“身在曹营心在汉”,将自我意识位移进虚构世界,以所扮演角色的思想和视阈来思考和面对所在“世界”。在武侠角色扮演游戏中,玩家选择一个角色而开始进入游戏的意义场,玩家的自我意识向所扮演的游戏角色敞开心扉,倾诉隐秘的追求和欲望,将游戏产品呈现的事件作为有生命的“世界”来体验。玩家消融现实世界中自我的主体性,而在虚构世界中依循新角色的“视点”重构另一个主体。
在武侠游戏可扮演的包罗万象的角色中,从斩妖除魔维护正义的侠客主角,到心狠手辣的恶人以及各种神鬼灵兽,角色的个性不同,战斗动作、刀剑法术的配置都有精细而严谨的区别。选择了某个角色,就选择了某种“思想”,选择了虚拟世界以不同的角色为界而反馈出的一个与之对应的观察世界的“视点”。进行思考与行动的,不再单纯是现实世界的自我主体,而是通过“再中心化”让渡给“江湖”世界被扮演的另一个主体。选择扮演主角“李逍遥”(《仙剑奇侠传》),就选择了“我成了李逍遥这样一个人”,以量化的体力、真气、武术等区别于“他人”;可以拿着李大娘给的50文钱去买虾米,去仙灵岛探险,用“飞龙探云手”功夫偷钱,在与恶人的大战中获得“灵珠”;可以谈恋爱,喝酒,休息,甚至是做梦。玩家自我意识会随之沉浸于游戏所提供的观念和意象中,为理念之物提供栖居地,做一个假装的游戏,以致完全转移进入眼前所专注的“世界”。
如同福里曼(Tzvi Freeman)在专业杂志《I Game Developer》列举优秀游戏与糟糕游戏特征清单时特别强调:“优秀的游戏让人感到清晰,你只要想自己就足够了,其他玩家也是如此;糟糕游戏总让人忘不了是在游戏中。”[5](p30)唯有玩家自我意识在游戏过程中,并从现实世界向虚构世界中的文本现实世界进行“再中心化”,才能沉浸其中。而此时,现实世界在让出位置,不仅仅是让位于游戏活动的形形色色的语词、形象和观念,而且是让位于这些语词、形象和观念所构筑的那个属于侠客的世界。
二、他我主体的建构:武侠角色沉浸与主体间性
武侠扮演游戏的“侠客”通常有这样的经历:思想是另外一个人的,而我却成了主体。自我需要直面“他我”所提供的问题,而且“此时”思考还需要以“他我”的视阈来施行。
相对于武侠影视作品虚构世界的重点是较为完美封闭地营造意义,在游戏设计的世界中,关键是要使玩家能够沉浸其中,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游戏互动中重新获得主体。游戏通过一系列元素与规则,构建起一个与日常生活相区隔的“江湖”空间,玩家获得有别于在现实世界中的体验,是武侠角色扮演游戏的特点之一。约翰·赫伊津哈定义“游戏”为:“游戏是在某一固定时空中进行的自愿活动或事业,依照自觉接受并完全遵从的规则有其自身的目标,并伴随紧张、愉悦的感受和‘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6](p30)而这种“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在游戏中则主要导因于主体性的变更。
在“平常生活”中,主体对所思虑的问题进行深入反思,自我就成为“思”的主体,“一旦我想到一个东西,我想的这个东西就在某种意义上难以确定地成了我的。我所想的一切都成了我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在武侠扮演游戏中,主体的实现方式则与此相悖。武侠扮演游戏提供给玩家一个可以使自我意识在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自由往来的无缝空间,而当玩家以游戏中某个角色或视角对游戏的进程作出选择的“当下”,自我意识中进行思考的主体却不是自我主体,而是来自隐匿于游戏的一个陌生位置的另一个主体。而唯有接受者——玩家消融自我主体,与这个陌生的主体进行交互,显现为“‘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重构另一个主体,才能游弋于游戏中,获得有别于平常生活的快感。
也就是说,那种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并非单纯的游戏设计者意识,而是玩家与设计者视阈融合的结果,它隐藏于游戏文本并在游戏角色的激发中逐渐生成。例如有研究者提出可从日内瓦学派领军人物乔治·普莱(Georges Poulet)提出的文本出发逆向推理来寻绎文本的自我这一观点,来理解电子游戏中的主体间性以及沉浸问题。原因在于游戏设计一直是在玩家的欲望召唤下完成,在中国的武侠角色扮演游戏中,同样如此。首先,众所周知,消费刺激生产,武侠符号一直在青少年男性群体中有着巨大的号召力,随着现代传媒形式的逐步演进,武侠符号与游戏联姻不仅势所必至,而且从一开始,游戏设计就是对玩家在武侠游戏中实现自由想象的利用;其次,从“游戏”的性质界定来说,设计者本身无法进入游戏情境。因为在设计者眼中,游戏的进程了然于胸,它不过是一个已知谜底的谜题;“游戏”唯有真正意义上的玩家介入才能实现其符号表意,游戏产品设计者的自由本质才能被感知。也就是说,游戏是一种介于随机与固定算法之间的互动,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玩家沉浸其中,重视在线甚于在场,重视过程甚于结果,本质在于对另一主体的陌生体认。
“我通过一种行为回溯到某一确定的作者对这种行为的意识,正是这种行为本身使我就在这意识实现其精神行为的时刻活生生地抓住一种思想的独特性以及它在其中得以发展的那种含义。”[7](p282-283)武侠扮演游戏作为一个完整文本的完成,是在玩家的操作中实现的,玩家的每次输入都是一个符号化行为,它以一种可被解释的方式改变语段,并在语段内产生意义,与隐藏的碎片式主体进行协商,逐步构筑以某个侠客为身份的“他我”的主体。如《仙剑奇侠传》(第三部)的玩家,对于游戏的不同输入可以导致游戏的不同结局:依据景天对龙葵及雪见的好感度的高低,景天会有不用的选择。若两人的好感度差不多,则可以让玩家选择。选择修复魔剑的话,雪见则会以神树之实来救回景天(龙葵结局or完美结局or紫萱结局);选择镇妖剑的话,龙葵将千年的修为给了景天后便会去转生(雪见结局or完美结局or花楹结局)。
即是说,武侠角色扮演游戏的这种即刻呈现的反馈,可以赋予游戏者强烈的认同意识,在角色扮演过程不断积累建构“他我”主体,玩家对游戏的沉浸,除了是游戏者认同虚构世界中化身的方式,来以第一人称视角如扮演“景天”理解虚构世界之外,也是将这个游戏构筑的虚构世界当作“有生命”世界的逐步体验与认同。[8]
三、结语:虚拟的快感与现实的撤退
“在符号化传播阶段,身体退隐为传播的终端,传播媒介却逐渐被外在于身体的物质技术和机器设备所取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越来越多样化、精细化。”[9]“在大众传媒时代,故事诞生为文学,成长为影视,终结为游戏。”[10]而艺术都在以不同的渠道满足人对自由的渴望,游戏也不例外。瑞恩(Marie-Laure Ryan)认为,不同媒介对叙述具有不同的表现策略,某些情节类型或人物类型最适宜小说,有些更适宜口头叙述,还有的更适宜舞台或电影舞台。武侠幻想叙述类型非常适宜数字媒体,武侠角色扮演游戏活动以其强大的媒介整合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更可以实现玩家主体选择和超越现实世界,确证人之自由本质。
根据《大众软件》杂志发布的《中国电脑游戏产业报告》,国产角色扮演类游戏的产量在逐年大幅度增长,由 1999年的18款已增长至2010年的314款之多,并且这些国产角色扮演类游戏当中,以武侠为题材占了绝大多数。众多玩家对武侠扮演游戏的钟情,可理解为是从现实世界的撤退和摒弃,以及对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
作为一种超文本活动,玩家可以不再只是旁观者,而可以做多向选择和能动介入:“超文本作品是‘活’的,在线空间的网民正是被活性的文本所激活,而且只有超文本能使欣赏者与文本之间物理上的互动成为可能,并同时为读者向作者转化创造了空前的便利……在这里,固定的作品结构被读者瓦解或重新构造了,意义也被新链接的文本给予了不同的阐释。创造性的阅读使静止的结构被召唤式结构所替代,结构成了一种在‘运动’中不断发展的东西。”[11]网络游戏的这种特性,使玩家可以扮演成侠客沉浸在“江湖”世界中,在与游戏的互动中沉浸入“忘我”的境界。
这种角色扮演式的“忘我”,使玩家将在现实世界无法实现的欲望投射入虚构世界,选择某个虚拟的侠客角色沉浸其中,在虚拟世界寻找自我认同,补偿与延伸现实世界的欲望,更具体的则牵涉到“有别于平常生活”中的内心暴力想象的满足以及建功立业的快感。而在这个“自我”形塑的虚构情境中,玩家所获得的“世界”体验将是一个悖论性的存在,因为它是虚妄的,又是现实的。
[1]Herman,David.Theories of Fiction and the Claims of Narrative Poetics[J].Poetics Today,1998,(4).
[2]Marie Laure Ryan.Narrative as Virtual Reality[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1.
[3]Marie Laure Ryan.Possible Worl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Narrative Theory[M].Ba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
[4]Chris Crawford.The Art of Computer Game Design[M].McGraw-Hill Osborne Media,1984.
[5]Tzvi Freeman.Monitoring Devices in Games[M].California:I Game Developer,April-may,1997.
[6]〔荷兰〕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关于文化的游戏成分的研究[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7]〔比〕乔治·普莱.批评意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8]王伟.超越现实的精神放飞[J].中南大学学报.2009,(1).
[9]王彬.现代传播的身体迷思 [J].符号与传媒.2010,(1).
[10]Johan Svedjedal.“Gaming for the academy”.http://www.axess.se/english/current issue[J/OL].2012-01-02.
[11]欧阳友权.网络艺术的后审美范式[J].三峡大学学报,2003,(1).
(责任编辑:张立荣)
SuppositionalPleasureofPlayingintheVirtualWorldsFrom“Re-centralization”toIntersubjectivity
SUN Jinyan
(College of Literature,Yunnan Minzu University,Kunming,Yunnan 650500,China)
Game players get the virtual pleasure through “re-centralization” and intersubjectivity in Wuxia role-playing games.In the “internal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the media,the role-playing provides characters’ perspectives for players,where the player from the real world re-centralization into the fictional world “Jianghu” that is being constructed by the words,images and ideas.At the same time,the players immerse in another subject,accumulate unceasingly and construct the subjects to understand “Jianghu”,and gradually experience and recognize it as “living” world in order to solve reality conflicts in imagination.
role-playing games;re-centralization;intersubjectivity
2014-04-16
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武侠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符号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研究”(编号:2014Y267)
孙金燕(1984-),女,博士,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符号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I01
A
1000-579(2014)04-007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