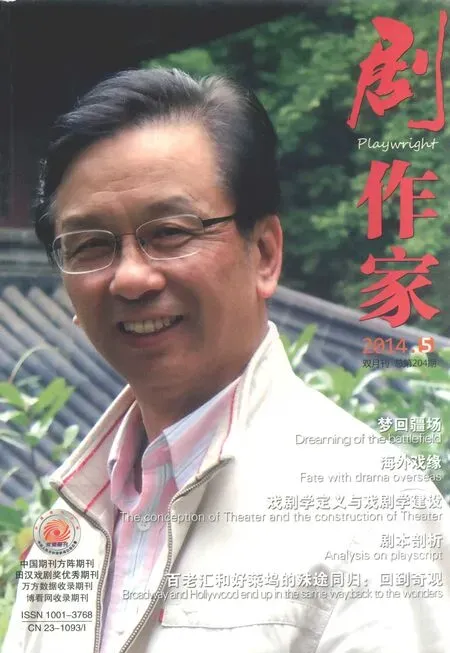烟雨迷离的那天,他来到祖父的旧居——徐志摩长孙故乡寻梦
赵家耀
烟雨迷离的那天,他来到祖父的旧居——徐志摩长孙故乡寻梦
赵家耀
岁月洗礼的花园洋房,庭院深深的花墙之后,每扇窗口都隐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不难感受到诗人的精神在此行走,那些动人的诗篇,将长久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他不在,这时我才明白,一些人有时多么在乎那一个人……

徐志摩故居外景
孤雁南飞。五十多年前大学毕业分配,我从北京南下上海,先后小住过流光溢彩的淮海中路,也住过电影厂的集体宿舍,至今乔迁至少五六次。对当年在上海居住之难,体会尤深。已记不清多少同事、朋友给我介绍过女友,但从未有人给我介绍可居住的房子。之后,终有幸单位经套配让我分到了上海现黄浦区南昌路,解放前称为“花园别墅”的新式里弄住房。万没想到的是,其中的一间书房竟是我国著名作家、文学家巴金先生当年的居室,而对面的一幢三层楼房则是我国著名诗人徐志摩和他娇妻陆小曼当年的“爱巢”。
提起徐志摩,人们首先会想到他那脍炙人口的诗句,然后是他与几个女人之间不尽如人意的婚恋故事。是的,文人总是纠结在各种情感之中,似乎失去了爱情,便失去了一切。然而也正是由于那些罗曼史,才让他这位“多情才子”的艺术思维生机勃勃,像着了魔似的不断爆发诗情,创作出一首首不巧的诗篇。
拍电影、拍电视的工作很忙,且经常乃至长期出差拍外景更是常事,没有更多的时间研究这两位文艺大家的精彩人生。但百年南昌路、思南路梧桐树下掩映的每幢房屋、每条弄堂,都有着写不完的故事,况且,如今更是个容易发生故事的年代……
哦,当我们说故事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故事就开始了……
深街雨巷de邂逅
“打扰了,请问先生,我们能不能去您二楼的房间,从窗口拍对面徐志摩先生当年的旧居?”未待我作答,那位中年女士立即补充道:“我们刚从美国来上海不久。”她吃力地说着我很难“破译”的汉语“密码”。这时,邻居走过来轻声地对我说:“那胸前挂相机的男士是徐志摩的孙子。”听罢,先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继尔既惊喜又愕然,于是我忙下意识地端详起这位身材高大、面容清秀、形象丝毫不逊于诗人祖父的后裔。同时,回想起前不久在介绍徐志摩的书上见徐志摩那戴圆形无框眼镜的照片,其形象和眼前的这位男士确有几分神似。鼻梁上同样架着一副圆眼镜,尽管无情的岁月距诗人逝去已80多个春秋……
一同前来的除徐志摩的孙子徐善曾先生外,还有他的夫人包舜女士。陪同徐先生夫妇的是一位拍过电视片《泰戈尔在上海》的印度朋友,当我告诉他们我们所在的这个亭子间的书房,正是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曾经的居所时,他们更加来了兴致,一气连拍了不少照片……
继而,徐善曾博士通过他夫人的解释,希望我前去说服现住在徐志摩旧居的房东,能否让他们进去拍照留念。从来文人孕盛事,时下,自旧居外墙钉有铭牌后,前来瞻仰拍照想入室参观的中外游人络绎不绝。该屋主人还是给足了我面子,破例允许并亲切地接待了这几位非同寻常的异乡宾客。他们鱼贯而入,简单寒喧之后,便一起诚邀房东合影。而后,在男主人陪同下,从底层至三层楼拍个不停。对此厚待,徐善曾等一行很是高兴,可谓精神焕发。徐善曾先生平生第一次亲临其祖父和祖母陆小曼的旧居,他们感慨万千。
面对八十多年前祖父生前的遗迹,他好想完成对这位著名诗人当年生活的指认。当他应主人邀请,坐上那把高背旧藤椅上的时候,徐善曾先生似乎听到了从那里面发出的一声熟悉、沉重的叹息。
端详着屋中的旧樟木箱,那锈迹斑斑的箱扣,古旧厚重的铜插锁,衣架上衣袂飘飘的睡袍、绸衣,禁不住想起上海二、三十年代才特有的梳妆台和台上面那椭圆形的穿衣镜,似乎又想象到那是岁月和一代诗人香火的延续……
在他的祖父母曾牵手居住过的“爱巢”,人们依稀可见二人身处爱情“四月天”的美丽风景……
是的,时光会让容颜老去,也会让其身影愈加动人……
此刻,平生第一次来到这里瞻仰祖父母旧居的徐善曾先生或许在想,在这里,消失的事物可能挽留,岁月遮掩的一切将会重新铺展开来,被时光磨损的一切会重新修复。这座三层小楼,他祖父母在上海仅存的旧居当是他记忆的陈酿。
我在想,作为徐志摩的孙辈,远居异域他乡的徐善曾夫妇虽然了却了心愿,但内心很可能是五味杂陈。他们似乎看到了诗人生命中辉煌的文学、戏剧之旅——诗人和他娇妻“眉眉”(陆小曼)共同创作并同台演出的剧目《卞昆冈》。他们丰满的爱情故事以及两颗在月光下纯洁的灵魂——更由于他们是首次前来而显得兴致勃勃。这座三层小洋楼里演绎、浓缩着世事风云突变,雨雪风霜、际遇因缘,苦辣酸甜和欢笑与泪水……他们要离去了,他和夫人包舜女士一步一回头,他们好不留恋……
作别时,他希望我们日后多联系,并留下了他在美国的通讯方式等。从此E-mail将地球“缩小”,并将这地球两端连成了一个微笑,以至我想赋小诗一首《弄堂邂逅有感》以赠先生:“不知多少年后/他从地球另一面/匆匆归来/烟雨迷离的那天/任怎么端详/都像个不慎走失的孩童/于弄堂前后/弄堂深处/眼睁睁地等待/快来人认领/一述衷肠……”

徐志摩故居一楼门口
徐善曾先生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他是1946年出生在上海。幼年时,由祖母张幼仪抚养,六岁时跟母亲辗转从香港等地来到美国,和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父亲徐积锴团聚。徐志摩和原配夫人张幼仪生有两个儿子,其中小儿子在三岁时夭折,大儿子徐积锴于2007年在纽约去世,享年90岁。张幼仪本人也曾在美国生活多年,徐善曾现在除了能听懂几句上海方言、俚语外,基本上不会讲中文。
回顾与书写,都是古老的方式,只有页码不断履新。之后,他不断发来邮件告之,上海一行,与我相识及频繁联系,他很是感慨,浮想联翩。每一个文字与诗人徐志摩邂逅的时候,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便不断诞生了。笔者以为应当让那些诗句播撒进更多热爱他的海内外读者的心中,或许是秉天地之灵气,或许是受他祖父文化传统与才情之浸染,我以为他很想将那段文人盛事化成文字留给后人……
我想,是诗人徐志摩一生中有众多可供人们言说、又津津乐道的片断,以及他那些带着人情人性的动人诗篇,让徐善曾先生找到了要诉说的理由。他会以一行行文字去点亮内心的灯盏,去打开那一扇扇幽暗的门窗。要感谢生活、命运,我相信冥冥中有股力量,会引领他去洞悉、开掘更深的爱与痛,他会时刻活在诗意的世界里。
近日,他更是多次通过E-mail请我尽快提供有关书籍、素材、旧居照片和我对他祖父、祖母的个人看法。其中,我要告诉他们夫妇的是,做为桂冠诗人,他祖父是一位著名的新文化运动者,是新月派的诗风和领袖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位爱国者。尽管他从英国回国后是春风得意,但面对的现实及从他的作品中,还是能反映出诗人生前身后的精神困境,从《这年头活着不易》等忧愤的诗歌中,不难见他无处安身的绝望。在令人窒息的生存环境中“我只要一分钟,我只要一点光,我只要一条缝”(《阔的海》),可现实却是“在妖魔的脏腑里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生活》)。面对二、三十年代旧中国的现实,他感到无望与不满,他的诗句、散文、书信等不断流露出对一种新的社会和现实的向往。他不但敢于公开拒绝为官,且还发誓不和官僚政客往来,然而,却又找不到驶向光明之路。于是长期陷于彷徨苦闷之中,以至有时产生消极悲观情绪,对社会生活的无望,也转移了他对爱情的期待。作为那个时代的人,徐志摩做到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能做的一切,他在追求自身幸福的同时,也对民族命运有过深刻的思考。想必徐善曾博士会考虑、赞同我的这一看法。
一个世纪以来,徐志摩和陆小曼等人的故事传颂不倦,在诸多文学作品中几乎已被渲染得扑朔迷离。作为名门之后,我相信他会将那段浪漫、美好姻缘背后的种种故事,随着他不懈的探寻,定会有更多的情节、细节面世。这对诗人、对祖父母难道不是最好的告慰?

徐志摩故居二楼和三楼
诗人徐志摩生前曾说:“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我有感徐善曾先生这次追寻祖父那难忘的故乡之旅。很显然,他创作的热情已被点燃,字里行间,循着他祖父徐志摩那条“感情的线索”,如数家珍地将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因和陆小曼之间轰轰烈烈的情感纠葛,以他自己的思维方式、独特的视角表达出来,将一个多情多才、风流倜傥的诗人生动、短暂的人生故事,展现得跌宕起伏、峰回路转,为海内外人士争相传颂。
通过频繁E-mail的传输、交换,笔者相继了解到徐善曾先生对于徐志摩这样一位文化名人祖父,他和三个姐妹以前都不太在意这回事。先生从小便跟着奶奶张幼仪长大,他认为祖母张幼仪心目中始终爱着徐志摩。他俩有着七年的婚姻,她“对祖父徐志摩有着很深的感情。”是的,张幼仪说过:“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自笔者搬迁至上海南昌路后,不久便得知正对门的三层楼就是诗人徐志摩和陆小曼当年新婚之“爱巢”。工作之外,有意无意间还是会很有兴致地浏览有关他俩的报刊杂志以及有关他夫妇俩的奇闻轶事。鉴于诗人不幸过早离我们而去,本人又多事缠身难得摆脱,无奢望写什么追念他的文字,大略知道他的初名是章垿,字槱森,小字又申等,仅此而已。
一晚,赶写一篇文字,久坐出神,不觉昏昏然,思绪拥塞,仿佛身披一副铠甲对窗独坐、闭目“思过”。青灯下眼前匆现历史的幻觉,冥冥中如有“神问”,不禁想起对面窗帘帐幔后,当年的那位如风行走在大地上的诗人,为何名称“志摩”,而非其他?想必背后会有几位仙风道骨的虚云老僧,于某静谧禅寺之点化?
自和徐善曾先生相识并多有联系后,对有关他祖父的大小事较前分外关注了许多。之后一日,有如“神助”,得知“志摩”这二字。原来这一名字的由来,背后还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据悉,当年在一禅房,有个叫志恢的和尚打坐入定后,以其淡定的模样摸着徐志摩的头,上下左右地朝他打量了一番之后,口中喃喃有词地断言,此男将来必成大器!当时这有如佛教禅杖梵语的一番话,正好迎合了其父望子成龙的的心意,听罢十分欣喜。1918年8月,徐志摩在前往美国克拉克大学求学时的护照上,便填上了“徐志摩”的大名。欣得此传,多年前的冥想至此像似回答了“神问”,告别了我思绪的荒芜与追问。
从此,这位来自衣食无忧、宽松自由家庭,活力四射的青年才俊,开始如飘向“西天的云彩”,留学世界各地,汲取各种文化的浸润与滋养。
写至此,我止不住地想向志恢和尚道谢一声,由于托了他的寥寥吉言,中国多了一位奕奕闪光、不可多得的传奇诗人。他的文字是中国语言的结晶,是世界文化的瑰宝。
E-mail继续在笔者与徐善曾之间传输、互动。当时,徐善曾先生每天都从他祖父徐志摩那穿着长袍马褂的照片前走过,可并不知晓他祖父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只感觉其祖父代表的文化和美国穿牛仔裤、T恤衫的文化大相径庭。徐志摩的后人中,仅有徐善曾的女儿是研究电影的,几乎无人从事诗歌写作。但多年以来先生总是不时听到有关他祖父的故事。他十几岁的时候曾意识到祖父是个著名的诗人,但没想到祖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有如此之深远。上大学的时候,曾听一位同学聊起诗歌,他提到近代中国有两位令他仰慕的诗人,其中一位就是“东方的拜伦”——徐志摩。后来徐先生看到一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不断看到祖父的名字,他才意识到继承祖父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此,他开始关注此事,潜心研究祖父的生平以及当年在美国的留学情况,回顾他所走过的路。

作者与徐善曾夫妇在徐志摩故居的合影
追寻诗人在异域他乡的故事
于是,他便奔走于祖父徐志摩当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图书馆,终有幸从该大学社会学系的档案中查到徐志摩当年在这所大学政治系就读时所写的以《中国妇女的地位》为主题的硕士论文。而后,徐志摩以至“摆脱了哥仑比亚大学博士衔的诱惑”,去英国准备向哲学家罗素“认真念一点书去”。有趣的是,或许是出于爱国的缘故,徐志摩在论文中并没有写中国妇女如何没有地位,而恰恰相反,在他的笔下,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并不比西方妇女低。例如,法国的妇女一旦结婚,便被视为丈夫的附庸,没有处置财产的权利。而中国的妇女一旦结婚便视为成年人,对自己的财产有完全的自主权。同时他也很客观地指出,中国妇女的受教育状况则需较大地改进。徐志摩的这一论点今天仍可得到验证。
“一代诗魂”徐志摩的诗歌佳作不断成为祖国各地及海外文化界、诗歌朗诵会上的保留节目。例如当徐志摩逝世80周年时,美国有关组织如华美人文学会、哥伦比亚大学中华法律协会和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举办诗歌朗诵会,参加者有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工作人员、哥伦比亚大学生、华美协进会博物馆馆长等人参加了诗歌朗诵会,令人难忘。因此徐善曾先生说,谁也未曾料到祖父的精神遗产能够活到今天,还能活在他的母校,活在像纽约这样的地方。
诗人御风而去,可至今人们仍朗诵他那些不朽的诗篇,属于他的风,依旧吹拂在人间……

外国旅游者在徐志摩故居前合影
奔走在“回家”的途中
徐善曾先生的行程每每都安排得紧凑、满满。2012年6月4日,他应邀参加2012年中国济南徐志摩研讨会,2012年6月10日下午4时,徐善曾夫妇带着强烈的探知欲,又匆匆赶到上海,继续寻求祖父的答案。那天笔者刚刚回家,回到当年巴金先生与其祖父旧居的门前,我有幸戏剧性地接待了这位大洋彼岸的稀客、贵客、著名诗人的后代。面对满口洋话的徐善曾先生,我们先是口谈无效后,又改用手谈、笔谈,大家情绪高涨,谈话未曾中断,大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
之后,他又发来邮件,感谢我向他提供的有关信息。并告之,他的朋友惊喜地将我发表在《人民日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上他和他夫人到上海寻根、瞻仰他祖父和陆小曼旧居的文章转发给他。他说,如果有个英文版的文章传给他,他会很有兴趣一读我写的文章,并向我致谢!
时下,他正在努力完成一个重大项目,还没机会将此文准确地译成英文,请谅解。
对于我替他补拍他祖父母旧居门前的铭牌彩照,他说,铭牌上很多字已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很是遗憾。
考虑他很忙,又为慎重起见,我特请几位英语专家将我发表在《人民日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有关他们夫妇俩来沪寻根续梦的全文,译校多次的英文稿立即传给他,想必他收阅后,会是很高兴的。
徐善曾先生到过祖国的许多城市,也先后去过英国、印度、俄罗斯等地,不断追寻着他祖父在异域他乡的故事。
徐志摩的长孙徐善曾先生还希望能再次访问欣欣向荣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他说,能和我及房东再次相聚,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徐善曾先生早年在密歇根大学修读电气工程。后来在耶鲁大学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多年来任职科技行业,后开始从事创业投资方面的工作。这位美国耶鲁大学物理学博士及具有理工、哲学、电子工程学位的学者,对重返故乡,重回上海追梦、寻梦充满了期待与热情,或许是春风扑面的日子,或许是橙黄橘绿的时节……
频繁的交流,终使笔者了解到徐善曾先生有为祖父徐志摩写部传记的念头。多年过后,当又有人谈及他应为其祖父著书一事时,对此事一直执着的徐善曾先生当即表示,他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可随着思虑日深及对中国文化更深入更广泛的了解,先生有感不少资料的匮乏,在对徐志摩生命历程的研究中,也发现有不少断链断层,更由于语言沟通的不便,时间的过长,素材搜集困难重重等诸多原因,他认为若撰写一部人物传记似乎不能够表达出祖父一代人的心路历程。他曾透露,待空闲时,他或许会构思一部传记体的文艺作品,或许是小说。故事情节只要是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不乏戏剧性。那么以小说的体裁表现,可以典型化地处理创作素材,让艺术真实更接近生活真实。对于未来那些文字的期许,或许能抚慰他那些无处安放的思绪……
在此当要提及的是,孰能想到诗人徐志摩的第四代人中,竟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希望之星,即徐志摩的曾外孙Bentley King,居然发表过关于曾祖父徐志摩的文章。不知为何我总是希望诗人的亲属和后裔撰写他的有关文字,我想这不是一个意外,不是一个偶然,这是海内外多少人的期盼。
我的居所和徐志摩陆小曼的旧居门户相对,于是我会经常“接待”海内外包括来自台湾、港澳等地来此参观、寻访、旅游的各界人士,有时应邀还要义务为他们在徐的旧居面前拍照留影,以至临时义务为他们担任业余“解说员”。他们很想了解当年徐志摩和陆小曼在此发生的那些可歌可泣或鲜为人知的故事,借以不虚此行。
是的,前来此处参观拜访的中外游客,无不用仰慕虔诚的目光环视着诗人徐志摩和他爱妻陆小曼曾经的“爱巢”。他们常对我提及一个问题,“楼房里住有居民吗?我们能进去参观吗?……”当时我就想,或许他们中间有人可能不善赋诗,或远不及诗人写的精彩,但他们的希求很真诚,很感人。时至今日,人们还依然如此痴迷地寻找着诗人徐志摩的足迹,实在令我感动。从他们那热诚的眼神里,我读到中国能有这样一位桂冠诗人,多么令他们骄傲和自豪。顿时,脑海里便跳出诗文《这里有永远难以打开的结》。慕名而来的人们啊/他们心中多么希望/出现这样一道风景/他们似乎看到/小曼画着柳叶娥眉/系着拖地长裙/妩媚地踱步窗前/只见那纤纤玉手/轻推窗扉/风溜进了她和诗人的婚房/她凝眸四望/窗下的游人闻其窗外/随帐帘幽香阵阵飘来/一朵绚美的葵花/醉了旅人/醉了晚风/醉了彩霞……
事后,忽有一夜,朦胧中,我感到似乎同天下那些想更多了解诗人徐志摩的人们有个约定,心中萌生了想写点什么的念头,责任驱使我尽可能快些、准确些,尽可能全面地向热爱诗人徐志摩的人们,以自己理解、感知的有关事迹,述之文字,向海内外各界人士介绍,共享诗人徐志摩的业绩,共享这笔永恒丰厚的文化财富。这是一本读不完、合不上的书。
于长街雨巷纠结的深处,美会在等待再次被人们唤醒……
“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理应属于自己隐秘的精神领地,都有一个精神的故乡。从这个意义上讲,托尼、徐善曾先生难道不是一位诗人?在追寻、实现美丽“中国梦”的行列里,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先生会带着春水一样丰沛的想象,将那些沉睡的时间摇醒,带着他或许未曾写罢的文字,一次次地从远方归来,奔走在“回家”的途中……
城市在整容中,岂能否定了她的记忆?
历史遗址是城市历史的文脉和“档案”,是更大范围人群的精神家园,何况有着岁月积淀,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地区。我们是一个有着丰厚历史文化的民族。
名人故居是一座城市的“根”和“魂”,这里是承载着历史和记忆最深厚的地方,蕴含了深刻的文明碎片。
一个城市的文化、文学和各界精英,代表了这座城市的精神高度,是这座城市的灵魂和心脏。他们留下的文学艺术遗产,将世世代代润泽着我们民族的心灵。
责任编辑 王彩君
——于毛泽东旧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