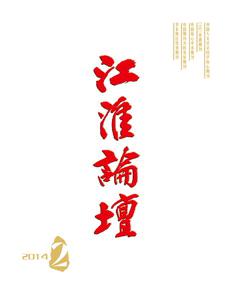张申府的不平衡的相对价值观
摘要:张申府的知识体系是彻底的科学知识体系,而其哲学体系又是一种价值哲学体系。这种价值哲学体系可归纳为不平衡的相对价值观。在不平衡的阴和阳的规律作用下,形成不平衡的宇宙状态。虽然宇宙存在着不平衡,但一直维持着并安定于此不平衡状态而生成进化。人要效仿之,针对世界上的不平衡积极地加以调节,才能达到心理上、生活上的平衡状态。这种不平衡的价值具体体现在“活着”的状态上,也即宇宙与人类本来的自然状态。人们必须按照所处的环境活在本来的、充实的生活状态中。
关键词:活的哲学;具体相对论;价值平衡观;相对绝对论;相对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2-0081-006
20世纪初,许多哲学家都表达出对生命的留恋与关切。其中,张申府(1893—1986)是比较耀眼的一位。他曾说,人最重要的是活着,其次是像人一样活着。[1]第二卷,304最根本的保障,就是真正建立公平、公正、合理、客观的社会制度。
为此,张申府认真比较了东西方差异,指出:像俄国那样将东西方文化机械地结合是错误的,而因袭中国传统的哲学抑或是单纯引入西方哲学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西洋哲学的一个不通之路是把主观方面的人与不依附人而独立的所谓外界,截然对立起来”[1]第二卷,335。西方文化及其背后哲学体系的主客二元性,导致主体与客体之间缺乏沟通,当时在欧洲爆发的大大小小、奇奇怪怪的战争,根柢即在这里。因此,唯一的出路是创造出第三种新的文化,[1]第一巻,64并以之作为建立保障人们生命的新制度的哲学基础。
一、 张申府的认识
(一)对世界的认识
张申府认为,“保守东方旧化说不可行”[1]第一巻,63。
在清朝灭亡后,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的正统性受到巨大撼动。一方面,儒家思想是在过去农业生产结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哲学体系,不能适应以工商业等综合性新产业为主的复合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从世间的角度来讲,国家已经从帝国时代发展到民国时代,因此无法对之进行修正或补充,只能重建新的哲学体系。
鉴于此,张申府认为,为了建设新世界,首先要对过去的历史与社会进行全盘评价、重估,“为理想之形成应将东西所有旧有的东西,都加以估重,评衡,及别择”[1]第一巻,63。未来的新世纪必定要建设人民作主的、能够保障人民幸福的社会共同体,因而要建设新的哲学观念体系以及客观合理的民主制度。否则,或左或右,都将成为时代与历史的罪人。新的哲学体系要以当时新发现的自然进化论为基础,并果断扔掉过去循环论哲学体系。因为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不是循环的,而是进化的,这是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
这个世界是人类所创造的,而不是任何神或者任何绝对者所创造的,更不是某种“理”所创造的。如果依据不正确的道理来建设新世界,自然也就不能够保障人民的幸福。[1]第三巻,214“显然的例子,历史是人类的创造物。”[1]第二卷,445
确实,过去人们如绝对真理般坚信的循环论理论体系已完全成为遗物了。达尔文自然进化论的出现,对过去的哲学体系提出严峻的挑战,这是近代知识分子的共识。因此,张申府所主张的新哲学观念是吸收当时知识界的成果提出的。由于人类新知识的飞跃发展,只抱有过去常用的知识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在历史不断前进中的一种必然。他站在知识的高山顶上既看到了左边的过去,又看到了右边的未来。[1]第二卷,445
张申府说,即使谁都相信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永远不变的,或许在某时就要被否定。如果其根据是不准确的哲学与逻辑,就理所当然要被否定,在这一点上无须考虑其自身的价值。这样的结论是他对真理体系作深刻思考后得出的。他说,至今只有几百年里所发现的真理,也不见得完全都对。这就是现实,并且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
1.对精神的见解
东方国家非常重视精神作用,但是张申府将之转变为物质的作用来解释。[1]第二卷,92在张申府看来,不这样是无法解释这个物质世界及其作用的,也无法解释其进化及发展。因此,人们的境界及其发展阶段,须依据物质的进化作用来说明。他说,这个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人也是其中之一。因此,人们应该用新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尤其要用创造的理性建设未来。
近代以来,人们试图将所有的精神现象换算成物质来计量,认为人类的精神只不过是物与物之间所产生的一种摩擦以及交互作用而已,甚至人类如果有灵魂,那么也同样是物质的一种作用。现代科学不承认其他的任何作用。过去科学不发达的时候,将精神和物质分开来解释,但到了近代,这样的解释就必须彻底抛弃。
人的力量也是一种物质的力量。马克思曾说过:“理论一旦把握了群众,就变成了物质的力量。”[1]第二卷,445
张申府说,人们的精神力量只是一种物质力量,因此能够用科学方法来证明。有人说,这是对理性的盲目相信,而现代医学慢慢地解开了生命的神秘。他认为,精神是在物质的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非常高级的作用,只有在高等动物中才出现。[2]第三集,210实际上,现代医学指出,人类此种伟大的精神是物质间交叉时发生的一种高级作用,也是进化中出现的物质的高级化的现象,这已经是常识,并且是社会的一种现象。
2.对物质的认识
世界是物质的,是客观的,尤其是实在的。人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人类发挥正常的作用时,这个世界会变得更丰沛。
世界是物质的、客观的、实在的,人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人可以影响世界,人和物质是不应该分开的,人也是物质。[1]第二卷,445
他说,这个世界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进化。在其进化中,通过一部分人的作用会更迅速地进化并发展。[2]第三巻,210
自然界中的物质在维持其平衡时,会有所变化,如果平衡被破坏,自然界会受到严重损害。张申府说,人类不能不介入这个世界,所以应该抓住其平衡。他认为,所有自然的变化都随其物质条件而有变化,随着其作用而作出一定调节。因此,因人类的积极作用而进化的这个世界,也必须顺应其物质条件来调整才行。endprint
(二)对知识的认识
张申府说,这个世界里没有固定不变的知识,几百年前人们还确信不疑的知识,如果因发现了新的知识,其中不可用的也应该抛弃。“譬如在十六世纪时哥白尼,曾经证明地球是动的,这种说法在现在看来就已经不完全对了。”[1]第二卷,446因此,这个世界并不是停止的,是持续地发生着变化的,人们必须不断地构建与创造新的知识,才能够开拓新的世界。
“世界上的一切都在进步或变动。”[1]第二卷,446张申府说,过去的知识是模糊的、不确切的,所以他向当时的知识分子强调要寻找新的绝对的认识。他说,虽然没有绝对知识,但有绝对化的认识。[2]第三集,210在相对的知识基础上,不断地进一步积累着相对的知识,即可变成为绝对化的认识。[1]第二卷,342这是对于过去先验的、尤其是没有怀疑即被承认的知识的否定,而且通过这种否定必定可以发现更为确切的知识。其解决办法的端绪,据他说,是从辩证唯物论中找到的。
他说,这种辩证唯物论在过去已经断绝,而且是种孤立的知识,如果能确立起联系,那么其知识就可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更简单明白说来,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论对于一句话,对于一个道理,或一种理论,都不可以孤立来看。”[1]第二卷,342他说,正是在这里,存在着世界与人类共同的活的生命。是以他要将此辩证唯物论建构成一种活的理论。
(三)对哲学的认识
张申府指出,哲学这种学问,应该首先能够评价人类已经发现的知识,但更重要的是用知识来开创未来(未知世界),尤其要能够创造性地进行建设。[1]第二卷,84他认为,这就是哲学最重要的任务。如果哲学不能实现其本来的任务,知识就找不到正确的路,人们就会在知识的迷宫中找不到出口。[2]第三集,66所以哲学家应该不断探索未知(世界)的可能性,由此不能不从根源出发来探讨。
“(哲学)是根本原则的学问。”[1]第一巻,474他说,通过探讨根本的规律与作用,人们自然能够收获物质上的丰富,以及精神上的满足。
能够做面面观,如实观,平等观,也能容纳多方面,重视种种不同的他方面。这都是充实民主所必需。[1]第一巻,474
通过哲学可以实现让人们像人一样活着的环境和制度,人们所需要的民主精神也能够从中构成。如果不通过哲学,是不可能把握实际的,也不可能养成创造的力量,甚至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也不能够建立起关系。因此,想要将民主制度实践,作为必要条件的哲学却不完备,那么人们所需要的民主制度根本不可能实现。
张申府所讲的哲学,以现实为其评判的标准,并首先要对人类过去所积累的知识作出正确的评价,同时也要包容人类过去创造的传统,进而打开未来创造的可能性。[2]第三集,66否则,其哲学就不是活的哲学,也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世界。他说,这样的哲学与科学不同,必须介入人类创造的理想价值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如果它不包含人类的价值,也就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1]第二卷,335
张申府认为,宇宙与社会也可以通过人类的价值变得更完美。[1]第二卷,445因此,敞开一切的可能性才能够成为一种有活力的哲学。[1]第二卷,474
二、 张申府的具体真理观
(一)对抽象的真理的排斥
张申府排斥抽象的真理,认为可以在具体的事实中寻找真理。他认为,抽象的真理更多是人们头脑中想象的产物,存在这样的真理是不可理喻的。
真理是表现许多事物间的关系或事物变化发展的情况,先事物而存在的真理是没有的。[1]第二卷,446
他说,如果一种所谓的真理,不依据任何实际,或不依据事实的知识和逻辑,那么最好把它抛弃掉。他强调,真理及知识必须依据具体的实际和事实。[2]第三集,215虽然如此,也不是说一切唯心论的哲学都要被抛弃或否定,因为它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具有时代的普遍性,也得到过创造性的生命力,因此也应该包容它。[1]第二卷,336
张申府说,真理应该寻找在具体事物中的理由,但是当时许多中国人把过去所讲的“理”认为是想当然的真理,因此他们的思维不能够得到发展。“中国人所讲的理就只是想当然耳。”[1]第二卷,446
许多哲学家将宋明理学家所讲的“理”认为是万古不变的法则,完全没有考虑其探讨的具体对象,并据之作彻底反省。张申府强调,过去对的,现在则可能不对,而过去错的,反而现在可能是对的。“过去的‘是现在可能是‘非,过去的‘非现在也可能是‘是。”[1]第二卷,446
真理处在时时刻刻的进化状态中,决不是在固定不变的状态当中。“真理也在一步步的进步中或变化中。”[1]第二卷,446
(二)具体的真理的必要
张申府说:“清楚明白的最后归宿或最后标准必须是说到具体事实上去。” [1]第二卷,342因此,假如要寻找一个真理,那么就必须在具体的事物里寻找。[1]第二卷,342在具体事物中寻找真理是非常容易确定的,并与实际结合起来,也能很好地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应用。因此,必须明确其根据,辨明其适用范围,因为知识体系中不该出现混乱和模糊的情况。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得到丰裕的生活,并据之建设理想的世界。
张申府进而分别真理和非真理,并提出了具体和抽象的标准与方法。其标准即是所、分、当。任何理论和道理,孤立的,笼统的,或模糊的,必须分辨得分分明明才行。他相信,这必定能够帮助人们判明一切知识以及任何真理的真相。
更不可以抽象来说,也不可以笼统模糊含混着就算了然,就断定其是非。[1]第二卷,342
所、分、当三者,第一个是存在的根据,第二个是存在的实在,第三个是存在的意味。张申府说,所有理论必须探讨其解释、对象、范围,才能判定它是否是真理。“一种理论对不对,要看它的解释它的对象它的范围。”[1]第二卷,446特别是在判定的时候,要审察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这样才是把握真理的正确角度。endprint
史达林曾说过:“一切都靠着时间、地点、条件。”一切事物都要以时间、地点、条件来衡量。[1]第二卷,446
张申府认为,只有根据正确的知识体系,才能开创出确实的未来。
三、 张申府的相对的绝对观
张申府不承认有绝对真理,只认可相对真理。绝对知识则是由相对知识转变而成的。一般的知识,大体上都是相对的知识,而且依据着相对的逻辑。但这样的知识是可以变换为绝对知识和绝对真理的,因为绝对真理必须是具体的,才有其实在的根据,才有其适当的事实。
(一)相对的重要性
张申府所说的一般的知识,大多数指相对的知识。“所以普通所有都是相对真理。”[1]第二卷,308
相对知识在积累过程中,其内部会有矛盾对立出现,而矛盾双方又是相反相成的,进而维持着平衡的状态,就成了绝对知识。也就是,乘着这样不断变化的平衡状态,才成为一种法则或真理。[2]第一集,130
“必积起来,即相反相成(乘)起来,乃能着绝对真理,必须审变持常,明权达经,乃由相对而到绝对。”[1]第二卷,308即便如此,这样的状态并不能永远维持下去,而是处在不断进化与变换过程中的,并且一心一意要驶向绝对的目标。这正是一种辩证的过程。
此辩证过程的前提是相对的对象。张申府在《易经》当中找到此辩证法的原型。[2]第五集,229《周易》云“一阴一阳之谓易”,他反问道,阳与阴之间是如何发生相互作用,然后才产生那么多现象的呢?[1]第二卷,446阳与阴之间的相互交叉生成万事万物,此变化过程正是《易经》所要记载的。其语言是相对语言,其知识也是相对知识。其意向是否面向着统一性的绝对呢?此种阳与阴之间互动并且相反相成的生成变化,是否与辩证唯物论中正反之间不断地反复并走向统一非常相似呢?[1]446张申府认为,这完全可与辩证唯物法配合起来。
(二)绝对观的必要性
张申府说没有绝对,但有绝对化的。在运动的世界里不可能有固定的绝对,但并非没有绝对化的。[1]第二卷,342他说,因为绝对存在于具体当中,所以绝对的真理产生于具体的相对的真理。因此,具体的、个别的真理即是绝对的真理,这又被包含在相对的真理里面。
“在客观的对戡法,绝对也要求于相对之中。”[1]第三巻,214绝对的真理只有在变化与进化中才存在,决不是静止地存在着。[1]第二卷,308
四、 张申府的不平衡的相对价值观
张申府说,如果要达到价值平衡(化),就不得不加入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因此,应该根据人类的理想来建立此价值标准,并按照此标准来调节这个世界。
“什么是价值?价值就是‘值,即恰逢,正当之义。”[1]第二卷,179这就是任何事物相遇时所发生的互相保持其适当状态的价值。因此,任何事情都必须加入人类的主观作用,并且外在事物不具备客观的条件时,就不可能得到价值的平衡条件。[1]第热卷,306由于这些客观条件,才可以维持主观的、本然的价值。[1]第二卷,336张申府所提出的价值的平衡标准就是“中”。“中正是价值的标准。”[1]第二卷,337“中”是一种估量平衡的秤杆,尤其是可称为一种价值的顶点。“中者天下之所终也。”[1]第二卷,343
这个平衡的价值到了完善的地步,必定能达到美的状态。
伟大艺术作品的长久普遍价值一部分就在这个地方。这种作品一定牵涉极广,一定涉到深处。[1]第二卷,336
由于从自然现象中感受到的与从艺术中感受到的美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估量的平衡标准是相同的,也是“中”。“中”也就是价值的平衡秤。
张申府提到的平衡秤“中”,是价值的标准,而此标准的标度则是“所”、“分”、“当”。假如从所、分、当的标度中脱离就是“失”,所以要尽量避免。“‘失所为愆。‘不中则失。凡话都有其所分当。得其所分当就是‘中。‘中者天下之所终也。失所,过分,无当,都是要不得的。”[1]第二卷,343-344
孔子之所以是圣人,在于他能够“时中”。他规定人的普遍本质是仁,这是时代非常需要的一个精神,这里已经包含有时代适当的平衡价值,因此人们称他为“时中”的哲学家。孟子称他为“时圣”。“‘中并不是一定。所以孔子要‘时中。”[1]第二卷,344
张申府的价值平衡观不通过人的主观作用决不可能实现。“价值是不能离开主观的。……不过于此所谓主观是社会或阶级的,却不必是个人的。”[1]第二卷,179
可见,张申府所说的这个主观作用不是孤立的,必须与客观连接在一起才可以发挥作用,否则主客观之间的作用就是不正常的。[1]第二卷,336由此,此平衡的秤杆才能起到正常的调节作用。
价值就是“值”,即恰逢,正当之义。但必人认识了或感到了或规定了,乃成了人的价值。[1]第二卷,179
张申府说,因为人们的主观与客观并非无关而孤立,所以理性调节才是可能的。他反诘道,不这样的话,又怎样才能建设富有价值创造的未来世界呢?因此,反过来说,不平衡的平衡观,乃是张申府哲学的顶点。[1]第二卷,344
(一)对生的认识——不平衡的平衡价值意识
物质生命本身是有优劣的,但是达到其生命的充实感觉状态时,则不可以论其高低。
在原则上根本上来看,我认为人生第一要遂生,第二要大生,第三要美生。首先应该满足人类的生活需要,满足了人类的生活需要之后然后扩大,最后再美化人生。[1]第二卷,447
生命不得不运动与进化,因此从生命的充实的价值角度可以将生命区分为三类,即遂生、大生、美生。生命的充实同时也无法避免其价值判断。价值的不同状态不能用高低的阶级来判断,只能根据其充实价值分别为三种:折中之中、射中之中、最中之中。
1.“遂生”——“折中之中”的活着状态endprint
人的自然生命必须处在充实的状态并维持活着的状态,就是遂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必须克服外在条件并充分发挥自己的生命活力。所有的个体生命必定会受到外在的压力,不得不做出防御及挑战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必定会发生矛盾与对立,也必须通过调节才能达到充实状态。因此,遂生就是克服矛盾对立并维持生命自身的活着的力量的状态。由此达到人们生命普遍价值的充实、充满的高潮,也可说是“折中之中”状态。[3]55
2.“大生”——“射中之中”的活着状态
张申府所讲的“大生”是人的生命自然地融化到社会生命中并成为道德的状态。如果能自觉到人们的个体生命蕴含在具体的社会里,那么就要将自己的自然生命投入到社会当中,与其他许多生命一起同心协力,进而扩大到社会生命,就是“大生”。也就是说,“大生”是自觉到自己生命的社会化状态,自己生命和社会生命同一而不可分割,并一直前进到未来的状态。这样,生命才能充实合一并充实到更为充沛的能够维持安定的状态。譬如说,两个生命融化为一体,如箭穿透箭靶,或如一个箭正好射中靶心的高潮时刻,也可说是“射中之中”的状态。
3.“美生”——“最中之中”的活着状态
将自己的生命融化在社会里,为了更大的生命而发挥自己的生命,特别要对与他者的关系作出调节,达到最和谐的状态,这就是“美生”。也就是说,认识到物质自然的不平衡,并以调节此不平衡的状态为己任。以艺术作品来作喻,在绘画中,可以放大或缩小,可以使用远近法和明暗法等,特别是时而留出空白又时而突出重点,但总是给人们全面的安定感。这一点告诉人们价值调节功能的重要性。
将此客观存在的不平衡状态使用明暗法等进行调节,进而维持安定和活力感觉,就是艺术。此种艺术行为可以将生命提高到最高状态,以此与他者的关系达到圆满与完熟的状态。一个人生命自身拥有的有限活力达到最高潮的状态,就是“美生”。“美生”可以说是将人们的创造理性发挥到最正常和高效的状态。
“美生”是他所说的“最中之中”状态,人们生命的充实度达到最高,并在这最高点上维持着最圆满的关系,特别是达成一个自动机构的状态而运动着。与各种各样的生命同时运动,却是矛盾最少的状态。生命的活力达成最完善的状态,因而人们的理性得以最正常发挥,其活着的生命力也达到其顶点状态,即是所谓的“最中之中”的状态。
(二)对美的认识——不平衡的平衡价值观
1.自然美观
张申府认为,自然本身具有普遍的美,可以被人内部潜藏的能力所认知,但不可以说本身已经充分含有客观的美了。“对于美,要有能感于美的主观,也要有客观上必须具备的条件。”[1]第二卷,336自然在实际上本身就含有美,尤其是处在高潮的平衡状态更能展现出美来。自然的美也不是恒常不变的,因为它是不停运动着的,而且是进化的运动。对此,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中已经举出其原因和实例了。
自然中最美的状态是在维持着物质间的平衡状态的时候。但是其平衡状态不可能永恒维持,会在特定的时候转变为不平衡的状态,不停地运动变化,才会有变化中的进化。总归来说,自然是由于不平衡的平衡才可能有进化。因而,自然的美是在不平衡的平衡与平衡的不平衡状态之间反复转化中产生美并得到生动的状态的。自然中普遍的各种美的现象正是由于相反相成的作用以及不断反复并对立统一,才能维持着不平衡的平衡状态。因此,这种观点可称为“不平衡的平衡观”。正因为自然物质间维持着不平衡的平衡状态,才维持了美。
2.艺术美观
艺术是通过人类加工而形成的创造物,所以不能不加入人类的价值。因此,艺术可以说是将人类的普遍创造性与时代生命力结合在一起产生出的一种创造物。人类的主观作用不可不发挥出来,而且是违背着客观条件出现的。由此,艺术作品中含有的普遍价值借着客观的形式表达出来,同时融化于社会价值中。因此,张申府认为,艺术价值也可说是社会的普遍价值,其价值是存在于公共场所里的。
“伟大艺术作品的长久普遍价值一部分就在这个地方。这种作品一定牵涉极广,一定涉到深处;一定所涉的是人与人间的共同之所。”[1]第二卷,336公共场所正是公开的市场。市场是形成社会价值的地方,因此可说是富有时代精神的。又,此普遍价值基本上就是不平衡的平衡价值,自然物质正是以不平衡的平衡形态存在着。他认为,将物质的不平衡状态加以补充,自然物质的普遍价值就可以生动地转成为活力状态。据此,张申府使用艺术价值来说明。确实,如果不将物质的客观价值里加入人类的普遍价值,其客观价值是孤立的,不具有活力。人类所追求的平衡价值也不过是一种不平衡价值,因而在此也流动着进化的作用。但为了维持安定的状态,所以必须强调不平衡的平衡价值。总而言之,艺术的普遍价值转换为社会价值,才是时代精神。
结 语
张申府追求的是使人们从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中解脱出来。为了将人生维持在“中”的最佳状态,先要了解人生的本质并予以阐明,尤其是要了解创造并维持人类自身活力的制度及系统。他一直在思考人如何才能活着,又怎样才能像人一样活着这两个命题。就这样,他成为思考着这两个哲学命题度过一生的哲学家。[1]第二卷,447他以解决这两个命题为己任而活着,一生都为此东奔西走。
他亲耳听到西方列强的铁蹄踏碎了国家大门的声音,而成为以学问来奋斗并坚守民族气节的一位书生。他亲耳听到日军空袭下百姓的苦痛、呻吟,而成为抱有建设新中国梦想并为之东奔西走的一位热血男儿。
他一生都在寻找能让人们焕发活力的哲学以及保障此种活力的社会和制度。他认为,不能开创新未来的可能性的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在他看来,哲学对根源加以探求只是抓住可以打开未来的初端,但初端与终端是链条的两头,所以终端也必须加以关注。[1]第二卷,447
如果一位哲学家忘记了生命怎样活着才最理想的问题,应该说不算是真正的哲学家。张申府对真正的哲学划出的一个标准就是看能否开拓出未来的可能性。他生活在生命受到巨大威胁的时代,因而开创出新的危机哲学。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人类生命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申府.张申府文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2]张岱年.张岱年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3]金周昌.张岱年兼和哲学的和平论构想[J].江汉论坛,2013,(2).
(责任编辑 吴 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