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娅的青春期传奇 等
胡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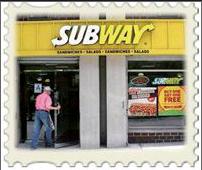


在美国的时候,遇到一位奇女子——索尼娅。她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在我们住处附近的一家赛百味快餐店打工。
当她得知我来自中国,惊喜地说:“我去过北京,七次。批发些衣服鞋子,运到我们国家去卖。”
哦,原来是与那批在中俄之间做贸易的“国际倒爷”一样的生意人啊!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可不是一般的能耐。
我问她为什么来美国了?
索尼娅朗声笑道:“有机会就来了呀!”
索尼娅7年前持访问签证到了美国,然后嫁了一个美国人,留了下来,现在已经拿到美国绿卡。
与常见的老夫少妻式的跨国婚姻迥异的是:她的美国丈夫比她小11 岁,今年42岁。
“你的丈夫这么年轻?”我十分惊讶。
“是的。我也很年轻呀!”索尼娅笑指自己的胸口说,“我心里很年轻,我的丈夫经常这样说我。”
她说:“我刚来美国时,不会英语。我以前在学校里没有学过英语。我们当时学的外语是德语。”
没有任何英语基础的索尼娅,在她46岁那年起步,通过日常的生活交流,像幼儿牙牙学语般,一句一句地学到了可以与外国人沟通的水平。
她年轻的心态、开放的性格、热情的生活态度、敢于从零起步的勇气,让她的人生散发出一种特殊的光泽,一种青春的朝气。
她兴致勃勃地规划未来。准备去学一个护士课程,拿一个初级护士执照,去牙科诊所工作,薪水比她现在工作的赛百味餐馆高。她已经打听到了,3000美元学11周,每周上一整天课。她以前在乌兹别克斯坦做过近二十年的护士,重操旧业,应该不难。
索尼娅的传奇故事,让我心有所感。一个人的“青春期”到底有多长?人为的招聘和退休的年龄设置,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催老我们的心理?有的人从懵懵懂懂中刚醒来,就发现自己已经被送入告老叹老的行列,几乎没有年轻过。
53岁的索尼娅依然健康、快乐、自信。“青春期”的这个阶段真好!
逝去的国祥
柏代华(上海,外企高管)
不久前闲聊时妹妹告诉我,韩国祥死了,你知道吗?胃癌还是肝癌吧。我心头一阵惊悸和悲怆,他是我中学同学,才五十多岁。
我问了才知道他一直住在我一个连襟的楼上,我内心又掠过一阵震颤,虽然住得很远但二十多年来去那里也不下几十次,居然完全不知少年时朝夕相伴的好友就居住在头顶上方的咫尺之间。我从来没有问起过他,也从来没人谈起过他,可见韩国祥卑微至不足外人道也。
国祥中学时的绰号叫“饼干”。他父亲长年病残卧床,但也没闲着,一口气鼓捣出三子三女。半寡的母亲全靠两只手把六个孩子拉扯大,日子显然不像拨弄六弦琴那般美妙。一天国祥吃了同学给的饼干后回味无穷,兴匆匆跑到门口对正在摊晒破烂的妈妈说:妈妈,买饼干。穷困窘迫的母亲抬起憔悴的脸一声狮吼:买屎给你吃!从此他有了“饼干”的绰号。嬉闹时每闻此号他都拔拳相向,但只是轻轻捶一下。对同学好友他一向忠勇相护,不畏凶险。
有一次我从二楼走廊向下吐了一口唾沫,高年级的一个小霸王恰巧走过,王颜大怒,直冲而上。国祥上前一步用高壮的身子挡在我前面。对方悻悻而退,撂下一句狠话“放学再说”。果然刚出校门,一帮人拿着棍棒汹汹而来。国祥见寡不敌众急忙拉着我夺路而逃。霎时砖石如雨般从身后飞来,国祥护在我身后推着我一路狂奔。在这场飞石战中我是众矢之的,只顾逃命,国祥是人肉盾牌,贴身护送。结果我毫发无损,国祥手臂有两处淤血。
有一年学校组织学生到郊外野营拉练,恰逢大雨。我一向身瘦体弱手脚笨拙,背着大包战战兢兢地走在泥泞狭窄的田埂上,三步一滑五步一歪。若不是紧跟身后的国祥屡屡出手扶住,我肯定摔成了泥人,放到当年红极一时的“收租院”泥塑展厅里客串一个佃农的儿子基本无需修饰。
虽然忠勇可嘉但国祥口拙寡言。除了几次震动全校的群架中勇猛的雄姿,很少有人注目。毕业后韩国祥参军去了,这差不多是当时最为令人羡慕的荣耀,街坊热议之炽不亚于今日中了头彩。国祥的部队驻扎在江西樟树,军队的生活想必是严峻清苦的。但那段岁月大概是他不长的生涯中最为灿烂的篇章,因为他空前绝后地受人关注、羡慕、尊崇。
复员后他回上海进了上钢三厂。渐渐不再往来,最后失去了音讯,直至噩耗传来。听说从就医确诊到撒手人寰只有短短两三个月。
岁月神偷
翁 俊(美国芝加哥,创业者)
从降落就在下雨。机场通关和租车都不顺。两小时后,我到了克拉拉楼下。她是几个月前搬到多伦多这间公寓的。
克拉拉很瘦小,灰色薄绒衫和蓝色牛仔裤,脸颊凹下去,原就凸起的颧骨,更显凸出。来之前,她说只有80多斤了,但吃得比原来健康。我想亲眼看看。
她给我做了乌冬面,放了鸡蛋花、甘薯条和虾仁,味很淡。她一向不会做饭。但我饿了,且在这个朋友面前,不必拘束。我要了盐和醋。
她像以前一样话多,谈起她的前夫,也谈到我的事。她谈起一个美女朋友,如何规划自己的感情和婚姻,把男友培养成忠心耿耿供养她的依靠;从这个朋友身上,她学到了以前忽视了的观念和本领。她说她不再去华人教会了,改去白人教会。华人素质低,嫌她资历浅,听她发表观点和意见,很不服气。女教友看到男的对她献殷情,就冷嘲热讽。她在网上贴了职业规划的文章,举了清洁工的例子,发给那些人看,引来口诛笔伐,说她看不起体力劳动。但在白人那里,她深受欢迎,找到了属于她的圈子。我问她是否考虑回国。她说,她已经西化了,接受不了国内的价值观和龌龊事。
第二天上午,我去接她。她在屋里放着宗教音乐。我问,一大早就听宗教音乐,信教是否有点过了。她反唇说,我听的陈淑桦的歌是靡靡之音。我聊起最近看的日本老电影,谈起川端康成,她说不知道。我又聊起《达人秀》,她还是不知道。她说,女的嫁给有钱人不一定好,教会里一个搞艺术的女人,嫁了个有钱的香港人,却得了抑郁症。我逗她说,都是信教害的。她非常生气,不再和我说话。endprint
我请她和我去千岛。她说有个网上课程,她还要参与讨论。我从千岛回来,她从外面回来,说网上课程取消了。她问千岛怎么样。我说一般。她说,我是人云亦云,别人去了,我也非得去。我累得不想说话,只请她去吃最后一顿晚餐。晚餐很丰盛,我不停地吃,她不停地说。
我想起大学时的克拉拉,夏天连衣裙,冬天红底黑格兜帽大衣,马尾辫,唱歌弹钢琴,向往住校生活,喜欢我们去她家。我想起6年前,她和前夫来芝加哥,红润的脸,抹得猩红的唇膏,旁若无人地笑。
回芝加哥的隔天晚上,我梦见回到了大学,那无忧无虑的时光。“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
爱心一日游
江凯南(石家庄 编辑)
六一期间,跟随某公司参加了其策划已久的“赴保定某贫困小学爱心捐赠活动”。
经过近两个半小时的舟车颠簸,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还未下车,便看到学校门口稀稀拉拉站了七八位小朋友,新奇又腼腆地笑着。乡镇及学校领导热情地将我们迎进学校。踏入校门,映入眼帘的是齐刷刷坐成七八排、佩戴红领巾的小朋友们和三层崭新的教学楼。
主席台上桌椅早已摆放好。对方满脸堆笑地将公司领导迎进简约的会议室,热心地捧着红枣让我们尝尝,笑着说:“都是自己种的。”
休息片刻之后,领导们就坐主席台。乡镇领导及公司领导依次讲话,一讲完,站在旁边貌似老师模样的中年男人,便带动孩子们鼓掌。这群小家伙们或许根本不知道在进行着一项怎样的活动,只是铆足了劲地拍手。炽热阳光的炙烤下,每个孩子都不由自主地皱紧眉头。
五个孤儿排着队依次领走了每人一千元的助学金,事先安排好的十几个孩子依次为公司领导系上红领巾,接着便是赠送锦旗、拍照。发放学习用品时,偶尔听到学校领导说:“为节省时间,我们安排了几个孩子,象征性地领一下就行。”
将近半小时之后,所谓的捐赠仪式结束了,孩子们纷纷搬着小板凳回教室。目送着这些孩子,他们的眼神里满是新奇和不解。有个扛着摄像机貌似当地电视台的记者说:“本来还安排了几位领导讲话的,但是天气太热了,怕孩子们受不了。”不远处,戴着红领巾的公司领导们兴奋地拍照、发微信——相信这些微信马上会在朋友圈里赢得很多个“赞”。
离开时,乡镇干部将我 们送到校门口,一再嘱咐照片记得给他们发过去。而等待我们的将是又一个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临上车时,我再次看了一眼这所拥有崭新楼房、平整地面的学校,一种无奈和讽刺感油然而生。此次之行完全打破了我当初的想象。一个企业想为社会奉献爱心本是高尚的事情,而我看到的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形式主义。
真正深入那些有困难的乡村和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弯下腰来,跟孩子们聊聊天,陪他们做做游戏、听听课,或者仅是简单地同他们一起吃顿饭,花上一天的时间真正走近他们,让孩子感觉到有温度的关心和爱,比单纯地送点钱物,摆拍几张照片,要有价值得多。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