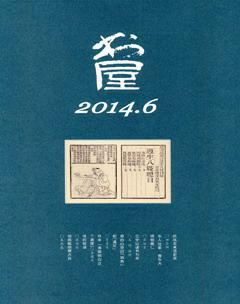泰戈尔与中国:如果没有谭云山
孙宜学
泰戈尔1924年访华期间,在喧天的热闹中,谭云山第一次被泰戈尔感染:“太先生游中国时,我们老大的华夏,也曾经宣传殆遍。我当时还在国内读书,因被其影响,即有‘心向往之之意。”谭云山也像当时的诸多中国青年一样,十分“关怀他在中国的活动,看过他所发表的所有讲话与演讲。我也读过他的作品的翻译和他写的英文书”。
可惜他当时并无机会见到泰戈尔。
1924年夏天,谭云山只身来到新加坡,教书、写文章、办杂志,并准备赴欧洲勤工俭学。1927年7月,泰戈尔赴东南亚各国讲演,在新加坡,谭云山得偿夙愿,拜访了老诗人。
“我一见到泰戈尔就觉得他是印度的代表与象征。”谭云山坦诚地向自己仰慕的诗圣谈了对印度文明的向往,对佛教的理解。泰戈尔为眼前这个年轻人的求知精神所感动,就谈及自己欲在国际大学开展中国研究的设想,并诚邀谭云山赴印度从事这一工作。
谭云山就此与泰戈尔和印度结下了永恒的缘分。
小人物做成大事情
1928年9月,受到泰戈尔感召的谭云山奔赴印度。他希望能和泰戈尔一道,把中印两个伟大的国家重新联合起来,使“当今充满残酷敌对、暴虐残害冲突的世界变得仁慈”,而他眼中的泰戈尔,“正是这种愿望的象征”。他到印度,最初只将国际大学的工作作为在印工作的一部分,但他很快就被泰戈尔这个“思维的聚焦”完全吸引住了,尤其是泰戈尔要通过国际大学实现“世界和平”与“东西汇合”的愿望,使谭云山深深迷醉。所以他一到国际大学,就完全被吸引到国际大学的教学和组织中国研究的工作方面,其他计划反而都退而居其次了。
泰戈尔1921年创办国际大学后,就欢迎世界各国的学者和学生到国际大学。1924年访华期间,泰戈尔就多次邀请中国学者到国际大学去工作和研究。“太戈尔先生本极盼望我们中国多有几个人来。当他游中国时,闻与梁任公先生曾有商量,想把国际大学学生与清华学生交换,不知怎的没有实现”。他还表示愿和中国学者一道共同组织中印学会,“共谋发扬东方文化,实最欣祷”。访华回国后,他一直希望尽快实现这个理想,推动国际大学的中国研究,但苦于无合适的助手。谭云山抵印后,他将这个愿望的实现托付于谭云山。
谭云山深以为荣,并视为使命。
1931年9月,谭云山“怀着师尊的理想与使命”回国。为了这个理想,此时他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去见了本国的许多要人”,他没想到的是,这些政要对他组织“中印学会”的“呼吁的应声,是出乎意外的与非常的顺利”。蔡元培、戴季陶、陈立夫、叶楚伧、许世英、叶恭绰、太虚法师等名流都表示大力支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院院长居正,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及国民党元老张继等都予以赞助,并且希望中印学会成立后即可“举行种种有关两国文化之事业。如创办学院,交换教授,交换学生,互派考察团等等”。
经过谭云山的不懈努力,组建中国中印学会一事渐现轮廓。1933年9月,谭云山从南京给泰戈尔写信,报告了此事的进展情况:
许多知名人士和云山正发起“中印学会”,目的在于把我们两国的文化联合起来并恢复亲切、古老的历史情谊。已经有适当组织并在中国得到广泛同情的中印学会不久将正式成立。……以中印学会为基础,经过我们共同努力,定能实现您通过发扬东方文明来构造宇宙和平的伟大理想。
1934年初,谭云山返回印度,向泰戈尔详细介绍了中国“中印学会”的筹备情况以及中国社会各界的支持。泰戈尔听闻非常高兴,立即请谭云山协助组织成立印度“中印学会”,并愿意以国际大学为学会的根据地,以国大党为中心,并亲自担任学会的领导。因为有泰戈尔亲自领导协调,印度“中印学会”的组织非常顺利。
1934年4月23日,印度“中印学会”在国际大学举行成立典礼。泰戈尔亲自担任会长,尼赫鲁任名誉会长。
中国官方、民间都很重视印度“中印学会”的成立,并寄予厚望:“中印民族文化复交与复兴之期,当不远也。”处于民族危机中的中国人,还赋予“中印学会”更深的内涵,即中印民族复兴:“今日两国之关系,实更为重要。不论在任何方面言,两国实有急急携手与联络之必要,即孙总理所谓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也。”
印度中国学会一成立,中国“中印学会”的筹备和成立就愈发迫在眉睫了。泰戈尔也一直在关注并推动着此事的进展。他还在印度发起签名活动,邀请印度各界著名人士联名致函中国学界,希望在中国尽快成立“中印学会”。1934年4月18日,他“致函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及各学术团体”,“提议组织中印文化协会,以联络两民族之感情,并阐扬中印固有文化”。他希望中印两国凭此再度携手“发起中印学会,以图恢复中印文化之沟通,与人民之联合,此实为吾毕生所致力之事业。今得诸位以为沟通奋斗之同志,使余至为庆幸”。戴季陶、梁漱溟等许多社会名流纷纷响应,并请谭云山具体拟定相关章程。
1934年12月,谭云山从印度返国,即以印度“中印学会”“主干”的身份,“向政府方面接洽中印学术合作事项”,得到积极响应。谭云山回印度向泰戈尔说明了进展情况。1935年2月2日,谭云山再次从印回国,“进行正式组织中印学会。因中印学会虽由中国方面发起,但尚未有正式组织。印度方面既已成立,中国方面自应从速组织”。在谭云山的不懈推动和协调下,1935年5月3日上午十点,“筹备甚久之中印学会”假借南京新亚细亚学会举行发起人大会,出席者有蔡元培、戴季陶、叶楚怆、陈立夫等二十四人。会议推举蔡元培为会议主席。戴季陶、谭云山首先报告了中国“中印学会”的发起缘由、筹备经过和宗旨,随后会议讨论通过了学会章程。会议推举蔡元培、吴稚晖、王震、叶楚伧、陈立夫、陈大齐、许崇灏、段锡朋、谭云山九人为理事;戴季陶、许世英、徐悲鸿、辛树帜、马鹤天五人为监事。会议随后举行第一次理事会和监事会联席会议,推举蔡元培为理事会主席,戴季陶为监事会主席。
中印两国“中印学会”的成立,使中印文化交流有了组织机构的保证。而作为其中最主要的推动者和桥梁,谭云山的努力得到了中印两国政府和学界的高度评价,被戴季陶誉为“不亚于佛教高僧玄奘、义净的壮举”。
中国学院首任院长
按照泰戈尔的设想,“中印学会成立以来,首要计划,先在印度创设一中国学院”。而这个计划,没有中国人的帮助和合作,是绝对不能完成的。泰戈尔迫切希望得到中国各界人士的帮助。他多次给戴季陶写信,“商陈此事”,并亲笔致函中国各文化团体和一些知名学者,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望贵国国学前辈加以提倡,与以维护,使贵国文学经术得以流传敝土。”“如有俯赐赞助者,乞函示鄙人。或予以年捐,或赠以书籍,皆学院急需之品。”1934年9月,谭云山在泰戈尔的帮助下,制订了成立中国学院的详细计划。泰戈尔很满意,并写下批语,希望中国各界“给予我的友人谭云山教授以慷慨的援助,俾使这个计划实现,为中印两国紧密的文化交流创造一个永恒的机构”。
1934年10月,带着这个计划,谭云山回国“化缘”。他向各学术、教育机构及政府相关机构表达了泰戈尔建立中国学院、中国图书馆和学生宿舍之事,并说明国际大学已为此辟出“地皮数亩”。他希望国内各界也能捐赠相关书籍。中国政府、学界没有辜负泰戈尔的希望,谭云山获得了当时“几乎所有重要人物的同情与热心”,包括蒋介石、林森、汪精卫、居正、于右任、蔡元培、戴季陶、叶楚伧、孔祥熙、陈立夫和朱家骅等。谭云山将情况写信报告给了泰戈尔。12月8日,泰戈尔回信说:我“真挚地希望中国学院的计划不久将会实现。”
谭云山也希望早日建成中国学院,“以符总理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共同奋斗,以沟通中印文化,促进中印邦交”。他实际上也已经有了周密的构想,包括:组织中印文化考察团;在中国设立“中印学院”或“印度学院”,在印度设立一“中印学院”或“中国学院”;出刊中印书报;建设中印图书馆及博物馆。谭云山对此充满信心:“只要事有计划,有办法,有人才,有精神,有成绩,实不难办到。”只可惜后因中国国内形势剧变,其中的很多计划都来不及一一实现。他还曾争取到新加坡华侨胡文虎的支持,愿意捐赠建设中国学院所需费用,可惜最终落了空。
泰戈尔的诚心感动了中国。为了实现泰戈尔设计的这个中印友谊蓝图,中国社会各界、各文化团体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进来,呼吁支持建立中国学院,捐钱捐物捐书。教育部还专为此向“各市县政府,省立各校场馆”发布第779号训令,征求图书等。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谭云山终于筹措到了建立中国学院所需资金和书籍,甚至超出了原计划。其中,中国的中印学会捐赠了建筑“中国大厦”的费用,并购买了十万卷中文图书。各文化机关、大学、出版社也都采取了积极行动,如商务印书馆也捐赠了约五万卷图书。1935年8月4日,泰戈尔写信告诉谭云山:“中印学会已经寄给我作为建筑中国学院费用的三万一千七百十二卢比七安那半的支票。……我知道,这件大事只有你那不知疲劳的活动才能办到。”
1936年6月19日,谭云山从香港乘轮船返印,“古籍万卷,戴院长赠予印国际大学,将由谭云山携往”,“第二批亦十万卷,俟汇齐后,即可运寄”。在香港,谭云山接受了《中央日报》记者的采访,特别感谢了国内各界在经费和图书方面对建设中国学院的支持,并说“一俟本人返抵印度,即行开始建筑”。
1937年4月14日,中国学院举行开幕典礼,泰戈尔请谭云山担任院长,甘地、尼赫鲁致信祝贺。甘地还专给谭云山写了一封信,特别表示:“我们确很需要中印两大民族间的文化交谊。你的努力很有价值!”在谭云山的细致策划下,蒋介石和中印学会蔡元培、戴季陶亦致电泰戈尔祝贺。中国学院成立后,泰戈尔亲书戴季陶,请他担任学院的护持人;谭云山也致信戴季陶表达此意。4月8日,戴季陶复信泰戈尔欣然应允。
在泰戈尔的直接推动下,经谭云山和中印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学院很快成为印度的中国学术和文化中心,对促进中印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11月,戴季陶率中国高级友好访问团访问印度,1942年蒋介石夫妇访印,1943年顾毓秀率领的文化教育访印团,可以说,中国任何访印团体,官方的或民间的,都把中国学院作为必经的一站。徐悲鸿、叶浅予、巴宙、周祥光、冉云华、周达夫等学者,也都在中国学院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就这样,通过中国学院,“泰翁的博爱精神,实已与中国的领袖和人民建立起永久的友谊。所以今天,他的肉体虽已逝去,而他的精神却仍把中印人民联在一起”。
在中国学院的创立过程中,谭云山是跨越喜马拉雅山的桥梁、纽带和彩虹。他用自己的热情和坚持,汇聚了中印两国的力量,将中印两国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并开通了中印两国一条友谊的通道。可以说,如果没有谭云山,可能就不会有中国学院。
“我对谭云山教授为建立中国学院而筹集基金的富有勇气的努力”表示敬佩。1936年4月,蔡元培在给泰戈尔的信中说。谭云山受之无愧。
泰戈尔理想的中国化身
中国人眼中的泰戈尔,有一个从虚到实的转变,而转折点,即中国的抗日战争。1924年泰戈尔访华前后,中国人崇敬泰戈尔,主要是因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敬慕的更多是奖章的荣光,是想像中的泰戈尔;这一时期泰戈尔一心要带给中国的,也多是中国人视为虚幻的爱与和平。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泰戈尔对中国的支持变得具体而实际,他作为世界著名诗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带给中国人巨大的信心和信任,他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也变得如邻里老人一样亲切实在。而促成这种转变的关键人物,就是谭云山。因为泰戈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和支持,主要是通过谭云山传达给中国政府和民众的。
泰戈尔第一次比较具体了解日本在中国的暴行,是1937年秋他重病期间。9月18日,听闻泰戈尔重病,蔡元培、戴季陶等人联名以中国中印学会的名义发来慰问电,请谭云山转告泰戈尔。谭云山将信翻译给泰戈尔听,并向诗人说明,这封信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敬爱之意,而中国此时正在日本飞机大炮轰炸之下。泰戈尔因病很少看报,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还不太清楚,听谭云山讲了日军在中国的种种暴行,他非常吃惊。9月21日,他口授了一封回电,对中国友人“在生死存亡奋斗之际”仍挂念着他的病情,深表感谢。他在信中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恶,并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不胜钦敬。”
“卢沟桥事变”后几个月内,对日本一直抱有敬意的泰戈尔多次公开发表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抨击,这对中国的抗战是极大的精神支持。“可以说是在这次的中日战争之中,几件最可宝贵的文献;并可以说是在人类正义与暴力奋斗之中,几个最尊严有力的檄告与宝筏。除此之外,太戈尔先生在谈话之中,在演讲之中,对于这一次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事,陆续不断地所发出的呼声,所表示的悲愤,更是难以尽述”。日本政客又惊又怕,就千方百计收买他,欺骗他,但都被泰戈尔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谭云山耳闻目睹了泰戈尔对中国的深情厚谊,深受感动:“他老对于这一次的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反抗的战争,始终是站在他自己的伟大的立场,发出他拥护和平与东方文化的呼声,伸张他维持人道与正义的主张。不论日本人是如何设计央求鼓吹,他老的立场与主张,总是不为所动,不为所变。”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加剧,他们在“中国所表演的暴举兽行愈来愈凶”,“所有这些事情,真使太戈尔先生伤痛到不可言说。他老人家除不断地大声疾呼之外,又申请印度人民捐募款项,以为中国学生及被难民众等作救济。他老并首先自捐五百卢比,以为倡导。国际大学又特别演过一次歌剧,以为中国难民筹款”。泰戈尔的这些支持活动,谭云山都以各种方式及时向中国政府和民众予以介绍。
1938年4月底,为了实地了解中国抗战情况,并向国内通报中国学院的建设情况,谭云山回国。4月12日,谭云山回国之前,泰戈尔亲笔致书蒋介石,另外还“写了一篇很长的‘使音(Message)”交谭云山呈蒋介石“转致中国人民,以表示他老人家的同情与敬意”。5月9日,谭云山从印返港;20日,谭云山在湖南对记者说:“泰戈尔先生,及印度国民大会领袖尼赫鲁先生等,大声疾呼,为我声援,并对日本在华惨无人道之举动,予以揭发与痛斥。……予侵略者之打击不小。”5月22日下午,他应邀在长沙的青年会演讲,赞扬了印度人民及泰戈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引起听众共鸣。
泰戈尔多次对谭云山表示:“我这一生总要再到中国去走一趟,心愿才得满足。”谭云山也一直在设法安排老诗人的第二次中国之行。不料日本侵略中国,计划受阻。当谭云山表示惋惜的时候,老诗人反而安慰他说:“等你们抗战胜利之后,我再到中国去庆祝。”谭云山深受鼓舞,对老诗人说:“等到我们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欢迎你老人家到中国去,也替你老做个大寿。一面庆祝中国抗战的胜利,一面庆祝和平正义的凯旋,同时并为人类前途祝福。”泰戈尔愉快地表示:我们共同祈望这个理想早日实现!
事实上,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也是泰戈尔的健康每况愈下的时期。1941年8月7日,诗人因病逝世。他再次访华的愿望,竟未能变成现实。
谭云山代表中国人民,陪伴老诗人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1942年8月6日正午,谭云山得知泰戈尔病危的消息,立刻从国际大学赶往加尔各答。8月7日,医生告诉他还有希望,他立刻出去给蒋介石和一位中国朋友寄信告知病情。等他回来,诗人已逝。
葬礼上,谭云山贡献了两个花圈,一个代表驻华中印协会,一个代表蒋介石及戴季陶、孔祥熙、陈立夫、朱家骅,“因为他们都是大师的好友和钦敬者”。
此时的谭云山,在一次次沟通泰戈尔与中国的努力中,也已完成了从一位普通的中国学者到现代“玄奘”的角色转换。泰戈尔融合亚洲文化,复兴中印文化关系的理想与希望,化成了其内心“同样的理想”并激励着他,“愿意协力为此共同目标而奋斗”。泰戈尔的世界大同理想,通过谭云山温暖了因战争和灾难而千疮百孔的中国民族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