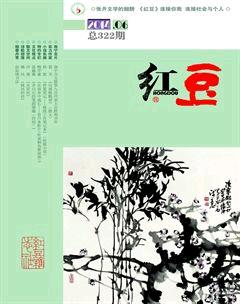杨柳青古镇二题
黄桂元,著名作家、评论家,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自由谈》杂志执行主编。著有大量理论评论和散文随笔作品,在文坛产生广泛影响。
时光深处的石家大院
造访石家大院,最好是在游客渐稀的时候,且以独自为宜。
徜徉于石家大院的甬道、长廊,好似走进背景斑驳的时光深处,又像是置身于一部怀旧老电影的默片场景。岁月的投影依稀映出百年前奢华的钟鸣鼎食和耀眼的杂树生花,纷沓的脚步声、激越的戏曲“锣鼓点”和一阵阵的观众叫好声,仿佛还在耳畔萦绕,瞬间又归于空无。曾经的繁华与衰败、热闹与冷寂生生灭灭,在此处流转,谁人知晓,大院里飘逝过多少人的悲欢喜乐?
当一切尘埃落定,物是人非,还原为传说般的那种寂静,只有缓缓穿过古镇的运河依旧流淌,见证着石家大院的百年沧桑。
旧时代大户人家,喜欢把苏州园林风格融入自家庭院的造型和装饰,石家大院亦不例外。楼、亭、榭、廊在石家花园里各展姿容,一应俱全。石家大院始建于1875年,方圆72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达2900余平方米,由12个院落组成,皆为正偏布局,四合套成,整体设计结合了王宫官邸与大户民宅的建筑特色,既豪华高贵,又祥和亲善,且有着浓郁的家庭气氛。无论其寝室、客厅、花厅、戏楼、佛堂、学堂,还是马厩,都保持了清末民初典型的北方民居形态,堪称北方近代乡镇史的微缩景观。而某些细节还体现出了中西合璧的味道,比如,在一座门楼的顶端可以发现两面小旗交叉形状,仔细辨认,原来是民国时期较为常见的五色旗和十八星旗交汇的图案。
甬道东侧的门楼,原是石氏家族的起居寝室,如今成了杨柳青博物馆的展品陈列区,藏有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历代杰作和砖雕艺术珍品,以及泥人张彩塑、民间剪纸、杨柳青风筝、民间花会道具、婚俗等民间文化作品。甬道西侧则别有洞天,石家戏楼赫然而现,厅堂足有两层楼高,400多平方米面积,立着若干旧式方桌、靠椅,桌上摆旧式茶碗,靠椅铺红色软垫。大厅前方还有一个几平方米的小戏台,两侧挂着布帘的小门,便于演戏者上场、下场出入。当年石家常在这里请戏班唱堂会,可容纳200人听戏饮宴,为北方最大的民宅戏楼,京剧名家孙菊仙、谭鑫培等曾在此各显身手。主要有花厅、戏楼、佛堂等建筑,是石氏家族会晤宾朋、娱乐消闲、诵经礼佛的场所,现辟为博物馆的“石府复原陈列区”,如同一个时代的活化石,储藏着丰富的中国文化符码和信息。
大院由盛而衰的拐点发生在民国后期,起因于后世子弟中多不思进取,挥霍老本,寄生度日。许多家族成员陆续离开大院,搬进了在市区购置的居所,大院的东西开始变卖流失。时光深处的石家大院,终于演绎了绝非戏说的跌宕剧情。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天津地委曾经把石家大院改做杨柳青中学30多年。1991年,石家大院被列为市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2006年,石家大院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随着石家大院的对外开放,吸引许多影视摄制组风尘仆仆,来来往往,张艺谋、葛优、巩俐、刘德华、林青霞、徐帆、刘德凯、张信哲、周迅、李成儒、张铁林等明星大腕都曾在这里隐现、出没,复制着前世今生的家国往事。
谈到石家大院,被誉为“话剧皇帝”的石挥似乎是个绕不开的话题。石挥固然提升了石家的知名度,但其本人并不属于大院的“嫡亲”。石家祖上是山东人,靠船运为生,生意日见兴隆,于是定居杨柳青,成为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石家后来分为四大门系,排行老四的是石元士,为尊美堂,也是石家大院的主人。石挥父亲石博泉排行老二,为正廉堂的分支恩德堂,后因家道中落而迁居北京。石挥出生于大院,但在嗷嗷待哺的婴儿期就随父亲离开了杨柳青,从此一直未曾回来。石挥后来走上表演之路,其演技几为出神入化、登峰造极,却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场劫难中过早辞世,走得决绝而凛然,给中国影剧史和他的观众,留下了永恒的缺憾和纪念。
我外出旅游有个习惯,喜欢选择游览一些人文景观而不是自然风光。基于此,外地朋友来天津,我也是一相情愿地建议他们去杨柳青石家大院走一走,其效果屡试不爽。石家大院的好处,正在于它拥有的独特人文内涵。那年暮春,美籍华人作家陈九回北京探亲,抽空来了趟天津,最初对我的建议还略有质疑,这位儿时曾在天津生活过几年的老兄用津腔调侃道:嘛玩意儿?石家……大院儿,我这个老天津,怎么没听说过?我说,你在纽约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少见多怪,也很正常。如往常一样,一路我仍遵循“三不”政策,不渲染,不灌输,不饶舌,让朋友自己去体会其间的奥妙。陈九果然直呼不虚此行,临别时还意犹未尽地啧啧着,这石家大院,还真是咱天津的宝贝,千万给保护好了!
古镇婚俗的前世今生
若称杨柳青民俗为“华北民俗小百科”,并不夸张。古镇的婚俗伦理更有其地域文化特色。有一部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杨柳青》,何彦霓主演小媳妇王雨荷,与演技派小生夏雨合作上演了一幕民国初年的杨柳青婚俗剧情。这位“80后”江南姑娘戴着红盖头,被八抬大轿颠到婆家,鞭炮声中拜堂、坐帐,尽享洞房花烛夜,过足了“穿越”瘾,直呼,“真希望我的婚礼也要这样隆重和美好”。
余生也晚,旧时杨柳青婚俗中那个八抬大轿娶亲的场景,对于50后的我就如同遥远传说。其实,我的父兄一辈亦如此,他们的结婚高峰期赶上了移风易俗、新事新办的年代,而1966年以后,结婚更是被简化成男女搭伙过日子的一种形式。通常是男方骑自行车来接新娘,或女方家人陪新娘乘公交车“过门”,就算成亲了。运气好一些的,由单位操办一个简朴仪式,而更多的新人多在公园或商场里转一圈,然后家人聚在一起吃顿捞面,喜事就算办过了。到了我辈成亲,“妈妈例儿”开始复苏,时兴自家搭棚摆五六桌婚宴。我图省事,选择外出旅行,回来后在单位撒几包烟糖,宣告单身汉的日子就此画了句号。
进入新世纪,身边的子辈陆续进入了谈婚论嫁的行列,这才发现,其风气变化之大,竟令人恍若隔世。过去我曾认为,婚姻属私生活领地,办喜事不宜过于透明,大张旗鼓则更是大可不必。近年却恍然悟出,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在日常生活中主角的机会实在有限,而婚礼就是普通百姓的一次最体面、最风光、最货真价实、最应该理直气壮的自我展示机会,耳边常听人说,“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不能太亏待自己”,大实话也。
我甚至幻想过,自己也时尚地“穿越”一次,穿过茫茫岁月,深入古镇的万家灯火,当一回杨柳青婚俗现场中的新郎官,身着簇新锦缎长袍,揭开新娘的红盖头,对视那羞涩、迷人的一笑,内心涌起执子之手、白头到老的融融爱意,那该是怎样的“良辰美景”!若把此幻想细化,必然绕不开传统婚俗的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这是从议婚至完婚的六个步骤,老天津卫婚俗也多遵循这个套路。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一定的,请算命先生批批八字也不能马虎,换龙凤帖,送彩礼和陪嫁妆,更是一样不可少。一旦婚期确定,便雷打不动,“改日子死婆婆”,须慎之又慎。亲事定下,还要讲究由“全可人”全程操持婚礼,所谓“全可人”,是指儿女双全(且无残疾)、夫妻圆满、父母健在的女人,她们会给新人带来吉利。新娘最在意坐八抬大轿出嫁,意谓堂堂正正,明媒正娶,然后由“全可人”梳成“抓髻”,取“结发夫妻”之意,再身着袍裙嫁衣,绿袜红鞋,环佩叮当,入得花轿。女方进门不得过午,鞭炮声中由“全可人”搀扶一对新人并肩而立,拜天地、拜祖先、拜父母,夫妻对拜。新娘步入洞房,须由新郎用系在一起的红、绿巾牵引,意取“绿叶配红花”。闹洞房既是尾声,也是高潮。四天后还要“回四”,新娘带新郎回娘家,要把“贞节红”布当众交给亲娘,并摆上祖宗供桌。这道程序事关男女双方的脸面,那样的旧年代,尤其不可省略。
过去相亲,没有互送照片的条件,全凭媒人穿梭往返,来回“忽悠”,口吐莲花,煞有介事。只有当新娘入洞房后被新郎揭下盖头的那一刻,双方才知晓彼此相貌,却生米已成熟饭,新人是否可心,全凭撞大运。一些情窦初开的杨柳青姑娘、小伙并不甘心,要提前搞清楚对方的“庐山真面目”。若彼此中意,便有了牵挂,正如晚清诗人史梦兰写的那首《天津竹枝词》:“杨柳青边杨柳青,郎来系马妾扬舲。莫漫回腰学妾舞,也须垂丝牵郎情。”把少女的缠绵心事描摹得深微曼妙。也有包办婚姻带来的悲剧隐患,另一位晚晴诗人华长卿的《津沽竹枝词》,反映的便是新媳妇一种无奈的寂寞忧伤:“杨柳青边多杨柳,桃花寺里近桃花。柳条折去花飞去,夫婿三年未到家。”青春易逝,柳条空折,丈夫离家未归,妻子独守空门,使人感受到了封建男权社会冷漠、无情、非人道的一面。我暗思,男人一去三年而不归,外遇的可能性不是没有,除此之外,是不是也与新郎揭下新娘的红盖头后而彻底失望、负气出走有关呢?亦未可知。
无论如何,杨柳青古镇婚俗的遥远诗意是如此令人回味。同时,如同对一切文化遗产那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时俱进,日臻完美地传承下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杨柳青婚俗伦理的前世今生,已经融入了时代的流行色,生活在新世纪的姑娘小伙们是幸运的,值得我们羡慕,并为之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