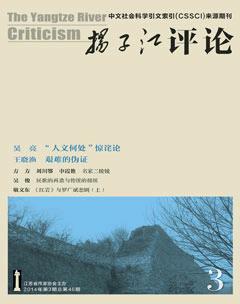边缘的意义──对新世纪“边地小说”的一种解读
于京一
边缘的意义──对新世纪“边地小说”的一种解读
于京一
新世纪的文坛,在《狼图腾》、《藏獒》、《蒙古往事》、《空山》、《水乳大地》等边地小说的轮番引爆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究其原因,“边地文学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火爆与其作品中渗透的意识形态符码——民族主义的膨胀和国家主义的至上密不可分,即边地文学的爆炸适时地迎合了当下我们整个国家对‘民族强大’的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幻梦。”①但是,在这种热烈而狂躁的“强大”诉求与梦幻中,边地小说却时常弥散出一种纠缠不清的忧虑与困惑,即当下沸沸扬扬而又人言言殊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纷争和矛盾。
一
当下的中国社会在一派令人眼花缭乱的真实与虚假的繁华下面掩映的是一个万花筒般绚烂多彩的镜像世界,现代化的种种魅惑在世俗的阳光下变幻出异彩纷呈的“恶之花”。置身其中的边地小说书写,同样无法回避现代化的灼灼之光,当然在宗教密布的边地,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辩证地剖析。
首先,从时间的维度看,边地离现代化确实相当遥远。我们知道,时间不仅仅是一个自然过程,而且还是一种历史现象,时间性的发现才有了历史的自觉,由此成为打开现代化之门的钥匙。正如有论者所言:“在前现代社会,自然时间还没有充分转化为社会时间,自然过程还没有充分转化为历史过程。时光是悠长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社会几乎是停滞的。这个时期,真正的历史还没有展开,时间性也没有被发现。……现代性发生之后,人的价值被肯定,生产力高速发展,社会剧烈变革,时间性才被发现,历史才真正展开。”②在边地中,我们身临的是一种封闭性/停滞性的时间,而这种属于前现代社会的时间观念主要是宗教作用的结果。在藏传佛教的观念中,时间是没有方向的,它是一个轮回的过程,一个封闭的圆圈,个体及其族类都是时间之维中渺小的衍生品和中间物,时间除了向人们显示因缘果报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伊斯兰教则认为今生是人类生活的全部,现世仿佛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生命只是一朵傲然挺立在时间之河中的花,怒放和枯萎是它注定的生命历程;享受现世、珍惜今生,他们追求的是将自我生命的灿烂熔聚到真主的荣耀中去,回归真主是个体存在的最高目标。以萨满教和原始苯教为根基而衍化生成的其它各种宗教,也以生命的轮回为根本的时间观,新疆、内蒙古草原上的牧民和东北原始森林中的游牧部落把时间理解为只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和轮回,长生天、腾格里等诸神赋予人以生命,而生命最终又复归诸神。由此可见,边地中的时间观念与现代诞生的时间观念在本质的意义上截然不同,彼此之间构成了一种传统与现代、自然与社会、封闭与开放、蒙昧与文明的矛盾和冲突。
然而,从发展的维度看,边地却又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融汇到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中去。当代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以摧枯拉朽般的汹涌之势席卷一切,交通的便利、信息的覆盖和知识爆炸的辐射力足以将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连结到一起。边地自然也无法逃脱这种“被现代化”的命运,边地与现代这对看似霄壤之别的词语就这样相当滑稽地被捆绑在了一起,由亲密接触到无法分开的故事顺理成章地上演了。
二
启蒙理性作为现代化的哲学支柱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获得了无以复加的推崇和张扬,然而随着现代化弊病的日益显露,文学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变得越来越沉重。新世纪以来的边地小说无疑是这种反思与批判的重镇。
首先,政治理想主义的没落。历史证明政治理想主义并非万能,一旦脱离现实便如脱缰的野马四处横行,某些时候甚至异化为令人恐怖的政治狂热和意识形态暴动,让现代中国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磨难。边地小说呈现的正是这种政治理想主义的没落。小说《狼图腾》中专横霸道的场部领导包顺贵常常以政治代言人的身份发布各种错误的号令,用空洞的政治热情压制牧民们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尤其对牧民领袖毕力格老爸更是颇具戒心,有时候甚至故意与毕力格对着干,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政治机器的孔武有力,而结果是整个草原惨遭破坏和蹂躏。包顺贵依靠政权的力量虽然暂时得逞,但是人心向背却使他注定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而毕力格老爸尽管伤心欲绝,郁郁而终,但是他的悲悯唤起了人们的普遍觉醒。也许被破坏的草原短时间内无法复原,但对草原的反思和重新认识已经开始深入人心,那种因为迷狂的政治热情而导致的狂妄自大终将破灭。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人定居点的建立,政府屡次以政治的名义号召游牧为生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并为其修建了条件良好、生活便宜的定居点;然而,鄂温克人对此却总是怀抱一种怀疑式的拒绝姿态,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舒适的生活并非就代表美好和幸福,他们需要的是自己适应的、有归属感的生活状态,下山定居确实可以带来很多方便,但却足以毁灭他们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并进而丧失民族历史的鲜活记忆,最终有可能导致整个民族的汉化与湮灭。总之,边地小说中密布的权力对人性的扭曲和戕害所显示的多是政治理想主义在现实实践中的失败,令人不寒而栗。
其次,技术全能主义的失败。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崇拜和信赖起源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间虽经政治理想主义的冲击,但丝丝缕缕延续下来,至改革开放重新散发出迷人的光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然而,这种在理性支撑下的技术全能主义还是遭遇到了现实境况的有力阻击,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让我们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尴尬,尤其是经济技术的发达所导致的人性扭曲与道德败坏真正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境地。小说《狼祸》表面上表达的似乎是狼给人带来的灾祸和痛苦,而实际上,无论是牧民还是猎人的痛苦并非真正来自狼,而是技术与物欲时代人心的残忍与道德的堕落。对金钱的追求已经让人们失去了理智和善良,他们任由自己的私欲不断膨胀:地方政府为了搞政绩修路而肆意摊派费用,导致官逼民反;被穷困逼急的张五只能背负沉重的道德重压替人打狼,而被逼得家破人亡的鹞子则更是红了眼,一切道德都不放在心上;牧民之间为了抢夺水源和牧草也分裂成南北两派,斗得两败俱伤。迟子建的小说向来以刻画人类在技术与金钱统治的世界中内心深处的孤独而见长,细腻的笔触下流淌着一曲曲令人柔肠寸断的悲歌,那些曾经朴实憨厚善良的人们在金钱的诱惑和威压之下纷纷放弃了各自的道德底线,随之而来的是更加难熬的孤独和空虚。
总之,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灾难,思想家们在严厉批判的同时纷纷陷入了沉重而痛苦的思索和追寻当中。海德格尔曾经指出:“现代性导致人与世界的关系变成了主体与图像的关系,世界图像化,产生了技术的统治以及‘弃神’等现象,因此现代社会是‘贫困的时代’、形成‘大地的荒芜’,‘现在一切无条件的物化’,人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④中国新世纪边地小说完成的正是对这种世俗的、偏激的现代化的深入反思,它们以文学的方式将一种深刻的反思精神和宏阔的批判思维注入了当代文坛。
三
边地小说对现代化的批判只是手段,其真正目的是要完成对它的超越——对理性垄断的颠覆和消弭。于是,一股弥漫着浪漫主义气息的文学思潮开始在边地小说中蜂拥而起。
遥望西方文学史,正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达完成了对现代化的第一次反抗,浪漫主义思想家马丁·亨克尔曾言:“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④由此可见,对现代化的反抗已经成为浪漫主义的基本品性。而回顾中国现代文学史,浪漫主义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或隐或现的挣扎和朦胧状态,一方面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民精神和实用理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现代中国救亡压倒启蒙、生存问题远胜精神思考的时代特征也注定了浪漫主义在中国暗淡的命运。而今,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早已实现,中国的经济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有必要也有能力对世俗化的现代性进行一次有力而有效的清查和省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边地小说得天独厚的优势将使其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最具冲击力、声势最为浩大的浪漫派。
首先,边地小说的作家队伍齐整、分布广阔。与二、三十年代的废名、沈从文和四十年代的汪曾祺、徐訏、无名氏等较为孤独的身影相比,新时期以来边地小说中的浪漫派却是一支相对庞大的队伍,其中颇富盛名的作家就有阿来、扎西达娃、郑万隆、红柯、张承志、迟子建、范稳、杨志军、冉平、董立勃等,他们各自都奉献出了相当有影响力的作品,曾经获得过“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各种奖项,而且大多正处于创作的高峰期,不断有新的更好的作品诞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边地浪漫派在新世纪以来陡然以集群的方式崛起于当代文坛,且热潮不断。另外,这些作家的生活地域也更加广阔,遍布于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青海、东北等地区,他们的作品以这些地区的生活状貌和人生故事为原本展开,形成了宽广的生活场景和叙述视野,这为边地浪漫派的健康成长和持续爆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石。
其次,边地小说创作目标高远、手法丰富。毫无疑问,新世纪边地浪漫派小说依循了传统浪漫派对现代化的强烈质疑,对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人类异化给予了最为猛烈的批判,对极具征服欲的工具理性思潮进行了无以复加的鞭挞和斥责,无论生活上还是情感上都要求返归自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与中国传统的田园牧歌式浪漫主义不同,边地浪漫派所追求和强调的回归自然,并非落脚于对前现代生活状貌的简单回归,而是更加注重对人性本身的恢复,追求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诗性生存状态,以实现生态平衡、人心平衡、文化平衡和社会平衡为最终的理想目标。在创作方法上,边地浪漫派小说反抗世俗现代化的武器是对感性和情感的依重与专注,它注重想象、抒情的主观化以及神秘主义、贵族精神等美学特质的凝聚。这里着重以想象和贵族精神为例来稍作阐述。想象是边地浪漫派最为锐利的武器,翻开每一部边地小说,几乎都密布着令人眼花缭乱、繁复绚丽的想象:营长眼中的宁静草原“炊烟升起来,升得很直,像是从白雪里升起来的。无边无际的雪原上几十个黑疤,升起几十道笔直的炊烟,烟柱子直接融入太阳,太阳像系在烟柱上的一个金黄的油馕,散发出食物的芳香。”(红柯《金色的阿尔泰》)在小说叙述者老人的眼中“火塘里的火一旦暗淡了,木炭的脸就不是红的了,而是灰的了。我看见有两块木炭直立着身子,好像闷着一肚子的故事,等着我猜什么。”(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些以比喻、拟人、通感、排比、夸张等各种艺术手段混合而成的想象在边地小说中俯拾皆是,读者在领略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同时,也享受着语言艺术固有的美妙与诗意,这与当下某些都市小说中用干楛的语言堆砌而成的潮烘烘的各种欲望气息形成了鲜明对照。而贵族精神无疑是浪漫派文学的精神支柱和气质追求,它抵制的是人的鄙俗性、世俗性和消费性,张扬高贵性、自由性和神圣性,以达到超越平庸的现实生活,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
第三,宗教信仰的张扬和神性之光的普照。毫无疑问,宗教信仰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必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任何时代,只要人们还需要某种深层的精神生活,“信仰还是不信”就是一个需要回答和抉择的问题。而边地浪漫派小说最为引人瞩目的正是其对宗教信仰的执着书写与热情张扬,他们以群体的力量集束性地在世人面前揭开了宗教的神秘面纱,展示出惊人的力量和美轮美奂的神韵,给当下物欲横流的世俗世界以当头棒喝。无论是藏传佛教的宁静致远,伊斯兰教的坚韧至诚,还是古老萨满教的回归自然、天人合一,或者其他各种虽早已在形式上遗失却以遗传因子方式渗入人们血液中的地方宗教的朴素真纯,都给我们敞开了精神世界的广袤和深邃,使现代人透过宗教的仁爱和慈悲,感悟到信仰的崇高和神性的伟大,使我们那颗在尘世的喧嚣中躁动不已的心灵得以暂获安宁与栖息。并有可能将这种神性的光芒普照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凝聚成一种日常性的精神源泉,让每一颗因欲望而焦灼的心灵都获得滋润和抚摸。
【注释】
①于京一:《在梦魇中前行——论新时期“边地小说”中潜隐的意识形态》,《东岳论丛》2011年第9期。
②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页。
③转引自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18页。
④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讲师
*本文系山东大学(威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创新基金资助项目[2013SKQP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