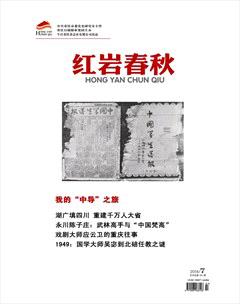戏剧大师应云卫的重庆往事
马拉



应云卫是中国早期著名的电影导演和戏剧活动家,1930至1940年代导演过《桃李劫》《怒吼吧!中国》《八百壮士》和《塞上风云》等名剧名片,抗战爆发后于1941年到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中华剧艺社(简称“中艺”)任理事长(相当于社长)。白杨、秦怡、舒绣文、张瑞芳、赵慧深都是中艺演员;郭沫若、老舍、阳翰笙、吴祖光、陈白尘、陈鲤庭都是和中艺紧密合作的剧作家。1942年,应云卫在国泰大戏院以最强的明星阵容,推出郭沫若的《屈原》,轰动山城。今年,是应云卫先生诞辰110周年。近日,应云卫之子应大明、应大白携家人顺江而上,从沪回渝,寻访父亲遗踪。
房子
应大明教授在应云卫6个儿女中排行老三,85岁,慈眉善目,是上海著名儿科白血病专家。应大白教授排行老五,79岁,高大俊朗,是杭州有名的文史专家。还在过三峡的船上时,应大白就给我打电话,说这次到重庆还有一要事相求,父亲当年有个老朋友,叫牛翁,年纪很大了,不知在哪里?我一听牛翁(本名杨钟岫)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他可是重庆新闻界老前辈,老爷子92岁了,身体好着呢!于是我马上给牛翁打电话,老爷子一听,非常高兴,说还记得应大白小时候的样子。
我把应家两位公子带到牛翁位于中山三路的花园书房,牛翁一眼就认出当年跟老爸在重庆混大的应大白:“你长得和你父亲太像了,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北余南应:‘北余是说国立剧专的校长余上沅,‘南应就是指‘中艺的应云卫,两个都是戏剧界的头面人物,都很风度翩翩。” 见到父亲的重庆老友,大白突然说起了小时候学会的重庆话,他已经多年没说了,这下子找到“组织”了。
牛翁说:“应云卫比我大18岁,我们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刘盛亚,说起来刘盛亚还是我的亲戚,表兄弟,家里是大绅粮。当时‘中艺的人病死几个,没得地方埋,刘盛亚就把他们家的地捐给剧社当墓地。”当时《十字街头》的著名导演沈西苓、“中艺”的导演贺孟斧、前台主任沈硕甫、社员彭波贫病而死,都葬在重庆。牛翁说:“沈硕甫心脏病突发,就死在临江门路边,当时我们刚离开重庆到乐山,走之前三天,他还请我吃过饭。你们应家还有一个老七蓓蓓,两三岁就死了,也埋在重庆。”
重庆朋友给应云卫提供埋人之地,也提供住人之地。牛翁说:“应云卫他们最初住在苦竹坝,成立剧社,没得钱,共产党资助了一点,但不够,棚棚搭起住,就找到刘盛亚和我。国泰对面现在新世纪百货,当时是个茶馆,我们老家三大房人就住在后面,我们这一房人住了三分之一,我们家上几辈号称杨半城,到我们这一辈不行了,但空房子还是有一些。”
张伯苓1936年创办南开中学,牛翁是南开第一班,文青一枚,“我当时很有爱国思想,爱跟文化人混。应云卫约我在国泰吃饭,我受宠若惊。他要我跟我父亲说,想住我们家的房子。”
应云卫没想到当时还是小牛儿一头的牛翁,给了他一个否定的回答。“我说不行,我的意思是根本不用先给我父亲讲,搬进去住起再说。因为事先讲了,我父亲可能不同意,旧社会老派旧观念,瞧不起戏子;但我们老头子喜欢画画,还是有点文化,搬进去了,他也不会生好大的气。果然如此,他们搬进去后再找的老头子。后来应云卫他们去成都几年,房子都给他们留起的。” 牛翁就这样先斩后奏,引艺入室,让“中艺”在自家的房子白住。
妻子
1943年,应云卫带着“中艺”从重庆移师成都,牛翁父亲把房子给他们留着,但自己儿子却没留住。也是这一年,牛翁离开重庆到了成都,开始了记者生涯。他说:“不客气地讲,当时我有点进步思想,看不惯社会,不想学商,就去当记者。1944年,我在《华西晚报》当文教记者,跟应云卫他们又混在一起了。如果不是我老头子反对我演戏,他们就吸收我了。但他们演《孔雀胆》时,我跟同事车辐还是上过台的。”
牛翁找出一张车辐前几年寄给他的照片,是他1943年和应云卫在成都的合影。他说:“这个合影,是从一张集体大照片上剪下来放大的。那天叶圣陶满50岁,各界朋友聚了一下,给他庆生。我跟老应站在最后一排,挨在一起。不光是照相,在重庆、成都啥子事情,我们都在一堆。在重庆支援昆明学生运动那次,在长安寺挨打,我们也在一起。”
挨打在一起,救急也在一起。“在成都,应云卫为剧社借了银行的4万块钱,可能相当于现在的40万块钱吧,到期了,那天还不出来,他找我想办法缓一阵。我就找了杨云慧,她是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的夫人,也是近代史上的名人杨度(著名政治活动家)的女儿,跟我父亲熟。”
除了钱这种大事,烟草和白糖这种小事,牛翁和应云卫也是打成一片。“中华剧艺社要吃白糖,找我,当时每户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一斤,白糖公司的经理李小明跟我熟,就专门供应剧社,白杨吃糖凶得狠,一个月可以拿一盆到三盆。我跟秦怡一样大,她可能记不得了,当年他们回重庆时,她抽烟抽得厉害。我找到蜀益烟草公司,供应她的烟,可以不要钱,当时蜀益的中等烟“主力舰”,应云卫也抽。”
在婚嫁之事上,应云卫成了牛翁的福星。“我跟老婆(夏庆英)认识是在成都,一认到就带去中华剧艺社跟应云卫他们见面,让他们看看。结果,大家都不看好,唯一赞成的是应云卫。订婚时,他自认介绍人,本来我请他当主婚人,但我老头子不同意,说这又不是唱戏。当时我22岁,妻子19岁。后来我们都认为,没得应云卫,我们的婚结不成。”
票子
1957年,当年一起帮助应云卫的牛翁和他的表哥刘盛亚,也一起落难。“他比我大8岁,我们两个都是极右派,发配到四川峨边沙坪劳教营,相当于西南的北大荒。”1961年,牛翁解除劳教,从有“西南夹边沟”之称的峨边九死一生,回到重庆。还好,当初应云卫独具慧眼看好的夏庆英姑娘,果然贤惠,一个人拖着几个孩子,艰辛地操持着一个温暖的家,终于迎来丈夫流放归来。“我被开除公职,又病得厉害,营养不良,全身浮肿,都肿到胸口了,我原来月工资108块,但现在身无分文。”
正在这时,一张从上海寄来的绿色汇款单,救了牛翁的急。“是应云卫。1950年,他前妻去世了,他用跟他同居的一个女人的名义,给我寄了40块钱来。他是第一个给我寄钱的,老伴说,任何人都可以忘记,应云卫不可忘记。”
应家两位公子都说,从未听父亲说过此事。牛翁说:“你父亲是‘狡猾人,有两次跟我联系,都没用真名,他是不得已而为之。其中一次是1946年‘六一大逮捕,国民党到处抓人,陈白尘‘傻,用‘白尘署名发电报问候我;你父亲打电报来,就‘狡猾得多,用的是你妈妈的名字‘梦莲。”
牛翁跟应云卫分别,是1945年抗战胜利,“他要回上海了,还到我家辞行,我跟我老伴,送他到千厮门。秋风萧瑟,结果他没走成,第二年才走成了。”到1967年,牛翁得知了应云卫落难的消息。
“克欲无贪疏离名”,牛翁书案上摊着一幅还没写完的诗或者说联。早在2004年,他就为老友献诗一首,收入他的手写诗集《俚词信笔》,他翻给我们看:
大场小景巧安排,
御敌豪情上舞台。
渝市过从师亦友,
锦城跋涉乐相偕。
嘉陵岸畔辞依惜,
黄浦江头寄缅哀。
泉下应知平反事,
百年盛祭可宽怀。
应家两位公子把他们编著的应云卫画传和纪念文集送给了牛翁伯伯,带着可慰父亲在天之灵的《俚词信笔》,前往国泰大戏院继续寻访父亲的遗踪。在国泰大戏院,得知应云卫已列入国泰前厅的10位陪都文化名人塑像计划而毫无争议时,哥俩都感谢山城人民还记得他们的父亲。
童星
当初,应大白能跟着父母在陪都重庆呆5年、在成都呆了3年,全靠妈妈“错误”地执行了爸爸“旨意”。他说:“这是我妈妈讲的段子。当时我父亲一人在武汉,我们全家留在上海,父亲给妈妈写信说,把大明带到武汉来。等我们去了,爸爸一看,怎么是大白呢!当时我才两岁,显然不方便带出远门,但从小跟妈妈,妈妈宠我,就把我带来了。”没被带走的哥哥应大明说:“8年离乱,我就和另外几个弟妹留在了上海。”
应大白现在对重庆最早的回忆,是在观音岩父亲当时工作的中央电影制片厂经历日机轰炸。“父亲抱着我,跑警报,躲飞机。后来在中华剧艺社,大家住茶馆,吃不起茶,周围有些大轰炸留下来的断垣残壁,清扫一下,就排练。都住得很挤,只有父母有一间单独的小屋。团里的人都叫我爸先生或应老板,叫我妈师母。”
应大白从小就被老爸“榨”着了,在剧团里当小演员。“我小时在剧团跑跑龙套,也不怯场,《屈原》里面,我跟老爸是父子上场;在乐山、内江、自流井、泸州旅行公演跑码头,演《棠棣之花》,还赚了一点钱。我七八岁,演一个小歌女玉儿,台词还是文言文的。当时,我虚荣心很强,全场鼓掌,就很得意,有时掌声小点,就不高兴。我还在成都演过《家》,演一个小辈闹新房,有一句台词,现在也记得:‘什么是家,就是上宝盖下面一群猪。”1947年,他还在爸爸导演的电影《无名氏》里面当童星,演秦怡的弟弟,虽然母亲反对他演戏,但爸爸私心里还是想让他多接触演艺。
老板
退休以后,应家两位公子的一个工作就是整理父亲的史料,拜访爸爸当年的老友。应大白说:“秦怡最初也是我爸发现的。她现在92岁了,还想拍电影,每天写3000字的剧本,上次我们去看她,她还在感叹,有一个老板说好了投资,她高兴极了,但后来又说不投钱了,她很郁闷。”黎莉莉、张瑞芳一看见他,就“小白”、“小白”地叫,说她们一下子想起老朋友应云卫。哥俩通过父亲老朋友夏衍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从侧面见识了老爸当时的地位。“夏衍当年从香港回重庆,到周恩来那里去领任务,周恩来说,回重庆,你不能去看老朋友了,但有两个人你必须去看,一个是老舍,一个就是应云卫。谁知十几年后,老舍在北京沉湖自尽,我爸在上海死在街边。”
应云卫去世时,世态炎凉,但当年“中艺”前台主任沈硕甫去世时,他却对员工尽心尽力。“搞了一次出殡,(沈)在重庆没有亲人,路祭时,我爸爸叫我充当他的孝子,披麻戴孝,走在最前面,捧着他的灵牌。”放到现在,应老板是人力资源管理的行家。旅行公演时演《天国春秋》,杨秀清的妹妹,本来是苏绣文演的,她走了,吕恩顶上去。团里有一个木匠,头有点秃顶,叫阿秃师傅,原来是中央电影制片厂的木工,从上海流亡到重庆,在“中艺”应云卫手下搞道具。“《雾重庆》开头有一个老鼠跑过舞台,活灵活现,就是阿秃师傅做的,为了发挥他的积极性,也为了别的团不把阿秃这样的高手挖走,爸爸叫吕恩和我拜阿秃做干爹,还有拜爹仪式。阿秃干爹还给了我红包。老爸很会团结人,一个大导演,叫儿子拜一个做道具的工人做干爹。”
有一个姓徐的银行家,对进步戏剧有正义感。应云卫为了团结他,也为了剧团的经费,跳交谊舞时,考虑他不会跳,应老板就找舒绣文教他跳舞,增进交情。据《小城之春》的编剧李天济回忆,在成都,剧团得罪了一个军阀的儿子,这人就来捣乱,在一个茶馆里头,把应云卫逼到一个墙角,用手枪比着他的头,他用双手护着头,对方就用枪把砸头,鲜血长流。剧团里有风言风语说老应在外头给我们惹麻烦,但更多人是气愤,想大闹一场,应老板说这时不能闹,就去找人说事和解。应大白还回忆:“团里没经费了,开不出伙仓(工资),我爸就躺在床上,项堃(艺术家)来看他,说我在内江银行界有个朋友,老爸一听,马上来了精神,立马起床,叫妈妈去剧服里找一件像样的,让项堃穿起去拉赞助。”
落难
1949年,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应云卫先去,不久捎信跟夫人说,你带小白来。应大白说:“作为列席代表,为什么可以带我呢,因为我也算是老中艺了,我的重庆岁月,连郭沫若都知道。”
全国文代会就是国统区、解放区两支文艺队伍大会师,但主要是安排国统区的艺人向解放区的学习,又跳又唱他们《兄妹开荒》之类的节目。应大白说:“1949年我13岁了,读初一,在舞会上,老爸把我带到周恩来身边说,这是犬子,交给党培养。周握握我的手笑着点点头,我就留在北京,读干部子弟学校。直到上北师大,毕业分到山东师范学院任教。后调到杭州师大教书,在那里退休。”
1967年1月16日,本来正患心脏病住院的应云卫,被造反派从医院里抓出来游斗。应云卫跟很多大导演、大明星同事一起,胸前挂着写有自己名字的大木牌,名字上面打着大叉。从淮海路电影局门口出发,走到兰心大戏院附近时,他已经不行了。当时应大白在外地,应大明在上海当医生。
应大明说:“我父亲都快倒下了,按理应当马上送医院急救,但造反派根本不管,临时拦下一辆三轮黄鱼车,把他推上去,由两个人扶着让他跪在车板上,继续游斗。游斗队伍回到淮海路思南路口时,一个急刹车,三轮黄鱼车上站着的红卫兵,和我爸一起从车上摔到马路上。我爸的假牙也从嘴里摔落出来,完全起不来,这时他们才把他送到瑞金二路上的瑞金医院急诊室抢救。”
应大明原来就在瑞金医院上班,当时已调往华山医院,离瑞金较远。“瑞金医院急诊室当值医生是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打电话说,你爸死了,来院已死,根本已无法抢救。我赶去,我爸已经停在太平间了。我去问造反派能不能办丧事,我永远都记得那个人先背诵了一句诗词‘冻死苍蝇未足奇,再撂下了一句,应云卫的问题还没定性,你们要办就办!”
1978年11月,上海市电影局为应云卫举行平反昭雪大会,并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夏衍从北京寄来了题为《悼念应云卫同志》的悼文:“云卫同志是早期的话剧运动的著名组织者和优秀的导演,云卫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对文艺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我们这些后死者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的话剧、电影史上,他的名字也永远不会磨灭的。”
(作者单位:重庆晨报。图片来源:除注明出处外由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吴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