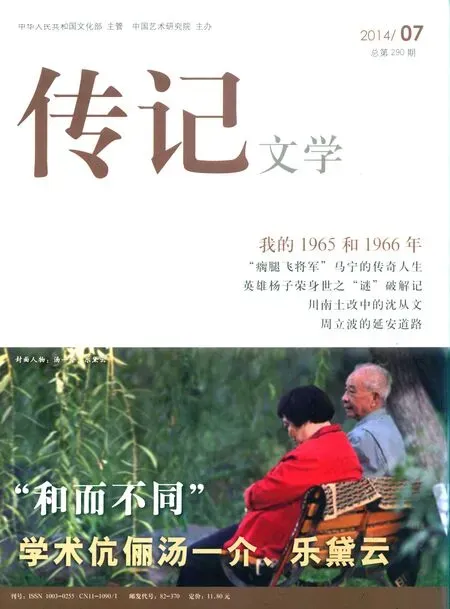从“世界图景”到“地方”言说
——周立波的延安道路
赵 楠
从“世界图景”到“地方”言说——周立波的延安道路
赵 楠

一
从高尔基的创作实践和倡导,到苏联作家协会成立并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红色的三十年代”曾弥散在“左岸”西方和所谓被压迫民族的整个世界,带给人们一
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国际形势的波诡云谲、国际主义思潮的发展壮大和共产国际的推波助澜,也进一
步促成中共和“世界”的对话。随着战事加紧,受苏联对外政策调整及共产国际策略路线转变的影响,仍然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之框架中认识和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瓦窑堡会议”后决意敞开大门、“从延安走向世界”;这也直接促成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从而推动美国乃至世界舆论接受(中国)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也被斯诺的后继者们塑造为“那个时代最富有吸引力的革命者”。在1939年以前,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即“鲁艺”)还曾要求每位学员撰写革命史自传,以期为共产国际的报刊贡献材料,随着延安的世界认知与革命目标被唯一
化为苏联,这个任务不了了之。除却斯诺们的政治朝圣,以马尔罗对“五卅运动”的想象和基希笔下《秘密的中国》等为契机,中国也以“文学”的方式受到国际主义者注目;“红色的三十年代”也在中国的文学和文艺工作者这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让我们把视角转到上海,或者说,转到国内的左翼文学。从“五四”时期翻译文学领域开始的对被压迫民族的观照,在30年代和左翼作家间得到空前的展开。无论是鲁迅还是茅盾,无论是对“拉美壁画三杰”的引介还是《铁流》《毁灭》等翻译作品的再度兴盛,都表征着中国左翼和中共对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努力。几乎与此同时,国内左翼主线开始大规模论争文艺“大众化”与探讨文艺的“民族形式”,很多问题被提出也被悬置,而一
切在延安时期、在“讲话”之后,得到了标准和方向。二
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作为“翻译者”的周立波开始真正走入我们的视野,也奏响了他“走进延安”的前音。从益阳农村到都会上海,周立波经历了从文学爱好者到“亭子间”左翼的成长过程。少年时期困顿的生活经历和老乡周扬的大力帮扶,使得周立波具有了某种天然的“革命的本能”。在左翼的崭露头角并非来自于周立波对“国防文学”的提出或他卷入“两个口号”的论争(“国防文学”或“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而是来自于他的翻译工作。为了适应中共左翼当时的斗争需求,在上海劳动大学(这是左翼自办的免费学校,旨在为其文艺工作培养后备人才)攻读夜校期间,周立波自修了英文,并且翻译了大量的战事报道和评论,以及一些散文和小说。从他30年代的翻译中,我们能够看到苏联人柯尔佐夫报道的《意大利法西斯蒂在瓜达拉哈拉的遭遇》,也能看到美国人柏索斯追怀第五纵队战斗的散文《西班牙游记》;既能看到马克·吐温的《驰名的跳蛙》,也能看到乔伊斯的《寄宿舍》。不论是《略谈刘海粟先生的海外画展》还是《最近的波兰文学》,从周立波撰写的评论中,都足以见得这位亭子间左翼开阔的文学视野和在文艺领域“取法乎上”的努力。在此期间,周立波不仅参与到世界革命文学的进程之中,更真正接触了欧洲小说的技法,也第一时间接触了报告文学——这个被战时苏联发明的“文艺轻骑兵”的文学体式,在30年代也以“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被中国左翼加以推重——这为他后来的教学和写作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给养。而令周立波一生引以为傲的,恐怕正是翻译了捷克记者基希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以及以英文翻译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记载苏维埃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
周立波认为基希的作品是报告文学的“模范”,希望中国的报告文学家也能“用那由精密的科学的社会调查所获取的活生生的事实和正确的世界观和抒情诗人的喜怒与力结合起来,造成这种艺术文学的新的结晶”。勤勉学习得来的扎实的英文功底和在翻译中所积累的外文写作技法(尤其是“报告文学”),使得周立波先后获得了给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美军情报官卡尔逊做翻译的任务与机遇。他陪同这些美国人先后到访过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和中共领导治理的晋察冀边区,也在战地上会见了领导广大军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八路军许多著名将领,见证了抗日战事的残酷和共产党人的热血与牺牲。中共安排并希望呈现给史沫特莱(们)的面象,与周立波一贯的立场和革命热情相互作用,使得周立波这样一位拥有“革命的本能”的年轻人,对于延安产生了比史沫特莱们更甚的朝圣心态。此外,周立波还曾被派遣担任苏联塔斯社记者瓦里耶夫的英文翻译,到江南的抗日前线采访。边区经历和战地见闻也为他写作报告文学搜集了大量材料。1938年,周立波陆续发表的战地报告,结集出版为《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两部报告文学集。他的报告文学承袭了左联在1930年代就提出的“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的主张,并获得了时评的高度认可。《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出版之初,《全民周刊》就刊载了这样的评价:“当我读基希的《秘密的中国》时,曾期望着报告文学《战斗与自由的中国》之出现,《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可说就是这么一部作品(罗之扬)。”这也为周立波“走进延安”做了很好的铺垫。
三
走进延安对于周立波来说,既有偶然也是必然。一方面,中央已经迁入并扎根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对边区开始了多方面的建设工作,文化建设又正是重要任务。纵观以“鲁艺”教员为中心的延安初期文人构成,奉命从上海到达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占了全部37人中的34人,这34人中,“左翼”占有半壁。而作为周扬的“左右手”和“左联”的得力小将,周立波自然接受也向往于调遣延安。担任美国记者和情报官的战地翻译,是周立波在去往延安途中临时被中共西安方面分派的政治任务。另一方面,1939年下半年以后,“鲁艺”的领导机构和文学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副院长沙可夫与时任“鲁艺”文学系主任、从苏联归来的萧三相继离任(这也许可以上溯到“左联”解散一事,作为“留苏派”的萧三在“鲁艺”与周扬、何其芳相处得并不愉快。而后来大量的苏联文献和文学作品翻译工作,落在了曹葆华等人身上)。最终没有认同和落脚延安的沙汀在1939年11月离开延安后,何其芳担任“鲁艺”文学系主任。此时,由周扬执掌的“鲁艺”面临着师资短缺的实际困难。于是张闻天和周扬联合致电奉命在桂林编辑《救亡日报》的周立波来到延安。周立波当时不仅担任“鲁艺”文学系教员,而且肩负起“鲁艺”编译处处长的要职。这也开启了周立波人生中令他自己和他的同事、学生们都无限追怀的“鲁艺”文学系“三足鼎立”(周扬、何其芳、周立波)的革命浪漫年代。
也许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左联”内部还是放眼整个中国,在劳动大学完成学业、并非“大知识分子”的周立波,其翻译理论主张和实绩并不突出,翻译工作也须前辈给以指点。在早期译著《被开垦的处女地·后记》中,他这样写道:“去年,许多青年朋友提议翻译这本书……译时和译后,得到周扬、杨骚、林淙诸先生的许多帮助……周扬同志把全书从头到尾校阅了一遍。”而到了延安,“鲁艺”学生对于周立波的爱戴和仰慕,是这个小小的“亭子间”左翼作家和翻译者前所未有的人生礼遇。在火红的年代里,在“整风”以前的延安知识分子界,周立波的经历,在“鲁艺”学生间显得尤其熠熠生辉。在周立波到达延安担任教职之前,学生们不但已经读过他的译作,而且还有关于他在上海参加“飞行集会”、在战地冒险采访等诸多传闻。而周立波在黄土高原上的“亮相”,很有电影式的传奇性和画面感:根据当时是“鲁艺”文学系英文班学生的冯牧回忆,一天,他去找老师曹葆华请教学习英文时遇到的难题,看到“在曹葆华窑洞外的小路上,有一个穿着灰色棉大衣的人,手里拿着一本英文原版的《雪莱诗选》,一边散步,一边大声地诵读着”。曹葆华告诉冯牧,这是即将为文学系学生开设名著选读课程的老师周立波。看见冯牧手里拿着从曹葆华那里借来的两本英文书,周立波脸上现出一种“温和而又略显惊异的笑”。他先询问了冯牧的英语水平,然后说:“以你的水平,读菲尔丁的书还太早。我建议你先读惠特曼的这几首诗,读懂了以后,再读别的。”
以翻译起家,初到延安的周立波兴致勃勃地讲授起“名著选读”课程。前文提到,延安“鲁艺”教员中,上海左翼人士占到了将近半数,当时延安也陆续招收了相当数量接受了进步文化的城市学生,颇有些“洋气”;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当时仍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奉行着以保卫苏联为核心原则、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相结合的路线方针,愿意将自身斗争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法西斯战争休戚与共——中共领导层主观的允许和周立波对外国文学作品驾轻就熟,使得“名著选读”课程一时间开展得如火如荼。尽管左翼、“鲁艺”的趣味有着较为明显的苏联倾向,“鲁艺”初期也专门为各专业设置了“苏联文艺”的共同课,但面对为中共的实际斗争需要而培养的“文艺干部”(也即“鲁艺”的学员们),从上海来到延安的周立波充满自信和希望地为学生讲授了从蒙田到莱辛、从《羊脂球》到《罪与罚》等等许多优秀的外国作家作品。而引导学生对《浮士德》《安娜·卡列尼娜》等名著的讨论,更是进行得热火朝天,也吸引很多外系学员前来旁听。当时周立波班上的学生岳瑟,跟着老师参与阅读和讨论《浮士德》的文章,整理为《读〈浮士德〉后记》,被周扬推荐到《解放日报》发表。岳瑟等许多学员也认为,在他们眼中富于传奇魅力的周立波,以及周立波所开设的斑斓多姿的“名著选读”课程,是“鲁艺”历史上“最具浪漫色彩的篇章之一”。不知是否要在学员当中获得某种崇拜感,还是周立波向来的认真与努力使然,“名著选读”开讲便是冷艳的蒙田,这令当时许多同侪感到惊讶;而讲授之系统完备,以及在讲授中着重介绍了一本冷僻的、很难找见的专书——佩因的著作《米舍尔·德·蒙田:〈散文集〉作者未经编辑也少为人知的事迹》,更为周立波赢得了敬意和掌声,也足见他相当了得的文学品味和日渐成熟的师者风范。
按照李书磊在《一九四二:走向民间》中的判断,周立波的“名著选读”证明了当时“鲁艺”文学课程教学的深度,也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共产党并不是没有真正的文化专家,二是这样的专家在延安并不缺少听众。”李书磊同时也捕捉到,“从总的倾向来看,特别是整风前的‘鲁艺’,大体保持了向整个世界文学艺术开放的态势”。与其按照斯坦福学者王斑的说法,周立波们所展开的“世界图景”是中共在山村窑洞中想象世界、以“人民”获得民族身份认同,不如说周立波的“名著选读”反映了30年代上海“亭子间”左翼对“世界”和“世界文学”的想象。
历史地看,为开设“名著选读”课程而撰写的《周立波“鲁艺”讲稿》无论从选材视野还是阐释角度还是教学方式上,都十分出色,但广博的面象背后也显现出许多问题,比如说:为中共后备文艺干部们授课的讲堂上,竟然除了法捷耶夫、普希金、托尔斯泰之外,还有梅里美;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除了阶级话语,还有人道主义、各派艺术手法等多重声音……这份驳杂——抛开年轻教员的炫技之嫌——是周立波个人文学修养和立场造成的,也是“亭子间”左翼的历史遗痕。老实说,它是开放性的,保留着知识分子的美学政治和乌托邦远景,并且迎合了中共当时对世界革命的认知和策略选择。但延安是抗战后方和真实的斗争场域,这份讲稿、或者说周立波的这种姿态,必然要受到抨击,尽管直到“整风”前的1941年,“名著选读”还保留在“鲁艺”文学系的“修业科目”上。
1941年春,周扬整顿后的“鲁艺”全院师生员工讨论通过了周扬亲自拟定的《艺术工作公约》:“一、不违反新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二、不违反民族的、大众的立场……”但对“鲁艺”和对“名著选读”的诘问,早在1939年周立波初到延安之时(甚至更早)便已显现。“鲁艺”建校初期,为积极配合中央提出的政治任务,进行了大量宣传抗战的编创和演出。1939年5月,“鲁艺”大部师生到敌后开展工作。但1939年底,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一次专门会议上,毛泽东评价:“‘鲁艺’过去培养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学校的基础,领导者虽努力,但工作做得不好,主要是中央领导没有抓紧,没有确定正确的方向。现在必须确定明确的方向与制度。‘鲁艺’的创作去年上半年较有朝气,后来差了,有许多非现实的非艺术的作品。”同样在1939年,毛泽东发出了当时并没有很多人在意的警告:“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真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初来乍到的周立波,也许还带着与史沫特莱相近的左翼想象,或者作为传奇教员的春风得意,而手到擒来开设的“名著选读”大受欢迎,更令他兴奋不已。虽然他也卷入到愈发尖锐的延安文艺的斗争当中(如1940年夏在“鲁艺”欢迎茅盾茶话会上,周立波对音乐系教师杜矢甲唱讽刺歌摔茶壶以表示不满;1941年他的小说《牛》在“文抗”的“文艺月会”上被萧军批斗),但在周扬的领导下,辗转大半个中国来到延安的周立波仍是延安生活的坚定的“歌颂派”,曾经写作《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作为对延安的颂歌。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名著选读”和文艺气息浓厚的“鲁艺”,已经面临着“暴风骤雨”。胡乔木回忆:“毛主席很反对‘鲁艺’的文学课一讲就是契诃夫的小说,也许还有莫泊桑的小说。他对这种作法很不满意。”“鲁艺”在作为一座文学艺术学院的正规化、专门化方面的努力和尝试,引起了毛泽东、贺龙等中央领导人、前方部队将领和边区某些文化界的不满,被尖锐地批评为“关门提高”。
对“鲁艺”和“名著选读”开火的背后,凸显了至少两样问题:第一,关于“知识分子”。某种程度上,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是在破除延安对知识和大知识分子的崇拜。与“争夺领导权”交织在一起的对“知识”的重新诠释和对“知识分子”自信的打击,无疑给延安各执一派的知识者们以冲击。周立波的“名著选读”所展现出来的“契诃夫”式的文化取向,必然受到批评。第二,基于现实斗争变化,延安对于“世界想象”的需要,已经发生转型。在毛泽东开始对“鲁艺”和知识分子有所警告的1939年底,正是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期。11月11日,国民党制造了“确山惨案”,12月间,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占领了镇原和宁县。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动摇于亲英反共降日与亲苏联共抗日之间”,中共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制止;同时派周恩来到苏联向共产国际面呈中共面临的状况,希望苏方予以支持。西方世界的英美等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打压已经显露无遗。尽管因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侵害了邻邦利益,苏联也表示:“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只有斯大林,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好朋友。”严酷的斗争现实呼唤最为行之有效的文化参照。紧迫的国际国内形势,结合毛泽东对“文化革命”的诉求,延安必须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而对于“世界”,延安的朝向,只消一个作为“未来式”的苏联便足够了,驳杂的趣味不仅不需要,而且不应该。“名著选读”也必然面临停课的结果。
四
1942年4月“整风”全面开始,4月10日“鲁艺”成立四
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扬、宋侃夫领导的“‘鲁艺’整风委员会”,在全院开展了“整风运动”。5月30日,毛泽东亲临桥儿沟,向“鲁艺”全体师生员工做了重要讲话,号召大家从“小‘鲁艺’”走到工农兵群众的“大‘鲁艺’”,深入斗争生活。“讲话”也明确表示了工农兵文艺的新方向。“鲁艺”同事何其芳“整风以后才猛然惊醒,才知道自己原来像那种外国神话里的半人半马的怪物,一半是无产阶级,还有一半甚至一多半是小资产阶级”。周立波亦深谙“名著选读”的危险,并惊惧于自己因与周扬特殊关系而获得的某种“赦免”,积极表示要彻底割掉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要“清除书本子的流毒”,住到群众中去“痛改前非”。“名著选读”取消后,精通英文但不会俄文的周立波,也被撤掉了“鲁艺”编译处处长的职位。“整风运动”后的延安更加推重《铁流》《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小说,《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的翻译作品,也大多是苏联的小说、诗歌和战地通讯等。尽管“鲁艺”文学系历来设有“写作实习”,但这种采风式的见习课程,显然无法达到毛泽东的深入“大‘鲁艺’”的要求。周立波主要为教学需要而从1941年开始写作的短篇小说,涉及他当年的牢狱生活和对延安地方农村的体察等题材。流畅的欧化语言与娴熟的叙事技法,加之战地速写和报告所培养的冷峻扼要的观察,使得这些小说在今天读来在艺术上都相当精致和成功。但在《讲话》以后,这样的写作也终止了。周立波这个有着“革命的本能”的作家,即刻又投奔到“大“鲁艺””,并“重操旧业”,于1944年出版报告文学集《南下记》。在当时作为“文艺的民族形式”之“权”的地方性写作,也被周立波这个“努力”的作家,在欧化语言和方言土语间进行着艰难的调和。
毛泽东《讲话》后,住到人民群众中去“痛改前非”是周立波反思自己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一个层面,而这样的反思促成了他后来的写作:“(我)在心理上,强调了语言的困难,以为只有北方人才适宜写北方,因为他们最懂得这里的语言”,因此没能在作品中很好的表现自己“所热爱的陕甘宁边区”。于是周立波决定“脱胎换骨,‘成为群众一分子’”,转而认为“语言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只要能努力。夸大语言的困难,是躲懒的借口”。这样一种改变自己语言的决心,是这位文学修养相当高的小说家在1942年以后的写作中特别重视运用方言土语的原因。而他写于40年代的小说《暴风骤雨》正是实践这一写作策略的尝试。为着“地方性”和“民族形式”的努力和克服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气的表现,周立波在小说《暴风骤雨》中,有意识的在写作过程中使用大量东北地区的方言土语,以加强作品的地方色彩。或许是因为这位作家改造自己文学语言的欲望过于强烈,使其对方言土语的使用毫无节制,让很多读者在方言注解的帮助下也难以将小说看懂。而周立波在各个版本的《暴风骤雨》中对东北方言不断“添注释”的行为,透露出来自延安的周立波们在写作过程中的尴尬处境。他们要响应毛泽东《讲话》的号召,“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并纳入其作品,力争为工农兵“喜闻乐见”,但效果往往如周扬所批判的:“有些作者却往往只在方言、土话、歇后语的采用与旧形式的表面的模仿上下功夫。”
而一直“努力”的周立波从《暴风骤雨》开始到建国后的作品,始终坚持用一种平板、客观的语言为方言土语做注,在知识的层面上获得对“地方性”的了解。某种程度上,周立波本人恐怕就是周扬笔下的“炫耀自己语言的知识”、用方言“装饰自己的作品”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但周立波仿佛并未将写作的分裂与旁人的指责放在心上。通过对方言注释的坚持,还能让我们看到这位水平相当的翻译家、“名著选读”的任课者对欧化语言的熟练运用,以及湖南人的倔强和那一点“知识分子气”。
责任编辑/赵柔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