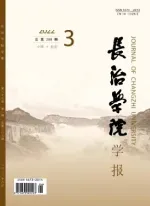郭店竹简《老子》的版本归属及其学术史定位
刘 晗
(济宁学院 文化传播系,山东 济宁 273155)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一部分是《老子》写本,整理者按竹简字体、形制的不同,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组,简文的总字数只相当于传世本五千余言的三分之一左右①据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前言》说:“简本现存二〇四六字,约为今本的五分之二。”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前言》,第1页。另有裘锡圭据彭浩说,此数字是把《太一生水》篇现存的三〇五字计算在内的,如将此数字除去,郭店《老子》简现存字数应为一七四一。由于甲、丙二组都有第六十四章后半,裘锡圭进而认为,如再将丙组相当于此章后半的七十五字减去,则为一六六六字,这样三组简现存字数仅为今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参见裘锡圭:《郭店老子简初探》,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6页脚注①。这里依裘说。。自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这批竹简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特别是竹简《老子》甲、乙、丙三组,更是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因为竹简《老子》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与我们所见到的帛书本及通行本有很大不同,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老子》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
由于竹简《老子》出土于郭店一号楚墓,所以郭店一号楚墓年代的确定,对于竹简《老子》版本问题的考证显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郭店一号楚墓的发掘者认为该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初”[1]。李学勤、裘锡圭、李伯谦、彭浩和刘祖信几乎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此墓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四世纪末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之岁是其下限[2]2。但也有不同意见,王葆玹推定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有可能较晚,其上限为公元前278年,下限为公元前227年;墓中的简书多数撰于战国中期或更早,但也包括白起拔郢之后的作品在内[3]366-389。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墓葬的年代是公元前300年左右,相关问题也基本上以此为基础展开讨论。裘锡圭指出:“墓中所出《老子》简的抄写时间,大概不会晚于公元前三百年左右,比已有的《老子》的最古本子——抄写于秦汉之际或汉代初年的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还早了一百年左右。”[2]26如果照此推论的话,《老子》书的早出似乎已经不是问题。张岱年认为:“竹简《老子》已经出现在战国中期,而且这个时候,《老子》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因为只有流行了,人们才能抄录它的一些内容来学习。这说明《老子》在春秋末年已经有了。”[2]24陈鼓应是《老子》书早出观点的坚定支持者,他根据竹简《老子》不反仁义的特点,在比较竹简《老子》、帛书《老子》与今本《老子》的基础上,认为《老子》晚出的观点已不能成立:“如今《老子》竹简抄本从郭店楚墓中破土而出,则为打破《老子》晚出说之最具说服力的实证。”[2]67王中江也认为,“简本《老子》仍只是《老子》的一种传本,而老子所著的《老子》原本,在时间上,不仅早于《孟子》、《庄子》,而且肯定比战国初还靠前,至少就像一种说法所认为的那样,是在春秋后期,它应该比《论语》和《墨子》还要早。《老子》出现不同的传本,肯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一次次传抄中,慢慢发生变化,后来成为不同的传抄本”[3]107-108。徐洪兴亦撰文指出,帛书《老子》毕竟出土于汉墓,尙不足以完全动摇《老子》“晚出论”,尤其是其中的“战国中期说”,而郭店竹简的出土,为我们进一步澄清《老子》成书年代提供了新的、更有力的证据,它把“晚出论”的立论基础都抽去了。因此,“本世纪初以来的关于《老子》成书年代及其真伪问题的聚讼,基本已经是尘埃落定,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那就是传统的说法大致是正确的,而‘晚出论’的观点则不能成立”[4]。相对于以上的大胆结论,李零的观点就显得十分小心。李零认为,《老子》一书的出现,既不会像有些人估计的那么早,也不会像有些人估计的那么晚。郭店《老子》的发现,“当然可以证明《老子》并不是公元前250年才出现,至少也是公元前300年左右的作品,但《老子》一书的出现到底有多早,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还是可以讨论”[5]。
伴随着竹简《老子》成书年代问题的争论,学术界纷纷撰文,从不同角度对竹简《老子》与帛书及今本《老子》的关系问题也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崔仁义认为,竹简《老子》是最早的《老子》文本,帛书《老子》汇集并发挥了包括竹简《老子》在内的老子学说,传世本《老子》是对帛书《老子》的直接修订[6]。郭沂认为,简本同今本相比在文字上有许多差异,在分篇和章序上也有很大不同。从文字差异看,今本的难解粗陋之处往往由讹误所致;从分篇和章次看,简本更合理、更符合原作者的本意,而今本打破了简本的这种原始联系,肢解之迹显然。而且,简本的语言、思想皆淳厚古朴,简本不含有今本中的高远玄虚之论、非黜儒家之语、南面权谋之术等,它有完全区别于今本的独特的思想体系,且前后一贯,意蕴精纯,显然出自一人之手笔,代表一人之思想,因此简本不但优于今本,而且是一个原始的、完整的传本。郭沂强调,简本和今本都吸收了不少古语,今本将简本悉数纳入,是后人在简本的基础上进行改造、重编、增订而成的。简本和今本是同一书的两个不同的传本,前者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后者出自战国中期的太史儋,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继承与被继承关系,却又有着互不相同的思想体系[7]。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关系到先秦老学乃至整个先秦学术的演变史。郭沂的观点得到了尹振环和解光宇的赞同[8]。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简本《老子》之前已经存在着一个类似于通行本规模与次序的《老子》书,简本《老子》的甲、乙、丙三组只是当时的节抄本。之所以如此,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由于竹简繁重,抄写不易,书写工具不便,流传受到影响,全本不易流传;二是抄写者根据自己的构思和意图来进行节抄,三组简文都体现出抄者的侧重,如丙组的主题是治国,乙组的主题是修道,甲组的第一部分的主题与丙组相似,主要讨论治国方法,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关于道、天道与修身的[2]67-69,149-166。简本为节抄本的另一方面的根据是,与郭店一号墓年代相先后的一些引用老子语句的材料,并不见于三组简文中,说明郭店《老子》并不是当时流行的《老子》全本[2]160-161。裘锡圭赞同这一看法,他指出郭店《老子》三组简的摘录确是经过筹划的,否则不会主题鲜明重复少,而且全见于今本[2]27-28。高晨阳的观点更为明确,他认为,从《论语》、《墨子》、《文子》等所引《老子》的情况来看,早在太史儋之前,就有今本《老子》或与其相近的本子流行。今本《老子》属春秋末期的作品,为老聃所著,“今本《老子》非太史儋所作,春秋时期老聃作《老子》的传统之见不能轻易否定。不可否认,今天所见到的《老子》,不可能完全是老聃所作的原貌,肯定经过后人修饰和损益,但其基本内容及其思想倾向甚至基本结构都是由老聃确定的”。他推断,简本是一个选本,它是简本的作者根据自己对《老子》的理解和现实需要,对今本《老子》进行了有目的剪裁并重新编排而成[9]。
二
郭店简本《老子》有不少内容能够与帛书甲、乙本和今本对应,但是在结构和某些重要的思想内容上与帛书甲、乙本及今本确实有非常大的差异,然而学术界以郭沂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却坚持认为简本《老子》是一个原始的完整的传本。这个结论恐怕为时尚早。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之后,就有人断言这是最古老的《老子》传本[10],结果二十年之后湖北荆门市郭店楚墓又出土了简本《老子》。根据郭店楚简的文字和内容,说它是比较接近原始传本的《老子》可能更为合适。楚简整理者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传抄本”[11]。这个提法是可取的。至于说它是“完整传本”更显得急躁了。因为郭店楚简的发掘者、整理者认为由于墓葬数次被盗,竹简有缺失,简本《老子》亦不例外,所以无法估计简本原有的数量。况且从简文内容看,确定有不够连贯或残缺之处,这是应该注意的。这一情况也可以从战国早中期的先秦古籍中所引《老子》文得到证实。例如《太平御览》卷322辑《墨子》佚文中引有《老子》的“道冲而用之有弗盈”的文句,简本中不见,而见于今本第4章。又如《战国策·齐策》的《齐宣王见颜斶章》引用《老子》“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句,在简本中亦找不见,而见于今本第39章。再有《战国策·魏策》的《魏公叔痤为魏将章》引用《老子》“圣人无积,尽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的文句,这在简本中也不见,而见于今本第81章。墨子是战国初期人。齐宣王,公元前319—301年在位。公叔痤,魏惠王时人,公元前369—335年在位。以上三证,皆在战国时期且早于郭店一号楚墓下葬之年,可见它们所引用的《老子》文句当时已在社会上流传,但都不在简本《老子》之内。这就足以证明简本《老子》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传本,在郭店简本《老子》三组之外尚有一些老子之言或其它传本流传。另外,与上述三条材料相印证,《说苑·敬慎篇》记叔向之言曰:“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这里叔向所引老聃的两句话均不见于简本,而分别见于今本第43章和第76章。这说明老聃之言早在叔向之时即已流传出来,而叔向是晋平公时人,与孔子同时而先于孔子。《说苑》虽是后出之书,但其所据必为先秦古籍,所以这条材料连同上述三条,曾为很多学者反复引证,而且也正如许多学者所据以推断的那样,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组很可能是社会上流传的多种老子之言或传本中的三组文字,是春秋末年流传下来而逐步发展演变成帛书本和通行本样式的[12]。当然,这里并不否认郭沂所做的大量工作。郭文确实提出了不少精到见解,如提出今本(王弼本)对简本进行了改造和编排等颇有见地的看法,后来又有对自己个别见解的修正[13]。但是若说楚简本是“完整的传本”,尚嫌根据不足。
郭店《老子》是一种原有《老子》本的选本或摘抄本,这种观点确实令人向往,也发人深思。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至少在郭店楚简下葬的时间即公元前300年前后,一个几乎是五千余言的《老子》传本就已经存在。这里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既然简本是原有《老子》的摘抄或节选,那么为什么要抄选成甲、乙、丙三组呢?按照王博等人的说法,摘选是有一定的原则和目的的,甲、乙、丙三组有着不同的主题,依主题摘选可能是为了教学之用,因为墓主人可能是东宫太子的老师[2]6。其说不无道理,但又有不能服人的地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组在竹简形制上不同,但根据世传文献所论,以及秦汉以来就有五千言的《老子》传本,因而它们理应被判定为一部在内容上互相关联的著作。然而简本《老子》与帛书本、通行本在内容上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帛书本、通行本中比较激烈地批评儒家仁义思想的话不见于简本,如今本第19章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在简本中作“绝伪弃诈,民复孝慈”①关于“绝伪弃虑,民复孝慈”句,学术界解释不一,其中“虑”字在注文中依裘锡圭按语作“诈”,刘信芳释为“怚”,张立文释为“珰”,季旭昇、庞朴不同意裘氏看法,而主张释为“作”。此据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释文。对于“慈”,研究者多数据《老子》今本,把“子”读为“慈”,把“季”看作“孝”的讹字,但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季子”是《老子》原文,不应据今本改读。见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0—241页。;第5章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不见于简本。研究者由此认为,早期的儒道关系并不像后来那样对立[2]69-70,423-435。但是,又有研究者认为,简本《老子》不仅是摘抄本,而且是“援道入儒”的产物,是“儒家化”了的改编本,是“稷下道家”或“邹齐儒者”的传本[14]53-63,484-492,493-498。照此推测,简本三组以长短形制不同的竹简抄写,只能是有意的安排而非不经意的举措。再者,简本三组自成系统,内容上各有侧重,且甲组篇幅较大,简文中有多种墨记符号,这就有可能暗示着抄写时的不同分类,也暗示着抄写者心目中思想内容的重要程度和一定的逻辑化编排意识,主题说大致不误,摘选也极有可能。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不能不考虑。古籍流传的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整部书的流传,又有单篇流传。整部书流传的情形非常普遍,而值得注意的是单篇流传。由于比较早的书都抄在竹简或帛书上,一方面这些材料较珍贵、难于获得,另一方面竹简的携带也非常困难,所以古书的单篇流传在古代同样普遍。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中对单篇流传的情形曾有讨论[15],这种例子在近年的考古发现中还可以看到许多。如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九主》,即是《伊尹》中的一篇。在张家山汗简中,也有《庄子》的《盗跖》篇。这样说来,《老子》在战国前期以单篇的形式流传,郭店楚简三组简文正是当时《老子》单篇别行的体现,也不是没有可能。进一步的推论是,三组简文可能是抄手根据三个不同时期的文本照样别录,然后分编成三册,也可能是墓主生前在三个不同时期陆续收藏的,这些可能都是存在的。由此看来,认为简本《老子》是原有《老子》的摘选本的可能性似乎又不大。它很可能是当时流传于社会上的多种《老子》传本中的三个本子。至于摘选的目的是为了教学之用的说法,也同样是一种假想。因为郭店楚墓墓主的身份至今仍然没有确定。虽然墓中发现有刻铭“东宫之师”或“东宫之杯”的漆耳杯,但学者们仍然不能据以确定墓主的身份[2]3。如果“东宫”是指太子,定墓主是太子的老师,则其墓葬的规模实在不相称。释为“东宫之杯”,则否定了墓主是太子之师的说法。其实彭浩早就对“东宫之师”的说法提出了怀疑。他说:“如果说郭店一号墓主是太子之师,其地位当在大夫或上卿之列,死后的入葬规模大致与包山二号楚墓、望山一号楚墓相当,而不至于沦为按‘士’礼使用一槨一棺。”[2]16可见,墓主不太可能是太子的老师。墓主的身份只是一位“士”,是一位喜读和爱好收藏儒、道著作的知识分子。所以摘选《老子》为教学之用的说法恐难成立。看来,要确定竹简《老子》的版本归属,还需要仔细研究。
三
1998年5月,在美国达慕思大学召开的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上,美国布朗大学的罗浩(Harold D.Roth)曾试图用三种模型来表示传世本《老子》与郭店简本《老子》可能存在的三种关系,即“辑选”模型、“来源”模型和“并行文本”模型。罗浩的这三种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老子》从简本到今本演变的几种可能性。所谓“辑选”模型,即是说郭店《老子》对文是《老子》祖本的“辑选”。而“来源”模型,是说郭店《老子》对文是祖本《老子》的来源之一。如果郭店《老子》对文自身构成一种独立的文本,同祖本《老子》及从罗浩的研究中提到的《管子·内业》等类似作品一样,来自更早的一种或多种原始材料,即称之为“并行文本”模型。罗浩还指出,竹简本《老子》甲组和丙组中都有相当于通行本第64章的内容,但语句差异较大。经过比较,他认为这两组简文不可能互相抄袭,“它们似乎代表两种独立的文本,由两位不同作者抄自两种不同的文本来源”[2]200-202。邢文进而认为,在郭店竹简本完成之时,《老子》的文本仍处于尚未定型的变化状态,作为一部整体的、完整的文献,《老子》一书也许并非完成于一时[16]。王博也注意到竹简本《老子》甲组和丙组所显示的传本的不同,他指出,就竹简本、帛书本和通行本在语句上的差异而言,通行本与帛书本不同的地方,并不就意味着晚出,而是它有另外的来源,即竹简本也是通行本的来源之一[2]154-163。随后,李存山根据这些学者的观点,在罗浩的“并行文本”模型的基础上,把老子思想的原始形态作为郭店《老子》的来源,归纳出《老子》演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另外两种模型,统称之为“演变模型”。李存山说,在他的“演变模型”中,还容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因为《老子》一书在逐步完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可能不仅是结构形式上的编辑,而且可能加进一些老子思想的原始形态所本来没有的内容。他进一步推论,就现有的三类《老子》版本而言,虽然帛书本早于传世本,但帛书本并不完全具有更接近老子思想的原始形态(或称“祖本”)的优越性;同样,虽然竹简本早于帛书本和传世本,但竹简本也不完全具有更接近老子思想的原始形态的优越性;而且,由于传世本有竹简本(以及推测性的其他简本)和帛书本两个来源,所以传世本并不一定就劣于竹简本或帛书本。这也就是说,就现有的三类《老子》版本而言,它们各有所长,我们若只根据其中的某一类来探讨老子思想的原始形态(或“祖本”),条件并不成熟[17]。李若晖也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老子》原本,我们必须将每一种本子都依其系统、年代编排序列,使每个本子都能说:我是我所是[18]。
确如李存山等人所言,从郭店楚简本、帛书本到以王弼本为代表的各种今传本,《老子》一书必然经历了一个流动而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断对《老子》进行编辑和整理,使得它在体例、结构以及语言文字等方面均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郭店楚简本《老子》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古的《老子》版本,此本的断代大体可以定在战国中期。因为根据发掘郭店一号墓的考古学家推断,该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其下葬年代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初。而郭店楚简的年代下限应略早于墓葬年代,即应在战国的中期。郭店《老子》的出土,为我们探讨《老子》形成的早期阶段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线索。当然,相对于世传《老子》完整的思想体系,郭店三组《老子》显然是不完善的。因为世传《老子》的不少内容在楚简本中都没有反映,二者之间在不少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指出,从《老子》一书的原始形态向郭店竹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及各通行本的发展,编者们都是在有意识地重新编辑《老子》,使之趋向更为合理化,成为名符其实的一部书或文章[19]。郭店《老子》应该说是今日所见较早的系统化、逻辑化传本,但不是原始的、完整的传本。帛书本和以王弼本为代表的今传诸本《老子》是战国中期以后《老子》传本的进一步系统化、逻辑化,而王弼本是一个较好的《老子》注本[20],但不是最后的定本。《老子》文本的这种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不同时期的《老子》样本,它们都有着各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应该产生过不同的影响。
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应当结合流传的多种版本,把《老子》放在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链条中,以动态的眼光,分析和把握《老子》传本的演变轨迹,更为准确地校正《老子》的文字。我们一方面既不可轻易否认《老子》一书是春秋末年的作品,另一方面又要明确战国中期以后形成的《老子》传本都是经过后人增补、修改的版本,而非所谓“定本”。基于这个认识,关于《老子》的文献研究,从方法论上说,二十一世纪的学者不但应该努力发掘《老子》新异本、新版本,而且应当考虑组织人力,集中全国著名文献学家、版本学家、古文字学家、学术史家、思想史家,将各种传世的版本(以王弼本、河上公本、傅奕本为主),与帛书本、郭店楚简本整合起来,经过长期研究,确定、认同一个类似王弼注本这样的新文本。这个新文本《老子》既可以代表老子本人原来的真实的思想面貌,又能够取得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共识。将来如果遇有新的版本或资料出土,再不断修改、补充。同时,应当写出反映最新出土资料、最新研究成果的“道学发展史”、《老子》版本演变史,以推动和深化老子思想和道家学派的研究。
[1]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J].文物,1997(07):47.
[2]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 17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3]姜广辉.中国哲学:第 20辑[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4]徐洪兴.疑古与信古——从郭店竹简本《老子》出土回顾本世纪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争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1):65.
[5]李零.郭店老子校读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1.
[6]崔仁义.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26-34.
[7]郭沂.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其人其书[J].哲学研究,1998,(07):52-53.
[8]尹振环.也谈楚简老子其书[J].哲学研究,1999(4):30-35;解光宇.郭店楚简《老子》研究综述[J].学术界,1999,(05):15-16.
[9]高晨阳.郭店楚简《老子》的真相及其与今本《老子》的关系——与郭沂先生商讨[J].中国哲学史,1999,(03):77-81.
[10]严灵峰.自序[M];严灵峰.马王堆帛书老子试探.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6.1.
[11]荆门市博物馆.前言[M].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
[12]丁四新.郭店楚简思想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36-41;聂中庆.郭店楚简《老子》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4.17;池田知久.尚处在形成阶段的《老子》最古文本——郭店楚简《老子》[M].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 17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67-181.
[13]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515-516.
[14]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15]余嘉锡.古书通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3-97.
[16]艾兰,魏克彬.郭店《老子》:东西方学者的对话[M].邢文编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66-71.
[17]李存山.《老子》简、帛本与传世本关系的几个“模型”[J].中国哲学史,2003,(03):70-74.
[18]李若晖.郭店竹书《老子》论考[M].济南:齐鲁书社,2004.1.
[19]丁四新.郭店楚简思想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36-41.
[20]刘晗,吴永.论王弼《老子注》的形成与玄学背景下的道儒融通[J].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104-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