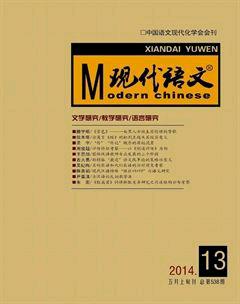从《心坚金石传》到《霞笺记》
摘 要:《霞笺记》是根据《燕居笔记·心坚金石传》改编而成的传奇,传奇从题目到内容遵循“一人一事”的原则构架作品,其中人物的增加和主人公形象的丰满,体现着晚明时代文人的科举心路。最重要的是传奇将小说的悲剧结尾改编成大团圆的喜剧,迎合了社会受众的心理,蕴含着时代的特色。
关键词:情义 信物 改编
《霞笺记》的作者姓名无可考。现存明万历间金陵广庆堂刻本,民国初年刘世珩《暖红世汇刻传剧》据之重印,题《镌新编全相霞笺记》,署“秦淮墨客校正”;明末汲古阁原刻初印本;汲古阁刻《六十种曲》所收本。凡二卷30出。据明吕天成《曲品》,本剧“即《心坚金石传》”。[1]《霞笺记》是根据《心坚金石传》改编而成。《心坚金石传》最早见于夕川老人的《花影集》卷二。夕川老人即陶辅,字廷弼,明前期(一说为嘉靖)凤阳(今属安徽)人。今所见《心坚金石传》有明何大抡《燕居笔记》卷7和明冯梦龙《情史》卷11。
《燕居笔记·心坚金石传》讲述的是元朝至元年间,书生李彦直和歌妓张丽容因诗相爱,却因身份的悬殊和豪强的欺压不能在一起,最后双双殉情,但二人情坚志确,各变为一小物如人形,其色如金,其坚如玉,其貌宛如李彦直与张丽容的传奇爱情故事。《情史》版在情节、人物方面基本与《燕居笔记》版相同。《霞笺记》丰富了主人公的形象并增加或改编情节,最重要的是将悲剧结局改为团圆场面,本文主要着眼于传奇与小说之间的变化之处,并分析原因。
一、《霞笺记》改编版本的釐定
首先从作品出现的时间来看,冯梦龙《情史》,全名《情史类略》,又名《情天宝鉴》,是选录历代笔记小说中爱情故事,略加整理而成的专题性笔记小说集,共二十四卷。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长洲(今苏州)人。《情史》的成书时间一直是有争议的,在《冯梦龙<情史>研究》一文中已经考证《情史》应出现在1622年左右。而现存最早关于《霞笺记》的记载、评述,为吕天成的《曲品》。据其《自序》,《曲品》成于“万历庚戌嘉评望日”,即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1611年1月28日),《霞笺记》的作者姓名无可考。这说明,《霞笺记》当作于万历三十八年之前,最迟在1611年。所以,在时间上,《霞笺记》很可能是改编于《燕居笔记》版。
在小说内容方面,《情史》与《燕居笔记》比较,故事的人物、情节基本相同,主要差异有以下几点:
一是《情史》省略了李彦直和张丽容唱和在霞笺上的两首诗以及丽容写的诀别诗。二是在篇幅上明显看出《情史》较短小,其语言较为精炼,叙述更具条理。仅举一例证:
妪止生一女,年一十七岁,名丽容,生得眉如染黛,口似铁红。又名翠眉娘,灵慧纤巧,不但乐艺女工,至于书画诗文,冠绝时辈,真一郡之国色。
——《燕居笔记》
姥止一女,名丽容,又名翠眉娘。衔其才色,不可一世。
——《情史》
《情史·心坚金石》很可能是由《燕居笔记·心坚金石传》删削、缩写而成的。三是《情史》中小说的末尾增加一段评语,与情节本身无涉,似作者本身附加的感慨评价,有助于理解作品本身,四是具体细节的出入。例:
……至次日,遂用白绞(绫)一方,遂韵和其上,复从原处投回。
——《燕居笔记》
……还从原处投去。
——《霞笺记》
……遂庚其韵,书于白绫帕上。他日,候彦直在楼,亦投墙外。
——《情史》
可见,“候彦直”相比于“原处投回”更加契合实际情况,所以,冯梦龙对《燕居笔记·心坚金石传》有所改动,而《霞笺记》在此处是对其的继承。
因此,《霞笺记》应当作于《情史》之前,至少也是同时期的作品。从文本比较和创作定时两方面来看,《霞笺记》取材于《燕居笔记》的《心坚金石传》,而不是《情史·心坚金石》。也就是说,《霞笺记》与《情史·心坚金石》都源于《燕居笔记》,但两者之间并无传承关系。下面对传奇《霞笺记》与《燕居笔记·心坚金石传》进行具体比较分析。
二、《霞笺记》内容的变化
传奇对小说在内容上有所改变,首先是对李彦直家世的提升,丰富了他的身份和人物背景。在《心坚金石传》中对李生的介绍仅是“金陵松江府学有庠生李彦直者”,在《霞笺记》中,将其家世提升为“家君讳栋,昔为都宪,今已归林;母亲何氏,深沐皇恩,颇称内德。”李彦直生活在这样的官宦之家,家里对他的期望定是很高,必将其培养成状元之才,科举之路是其必然选择,这不仅使主人公的身份悬殊,而且也突出了时代背景。而男女主角社会身份的悬殊构成了以后戏剧冲突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霞笺记》对李、张二人关系的改变。在小说中,张丽容虽生活在烟花之地,但是其为“留心伉俪,不染风尘。人或挥金至百,而不能一睹其面”,她与李彦直二人也只是远远对视,一见钟情。《霞笺记》中增加了李、张二人的肉体接触,强调灵与肉的交融,这种改变让两人的爱情更大胆,更深刻,更容易激起读者心中的涟漪,也对传统贞洁观念有所冲击。
最重要的是将原本悲剧性的结局改造成喜庆式的团圆,为此增设了很多人物和情节。这种改编,其一是为了迎合观剧大众的心理;其二是理想化外力的介入;其三是李彦直最后能高中状元。在小说中李彦直是“将及一年,而彦直学业顿废,精神渐耗,忘餐失寐,如痴如醉”,在传奇中则是“昼锦荣归”,也暗示仕途的重要性。李彦直中状元由落魄书生跻身于统治集团意味着身份的改变,是二人团圆的现实基础。而结局的改变消减了小说中荡气回肠的爱情冲击力,又恢复到世俗的审美当中,也落到了大团圆的俗套当中。
三、《霞笺记》结构遵循“一人一事”
戏剧冲突的单一和戏剧结构的整一,促成了传奇戏曲作品结构技巧的精致,乃是这一时期传奇作品叙事结构的又一个突出特征。[2]正是有鉴于此,明清戏曲家要求每部传奇戏曲作品都要有一个中心,一个聚焦点,王骥德、徐復祚等称之为“头脑”或“大头脑”,而李渔则称之为“主脑”。[2]《霞笺记》和《心坚金石传》在题目上便能看出两种文体的偏向,传奇是以信物主导整部作品,而小说是以情感为导向;《霞笺记》在内容上的增加也是为“霞笺”这一引导传奇的主线索而服务的。这种变化不仅在结构上是对“一人一事”原则的遵循,而且在精神层次方面也解放了人性,具有民主精神,更是对“至情论”的宣扬。endprint
从小说、传奇的题目上来看,“心坚金石”是情感的外化,在文中便指出“精诚坚恪,情感气化”,“男女之私,情坚志确而始终不谐,所以一念成结,感形于此。既得合为一处,情遂气伸,复还旧物,或有之矣”。李彦直和张丽容二人的真情所归之处便是最后幻化成金石,小说中只有这一条主线,赞美男女二人的爱情坚不可摧,从题目便可一目了然。传奇作品以“霞笺”为题,霞笺是李、张二人爱情的信物,《霞笺记》也正是以互赠爱情信物的模式来结构全剧的戏曲作品。从“霞笺题字”“和韵题笺”到“得笺窥认”“霞笺重会”,“霞笺”是贯穿整部传奇的主线。由此,也可以看出传奇作品具有一定的民主精神。其一,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的反抗。明代程朱理学盛行,“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盛行,同时八股取士的制度桎梏着人们的思想,对妇女的压抑程度也很严重。王阳明的“心学”极大地冲击了理学的地位,引发了人们独立意识的觉醒,后来李贽(1527-1602)的“童心说”即是“绝假存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社会思潮影响到文学领域,汤显祖便提出了“至情论”,这样的大潮便催生出了大量的关于宣扬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文学作品。《霞笺记》:“男女之际,大欲存焉,两心相得,虽父母之命不可止也。”[3]李彦直生于显宦之家,张丽容则流落红尘,二人在封建时代的地位悬殊,张丽容自己也说:“思省。我是败柳残花,怎插君家孔雀屏?”[3]但二人依旧不改初心,矢志不渝,留有一段情真意切的对话:
(生)请问小娘子,既混风尘,即由造物;自甘苦守。实出何心?(旦)李郎说那里话!今见君子,可托终身。即便洗干红粉,焉肯再抱琵琶?若不捐弃风尘,情愿永侍金栉。(生)既蒙卿家真心待我,愿为比翼,永效鹣鹣。若有私心,神明作证!(旦)若然如此,和你对天盟誓。将此霞笺,各藏一幅,留作他年合卺。
——《霞笺记·端阳佳会》
此等誓言便在今时今日也令人动容,在当时的社会必然会有一定的反响,而且“霞笺血诗”更是剧中的高潮。在小说中,二人因“霞笺”定情,而后故事的发展并无“霞笺”之事,所以,“霞笺”在小说中的位置没有在传奇中重要,从题目的比较上便可看出两种文体侧重点的不同。其二,从侧面也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推翻。在小说中,“彦直阅毕,遂登太湖石而望之。适丽容独坐于对景楼上,彼此一见,魂志飘荡,不敢错(措)辞者良久。”在传奇作品中,李生是先看到霞笺上的诗句,加之平时对翠眉娘有所耳闻,才要想见此人,所以是先见诗,后见人,比小说中更重视女子的才情。
在结构方面,《霞笺记》也是谨遵“一人一事”[4]的宗旨。《霞笺记》三十出,以“一首诗结三生愿”为主旨,敷演李彦直与张丽容的悲欢离合。如上文所说,《霞笺记》比《心坚金石传》增设了很多人物与情节,但其均是为李、张的爱情故事而服务的。传奇中有两条线索,主线是以“霞笺”为信物牵住二人的情感脉络,副线是对二人爱情道路的阻碍,副线中的人物是为主线而服务的。洒银公子起衅、教官告状、父子伤情一系列情节反映出这第一重风波便为两人的爱情构置了重重社会性障碍;聘求佳丽、丽容行售、得宠遭妒则是社会权豪势力的介入,构成了第二重风波,渲染了二人爱情的真挚和深厚;最后驸马作合,霞笺重会,充分铺垫、收拢线索,二人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虽然副线始终穿插在主线之中,但主线始终突出,一直贯彻以“一人一事”为“主脑”,明确地揭示了传奇戏曲结构集中单一之美的本质特性。
总之,古代小说、戏曲由于覆盖面广、心理影响深入、文化信息含量大而发挥了重大的社会教育作用,在中华民族文化总构成中则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一方面它与经典相比是粗鄙的,与诗文比是俗野的,与正史比是偏记的这样一种处境,另一方面则发挥着经典、诗文、史书无法替代的社会作用,同时又为经典、诗文、史书的传播承担了媒介和发挥了载体的作用。[5]然而,戏曲因作家要重视场上效果,作者增加人物冲突,其感染教化的能力更强。所以,如果说《心坚金石传》体现的是李彦直、张丽容二人坚守盟约、百折不挠的凄美爱情故事,而《霞笺记》强化了科举的重要意义,同时对人性的解放和自主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增强了士人的主体意识;才色兼重,也对传统妇女观念的冲击,普世性更强。这也正是传奇独特价值的所在。
注释:
[1][明]吕天成撰,吴书荫校译:《曲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3页。
[2]郭英德:《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20-347页。
[3][明]毛晋:《霞笺记》,载《六十种曲》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2页。
[4][清]李渔著,张萍校点:《闲情偶寄》,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
[5]许并生:《古代小说与戏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参考文献:
[1]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2][明]詹詹外史评辑.情史[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
[3]《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古本小说集成(卷七)·燕居笔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李雪梅.明传奇中的爱情信物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1.
[5]丁琼.冯梦龙《情史》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09.
(丁雪松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15008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