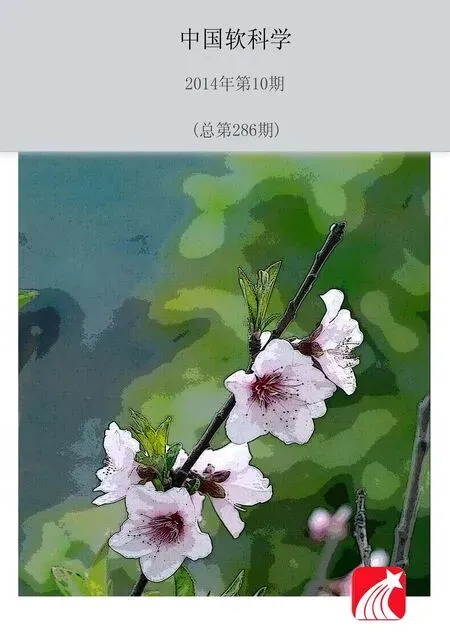养老金红利:理论与来自中国的实证
殷宝明,刘昌平
(武汉大学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是一个国家向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经济过程,无论是发达国家以往的历史经验,还是发展中国家当前正在经历的现实,都验证了或正在验证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移[1]。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和制度障碍不断消除,人口迁移的自主性和流动性不断增强、迁移规模逐渐增大,基本进入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人口迁移的活跃度明显提高,年度迁移率从1978年的2.26%提升到2000年的4.99%,人口迁移数量也从2100万上升到6300万[2]。1990—2000年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人口为1.25—1.29亿人,而2001—2020年转移的人口总量将可能达到3.2亿[3]。
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迁移将对中国的城乡人口老龄化趋势产生重要影响。袁志刚[4]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0.95‰抽样数据估算,2000年的“乡—城”迁移人口中16—60岁人口占90%。刘昌平等[5]预测了“乡—城”人口迁移背景下城镇未来的社会人口老年抚养比,结论显示:2020年新增农村迁移人口使城镇老年抚养比从不包含迁移人口的29.62%下降到25.99%,2030年从50.25%下降到43.30%,2040年从72.34%下降到59.02%,2050年从87.31%下降到71.65%,城镇人口老龄化趋势因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迁移而明显减缓。“乡—城”人口迁移在改变城镇人口老龄化趋势与程度的同时,也必将对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农村迁移人口到底会对城镇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公共养老金制度内现存群体的福利效应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当前正面临财务不平衡风险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意义是什么,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哪些制度缺陷以及应该如何进行调整和改革以适应这种社会经济趋势,这就是本文拟探讨和回答的主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
Razin & Sadka[6]最早在一个静态模型中分析了外来低技能移民对一个福利国家居民的负面影响,从而解释了抵制移民的现象。Scholten & Thum[7]则建立了一个三期迭代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解释了由于外部性难以在代际之间内生化而导致的民主社会决策体制下所产生的抵制移民倾向,但同时指出持续稳定的迁移人口能够提高迁入国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中所有人的生命期预期收益,带来社会福利效应的帕累托改进。由此产生了关于外来移民对迁入国居民公共养老金制度下福利影响的持续研究和争论。Razin & Sadka[8—9]基于萨缪尔森(Samuelson)提出的“整体经济是个永动机”理念(the Economy as an Everlasting Machinery),认为尽管低劳动技能移民是福利制度的净受益者,但在一个动态环境下,迁入国内所有的收入和年龄群体都因为外来移民的迁入而得到福利改进。Casarico & Devillanova[10]的研究则表明尽管外来移民有助于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但同时也会造成代内和代际的福利再分配冲突。如果进一步考虑外来移民的高生育率和后代的低技能,其福利影响将是负面的[11]。而Lacomba & Lagos[12]在一个连续的迭代模型中证明了尽管低劳动技能迁移人口平均生产率较低,但在一个完全再分配(Fully Redistributive)的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下迁入国现存所有群体获得了帕累托改进,且这种作用与移民规模正相关。Jinno[13]在此基础上总结得出福利效应的正负与否取决于外来移民的数量和技能水平。此外,Kemnitz[14]的研究结论显示尽管外来移民对低技能的原住民带来失业和低收入,但是公共养老金覆盖群体却获得了很大受益。Krieger[15]扩展了Scholten & Thum的结论,指出现收现付制公共养老金制度内现存群体更倾向于接纳能够给制度带来更大净收益的返迁移民(Return Migration)。关于外来移民对公共养老金受益者福利效用影响的讨论则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对制度财务可持续性的研究上。Munz & Werding[16]利用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的经验数据分析得出,外来移民能够缓解非积累型公共养老金计划的财政压力,且这种作用是长期的。Blake & Mayhew[17]指出外来移民将是维持英国国家养老金计划有效运转的重要力量。Serrano等[18]研究则表明外来移民还不足以解决西班牙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务不可持续性问题。
国外研究主要从国际移民的角度,且由于研究的出发点和国别之间公共养老金制度模式及运行状况的不同,研究结论存在很大争论,难以充分解释中国“乡—城”迁移人口对城镇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产生的具体影响。而国内关于“乡—城”人口迁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红利”方面,缺乏对养老保险制度影响效用的整体性研究。何樟勇和袁志刚[19]基于经济动态效率考察得出现收现付制筹资模式是当前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合理选择时,指出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未实现全覆盖时,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进入增加了制度内的有效劳动力供给,为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提供了可靠的缴费收入保障。彭浩然和申曙光[20]也认为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扩大能够使制度内人口的年龄结构年轻化、赡养比率降低,从而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促进经济增长。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则主要集中于农民工和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侧重于从保障迁移人口在城镇享有社会养老保障平等权益的角度进行政策分析。尽管这些研究成果认识到了覆盖面扩大对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未能进一步探究农村迁移劳动力在其中所起到的具体作用,也没有细致刻画这种作用产生的条件及其效应大小,更鲜有基于数量研究方法探讨农村迁移劳动力对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内部财务平衡性影响的研究成果。
本文将试图针对以上不足进行初步探索。论文剩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将迭代模型应用于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中并构造个人生命期效用函数,建立养老金红利(Pension Dividend)存在的理论前提并对其进行界定,分析养老金红利产生的具体条件;第四部分对养老金红利存在于中国的外部条件进行判定,并测算和评估养老金红利规模及其演变趋势和对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平衡性所产生的影响;最后是研究结论和政策涵义。
三、养老金红利的存在前提与理论界定
(一)从个体角度的微观前提分析
1.有效劳动供给
假设一个两期迭代模型(T0,T1),将个人的生命周期分为青年期和老年期。在“乡—城”人口迁移的分析框架下,每一期城镇劳动力供给由内部劳动力和农村迁移劳动力两部分组成。假设城镇内部劳动力的再生产速度为n,农村迁移劳动力使城镇劳动力总量保持以m的速度增长。按照Razin和Sadka[8]关于有效劳动的界定和标准化方法,将城镇劳动力划分为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两类,单个高技能劳动力能够提供单位有效劳动,而单个低技能劳动力只能够提供μ(0<μ<1)单位有效劳动,但是低技能劳动力能够通过在青年期投入ε(0<ε<1)工作时间进行学习和技能培训来提高技能水平而成为高技能劳动力。假设T0期出生的城镇初始劳动力存量为L0,则可表示为ε的累积函数:
Q(ε|ε1)=L0
(1)
假设单位有效劳动的劳动报酬为w,由于两类劳动力在劳动报酬和工作时间投入上的不同,低技能劳动力存在一个实现最大化劳动报酬的最优技能培训时间投入平衡点,即
μw=w(1-ε)
(2)
农村迁移劳动力满足以下几条假设:其一,迁移劳动力都是年轻的*从劳动生产率低的传统农业部门进入劳动生产率高的现代工业部门,只有具有较高劳动禀赋的劳动力才有能力和机会进入城镇工作。;其二,属于永久迁移*短期移民会因为反迁等原因而丧失养老金资格,对制度的净贡献显而易见。,这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在进入城镇后将保持与城镇劳动力相同的再生产速度;其三,属于低技能劳动力*迁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力一般劳动技能水平不高,劳动有效性低于城镇劳动力。。因此,农村迁移劳动力在有效劳动投入上有两个选择:其一,在整个工作期以低技能劳动力工作;其二,在1-ε工作时间里以高技能劳动力工作(假设低技能劳动力学习培训的成本等于其放弃工作的机会成本)。求解方程(2),可得ε=1-μ,令平衡点为ε*,即当ε<ε*时,农村迁移劳动力会选择通过培训成为高技能劳动力;当ε>ε*时,农村迁移劳动力则会保持自己的技能水平。因此,T0期城镇劳动力的总量TL0可通过有效劳动表示为:
Q(ε*))+L0μ(m-1)
(3)
式(3)右边第一项表示城镇内部高技能劳动力提供的有效劳动总量,第二项表示城镇内部低技能劳动力提供的有效劳动力总量,第三项表示农村迁移劳动力提供的有效劳动力总量。相应的,T1期城镇劳动力有效劳动力总量TL1可以表示为:
2.对养老金水平的影响
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下参保者的人均养老金水平根据处在工作期内参保劳动力的供款总额确定,采取统一额度方式给付*现收现付制养老金计划中养老金待遇确定的方式有很多种,本文在理论分析部分只考虑最简单的统一额度给付的形式。。假设以单位有效劳动报酬(即工资)为基数的供款率为t,则T0期城镇参保劳动力供款总量为:
T1期城镇参保劳动力供款总量为:
则T0期参保者人均养老金水平为:
T0期退休人口总量为L0/n。T1期参保者人均养老金水平为:
T1期退休人口总量为L0m。
由式(7),∂b0/∂m=wtnμ>0,即T0期参保退休者的养老金水平随着农村迁移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上升;又由式(8),∂b1/∂m=0,即农村迁移劳动力对T1期参保退休者的养老金水平没有影响。因此,在含有农村迁移劳动力的两期迭代模型中,只要现收现付制度养老金制度延续,制度从T1期开始达到稳态,未来各期退休者养老金水平均不受迁移劳动力的影响。因此,农村迁移人口推高了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中至少一代人的养老金水平。
3.对总效用的影响
进一步的,在存在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下个人生命周期内的预算约束方程为:
(9)
式中C1,C2分别表示个人在青年期和老年期的消费,r表示利率。假设个人在生命周期内所获得消费的效用是相同的,即具有不变的消费偏好,其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10)
式中λ表示个人的主观偏好率,U(C1,C2)为固定相对风险厌恶(Constant-Relative-Risk-Aversion)效用函数,表示个人消费的边际效用关于消费的弹性为定值(ρ)而与消费量的具体数值无关[21]。个人生命周期内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表示为:
(11)
求解方程,可得:
(12)
(13)
为分析方便,假设ρ=1*相对风险厌恶固定系数ρ(大于,小于或者等于1)表示边际效用关于消费的弹性,其具体数值只影响个人在不同期内对消费储蓄的安排,对消费总效用没有影响,,即U(C1,C2)=lnC1+λlnC2,简化为关于消费的对数线性效用函数。式(12)和式(13)可以简化为:
主观偏好率λ和利率r是定值,消费函数关于工资w、养老保险税率t和养老金水平b的全微分式为:

由于0
(二)从制度角度的宏观条件分析
1.养老金红利的理论界定
按照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平衡原则,一定时期内养老金供款与给付相等,财务平衡方程为:
No·p=Na·w·φ
(18)
式(18)是一个静态平衡式,其中No表示养老金领取者人数,Na表示供款者人数,p表示平均养老金,w表示供款者平均缴费工资,φ表示缴费率。财务平衡表达式的常用形式是:
(19)
式(19)中No/Na为制度抚养比(用η表示);p/w为养老金目标工资替代率(用φ表示)。将式(19)改写为函数形式:
F=φ-η·φ
(20)
由于φ和φ一般情况下是外生变量,财务平衡函数F将由制度抚养比η决定。制度抚养比与制度覆盖范围和社会人口老年抚养比有关。二元经济下,由于农村迁移到城镇的人口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迁移人口的老年抚养比要低于城镇内部的老年抚养比,因此农村迁移劳动力能够缓解城镇的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进而存在降低城镇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抚养比可能性。在制度所设计的缴费率与养老金目标工资替代率不变的情况下,制度抚养比η下降,养老金制度出现财务盈余,即F>0,本文将盈余部分界定为“养老金红利”。
2.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财务平衡式的动态扩展
加入时间变量的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平衡函数为:
Ft=F(φt,ηt,φt,t)=φt-ηt·φt
(21)
式(21)是一个动态财务平衡函数。函数中的各变量是在制度封闭假设下的界定,如果考虑到外部因素的干扰,还需要进行相应的扩展。设劳动年龄人口为La,老年人口为Lo,δ表示老年抚养比,χ表示劳动参与率,γ表示失业率,π表示参保率或制度覆盖面,则:
(22)
式(22)是离散型的,下标t-1表示老年人口在工作期的相关指标,可以继续转化为连续型函数*根据同期群(cohort) 理论,假设人口生存概率保持不变,当||△t||→0时,通过无限期跨期迭代并取极限,可将非同期人口近似转换为同期人口。:
ηt=δt·Δχt·Δτt·Δπt
(23)
即动态的制度抚养比可表示为人口动态老年抚养比δt*在后文的分析中,老年抚养比都是以变化率的形式出现的,而且老年抚养比关于时间的变化具有连贯性,因此基础数值并不会影响分析结论。、劳动参与率变动倾向Δχt、就业率变动倾向Δτt*此处用就业率代替失业率。与参保率变动倾向Δπt的乘积的函数(Δ>1、=1和<1分别表示相关指标上升、保持不变和下降)。
(24)
扩展后的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财务平衡函数为:

3.养老金红利出现的理论条件
(26)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年度平衡模式的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通常会采取上调缴费率的应对策略,阶段式平衡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则可以保持不变。
(1)当dφt/dt>0时。先不考虑外来迁移人口,简化式(26):
(27)
由式(22)和式(23)的界定可知,用υt代替1/Δπt也可以表示覆盖面的变化。由于已经判定了φt,式(27)可直接化为:
(28)
对式(28)两边取自然对数并对时间求导可得:

(29)
可以得到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内部财务平衡的条件:gφ=gδ+gp-gυ-gw。
考虑外来人口,外来人口将对δt和υt产生影响,如果ρt<δt且养老金制度接纳外来人口,则dδt/dt<0,dυt/dt>0,进而gδ<0,gυ>0,又因为gw>=gp*养老金目标工资替代率一般是指退休者退休当年的养老金平均水平占上一年在职者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随后养老金水平仅根据工资增长速度的一定比率增长,所以养老金水平的增长速度不会高于工资的增长速度,参见程永宏[24]。,在gφ=gδ+gp-gυ-gw的状态下,gφ<0,则在dφt/dt>0的前提条件下制度将出现财务盈余,即外来人口产生养老金红利是显而易见的。

对式(30)进一步变形可得:


在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满足平均缴费工资增长率与平均养老金增长率之差等于老年抚养比的增长率与制度覆盖面扩大速度之差时(此为财务初始平衡的条件),如果外来迁移人口满足包含迁移人口的总体老年抚养比增长率小于制度内部的老年抚养比增长率的条件时,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出现财务盈余,即农村迁移人口给城镇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带来养老金红利。
四、养老金红利存在于中国的实证
(一)存在条件判断与解释
1.“乡—城”迁移人口显著年轻化
图1给出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迁移人口年龄结构和城镇人口年龄结构。从图1可以看出,迁移人口集中于20—40岁之间,该年龄段的迁移人口分别占到总迁移人口的41.5%,33.3%。根据“五普”长表7—3计算,农村迁移人口占全部迁移人口的78.0%,且迁移人口的88.2%流入城镇。移民迁移时的年龄段多在20—25岁之间[25]。根据“五普”抽样调查数据,在按照户籍、迁移原因划分的迁移人口中,务工经商、随迁家属和结婚迁入中农业人口比例最高,分别为88.0%、80.2%和72.0%[26]。如果只统计上面三类迁移人口,由“五普”中长表7—5可计算得出20—40岁的迁移人口占67.9%。

图1 迁移人口与城镇人口年龄结构比较注:统计资料中分年龄迁移人口年龄统计上限为65岁并将65岁及以上年龄数据都归为65岁,图中剔除了65岁及以上年龄的数据;(b)中剔除了与“乡—城”迁移人口明显不相干的市区内人户分离数据。资料来源:《中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2.养老金红利产生的外部经济变量和人口动量满足
由理论分析可知,城镇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是养老金红利实现的外部影响因素。长期来看,许多国家都经历过劳动参与率降低的过程[27]。但由于我国城镇居民工资收入偏低且劳动收入比重大,就业关联型社会福利政策和改革时期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必将是缓慢而长期的,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释放使城镇劳动参与率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是可能的。由于人力资本的局限和户籍制度、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限制,农村劳动力大多进入城镇本地从业者不愿从事的行业,二者并不在一个劳动力市场竞争。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和农村迁移劳动力的从业特点决定了其对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影响不大,对城镇本地从业者的挤出效应有限。由人口统计资料分析,农村迁移人口流入率与城镇本地非农业人口的失业率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也基本不受城市失业问题的影响[28]*袁志刚[29]的研究表明农村迁移人口对城镇的失业率没有影响。。城市化率通常是衡量“乡—城”人口迁移阶段的重要指标。2013年我国城市化率为53.73%*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OL].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2/t20140224_514970.html, 2010002024.,而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饱和值约为80%左右[30],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大规模的“乡—城”迁移人口在中国未来较长时期内将持续存在,产生养老金红利的人口动量是满足的。
3.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有利于养老金红利的形成
中国的二元经济差别不仅表现在生产要素的分割上,而且表现在制度的差别供给上。囿于统筹层次低、地方利益割据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缺位,参加了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乡—城”迁移劳动力难以在各统筹地区和城乡之间转移与接续养老保险关系,也难以转移城镇基础养老金受益权。因此,迁移人口在现行制度限制下面临缴费损失,产生“缴费沉淀”,为城镇制度带来净收益。从制度财务平衡看,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账户由于被赋予了清偿制度改革时所产生的转制成本的功能,其设计并不是一个精算平衡的制度,而是一个精算盈余的制度;从待遇领取资格看,城镇基础养老金为典型的月缴终身年金,设定了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限制,从而新参保者在前期能为制度带来巨大的缴费积累收益;从待遇确定方法看,城镇基础养老金既不是单纯的供款基准制,也非单纯的待遇基准制,其以参保者的指数化平均缴费工资和社会平均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采取定率方式确定,在实现代际之间再分配的同时建立了与个人缴费相关联的激励机制,这种待遇确定方式显然不利于工资收入水平低的农村迁移人口,其通过养老金替代率和收入关联效应传导到养老金水平,从而减轻了农村迁移人口对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压力。
(二)存在规模测度与效应评估
由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转制成本的存在,同时养老金红利依赖于制度设计和对农村迁移人口的接纳程度,因此对理论条件下养老金红利出现的临界点难以进行精确的量化判定,只能对养老金红利的规模和期限结构进行宏观上的测度。下文将对农村迁移人口在《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 38号)文件所形成的制度模式下产生的养老金红利进行测度。
1.模型与数据来源
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在职迁移人口在t年的社会统筹账户缴费总额为:


按照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参保者最低缴费满15年才能获得基础养老金且缴费满1年发给相当于计发基数1%的养老金,制度规定的最高缴费年限为35年*参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宣传提纲》(劳社部发[2005]32号),参保职工获得制度设计的养老金目标替代率的缴费年限为35年。,假设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农村迁移参保者第一批退休人口基础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为15%,随后逐年增加并最终达到35%,其后保持不变。
在t年退休人口基础养老金支出总额为:
(34)
t年社会统筹账户基金平衡式为:
(35)
测算所使用的参保人口数据来源于邓大松等[32]测算的2000—2050年“乡—城”迁移人口数据。其他参数来源于刘昌平[33],包括名义工资增长率2010年前为10%,2011—2020年为6%,2021—2050为4%;退休人员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为0.7;通货膨胀率为3%;利率为4%*此处的参数取值与下文所使用到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财务平衡数据在测算时的参数取值保持一致。。
2.测算结论
在制度实际运行中,100%的覆盖率是难以实现的,同时参保者的缴费工资比例也会对养老基金平衡性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测算参保率为90%、缴费基数占人均工资90%的实际参保缴费状态下的养老金红利*此处的设定与下文所使用到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财务平衡数据在测算时的设定保持一致。,以及所有“乡—城”迁移的就业人口均为正规就业和均为非正规就业两种极端情况下的养老金红利*根据国发[2005]38号文件的规定,正规就业人员与非正规就业人员社会统筹账户缴费率分别为20%、12%。。从2006—2050年养老金红利的期限结构看(图2),两种就业类型下养老金红利均呈现出前期平稳增长,后期加速下跌,年度最大值分别出现在2033年和2027年,而由红利转换为赤字的时点分别为2048年和2039年,养老金红利存在着大约40年的“机会窗口”开启时间。

表1 2006—2050年“乡—城”迁移人口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数据(万人)
注:参保起始年龄统一为20岁,退休年龄统一为60岁且假设参保率为100%。
非正规就业人员相对于正规就业人员低8%的缴费率造成养老金红利的大量流失(表2),非正规就业类型的养老金红利的“机会窗口”关闭时间大约提前了10年。吴要武[34]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计算得出城镇中本地人的非正规就业比例为49.9%,农村迁移者非正规就业的比例为68.7%,若采用这一结论并假设农村迁移人口非正规就业比例最终与城镇本地人一致,则可推算养老金红利的规模为5.3万—6.2万亿之间。
表2两种就业类型下养老金红利的现值总量

正规就业类型非正规就业类型PPB①(亿)PPB/GDP②(%)PPB(亿)PPB/GDP(%)86362.041.237654.418.0
注:①为养老金红利在2006年的现值;②为2006年中国的GDP,为209407亿元,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OL].http://www.stats.gov.cn, 2007-02-28.
3.养老金红利对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财务平衡性的影响
在社会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由图3所示,在本世纪的前30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账户基金由于巨额转制成本的重负而面临严重的财务不平衡风险。但是“乡—城”迁移人口带来的养老金红利将有效化解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危机;在随后由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度过老龄化高峰和本身的精算盈余性,内部盈余量逐年增加,财务状况逐渐好转,到2040年之后的年度盈余量接近1万亿元,反过来将有助于补偿因为迁移人口自身老化而产生的养老金赤字。

图2 两种就业类型下养老金红利实际值的期限结构(亿元)

图3 养老金红利对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财务平衡的影响(亿元)注:养老金红利为正规就业类型的数据;“不含迁移”表示城镇制度自身的财务平衡状况,数据来源于刘昌平[33]。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涵义
农村迁移人口能够提高城镇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内现存群体的养老金水平,进而提高其生命周期内的消费总效用,其潜在的养老金红利对于人口老龄化危机下城镇现收现付制公共养老金制度具有重要的输血作用。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一个永恒的过程,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在人口老龄化危机下的财务风险也不会永远存在。中国当前年龄结构显著年轻化的农村迁移人口与老龄化程度严重的城镇人口处于人口转型的不同阶段,其老龄化进程的不一致使二者人口老龄化的波峰波谷相“咬合”,潜在的养老金红利有助于正在承受巨额转制成本和隐性债务之痛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财务可持续性。
然而,对养老金红利出现的理论条件的分析以及对其规模的实证测算都显示和证明了养老金红利存在有限的机会窗口开启时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逐渐缩小,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乡—城”迁移人口规模,尤其是其中经济活动人口规模必然不断缩小。尽管由青壮年劳动力占主体的农村迁移人口在初期老年抚养比很低,但这批迁移人口20—30年后进入老年,人口老龄化高峰也随之来临。养老金红利是稀缺的,但当前的现实却阻碍了其实现。一方面,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大,城镇生活成本的提高使迁移者更倾向于短期流动,而不是长期迁移;另一方面,迁移到城镇的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处于灵活就业或非正规就业状态,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于劳动关系和正规就业设计的特点以及统筹层次不高和存在最低缴费年限门槛,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难以转移接续,阻碍了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向农村迁移人口扩大。目前,我国已有农民工2.3亿人,但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只有2000多万,仅占城镇就业农民工的17%左右*数据来源:陈圣莉.养老保险转续新办法即将实施[N].经济参考报, 2009-12-24.。大量的农村迁移劳动力游离在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之外,是对潜在养老金红利的巨大浪费,但同时也不能透支养老金红利,防止挪用农村迁移参保者的个人账户基金积累,避免重蹈城镇制度“空账”覆辙,这些都为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毕竟社会承担了养老保障的最终责任。因此,一方面要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继续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合理转移,实现二元经济转化;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适应农村转移劳动力参保。应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统筹层次,实现异地转移就业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与接续;加强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建设,提高管理水平,减少农民工参保、转移的手续与环节,便于其养老保险关系接续。
参考文献:
[1]蔡昉.作为市场化的人口流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 2003(5): 11-19.
[2]杨云彦.中国人口迁移的强度测算与规模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 2003(6): 97-107.
[3]胡英.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数量分析[J].统计研究, 2003(7): 20-24.
[4]袁志刚.中国的乡—城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一个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 2006(8): 28-35.
[5]刘昌平等.“乡—城”人口迁移对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及养老保障的影响分析[J].经济评论, 2008(6): 25-33.
[6]RAZIN A, SADKA E.Resisting migration: wage rigid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995, 85(2): 312-316.
[7]Scholten U, THUM M.Public Pension and immigration policy in a democracy[J].Public Choice, 1996(87): 347-361.
[8]RAZIN A, SADKA E.Migration and pension with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bility[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9(74): 141-150.
[9]RAZIN A, SADKA E.Unskilled migration: a burden or a boon for the welfare state[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102): 463-479.
[10]CASARICO A, Devillanova C.Social security and migration with endogenous skill upgrading[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3(87):773-797.
[11]KRIEGER T.Fertility rates and skill distribution in razin and sadka’s migration-pension model: A note[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4(17): 77-182.
[12]LACOMBA J A, LAGOS F.Immigration and pension benefits in the host country[J].Economica, 2008, Dec: 1-13.
[13]JINNO M.Assimilation, immigr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J].FinanzArchiv: Public Finance Analysis, 2011(67): 46-63.
[14]KEMNITZ A.Im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pensions[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105):31-47.
[15]KRIEGER T.Public pensions and return migration[J].Public Choice, 2008(134):163-178.
[16]MUNZ S, WERDING M.Public pens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ome clarifications and illustrative results[J].Journal of Pension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5, 4(2): 181-207.
[17]BLAKE D, MAYHEW L.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UK state pension system in the light of population ageing and declining fertility[J].The Economic Journal, 2006(116):F286-F305.
[18]SERRANO F, EGUIA B, FERREIRO J.Public pensions sustainability and population ageing: is immigration the solution[J].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201(150):63-79.
[19]何樟勇, 袁志刚.基于经济动态效率考察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研究[J].世界经济, 2004(5):3-12.
[20]彭浩然, 申曙光.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与中国经验[J].世界经济, 2007(10):67-75.
[21]ROMER D.Advanced macroeconomics[M].New York: The McGtaw-Hill Companies, 2006: 77-78.
[22]LEWIS W 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54, 22(2): 139-191.
[23]SOLOW R M.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70): 963-985.
[24]程永宏.现收现付制与人口老龄化关系定量分析[J].
经济研究, 2005(3):57-68.
[25]“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与劳动力流动[J].管理世界, 2002(3): 1-13.
[26]李强等.城市外来人口的现状和管理对策[M].//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主编.转型期的中国人口.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309-324.
[28]左学金等.城市流动人口的现状与管理方法研究[M].//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主编.转型期的中国人口.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337-359.
[29]袁志刚.中国的乡—城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一个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 2006(8):28-35.
[30]陈彦光, 罗艳.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速度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速度和城市化水平饱和值的初步推断[J].地理研究, 2006, 25(6): 1064-1072.
[31]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23.
[32]邓大松等.2007—2008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3-23.
[33]刘昌平.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30-40.
[34]吴要武.非正规就业者的未来[J].经济研究, 2009(7): 98-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