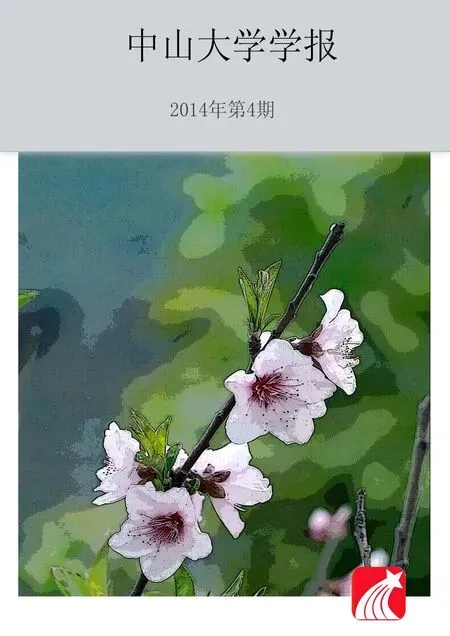体制转型与户籍身份转化:“农转非”微观影响机制的时代变迁*
边燕杰, 李颖晖
户籍是我国的基本制度安排,由此形成了城乡社会的二元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农民身份和非农身份具有重大的阶层划分作用,因为户籍的背后是社会保障、住房状况、求学机会、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等一系列资源配置和人生际遇向城镇户口倾斜的严重不平等(Chan,1996;Cheng & Selden,1994;陆益龙,2002、2008;李春玲,2006;吴晓刚,2004、2007;王美艳、蔡昉,2008)。面对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这些不平等,农村出生者转换其户籍身份,即“农转非”,是改变生活机遇的一个根本途径:成功实现身份转换不但使自己跨越了城乡壁垒,实现了自身的社会流动(李强,1999;刘精明,2001;吴晓刚,2007;林易,2010),而且为子女的发展争取了基本权利、创造了条件(Wu & Treiman, 2004)。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成功实现“农转非”身份转换的毕竟是农村出生人口中的少数。那么,哪些人能突破户籍制度障碍获得非农户籍身份转换?用学术语言表达,哪些微观机制促进人们成功实现“农转非”?这些微观机制是如何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和户籍制度的松动而发生历史变迁的?这些变迁对于我国当前劳动力管理的社会意义何在?本文基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①该项目为中山大学三期“985”建设项目,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为广东地区补充样本的调查提供了资助。的分析 ,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体制转型下的户籍制度沿革
目前实行的户籍制度是再分配经济时期形成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就业、居民住房面临强大压力,开始限制“由乡入城”的人口流动,并于1958年颁布户籍管理法规,通过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限制农村人口迁往城镇。1962年,公安部进一步出台《关于加强户口管理工作的意见》,强化了从农村迁往城市的限制,并在1963年,依据是否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作为划分户口性质的标准,形成非农户口和农业户口两种户籍身份,严格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城乡各自区隔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模式应运而生(马福云,2001)。
这种严格的户籍壁垒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松动。1978年,国家对返城知青和下放干部调整了户籍政策,放宽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政策。1984年,明确允许离开土地、从事非农劳动的农民以自理口粮落户集镇,容许他们在集镇有固定住所,在二元户籍制度上划开第一道口子。之后,国家颁布了《暂住人口管理方法》和《居民身份证制度》的管理制度后,于1997年开始实施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规定凡在小城镇能够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均可以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从此户籍制度弱化,城乡流动的大门渐渐打开,为农村人口带来了更多自由流动的空间,增强了个人择业、家庭择居、儿童择校的自由度(刘精明,2001)。
必须看到,户籍制度从未完全阻断城乡人口流动。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每年容许1.5—2‰的“农转非”流动指标。改革开放之后,城乡流动逐年增加,流动途径也增多,其中一个重要的流动群体是“农转非”群体:他们不但获得了非农职业,还获得了非农户口,成为城镇居民,享受城镇常住人口的制度待遇。这种生活地域与户籍身份的双重跨越,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发现“农转非”群体在社会保障、住房状况、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等生活机遇方面确实获得了巨大提升(Fan,2002;吴晓刚,2007;陆益龙,2008;Logan et al.,2009;林易,2010)。这些研究呈现了“农转非”群体地位变迁的后果,但忽略了“农转非”的过程:什么样的人成功实现了身份转换?换句话说,“农转非”的微观机制是什么?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些机制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理论上涉及了改革开放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意义,也涉及了户籍制度松动的政策效果,所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选择性理论
所谓选择性,是指完成“农转非”的过程是基于个人选择而实现的,选择的基础是个体禀赋。这是吴晓刚和特雷曼分析1990年代数据得出的结论(Wu & Treiman,2004)。他们发现,在严格的户籍藩篱下,农民要想摆脱先赋性的农民身份,突破户籍限制实现“农转非”,国家制度提供的升学、参军、入党提干是三条主要途径,且都是能力出众的农民可以选择的途径。虽然选择并不是自由的,但是选择性假说的理论立场是明确的:冲破强大的户籍制约必须具备较为出众的个人禀赋。这一理论立场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所支持(吴晓刚,2007;郑冰岛、吴晓刚,2013)。
选择性理论强调个体禀赋等微观要素在“农转非”地位转换中的作用,但是该理论对于地位获得模型中的先赋性因素,以及选择条件的制度变迁缺乏充分的关注(Blau & Duncan,1967)。具体地说,由于个体禀赋是在一定的家庭背景中获得的,那么家庭背景变量,如父代的阶级成分、职业地位、教育程度,对于“农转非”身份转换发生怎样的作用?另外,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是不断深入的,户籍制度的调整和松动也是有阶段性的。那么,家庭背景和个人禀赋对于“农转非”的影响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于关心社会分层的政治逻辑的学者(刘精明,2001;李路路,2002a),这些变化体现着我国从再分配向市场体制的过渡。
(二)本文的研究假设
本文作者的理论立场是,影响“农转非”的微观要素是在宏观制度的结构制约条件下发挥作用的。宏观上,户籍制度的沿革同步于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过程,这是“农转非”的机会结构和制度空间。微观上,家庭出身、父代资源、个人教育、参军经历是重要的个人特征变量,影响着社会成员能否成功实现“农转非”。它们的影响也是随着“农转非”的机会结构和制度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的研究假设关注这些微观影响要素在宏观背景下的动态过程。
1. 家庭出身
家庭出身是指家庭的阶级成分,曾是我国社会分层的至关重要的微观机制(李强,1997;Walder,1985;Bian, Shu, & Logan 2001;怀默霆,2002;白威廉,2002;Bian, 2002;李春玲,2003;吴晓刚,2007;吴愈晓,2010;孙明,2011)。阶级出身作为关键的政治身份标准,在建国后就开始发挥作用,到了十年动乱期间,“红五类”和“黑五类”成了政治庇护和政治迫害的分水岭。改革前,家庭出身也作为一种政治资本,对个体的地位获得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再分配精英选拔与地位获得的重要考察方面。那时,户籍制度藩篱严格,仅有一小部分“农转非”的机会,“好出身”成为抓住这一机遇的重要条件。改革之后,再分配力量渐渐削弱,阶级出身的政治资本作用日渐降低,对“农转非”的影响随之下降。因此,
假设1:改革前,阶级出身显著影响“农转非”,其后该作用淡化、消除。
2. 父代资源
根据地位获得的研究传统(Blau & Duncan,1967),我们考虑父代的两大资源,即职业和教育。研究表明,在我国,父代的职业地位高、教育程度高,能够创造较为优越的家庭学习环境和就业机会,子代由此获得较高的教育程度、单位选择、职业分配(林南、边燕杰,1989;李春玲,2003;李路路,2002b;郑辉、李路路,2009;吴愈晓,2010)。父代资源对地位获得的这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当下社会仍有延续(李路路,2002b;李春玲,2003),因此,我们认为,逻辑上,父代的资源效应也将表现在“农转非”的身份转换过程之中。
假设2:无论改革前后,父代职业地位越高,子代越有可能实现“农转非”;
假设3:无论改革前后,父代教育程度越高,子代越有可能实现“农转非”。
3.个人教育
基于“选择性”理论,提升教育程度是获得“农转非”的重要途径。改革前,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根据国家户籍政策与就业制度,获得中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村学生可以随迁户口到就学所在地,毕业后获得城镇就业的分配机会;同时,技校和大中专毕业生被视为特殊性、专门性人才,可以分配到城市工矿企业工作(Chan,1999;马福云,2000;王海光,2003 )。改革后,虽然升学包分配政策逐渐弱化,但劳动力市场对教育资质和专业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1999年高等学校扩招,增加了农民子弟在城市就学、就业、落户的机会。为此,
假设4:教育程度越高,“农转非”的机会越大;随着改革的推进和高等教育扩招,这种效应在高等教育程度的人群中具有加强趋势。
4. 参军经历
农村青年和城镇待业青年是征兵的主要对象(肖季文、朱 鹏,2009)。根据既往研究,退役安置是国家提供的“农转非”的一种政策通道(Wu & Treiman,2004)。这种通道的时代差别是,改革前它是国家保护的相对有效的“农转非”途径;改革后,随着民工潮和户籍制度的松动,自愿进城打工、自主流动择业以及获得中专、大专、大本学历后留城工作,已经越来越普遍,所以参军经历对于“农转非”的相对重要性大大消弱了。为此,
假设5:个人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参军经历有利于“农转非”的实现,此效应改革前大于改革后。
三、研究设计和样本描述
本研究使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个体与家庭数据。该调查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收集,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法,样本覆盖除港、澳、台、西藏、青海的大陆地区15岁及以上的个体。基于“农转非”这一研究主题,本文将“农转非”群体界定为出生时为农业户口而调查时为非农业户口的个体,它的比较参考群体是出生时和调查时皆为农业户口的个体。在家庭问卷、个体问卷共同被访者中,研究选取1944年后出生且出生时为农业户口的个体,实际有效样本6 762个。
以是否“农转非”为因变量,根据户籍制度的动态考察,我们把握三个时期:1984年前户籍制度具有很强的刚性;1984—1997年之间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户籍制度开始松动和调整;1997年以后小城镇户籍改革推进,许多省市开始试行地方性的管理政策,对户籍制度做出重大的改革并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推进逐步深化。为了叙述简便,我们在行文中把三个时期分别表述为改革前、改革初期、改革后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没有询问被访者“农转非”的时间。我们分析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数据,结果表明,3/5“农转非”发生在14岁—25岁之间,并集中于18岁—22岁之间,20岁是众数。基于这一经验事实,我们用20岁作为切割点,1984年前进入20岁的被访者划入改革前,1984—1997年进入20岁的被访者划入改革初期,1997年以后进入20岁的被访者划入改革后期。这样的分析存在一定的测量误差,因为被访者的“农转非”不见得发生在所划入的时期。所以,我们的分析是趋势性的探索,不能作为严格的统计预测。样本分布和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我们围绕“农转非”机会的变化趋势,简述主要结果。

表1 样本分布和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表1显示,出生时是农村户口的6 762个被访者中,16%实现了“农转非”,是绝对少数。三个时期的“农转非”比例,改革前是14%,改革初期上升为18%,改革后期是16%。每个时期的“农转非”比率分别为0.16、0.22、0.19,即:相对于每100个未实现“农转非”的人,实现“农转非”的人,改革前是16人,改革初期是22人,改革后期是19人。我们的时期测量是基于被访者进入20岁的年份为标准的,可能低估改革后期“农转非”的实际比率,但基本反映了“农转非”的机会在经济改革开放和户籍制度松动后呈增长态势这一趋势,是历史的进步。在这种进步中,“农转非”的机会平等是否也在与日俱进呢?
我们先看个人特征变量。虽然“农转非”总样本中男女比例趋于均等(男48.7%、女51.3%),但是改革前男性超过女性(男55.6%),而改革初期和后期女性超过男性(女性“农转非”分别是55.4%和54.5%)。“农转非”的男女比率更清楚地描述了这个趋势:对于每100个成功实现“农转非”的女性,男性实现“农转非”改革前是125人、改革初期是80人、改革后期是83人。参军经历和中共党员提高“农转非”的机会,但是其优势也出现下降趋势。总样本中参军经历的人占3.4%,但是改革前“农转非”人员中有此经历的占14.1%,改革初期和后期下降为3.8%和4.8%。同样,总样本的中共党员比例是8.4%,但是改革前“农转非”人员中的党员比例是28.5%,而改革初期和后期分别是18.1%和20.4%。这些数据说明,改革开放和户籍制度的松动,对于“农转非”的机会而言,消除了男性的优势,弱化了参军经历的优势,降低了中共党员的优势。
教育程度的优势却是上升的状态,主要体现三个方面。一是获得9年义务教育的人员(初中及以下)历来没有“农转非”的优势,更多的是保留农村户籍,这从百分比分布一目了然。二是获得中专和高中教育程度的人员具有一定的“农转非”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改革前比改革后要大得多,这从“转非”和“未转”的同时期的比率可以得到证明。三是获得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员“农转非”的优势不但相当大,而且是随着时期而攀升的:改革前“农转非”人员中9.5%具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改革初期上升为28.5%,改革后期继续上升为54.9%。所以,改革开放时代对“农转非”机会分布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一方面消除、弱化、降低了再分配时期对男性、参军、入党等优势群体的制度保护,另一方面又发展了对高等教育群体的特别偏好。这种偏好与市场化息息相关。一个初步的证明是,改革前“农转非”人员的初职58.9%在国有部门,而改革初期和后期国有部门的比例分别下降为51.7%和38.4%;与此同时,改革后期非国有部门(34.5%)和自雇职业(27.1%)的作用大大上升了。
家庭背景的作用是研究“农转非”机会分布是否趋于平等的重要视角,表1数据给出三项初步答案。首先,家庭出身的跨时期分布没有很大差别。按照文革时期的标准,“好成分”包括工、农、军、干,而“旧精英”指的是地主、富农、资本家、旧官僚等。表1显示,两类成分的“农转非”的比例分别是94.7%和5.3%,跨时期的差异是1—2个百分点,很小。改革前“旧精英”的子女反而具有较高的“农转非”的比例(6.63%),估计是由于建国后的17年这些子女的就学率、升学率比较高造成的。其次,父亲的职业地位的影响是明显的。虽然绝大部分“农转非”人员的父亲都是农民,但是工人父亲使子女获得“农转非”的机会,从改革前的4.1%上升为改革初期和后期的6.0%和11.4%;与此同时,从事行政管理、专业技术、商业服务业工作的父亲,其子女的“农转非”机会从改革前的8.1%上升到改革初期和后期的12.1%和16.8%。最后,父亲教育程度的正向影响是不断上升的,主要体现在初中教育程度特别是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父亲,其子女 “农转非”机会的呈现跨时期迅速上升的趋势。
四、多元分析与假设检验
表1描述的这些趋势是基于单变量的样本分布。现实社会中,“农转非”的机会分布是多种要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某些人的“农转非”是由于个人特质和家庭背景的多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受时代变迁的影响而实现的。所以,我们对研究假设的检验是基于多元分析的结果,见表2。每个时期都是两个模型:模型1考虑家庭背景变量,单看家庭背景对“农转非”的影响效应;而模型2增加个人特征变量,考察家庭背景和个人特征对“农转非”的综合影响效应。我们按照研究假设的顺序分别讨论分析结果。

表2 影响“农转非”机会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报告值为发生比率;双尾显著水平:!p < 0.1,*p < 0.05,**p < 0.01,***p < 0.001。
1. 家庭出身
改革前,家庭出身对子代能否“农转非”有着显著的正效应,而在改革后的两个阶段中这种效应消失了。具体地说,模型1显示,在不考虑个人特征的前提下,改革前,家庭出身为“好成分”的人,其“农转非”几率是“旧精英”家庭出身的人的1.6倍(相对比率系数是1.627);改革后,相对比率系数低于并接近于1,说明“好成分”再也没有优势了。模型2显示,在个人特征一致的条件下,改革前“好成分”的相对优势是“旧精英”的4倍多(4.471),而改革后的两个时期这一优势都不复存在了。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治目标导向下的政治因素考察,随着改革开放发生了质的变化。此分析结果有力地支持假设1。
2. 父代职业
模型1显示,与农民父亲相比,工人父亲使子女“农转非”的机会,改革前提高了约4.5倍(5.475-1=4.475),改革初期提高了2倍多,改革后期没有提高;同时,父亲从事其他非农职业,对子代“农转非”的机会,改革前提高1.8倍,改革初期提高1.9倍,改革后期提高1.3倍。模型2显示,当个人特征一致的条件下,工人父亲的相对优势改革前和改革初期保持,改革后期消失,从事其他非农职业的父亲的相对优势改革前不显著,改革后两个时期都是存在的。所以,整体的态势是,父亲的非农职业及其地位,有利于子代获得“农转非”的机会,这一实证发现在总的趋势上支持假设2。
为什么改革前工人父亲具有相对优势而从事其他非农职业的父亲没有这种优势呢?为什么改革后工人父亲的优势消失了而从事其他非农职业的父亲的优势增加了?我们应该从改革前后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理解这些数据。改革前,由于城市地区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户籍转换实行严格的“农转非”指标控制,城乡流动甚至一度被隔绝。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农转非”的潜在影响被大大限制,因此,父亲从事其他职业(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商业服务业人员、办事人员)相对于父亲务农,职业地位的优势并不存在充分的作用空间。但与此同时,一些特殊的政策安排,如以工人为主要对象的“顶替”安排、对艰苦行业工人的照顾政策等,却可以使工人的子弟在“农转非”上直接受益:他们或“顶替”父母岗位,或作为工人家属户口随转(马福云,2001;王海光,2003),“农转非”的机会相对于农民子代大大提高。1985年后,“自理粮落户集镇”、“蓝印户口”推行、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政策安排逐步实施,户籍藩篱渐渐打开缺口。此时,“农转非”的机会空间大大增加,父亲职业地位的优势得以释放。到了改革纵深的2003年之后,之前针对工人子代的庇护政策弱化甚至被取消,城镇户口准入条件也进一步降低(姚秀兰,2004),农民子代“农转非”的机会大大增加,父亲是工人的职业地位对子代“农转非”的相对优势也便相应消失了。与此同时,父亲从事其他非农职业,特别是行政管理和专业技术职业,不但可以为子女创造“农转非”的机会,而且可以通过家庭状况的改善而激励子女实现“农转非”。
3. 父代教育
模型1显示,与小学教育程度的父亲相比,初中教育程度的父亲对子代“农转非”的提升作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的统计是显著的,相对比率系数分别是1.520和2.584,但是改革后期统计不显著,虽然相对比率系数1.281也是正向。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父亲对子代“农转非”的提升作用,从改革前到改革后期一直存在,并且统计是显著的,相对比率系数分别是2.048、5.138、2.008。这些结果说明,总的趋势是,父代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农转非”的机会越多,其相对优势在改革前后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支持假设3。
基于模型2的结果,我们必须深入分析上述研究结论。模型2显示,当个人特征一致的条件下,父亲教育程度对子女“农转非”机会的提升作用,在改革后期不复存在:初中教育程度的父亲、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父亲,两个系数统计都不显著,接近1。其含义是,无论父亲的教育程度如何,子女的“农转非”机会没有显著差别。我们的数据分析表明,这主要是由于,进入改革后期,父代教育程度的影响,是通过子女教育程度的高低而发生影响的。这是一种间接影响的模式:父代教育影响子代的教育,从而影响子代的“农转非”的机会获得。事实上,这一间接影响模式,在改革后期,适用于所有家庭背景变量:家庭出身、父亲职业、父亲教育的直接影响都不显著。这是一种历史进步:“农转非”作为社会地位转换的机会,不是先赋性的“送”给优势家庭背景的人们,而是被那些利用家庭背景的优势而获得人力资本的人们得到。
4. 个人教育
上述研究结论促使我们认真讨论个人教育对“农转非”的影响方向和效度。表2显示,改革前,教育程度每增加一个水平,“农转非”的机会就增加一个很大幅度。具体地说,如果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农转非”机会为1,那么初中毕业生的机会近似是前者的1倍半(相对比率系数=1.558),高中/中专毕业生的机会接近4倍(3.881),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机会是16倍多(16.407)!这种正向影响改革初期加强了:上述比值分别为1.6倍(1.565)、6.0倍(5.978)、59倍(58.894)!到了改革后期,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教育对“农转非”的效应在初中程度已不复存在,在高中/中专程度的影响力大大降低,而在高等教育程度仍然明显存在,虽然已不同于前一阶段。总的态势是,数据结果有力地支持假设4。
教育程度对“农转非”的正向效应在各个时期是普遍存在的,这体现了教育程度对升学和就业机会的提升作用。与此同时,以教育为标准的筛选要求在改革后期有所提高,但教育程度对“农转非”的影响较改革初始阶段有所减弱。这种变化趋势透露出改革后两种制度力量的共同作用:一是户籍壁垒的日益松动,这使得教育程度作为一种户籍身份转换的限制条件的排斥性降低;二是高考政策恢复后,扩招政策带来的教育机会的扩散,国民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从而抬高了凭借教育的影响实现“农转非”的门槛。
5. 参军经历
参军经历对“农转非”的影响在不同转型阶段存在差异。改革前,参军经历并未提升“农转非”的机会(相对比率系数=1.357,统计不显著),说明1958年之后关于农村籍退役军人实行“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原籍安置原则*参见1958年5月3日《国务院关于处理义务兵退伍的暂行规定》。一直发挥作用。改革初期,参军经历大大提升“农转非”机会(相对比率系数=3.390,统计显著),反映了1984年后农村退役军人安置实行原籍安置与鼓励自谋职业的双原则效应*参见1987年12月13日《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与此同时,“自理粮落户集镇”等一系列户籍壁垒松动的政策也大大增加了户籍转换的机会,这种机会往往借助战友关系令参军经历发生效应。而到了改革后期,随着户籍政策整体上的进一步放松,在同等条件下,普通农村出身者也具有更大的机会跻身“农转非”队伍,参军经历不再具有排他性作用(相对比率系数=1.527,统计不显著)。
6. 其他变量
虽然表1显示改革前男性比女性有较多的“农转非”机会,而表2分析表明,这种性别优势事实上主要体现为男性具有较为优势的个人特征(主要是教育程度)。当个人特征和家庭背景一致的条件下,如表2中模型2显示,改革前和改革初期,女性的“农转非”机会大大高于男性,但是到了改革后期,男女的机会趋于平等。个人特征和家庭背景一致的条件下,中共党员的相对优势也发生在改革前,改革时代这种优势不复存在了。但是,无论改革前后,只要人们在组织化的某个单位工作,特别是国有部门工作,“农转非”的机会都大大高于自雇或其他形式的非组织化工作状态。
7. 改革前后“农转非”机制的差异
上述统计结果表明,“农转非”的微观影响机制,在户籍改革前后经历了从多重标准到能力主导的变化。改革前,再分配制度下的工业发展战略,对“农转非”人员的筛选机制是既包括政治出身,又兼顾父亲的职业背景,同时还依据教育程度的考察,这是特殊主义与能力主义相结合的多重筛选机制。特殊主义的核心是,再分配制度对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庇护:阶级出身好、工人的子代获得“农转非”的庇护。另一方面,再分配制度需要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的力量注入城市经济体,所以能力主义也是筛选原则之一:较高教育程度的人也获得较多“农转非”机会。改革后,特殊主义的庇护机制弱化或消除了,除参军经历在改革初期产生影响外,凭借阶级出身的“农转非”机会优势不复存在,工人的子代的优势也渐渐淡化至无;父亲职业地位、父亲教育程度的正向影响也在减弱,到了改革后期基本消失了。而个人教育的影响在改革后仍然持续,市场化大幅度推进后虽有回落,但筛选的门槛在增高。
同时,“农转非”的实现方式在改革后更加随机化、多元化,而不再集中于基于“选择性”因素的筛选。这从分析模型的已解方差可以窥见一斑:改革前为45%,改革初期为49%,到了改革后期下降到34%。这意味着,“农转非”渐渐倾向于通过家庭背景、个人特征等影响因素外的途径实现。户籍壁垒渐渐放松后,除了升学、参军等途径,自理粮落户、户籍购买、“村改居”等,都可以获得非农户口。如图1所示,基于选择性因素(升学、参军、招工、转干)实现“农转非”的群体比例持续下降,由最初的61.4%下降至34.0%,“农转非”群体更具异质性。综上,随着改革的推进,家庭背景的影响降低了,个人特征的影响在改革后期没有增加或者降低,而“农转非”的渠道日益多元化了,“农转非”的机会分布整体而言较改革前趋于平等化。

图1 “农转非”途径的时期变化
8. “农转非”机制差异下的不同职业分布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整体而言,改革后的“农转非”群体同改革前相比,不再是经历多重筛选的、相对均质的群体,出现了并非建立在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等微观个人特征选拔上的“农转非”人群。因此,如果说改革前的“农转非”在再分配力量的主导下带有一定“精英选拔”色彩的话(吴晓刚,2004,2007,2013),改革后出现的“农转非”群体其异质性更强。那么,这些人在“农转非”机制上的差异是否会在他们当下的职业获得上也有所反映*由于在此关注职业级别这一更能体现职业地位优势性的变量,而其在农村地区有关“工作经历”的调查中未涉及,所以本部分“农转非”群体来自城市地区。农村地区“农转非”样本比例仅为5.2%,故不纳入考察。职业级别方面,将处于行政级别序列的人员划分为行政管理类,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序列的人员划分为专业技术类。?换句话说,改革前的“农转非”群体较改革后的“农转非”群体而言,是否会由于再分配制度的庇护与工业化发展需求,更容易从事行政管理类或专业技术类(具有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优势性职业,抑或进入国有部门呢?表3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表3 不同“农转非”群体的职业类型、工作单位的分布(%)
表3显示,实现“农转非”的群体中,进入行政管理序列的比例改革前为8.6%,改革初期为3.0%,而转型深化期为1.5%。进入专业技术人员序列的比例,其趋势保持稳定、略有降低,各时期分别为4.3%、3.3%、3.5%。相应地,进入体力劳动者群体的比例逐步上升,各时期分别为87.1%、93.7%、95.0%。可见,在“农转非”群体异质性日益扩大的今天,相关人员进入行政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的比例降低,机会更多的是进入体力劳动者的行列。另外,进入国有部门的比例改革前是63.7%,改革初期是46.2%,改革后期是36.9%,直线下降。与此同时,进入非国有部门和自雇群体的比例相应地大大上升。
五、总结与讨论
通过分时期考察,本文探讨了家庭背景、个人资质等微观因素在不同时期对“农转非”的影响变化,并分析了不同“农转非”群体职业路径的时期变化。研究发现,改革前后,“农转非”机制呈现由特殊主义、能力主义相结合的混合筛选模式向能力主义主导、途径更加多元、机会更加均等的模式转变。“农转非”人员所进入的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改革后也更多地是体制外体力劳动群体,而较少进入管理层和专业技术层。这些结果表明,再分配力量干预下的“农转非”机制更具排斥性,而改革开放的进程使“农转非”越来越具有随机性了。这些变化反映了转型过程中身份转移、地位分化的内在逻辑伴随制度变迁正在发生趋于机会平等的变化。
从微观机制的时代变迁可以看到,改革前后的“农转非”人员事实上是两种不同的群体。改革前,“农转非”筛选严格,国家依据政权建设和工业化、城镇化的需求,在农村地区相应的筛选政治忠诚、有文化知识、有专业技术的农民出身人员,给予其非农身份。这一群体比较容易融入城市社会,相当一部分又是进入国有部门,进入管理和专业技术阶层这些优势职业,所以社会治理的负担较小。改革后,“农转非”人员异质性迅速增强,大多数是在非选拔性的过程中进入非国有部门或处于自雇、无业状态,所处职业阶层相对较低,非组织化程度很高,个体的现代性水平较低,融入城市社会较困难,社会治理的成本很大。这些人员在身份转换之后,还需要实现技能转换、理念转换、行为转换、生活方式转换,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这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社会治理的重大课题。
本研究预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一些问题。首先,有关“农转非”机制的时期变迁的影响。我们主要考察了职业分布和体制分布,类别很粗,同时许多变量都需要进入研究范围,如工资收入、工作小时、医疗保险、福利水平、子女就学状况等,都是反映“农转非”真实情况的方面。其次,未来研究者需要更加细致地考察不同城市等级的非农户口的获得机制及其变迁。我国的社会分层体系的重大特征是城市分层,工作机会、发展机会、生命意义、快乐程度、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子女教育和成长条件等等,都受城市地位的结构制约。北、上、广、深是一线城市,各省会是二线城市,其他百万人口的城市是三线,地级市是四线,县级市是五线,中小城镇是居于乡村之上的底线;非农户口的获得机会与这个城市分层体系是负相关的。这一负相关的现实状态及其社会意义,需要从时代变迁的视角去考察。
[参 考 文 献]
白威廉.中国的平均化现象.边燕杰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北京:三联书店,2002:42—82.
怀默霆.中国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层.边燕杰 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北京:三联书店,2002:3—41.
李春玲. 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之比较. 社会学研究,2006,(5):85—106.
李春玲. 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 中国社会科学,2003,(3):86—98.
李路路.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理论与问题. 江苏社会科学,2002a,(2):7—12.
李路路. 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 中国社会科学,2002b,(6):105—118.
李强. 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 社会学研究,1997,(4):32—41.
李强. 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 社会学研究,1999,(3):93—101.
林南,边燕杰.中国城市中的就业与地位获得过程.边燕杰 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北京:三联书店,2002:83—115.
林易. “凤凰男”能飞多高 中国农转非男性的晋升之路. 社会,2010,(1):88—108.
刘精明. 向非农职业流动:农民生活史的一项研究. 社会学研究,2001,(6):1—18.
陆益龙. 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结构与变迁.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123—130.
陆益龙. 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 中国社会科学,2008,(1):149—162.
马福云.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
倪志伟.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由再分配到市场.边燕杰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北京:三联书店,2002:183—216.
孙明. 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1950—2003). 社会,2011,(5):48—69.
汪建华. 参军:制度变迁下的社会分层与个体选择性流动. 社会,2011,(3):138—154.
王海光.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形成与沿革的宏观分析. 中共党史研究,2003,(4):22—29.
王美艳,蔡昉. 户籍制度改革的历程与展望. 广东社会科学,2008,(6):19—26.
魏昂德.职位流动与政治秩序.边燕杰 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北京:三联书店,2002:145—180.
吴晓刚. 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 社会学研究,2007,(6):38—65.
吴愈晓. 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 社会学研究,2010,(2):125—150.
肖季文,朱鹏. 新中国60年兵役制度的调整改革与发展趋势. 军事历史,2009,(4):6—10.
姚秀兰. 论中国户籍制度的演变与改革. 法学,2004,(5):45—54.
郑冰岛,吴晓刚. 户口、“农转非”与中国城市居民中的收入不平等. 社会学研究,2013,(1):160—181.
郑辉,李路路. 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 社会学研究,2009,(6):65—86.
Bian, Y., X.L. Shu, J. R. Logan.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and Regime Dynamics in China. Social Forces,2001,79(3):805—841.
Bian, Y.,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2,28:91—116.
Blau, P.M., O. D.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New York: Wiley,1967.
Chan, K.W. Post-Mao China: A Two-class urban society in the ma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6,20(1):134-150.
Chan, K. W., L. Zhang. The Hukou system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Processes and changes. China Quarterly,1999(160):818—855.
Cheng, T.J., M. Selden.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China Quarterly,1994(139):644—668.
Fan, Cindy. The Elite, the Natives, and the Outsiders: Migration and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in Urban Chin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2, 92(1):103—124.
Logan, J.R., Y.P. Fang, Z.X. Zhang. Access to Housing in Urba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9,33(4):914—935.
Wu, X.G., D. J. Treima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1955—1996. Demography,2004,41(2):363—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