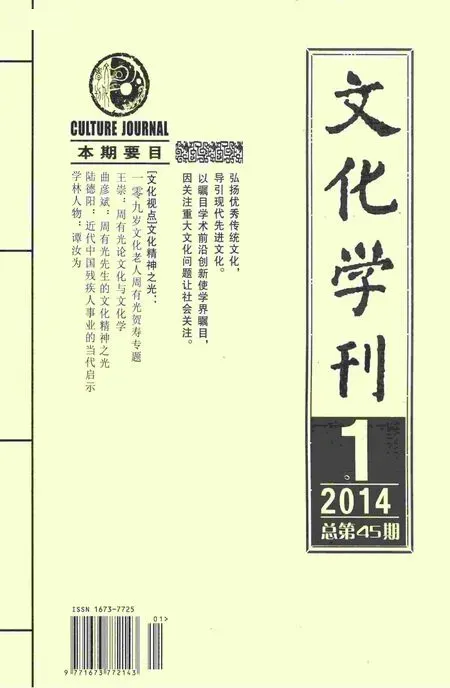从底层精神到底层娱乐精神——赵本山系列农村题材电视剧的走向特点
何 杨 董丽娟
(大连海洋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3;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1)
一
赵本山主演或制作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以下简称“赵氏农村剧”),如《刘老根》《马大帅》和《乡村爱情》。赵氏农村剧大多以喜剧的方式展开农民、农村的生活景象,所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来源于生活底层,要么是普普通通的农民,要么是进城务工人员;故事情节线索由生活中面临或可能遇到的种种琐屑小事连缀而成。以底层农民人物形象、农民生活为表达内容,用最朴实的语言、最生活化的方式展现东北农村、农民的喜乐人生,从形式和内容上鲜明表现东北地域文化特点,这是赵氏农村剧一贯的美学风格。
赵氏农村剧多次登陆央视黄金档,且一次次打破电视剧收视率的记录,其在电视剧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不言而喻。成功之处在于:它相当真实地还原了底层生活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并突显了底层素朴的情感和人生理想,用底层意识来对抗长久以来占据荧屏的现代化和都市化的电视剧创作风气;同时,它又与国家在文艺政策主导方向上保持一致——这是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王孝坤在《中国现实文化选择与发展状况的隐喻——赵本山影视文化现象的文化诗学解读与思考》一文中指出:“尽管对赵本山的评价其说不一,但都不否认赵本山影视形象在目前中国现实文化语境中是成功的。他成功的奥秘在哪里?我认为他成功的奥秘主要是以大众文化认同的文学修辞策略言说主导文化话语。这种用通俗的大众化的‘瓶’装主导文化的‘酒’的文学修辞策略,适应了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的文化市场需求,既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不同层面的大众文化消费口味,又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1]
二
本文所讨论的赵氏农村剧主要是指《刘老根》《马大帅》和《乡村爱情》三个系列电视剧。《刘老根》主要讲述一个被选举“选下来”的农村基层干部刘老根通过引进外来投资创办旅游产业而引领农民致富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形象。《马大帅》主要讲述一个普通农民马大帅进城寻女滞留城市,后利用偶然获得一笔巨额遗产开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帮助生活在城市底层的进城务工人员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善良、正直、乐于助人又有点儿狡猾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形象。《乡村爱情》则展现了一幅东北农村宁静优美又富有生活气息的画卷,包含了以王谢、刘赵等几家为主的情感纠葛,以及年轻人在家乡实业致富的故事,塑造了一批鲜活的新农村中的小人物形象。
上述三个系列电视剧,在摹写现实生活方面,完成了从底层精神到底层娱乐精神的转变。
刘老根并不完全是一个“底层”百姓,他曾经的身份是一个“村官”,因而这个人物身上不可避免的带有具有主流意识形态色彩,但另一方面,刘身上也具有倔强的反对城市文明和现代商业的精神,在企业开办过程中与现代资本和基层官僚主义矛盾重重并屡屡受挫。就其现实主义表达的倾向上来看,保守的农村现状和必需进行的改革和发展是一对主要矛盾。刘在投资人韩冰的资助下建立温泉旅游疗养度假村这一新兴产业,无论是从“国”还是“村”抑或“家”的角度上来看,这种具有超前意识的生存自救之路,是主流意识形态与市场的共同需要,然而,外来资本与民间、土地的融合,并不能做到没有“排异”反应。在《乡村爱情》中,赵本山饰演的王大拿给象牙山注资的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类似问题。民间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在21世纪前,多体现为民间对现代性的排斥;而进入21世纪之后,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愈来愈表现为共生甚或现代性压倒民间文化。《刘老根》剧用幽默且现实的方式展开了乡土与现代性的碰撞。在建立了“华西村”式的家族企业后,刘先后面对商业运转、权力膨胀、人事管理、对外联系及扩大经营等多方面的问题,且这些不是靠个人品德或资本援助就能解决的问题。在剧中,每个人都面临现代性转型的困惑:丁香自诩当上老总夫人并东施效颦般的改变外表服饰,热衷于虚荣的权力之争;药匣子卖弄才学,力图用故弄玄虚的理论来维护其在山庄的地位;冯乡长、胡科等乡霸职权滥用、胡作非为等。片尾,刘虽拼劲全力致力于改变作为整体的故乡的生存状态,但在不能对权力收放自如的控制和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中导致巨额财产被骗。大团圆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式的结局必然需要挽回损失,但刘老根及其家长企业管理者最终认识到,若要真正改变乡土蒙昧的精神面貌和匮乏的物质基础,仅仅依靠经济投入不能解决问题,更要靠现代化的知识和技术——顾晓红作为先进文化管理者的形象出现在龙泉山庄,就是乡土对现代性的接纳,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顾所代表的凤舞山庄与刘所代表的龙泉山庄是竞争伙伴关系,她能毅然决然的放弃凤舞山庄的利益回报,选择揭露胡言、胡科的罪恶行径,也暗喻着现代都市对乡村精神家园的皈依。
相比之下,马大帅、范德彪这种形象更符合城市底层身份,是离开土地到城市求生存者的形象。马的女儿小翠被村干部逼婚后出逃,这说明他们在家乡已经没有退避的空间,殊不知城市也不会大度包容没有选择的闯入者。马到城市寻女,一出火车站就遇到生存和身份问题——穿个破棉袄、宿火车站、伪装成盲人卖唱,这是底层外来务工者在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初入城市的相当生活化的、真实的写照。之后的玉芬重病无钱医治、马开办打工者子弟学校屡屡受骗受欺,这也是对生活相当真实的还原。由经济带来的苦难和困顿,是底层首要解决的问题——生存问题;紧随其后的,就是要解决融入城市后所面对的各种精神困惑。《马大帅》2以马大帅艰苦办学为中心,他被塑造成为一个清教徒般的创业者、一个大公无私的领导者、一个在道德上几乎完美无缺并且极富社会责任心的男人:他为了办学历尽坎坷,不断克服诸如资金短缺、师资匮乏等等困难;由于忙于办学,他一再推迟婚期;为了支付教师工资,他甚至不惜变卖家具、房产。[2]而他做出这一切善举的动机,并非为了赚钱,而仅仅是出于责任心、同情心和善意——为了给那些无力负担普通学校学费的打工子弟一个接受教育的机会。暂且不论人物形象塑造的得失,创作者希望用“无私利他”的至善行为来唤起人们对底层救赎的渴望和希望,在交织着日常伦理和道德伦理的生活空间中,找到一个可依托、有担当的肩膀,这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延续的精神力量——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份真诚的表达难能可贵。赵本山在现实中对故乡的回报即是基于此。面对生存困境时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重情重义的精神品格、为他人不惜牺牲自身利益的无私精神,这些都丰富了我们对底层的认识,也通过这一“观看”被感染着。因而,我们可以在这一处看到赵氏农村剧的最大的亮色:许多文学和电影艺术的“底层叙事”往往是从启蒙的精英视角来挖掘群体的麻木、愚昧、落后、自私;但在现实生活中,每个阶层都有自己内在的情感、智慧和追求,这种书写并不违背生活逻辑。真正的底层是什么样?答案未必唯一。我们得承认赵氏农村剧是其中的一种解读方式。[3]
如果说《刘》和《马》系列在喜剧中饱含了对现实困窘的忧患,那么到了《乡》系列,则渐渐走上了将底层生存关注转移到底层娱乐精神的道路上来。这里的乡村印象是山清水秀、没有生存危机、不涉及俗世纷扰的宁静之所,是理想主义者和家长理短、鸡毛蒜皮的集合体。曾庆瑞教授曾批评赵本山是“伪现实主义者”,恐怕也是基于此——剧作所展现的乡村生活未能涉及深层次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困境。其实赵本山对这一点并非毫无认知,在2004年一个研讨会上,他坦言:“《刘老根》不好再拍了,因为刘老根是农民企业家,再往前走越走越大,而越大就越不好看,越大就会越离开土地。马大帅整了个学校,但不行后他还得回到土地上来,就是不能让他得好。你想让他好但他没有好,这才有戏看。”不难看出,无论是出于艺术观点、现实观点还是商业准则,赵本山本人对乡土的感情是深沉而真诚的。可脱离了生存不能承受之重的《乡》系列收视率屡创新高的时候,研究者不得不正视赵氏农村剧利用喜剧和并不高雅的幽默给观众带来快乐的现实。电视剧艺术不同于文学、电影以及音乐、绘画等艺术方式,它自产生就带有娱乐和文化的双重烙印。而东北的文化血液中,带有着其他地域所无法理解的幽默、乐观基因。东北气候寒冷,冬季较长,一进入冬天就是农闲。严寒中最幸福的事儿就是“猫冬儿”——室外霜天雪地,室内暖意融融,家人、朋友弄个火盆围坐一堆,唱唱“二人转”,讲故事、说俏皮话、斗斗智,哈哈一笑,各种情绪、情感就都得到了宣泄。东北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属于北方特有的文化——无论多艰难的环境和自然气候条件,在生存意志中都被转化为乐观豁达的情绪;辽北语言充满了生动、鲜活的因子,生命力非常旺盛;再加上,东北人性格开朗、率直,形成东北文化土层里特有的幽默感。[4]这种幽默渗透到生活中、代代相传的骨子中,变成了一种文化,一种生存意识和生存状态,即苦中作乐的坚韧性。因而,赵氏农村剧的幽默是一种地域文化的独特表现,而这种文化特征又极易与娱乐合拍。《乡》中存在的爱而不能结合的痛苦、创业屡屡失败的艰难、年轻人对追求的迷茫等具有可深化的矛盾被片中经常刻意展现的宁静的河水和悠扬的音乐消解掉。这种日常生活流的美学追求,就是要将所有琐屑的生活内容均匀的洒在生活的每一处。不过不可否认,在《乡》系列随后的续集中,过多追求娱乐效应、夸大生理缺陷和粗鄙的搞笑方式这样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自然易被人诟病。
三
无论怎样娱乐,赵氏农村剧自始至终守护着比较恒一的价值信念,那就是无论是困境还是顺境、悲还是喜,都怀揣着一种理想的伦理道德,用“好人”“善”这样的道德主体、道德行为来化解矛盾、消除灾难,从而让小人物、底层在生活中保持一种比较稳定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赵氏农村剧所体现出来的底层意识,是温情、柔软、不冲突、不激烈的。
从《刘老根》和《马大帅》中的主要人物设置和人物性格来看,两部剧中的正反面人物可以大致做出平行排列 (见表1):
刘老根和马大帅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最普通的百姓、农民,无权无势,也没有英俊硬朗的外形,超人的智慧和才学;有的是长年累月农田耕种带给他们的满面风霜,有的是坎坷生活教给他们的生存智慧,有的是打不垮的不服输的精神。刘和马都是鳏居带着儿女,但他们的感情生活也并非空白,都有勤劳、朴实并愿意为其默默付出的女人在后面支撑着他们的心灵和精神世界:丁香和玉芬,她们的生活遭遇不太顺利,但也不影响她们痴长而执着的等待和付出;药匣子和范德彪都是稍有一技之长但又眼高手低的那种人,有最淳朴的善良,乐于助人,但因为爱吹吹牛,显摆一下自己的能耐,所以总惹点儿小祸,让别人帮着收拾残局。在这两部剧中,都有个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虽然称不上主角,但却是故事得以发展的非常重要的线索——没有韩冰的投资,就没有刘老根的龙泉山庄;没有李萍的鼎力支持,马大帅的打工子弟学校出现的诸多问题难以解决。另外,反面人物也是按照传统“坏人”的模式来塑造的,冯乡长、胡科、王彬、老疤、牛二,是依仗权势的泼皮无赖,道德品质底下,为谋私利激起众怒,最后会得到应有的下场。

表1
在这一结构上的重复和复制,也是赵氏农村剧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批判者眼中,赵氏农村剧在“苦难”主题上只是表达了其表面含义,这是一种未能与残酷的现实生活接轨的理想状态,是人们对公平正义、善恶等伦理行为期待和渴望,而未能深刻、立体地表现出生活所包含的各个方面。
中国文学有关心民生疾苦的传统。古人评价杜甫是“饥寒而悯人饥寒”,白居易是“饱暖而悯人饥寒”。赵氏农村剧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农民复杂的现状、心态,但也要看到他在商业利益与过度追求娱乐和喜剧形式中的迷失。我们期待赵氏能够逾越结构和人物的鸿沟,推陈出新,制作出更多更好的解释现实的农村题材影视剧。
[1]王孝坤.中国现实文化选择与发展状况的隐喻——赵本山影视文化现象的文化诗学解读与思考[J].剧作家,2005,(2):71 -75.
[2]苏涛.马大帅:农村题材的话语转型[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3):38 -43.
[3]李云雷.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底层叙事[J].艺术评论,2008,(3):43 -47.
[4]解读赵本山[EB/OL].http://chinaneast.xinhuanet.com/content_3116922.htm.2004 - 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