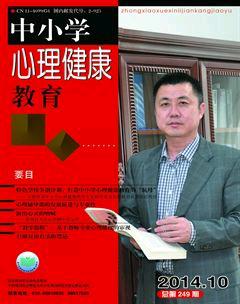“教学恐惧”:基于教师专业心理维度的审视
孙贞锴
〔关键词〕教学恐惧;教学勇气;专业自信;推门听课
一、问题的提出:“教学恐惧”为哪般
帕尔默在《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中提出了这样一种核心观点:很多教师的教学常常处于一种“心灵失落”的状态,优秀的教学源自教师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完善,教师应该找回自己失落的心灵,重新鼓起“教学勇气”,以此融入到自己的专业生活中。书中谈到:
“如果一项工作是我们内心真正想做的,尽管连日辛劳,困难重重,我们仍然乐此不疲,甚至这些艰难的日子最终也会使我的生活充实快乐,因为这是我真正倾心的工作,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正好帮助我成长。
“教师的内心不是良心的呼唤,而是自身认同和自身完整的呐喊。
“那些内心世界长期被忽视的教师,拼命想得到我们对其心声的倾听……其实,只要我们稍微给自己内心声音一些注意和尊重,它就会以一种更温柔的方式回应。
“我们要关照教师内心,使其不会僵化,对深层的自我待之如友,培养一种自身认同和自我完整的意识。
“除了等待,我们还有另一种选择:我们可以找回对改变工作和生活的内部力量的信念。”
帕尔默论述的实质,在于强调“心灵才是干好所有工作的源泉”,树立“教学勇气”,重建“专业信念”,教师才会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专业幸福。 在我看来,其实质可以归结为一种教师必须具备的“专业心理品质”。古希腊有句名谚:“没有心灵去支使,纵有知识又何用?”所以,仅从外部世界、一般层面去改善教师心理状态远远不够,还必须同时从挖掘、激发教师的内部潜能入手,增强其作为“专业工作者”的内在动力,才能使“教师心理”真正趋向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书中与“教学勇气”相对的一个词语是“教学恐惧”,帕尔默谈到:“我虽然教了三十多年学,至今仍感到恐惧无处不在。走进教室,恐惧在那里;我问个问题,而我的学生像石头一样保持沉默——恐惧在那里;每当我感到似乎失控,诸如给难题难住,出现非理性冲突,或上课时因为我自己不得要领而把学生弄糊涂,恐惧又在那里。当一节上得糟糕的课出现一个顺利结局时,在它结束很长时间内我还恐惧——恐惧我不仅是一个水平低的教师,还是一个糟糕的人……据我的经验,学生也是害怕的:害怕失败,害怕不懂,害怕被拖进他满想回避的问题中,害怕暴露他们的无知或者他们的偏见受到挑战,害怕在同学面前显得自己愚蠢。”最后他特别指出,当学生的恐惧和教师的恐惧混在一起时,恐惧就以几何级数递增,这样教学就瘫痪了。
帕尔默谈到的这种感受,实际上很多教师,包括像他一样有着长时间教龄和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也多少会有。但是,对于这种普遍存在的“教学恐惧”,很少有人像帕尔默一样去作这样的反思。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教学恐惧”又是怎样的情况?
二、“教学恐惧”的背后:两个“推门听课”经典案例的对比解读
帕尔默讲的是自己上课获得的体悟,他所谈及的课堂现场除了自己和学生,并没有“第三人”。没有“第三人”出现的课堂上,有三十多年教学经历的老教师尚有如是感受,那么,出现“第三人”,而上课人本身还不是老教师、教学经验还谈不上成熟老到的教师——又会处在一种什么状态?这里所说的“第三人”,就是外来听课者、课堂观察者。
这里,以大家熟知的“推门听课”作一下具体分析。
在长期的观察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很多教师,一听到别人要来听自己的课,常常表现得不太欢迎甚至有抵触情绪,“推门听课”就更不用说了。归结为一点,害怕、不愿意别人来听课(当然这里的“害怕”是概括性说法,实际情况比较
复杂)。
对于这种现象,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教师素质、道德问题,或者由此推测教师平常上课有问题,或对领导、同事的态度有问题。按照这个逻辑,帕尔默也是如此了。为什么?他在没有人来听评课、守着自己的学生而且有30多年教龄的情况下尚且“怕”,如果一下子有很多领导、教师“闯”进他的课堂,他是不是更“怕”了呢?
在中国大陆,“推门听课”这种提法及其宣传推广至多是近三十年的事情。其实,早在民国时期的“视学”中它就已存在了。从金克木先生所撰《化尘残影(五则)》一文“视学”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略知一二(参见商友敬主编《过去的教师》第33~35页)。尽管是对旧时代的回忆,我们却也能够从中多少感到“推门听课”对教师及其教学产生的心理影响。请看这个故事:
将近六十年前,一位朋友受聘去当县立初级中学的教务主任。承他不弃,约我去教国文以免饿死街头。
糊里糊涂教到学期中间,忽有一天课堂的靠学生后面另一扇门开了,进来三个人。一个是很少光顾的校长,一个是矮胖子,两人后面跟着我那位朋友。我当时正向学生提问,照例找的是我估计好没学会的学生。他站在那里疙疙瘩瘩回答不好。我让他站着想,又叫起另一个程度差的学生,当然不会比前一个好。有的学生已回头去观望来客了,我还未注意,又想问第三个。忽然惊醒,有参观的人,不能再展示坏学生。赶忙叫他们都坐下,我自己解答,我没说几句,那三位不速之客已经不辞而别了。
后来我那朋友笑着告诉我,他和校长陪同来的是县教育局的视学员。他听课后给我的批评是四个字:不会教书。我一听,猛然觉得一只饭碗掉下来打碎了。朋友笑着叫我不要在意,不会有什么的。可是我仍然有点忐忑不安。
又过些时,我把这事差不多忘了,没想到旧戏重演。有一次我上课一多半,远处那扇门又开了,又进来三个人。原班人马只换了一个,矮胖子变成穿西服的高瘦子。当时我正在讲朱自清或是别的名家的一篇短文,是补充课文。我既未提问,也没有讲解难字难句段落大意,只是在自问自答:这段文为什么要这么讲?换个讲法行不行?为什么接下去一段又那样讲?能不能改头换面颠来倒去?这个词,这个句子,若不用,换个什么?比原来的好还是不好?为什么?我边讲边举例,滔滔不绝。学生都不看书,只望着我,也不管有没有外人,我忽然想起,又来了客人,莫非又是来视察我的吧?连忙打断,改讲课文。客人一听我讲的告一段落,转身出门。随后不久下课铃就响了。
后来教务主任朋友对我说,那是省里的视学员来检查学校教学。我一听,心中的饭碗顿时成为碎片。
朋友问:“你猜他给你的评语是什么?”说着大笑起来。我没法回答,该不会是立即革职吧?
“这位省视学听你讲课居然迷上了。一直听下去顾不得走,听完出门就下课了,还有一个班也不去听了。中午县里大家陪他吃饭时,他还发挥一遍,说是从省里出来到过几个县,这次才听到了新鲜课,这样讲才能吸引学生。”
“你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
“哪里的话?那位视学员还想问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我只说是我的朋友,给蒙混过去了。你的名字也没告诉他,所以在座的县视学员也不知道说的是你。”
我到底是会教书还是不会教书呢?
这个故事很值得咂摸,作者当年是刚刚工作的临时“代课教师”,为了保饭碗,他对外来的“推门听课”自然怀有一种“恐惧”。他的这个案例和帕尔默的案例似乎恰好又能对照起来:帕尔默是从教三十多年、工作稳定的老教师,没有外来的“推门听课”,竟然也怀有一种“恐惧”。(帕尔默谈及的“恐惧”对象也包括了学生,这一点我们要注意。)那么,现在对于很多教师来说,工作相对稳定,教学经验日渐丰富,为什么面对外来听课仍然时常有一种 “教学恐惧”呢?
在我看来,对于“推门听课”中教师的这种反应必须从教师心理的角度加以考察,才能有更好的结论。否则,就不能对以上疑问作出确切而有说服力的回答。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麦考特的《教书匠》中生动地描述了一次典型的美国版“推门听课”及其对当事人产生的心理影响
当麦考特发现学生伪造的假条富有文采,正给学生上着“世上第一堂研究假条的课”时,校长和区教育局长闯进了他的视线,一位学生提醒他:“校长在门口。”
我的心猛地一沉。
校长陪着斯塔滕岛区教育局长马丁·沃尔夫森走进教室……他们沿过道走来走去,凝视学生的文章。为了看得更仔细些,他们拿起了一些,局长让校长看了其中的一篇。局长皱了皱眉头,撅了撅嘴。校长撅了撅嘴。全班同学都知道这些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为了表示忠诚和团结,他们强忍着不向我要出入证。
在他们离开教室的路上,校长冲我皱了皱眉头,小声说局长无论如何都要在下节课见我。我知道,我知道。我又做错什么了。愚蠢酿成大乱,可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档案里将会有一条不良记录。你抓住时机,尝试了整个世界历史上从来没人做过的事。你让你的学生们充满激情地忙着写假条。但是现在报应来了。
校长坐在办公桌旁。局长在屋子中间站立的姿势让我想起了忏悔的高中生。
啊,迈……迈……迈考特。进来,进来,就一分钟。我只是想告诉你,那节课、那个计划——不论你到底在那儿做什么——都是一流的,一流的!年轻人,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脚踏实地的教学。那些孩子的写作达到了大学水平。
他转身面对校长说:那个孩子为犹大写了个假条,很有才气。但是我有一两条保留意见。我不知道为恶人和罪犯写假条是否正当或明智,但转念一想,律师干的就是那个,是不是?根据我在你班上所见到的情况,你可能会在这儿培养一些有前途的未来律师。因此,我只是想和你握握手,告诉你:如果你的档案里出现一封证明你的教学充满活力并富有想象力的信件,请不要感到吃惊。谢谢你。也许你应该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历史上年代较为久远的人物身上,为阿尔·卡彭写假条有点冒险。再次谢谢你。
天哪!来自斯塔滕岛区教育局长的高度赞扬!我是应该沿着楼道跳舞,还是应该高兴得飞起来?如果我放声高歌,这个世界会反对吗?
我决定放声高歌。第二天,我对班上学生说我知道一首他们喜欢的歌,一首绕口令似的歌。
……我们一段接着一段地唱。
此后的麦考特,更加注重针对学生特点改进课程,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从本例中不难看出,面对“推门”式的听课,教师本身必然会有紧张感,但在获得及时、恰当的评价反馈特别是受到鼓励、肯定时(如教育局长评价麦考特时商讨式的言辞,可谓别有意蕴、富有民主气息而非武断地拔高或贬斥,更不是居高临下、似懂非懂、不着边际的“指点”),其自我效能感增强,随之获得愉悦的沉浸体验,“教学勇气”由此倍增,教学状态和师生关系亦得以改善。
这启示教育管理者:要想使“推门听课”切实发挥提高课堂效益、促进教师发展的目的,对“推门听课”之实施目的、价值定位和实践取向有必要作出审视和改进。
三、激发和培育积极专业心态:应对“教学恐惧”之本
不难发现,帕尔默揭示的“教学恐惧”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教学心理表征,是广泛存在于教师中间的一种常态因素,而“推门课”中很多教师的“害怕”反应也是一种普遍的无可苛责的现象。
所以,面对“推门”,教师的“害怕”“不愿意”等种种表现,属于一种正常反应,不忧虑反而不正常。教师都想尽量把课讲得好些,别人来听自己的课时更是如此,为此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紧张,这很正常。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教师外在表现上的怕不怕,而在于教师在“久经考验”后到底怎么认识、把握和处理这种既来自于群体也生根于个体之中的“教学恐惧”心理,教学管理者又该如何有针对地认识和处理这种“恐惧心理”,从而使其为促进教师发展、重建教学勇气、找回专业自信起到推动而不是阻碍作用。
虽然“教学恐惧”是一种常态心理因素,但是,绝不能把这种“常态”发展成一种自我的“病态”,而是要把它发展成一种健康的积极的因素。“如果我们懂得怎样去破解恐惧,许多恐惧就能帮助我们生存,甚至帮助我们学习和成长”,我们需要的是那种“对真正的学习有所感悟、有所触动的恐惧”,而不是那种“自我封闭、无动于衷的恐惧”。
令人欣喜的是,更多的教师把这种原始的恐惧心理转化成了激励自己认真备课、上好课的动力,因而面对“推门听课”,他们和学生常常会有更大的收获。在“害怕”的背后,他们并不害怕暴露问题,害怕的是自己的课还是和从前一样没有进步,因而在平常比较注意向他人学习,反思和改进自己的教学活动。克服教学恐惧,重建教学勇气,找回专业自信,这是很多教师正确应对“推门听课”所获得的成长与进步。
有的教师消极对待“推门听课”,把别人的听课假想成一种不怀好意,以一种平静的对抗态度来应对,例如,你来听课我就专门做练习,导致听课人很尴尬。这种教师,即使平常上课不错,但可以想见其后续的成长状态。
有的教师表现得很紧张,小心翼翼,唯恐讲不好,让人看出破绽,损坏自我形象。因为比较关切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所以能够认真对待。但其主要目的就是应付过关,更看重的是一时的应付,并不注重持续地规划、思考和建构常态教学。实际上,他们的“教学恐惧”并不是一种“有所感悟、有所触动”的恐惧。说到底还是帕尔默说的那种“自我封闭的恐惧”,在这种恐惧之下,教师并不注重主动自觉地和别人进行沟通、交流,也缺乏有效的学习、反思。
还有些教师表现出无所谓:你来听就听,不来更好,来不来我都那样;你怎么评价我不在乎,随你便,你听课对我来说有没有都一样。这是一种以表面的“无所谓”折射内心“教学恐惧”的特殊表现。这种心理,其实还是帕尔默所说的“自我封闭、无动于衷的恐惧”,或者说是从一开始的恐惧走向无所顾忌的“无所谓”,这些教师不求发展,不要求“成长”“进步”,也谈不上真正的学习和反思。
综上所述,对“推门听课”中教师的反应必须从教师专业心理角度加以考察,否则,很多问题就会简单化。美国著名教育学者安奈特·L·布鲁肖曾说:“教书是一项艰辛的工作,有时候精疲力竭,难免就会偷偷懒,省省事,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一定要克服这种懒惰的想法。”一位支持“推门听课”的校长也坦言:“在任何一所学校,绝大部分优秀教师并不需要非常严格的‘他律,他们始终坚持着比较认真积极的工作态度。”所以,“偷懒”虽是人之常情,但很少会成为广大教师的个体常态和群体常态,它的存在只能说明学校管理存在问题。可见,必须从把握教师心理出发采取具体措施,努力把教师的紧张感转化、催生成持久健康的动力,而不是变成“常态的病态”或“病态的常态”。
有的学校改进听评课制度,推行“主动邀请课”“对比研究课”“课例展示课”等多元结合的听课体系,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经常主动邀请校领导或者同事来听课指导,以此提高教学水平。
总之,教师应树立正确认识,从“推门听课”中锻炼和培育积极的专业心态,如此,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成长和进步。
(作者单位:山东省烟台市实验中学,烟台,265500)
编辑 / 黄才玲 终校 / 于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