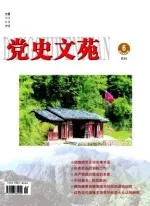百年中国大师恩怨录
■程丕来
章太炎的举动与打扮十分离奇。他经常穿长袍,外面罩上和服,头发留五寸许,左右两股分开梳理,下垂额际,不古不今,不中不西。蒋维乔 (清末至民国时期气功学家)曾与他同住一屋。一天,蒋维乔看见章太炎有一张写给汪允宗 (曾与于右任等人创办上海 《神州日报》)的纸条: “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蒋维乔笑着对章太炎说: “既已向人借钱,曷勿多借几元?”章太炎则回答: “此君只有两元之交情。”
章太炎的弟子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他在北京住在吴承仕 (亦为章的弟子)的一所房子中。本来挺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吴承仕叫他搬家。黄侃在搬家的时候,爬到房子的梁上写了一行大字: “天下第一凶宅”。
有一段时间刘师培失业在家,黄侃向蔡元培推荐他到北大任教。蔡元培以刘师培曾经依附过袁世凯不肯聘任,黄侃坚持说: “学校聘其讲学,非聘其论政。何嫌何疑?”最终蔡元培接受了黄侃的意见。
谭鑫培的戏风靡北京,各大学多有谭迷。一天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的 《秦琼卖马》,胡适插话:“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都静听高论,无人说话。只有黄侃立身而起,道: “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1985年11月,宗璞曾经打电话邀请梁漱溟出席她父亲冯友兰的寿宴,谁知道作为老友的梁漱溟一口回绝,在给冯友兰的信上连冯友兰的姓名都不愿写,即无上款。信中直言: “尊处来电话邀晤,我断然拒绝者,实以足下曾谄媚江青。”
齐白石家里人口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他亲自量,用的是一个香烟罐头 (盒)。 “一下、两下、三下……行了!”——“再添一点,再添一点!”——“吃那么多呀!”有朋友曾提出把齐白石接出来住,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再操心这样的家庭琐事了。老舍知道了,拦住了说: “别!他这么着惯了。不叫他干这些,他就活不成了。”
艾青多次陪外宾去访问齐白石。有一次,齐白石很不高兴,艾青问他为什么,他说外宾看了他的画没有称赞他。艾青说: “他称赞了,你听不懂。”齐白石说: “我要的是外宾伸出大拇指来。”
五四前不久的一天,陈独秀在朋友家里,看到了沈尹默写的一首五言古诗,便问沈尹默何许人。第三天,陈独秀到沈尹默的寓所拜访,一进门,就大声说: “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 (刘三原名刘季平,为当时颇有名望的文人,与陈独秀友善)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沈尹默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从此就更加发奋钻研书法。
1914年,康有为作了著名的《物质救国论》一文,正好撞在辜鸿铭对 “中体西用论”所惯持批评的枪口上。据胡适记述说,辜鸿铭同他谈起孔教会时,曾大骂 “陈焕章当读着 ‘陈混仗’”,又骂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根本不懂孔子,连拜孔子的资格也不配有: “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注:1912年10月7日,康有为授意其学生陈焕章等在上海成立 “孔教会”,以 “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实则是反对革命,力图复辟清室。并希望其成为“国教”——一个宗教实体,把孔子作为中国儒教的教主,以对应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天主教等。)
老舍在北京教育会做文书时,同时在第一中学兼任两小时国语,每月收入四十几元。除奉母自瞻以外,还要到燕京大学去念书。但他艰苦挣扎,谢绝各方的引诱。一天晚上,罗常培去教育会会所看他,老舍含泪告诉他: “昨天把皮袍卖掉,给老母亲添制寒衣和米面了。”罗常培说: “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还拿得出这几个钱。何必在三九天自己受冻?”老舍答道: “不!冷风更吹硬了我的骨头!希望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
1934年的一天,山东大学请老舍作学术报告。老舍讲到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时,说: “一般文艺作品中的坏人形象大都是脑满肠肥、一脸横肉的大胖子。”第二星期的学术报告,走上讲台的是一个比较粗大的白胖子,西装革履,举止稳重,看来颇有几分洋绅士派头。这就是山大外文系的系主任梁实秋。他针对老舍上周所讲的坏人形象问题,振振有词地说: “就我个人所知,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坏人都是些瘦子,脖子细得像猴儿子一样……”
1956年北京金秋的一个下午,阳光灿烂,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见了一批作家和文艺家,老舍在座。老舍在会上谈到自己想到新疆石河子军垦农场去住些日子。周总理表示异议,老舍年纪大些,边疆地区条件比较艰苦,怕他不适应。周总理感觉自己打断了老舍的话,表示歉意,要老舍继续把话说下去。老舍提高了声音: “话都给你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周总理深深地望了老舍一眼,微微一笑。他很了解老舍这个耿直的脾气。
北伐胜利之后,一天,在蔡元培家里,傅斯年和几个同学都喝了点酒,蔡元培喝得更多。傅斯年就肆口乱说: “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但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到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 ‘郡县之’。”蔡元培听到这里,不耐烦地、声色俱厉地说: “这除非你作大将。”见先生如此神情,傅斯年的酒马上就醒了。
20世纪40年代,傅斯年干得最漂亮的事情,是先后赶走了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蒋介石为了平息此事,曾请傅斯年吃饭,并说: “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傅斯年经常向罗家伦夸赞自己的夫人大綵的小品文如何好,小真书 (即小楷书)写得如何好,说得津津有味。一次罗家伦和傅斯年开玩笑说: “大綵赏识你,如九方皋相马。”傅斯年大怒,要来扑打罗家伦。当傅斯年对罗家伦盛夸自己的儿子仁轨如何聪明时,罗家伦笑着说: “犬父竟有虎子。”傅斯年却为之大喜。
北平解放后,北大教授冯至和季羡林在这考验的关头都留了下来,从此他们一起共度了一段欢喜、激动、兴奋和甜美的日子。然而跟着来的还有长达40年的开会时期。50年代的一次会议上,周扬笑着对冯至和季羡林等人说: “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冯至也套用李后主的词说: “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
20世纪20年代,陈寅恪在德国留学。一天晚上在一家华侨开的饭馆里,他无意中和周恩来、曹谷冰(曾任大公报经理)等三人相遇,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很雄辩,曹谷冰等人都说不过他。曹谷冰恼羞成怒,动手就打,竟同时连陈寅恪一起打。陈寅恪和周恩来一同退入老板娘的住房,从里面锁上门,直到曹谷冰等人走后才出来。陈寅恪笑着说:“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是听他们辩论。”
有一段时期,戴季陶想到美国去读书,托蒋梦麟向孙中山请求。孙中山说:“老了,还读什么书。”蒋梦麟据实报告戴季陶。戴季陶就自己去向孙中山请求,孙中山说:“好,好,你去。”一面抽开屉斗,拿出一块银洋给戴季陶说:“这你拿去作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跟我开玩笑吧?”孙中山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了。”
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博士,包括福州话、厦门话和北京官话在内,能说十多种语言,照 “草上之风必偃”的逻辑来说,在当时厦门大学中是具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气息的,鲁迅于是在1935年11月写的一篇《理水》中说,文化山上,聚集着许多学者,“只听得上下在讲话:‘古貌休!’‘好杜有图!’‘古鲁几哩……’‘OK!’”
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傲”,唐德刚有一段总结:“乍闻之下,我们会觉得康有为害了自大狂。其实非也。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是个人英雄的‘单干户’和‘个体户’。他们真要中了头奖,当了‘总统’之类的,未有不是‘独夫’的。得不了奖,赍志以殁的,也不甘心与草木同朽。他们还是要以‘帝王师’自诩。大家都有‘舍我其谁’的抱负,谁也不会想到‘以天下为“公”任’”。
1936年,鲁迅逝世,郭沫若题写挽联:“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1940年,蔡元培逝世,周恩来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吴宓乍闻罗家伦要来清华,“颇不舒”,因为就在前两天,吴宓私下里还大骂“彼胡适、罗家伦之流排除异己,以邪说曲学召世惑众”,这会儿哪能不紧张呢——“虑罗氏不能容我”。于是吴宓找杨振声刺探风声,听说“罗家伦氏托其致意于(吴)宓,愿在校合作,勿萌去志。罗君不以个人意见为好恶”。吴宓心仍不敢放下:“罗君他日在此稳固,不能排宓”,无奈何“与之委蛇”吧,就对杨振声表态,“自愿与之合作”。
画家钱化佛是章太炎家的常客。一次钱化佛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咸蛋,章太炎见了欣然大乐。他深知钱化佛的来意,便说道: “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钱化佛马上拿出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都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要用“章太炎”三个字落款,不要用“章炳麟”。章太炎不出一声,一挥而就。隔了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极臭的苋菜梗,章太炎竟然乐不可支,又对钱化佛说: “有纸只管拿出来写。”钱化佛仍然要他写“五族共和”四字,这回章太炎一气呵成写了四十多张。后来钱化佛又带了不少臭花生、臭冬瓜等物,又写了好多张 “五族共和”,前后共计有一百多张,章太炎也不问钱化佛用处如何。章太炎的弟子陈存仁和钱化佛极熟,问他何故。钱化佛告诉陈存仁: “三马路一枝香番菜馆新到一种 ‘五色旗’酒,是北京欢场中人宴客常见的名酒,这酒倒出来时是一杯混浊的酒,沉淀了几分钟,就变成红黄蓝白黑五色的酒,此酒轰动得不得了。”于是钱化佛念头一转,想出做一种 “五族共和”的屏条,汉文请章太炎写,满文请一位满族人写,蒙回文请城隍庙一个写可兰经的人写,藏文请一个纸扎铺的人写,成了一个很好的屏条。裱好之后,就挂在番菜馆中,以每条十元售出,竟然卖出近百条,钱化佛因此多了一大笔钱。
1901年6月12日孙宝碹在日记中记下:“枚叔 (章太炎)辈戏以《石头》(《红楼梦》)人物比拟当世人物,谓慈禧为贾母;光绪为宝玉;康有为为林黛玉;梁启超为紫鹃;荣禄和张之洞为王熙凤;钱恂 (钱玄同弟,为张之洞帮办洋务——编者注,下同)为平儿;樊增祥和梁鼎芬(二人皆为张之洞的弟子)为袭人;汪康年为刘姥姥;张百熙(清末政治家、教育家、管学大臣,负责重建京师大学堂)为史湘云;赵舒翘(刑部郎中、依《辛丑条约》被处死的“首祸”)为赵姨娘;刘坤一(两江总督)为贾政;黄遵宪(湖南按察使,曾协助巡抚陈宝箴创办新政)为贾赦;文廷式(支持康有为发起强学会)为贾瑞;杨崇伊(李鸿章的亲家,属于“后党”)为妙玉;大阿哥(溥俊,戊戌政变后慈禧欲废光绪而立他为皇帝)为薛蟠;瞿鸿玑(和袁世凯斗法落败,被放归原籍)为薛宝钗;蒋国亮(育才馆汉文教习)为李纨;沈鹏 (著名书法家)、金梁(曾上书杀荣禄)、章太炎为焦大……”
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周游欧美,对近代物质文明更加倾心,主张“物质救国”,也就是主张中国仿造资本主义。他甚至比附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的国教角色,倡导孔教。梁启超言:“吾中国非宗教之国,故数千年来,无一宗教家。”康有为不同意此种说法,认为 “谓宗教必言神道”者乃“奇愚”。因为康有为所言的宗教,其意甚宽:“夫教之为道多矣,有以神道为教者,有以人道为教者,有合人神为教者,要教之为义,皆在使人去恶而为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