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集(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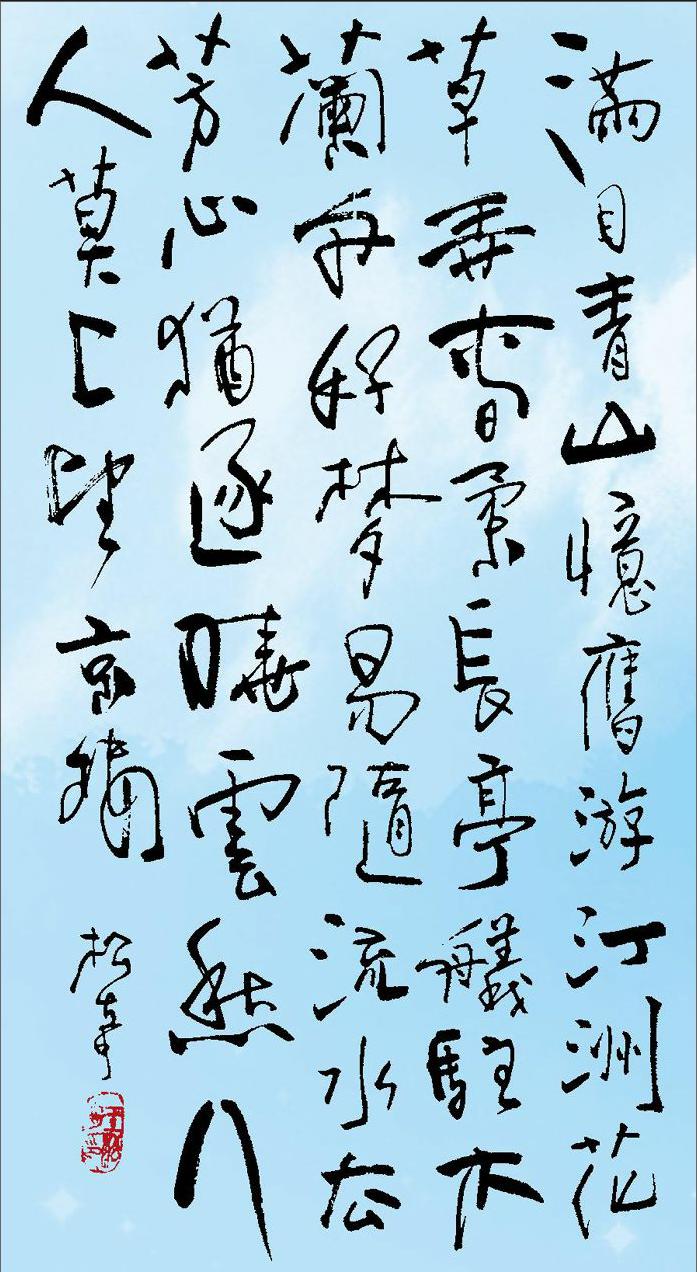
王青石
罗切斯特写满阴影的漫长寒冬终于有些遥远,而我一度抑郁的精神状态在历经了大半年缓慢调整后,也终于被北京6月的阳光唤醒自曾似深渊的昏昏大梦。这情形让人不得不充满感激,虽有些夸张,但自己仿佛真的曾远离红尘整整一年,方才回到这车水马龙的人世间。顽疾初愈的日子美好得有些令人受宠若惊,思索起这一程难言之苦的泯灭,我唯有心如止水,又心如止水。我不明白世界为什么给我如此令外人不可理喻的起落,多想之,则会百感交集甚至要涕零。如此一圈一圈地捉摸不透所谓命运,终究还是不如找个理由散散心,于是决定在月底独自回到湖北黄石,去探望在家静养的姥姥姥爷。
记忆里,去那黄石小城总是要坐一路漫长的老火车,并在有些颠簸的隆隆响的铁轨声中安然入睡,梦里憧憬着天明后见到两位老人。不曾想过这段不深不浅的记忆居然就从此成为了记忆,此中华大地早非彼中华大地,红旗飘遍山河,高铁四通八达,以往,清晨在武汉下火车后再奔赴黄石的三四个小时,如今浓缩为城际列车的30分钟呼啸。我望向车窗外一座座骤然消逝身后的青山绿岭,实在是有些高兴,夹杂些感慨与欣慰,如同我对于那恍然清晰的儿时回忆一般。
提着行李走出车厢,我没料到的是,纵然快车载我跨越了十余年的过往,黄石的容貌却一如当年,如前年山脚下炊烟袅袅的土家菜馆粉蒸肉味道,如小学时舅舅教我在烈日下甩出钓鱼竿的汗水湿透T恤,如尚在襁褓中的我躺在摇篮里所仰望的湖北天空。
姥姥家门口那不能更熟悉的两座石狮子早已没了被幼年王石头攀爬的痕迹,然而当我看到它们依然屹立不动在那里的时候,就像是看到了姥姥站在身旁紧张地伸手护着笨拙向上攀爬的我,口中欲作严肃却严肃不起来地令我马上下来,而我扮着鬼脸充耳不闻。
一楼供电局的牌子换了又换,姥姥家的单元门却还是藏在石墙与水沟的同一个拐角,那生锈的不知用了几十年的语音呼叫,那曾令我气喘吁吁的光线阴暗的五层楼梯,那才走到三楼就硬是跑来夺过我行李箱的笑呵呵的姥爷,全都像是每个回到黄石的过去,而姥爷书房阳台的杂物箱里,依旧放着我五岁时买的那支塑料冲锋枪,虽早已破得与废品无异,但却还是被擦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儿时的我是真实而不真诚的,次次来湖北其实只是想吃热干面和豆皮,对小城里其余的都并不在意。但那时的我年岁小,大概不能责备,我想也只有到了18岁,我才真正有了去“走一座城市”的资本,而此刻它是黄石,我从小到大最熟悉的地方之一。姥爷穿着宽松朴实的米色大褂,领着我走过长江大桥下芳草茵茵的公园。闲暇的大爷大妈们在桥下阴凉处摆上了数十个折叠小桌,四四相围热火朝天打着麻将,周围的儿童们在一座不大的充气城堡里你追我逐,欢乐无穷,而更远处的绿地上更是有几排身着统一鲜艳服饰的阿姨和奶奶们,她们笑容可人,扭动腰肢排练着一套颇是妖娆的广场舞,翩翩而动。眼前这一幕是那么自然和谐,没有wifi,没有微信,人们却各自沉浸在各自的乐趣里,整个情境恍若回到我儿时那简单的北京。依稀,我听见江水声就在树林那一头,于是和姥爷踏着石阶而上,直到磅礴大江展现在眼前,江水其实并不汹涌,但江面宽阔辽远,水流沉缓有力,仿佛苍天在中原大地的宣纸上用狼毫狠狠题了一印墨迹,也许正是这般不知蕴含了多少载春秋奥秘的水,才滋养出了这一方民生面貌如浴春雨的黄石人。
“我小时候就在这老房子里上学,但后来知道隔壁是个天主教堂后,家里人不放心便把我撤了出来,”姥爷指着路旁丛丛绿树后的一座灰瓦墙建筑,边走边说道,“那教堂里曾经有不少老外,都是西边来的传教士,但后来教堂还是被拆了。”说到这儿,他面露一副猜不出是苦还是喜的笑容,“再前面那个大院你看到没有?那是毛主席住过的,我们一直都保存着。”
姥爷的精神面貌一如既往地平和深沉,像棵繁密大叶间闪耀着灵光的古树,尤其是当他从怀里掏出老花镜开始细细研读书作时,那沉默的灵光便闪耀得最是威严且令人敬畏。从小到大我一直深知姥爷的渊博,但最忘不了的却是他同儿时的我嬉闹时的模样:当穿着花毛衣的我从小木床上飞身跃下,使出一套我爸教的太极云手,自以为可以刀枪不入时,姥爷一个箭步上前将我双手擒住,然后眯眼露出一副得意的笑容,大声调侃道:“你有你的云手,我有我的乌龙爪,我要比你厉害!哈哈哈哈!”
姥姥的模样则是另一种充满母性的祥和,就像她双眼里永远流露出的会心微笑。她平时总是慢慢提着步子静心看着身边一切,但一旦亢奋的我玩出了汗,她就再也静不住,一定会惊惶地左翻右翻,然后找出一条毛巾急急塞到我湿透的衣服里,再轻声地训斥我个一两句。说实话我从来不喜欢后背裹着条毛巾的别扭感觉,但毕竟姥姥是担心外孙会着凉感冒,我也难以反驳,最后唯有背后插着半条毛巾甚是不舒服地去继续蹦跳,而姥爷只是坐在大木椅上望着我,不慌不忙喝着崂山茶、摇着黑羽扇,然后一边笑着一边对姥姥讲着我听不大懂的湖北话。
平心而论,与二位老人在一起的生活让我难以不想起何一禾曾经跟我说的一句话:“同一个人,十五岁和二十五岁是天差地别,但六十五岁和七十五岁就没什么不同的了。”仔细一想,确实没错。在我眼中,姥姥姥爷一直是他们现在的样子,不曾变过。也因此,纵然我已与自己有了十年的天差地别,甚至步入成年,但他们给予我的亲近感却还是一如既往,透着十多年前一模一样的慈祥,当老母支撑着我爸在医院与命运殊死搏斗时,他们是我唯一的守护者;当我坐在潘家园的窗台上静静数着星星,他们督促我早些去睡觉,次日还要上幼儿园……
岁月如梭,但这种感情被永久保留在了目光的交汇间,就像姥爷在江畔指给我看的那座建于唐代的楼宇,任东流江水千百载地经过黄石两岸一去不返,它就一直屹立在那里,不受春去秋来左右,不为阴晴圆缺动摇。
黄石是座与水结缘的城,除了浩荡长江,市区里还有那依山的磁湖。这几天的晚上,舅舅舅妈便领着我绕着那湖水散步,走过沿湖而建的一个个中年人们跳着舞的广场,和一座座立于水上曲折精致的小桥;当天完全黑到可见星星时,远处水面上还能看见黄石城几座高楼大厦的光的倒影。endprint
“在我小时候,这里还是一片湿地,我和你妈常在这个湖旁边捡田螺,捉虾子,钓鳝鱼,拎着桶回去一烧,非常好吃,”纵然西裤衬衫焕发出截然不同的气质,但舅舅说话的语气颇有几分神似姥爷,“后来我们把这湿地开发成了一条步行街,环境优美,有许多餐馆,吃完饭出来就可以绕着沿湖小路散步,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黄石也是舅舅舅妈从小成长到大的地方,未曾离开过。虽说是老母的亲哥哥,但舅舅似乎从来没有像老母那般天南海北地闯荡,而是脚踏实地在黄石这小城一步步做着让自己舒服的事情,直至今日,守着一份安稳的工作,衣食无忧,小小的城市满大街都是他的熟人朋友,这何尝不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逍遥。
舅舅热爱并有着精湛的厨艺,不是我爸那种馋什么就往锅里丢的前郭尔罗斯式乱炖,而是确切有着讲究的南方小厨技艺。黄石的夜市里有各式各样的地方小吃,包括在北京鲜能尝到的小龙虾、田鸡、王八等等,这么些小众美味,舅舅竟然还都会做,他娓娓向我道来,传授了许多烹饪技巧,供我在剩余的无趣的大学课余时间里自己琢磨,让我实在受益匪浅。
我不否认,下厨风格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生活态度,而老母有时候会讽刺舅舅的小男人风骨,甚至调侃他窝在黄石小老家的人生选择。但我却不是很认同,话不能说得如此绝对,因为当你身临其境地走在一座哪怕小如黄石的城市里,你的心也会随城市氛围而动。在这种环境里,走出去或不走出去,无非是一念之差的两种等同的未来,或者说是两条方向相异但同样通往湖对岸美好光景的沿湖小路。的确,在许多年前老母选择了向左走,而她的哥哥选择了向右,但湖是一个圆,而如今的他们同样知足,因为他们一直在不停行走,并不断接近那个年轻时遥望的对岸,这不就足矣。
换句话说,老母可以在颐和园里望着涟漪和柳絮享受她所拥有的生活,但舅舅同样也有他深爱的磁湖,那倚着黄石市的一汪深情的水,那洗去了他青春却依然宛若初恋时节不曾改变过的荷塘。
所以,每每当深夜散完步的我乘坐老式公共汽车返回姥姥家时,我都难以把心中这黄石的味道挥散。
我想,这便是我的2014黄石印象。
我的家乡是北京,但北京早已不是那个在龙潭湖公园里三岁的我学不会竹蜻蜓便哭着要离家出走的北京,而是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我渐渐不敢看的花花世界。确实,当牛气冲天的高楼大厦拔平地而起,当北京地铁打通了世界上任何地方无可比拟的交通奇迹,当三环四环五环的夜晚没有星星却一天比一天繁华明亮夺目耀眼时,没人能否认北京这些年的变化正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但这与时间赛跑般越来越快的节奏,难免也变成了大街上一张张越来越浮夸的面孔,和对我而言一个越来越陌生的家乡。相比之下,我竟然只想感谢黄石没变。
从小到大我不曾把巴掌大的黄石视做家乡,但此时此刻,这种想法却轻轻地占据了我的心灵,像一股被等候了许久的清风从窗外飘进房间。
我叫王青石,姓王,青字辈,若别人问起怎取了个“石”字,便机械答道是由于老母是黄石人。其实这么说是很勉强的,因为单单一个石怎能代表黄石?若真是这样取名,那孩子的父母实在是有点草草了事的嫌疑。以往我总是在内心处计较这件事,但现在我觉得可以放下了,黄石这座城市,于我的意义已无须多言,它完完全全对得起我的名字,更对得起我这小小的生命,记得上次来这里我还自作聪明地贬低它相比于我所生活的世界的落后与老土,今天我却感到了些许羞愧,我才知道,当一切一切都在竞相变化时,那不变的才是最美好的,美好得深沉而温暖。
对,我可以再次肯定,这就是我的2014黄石印象。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