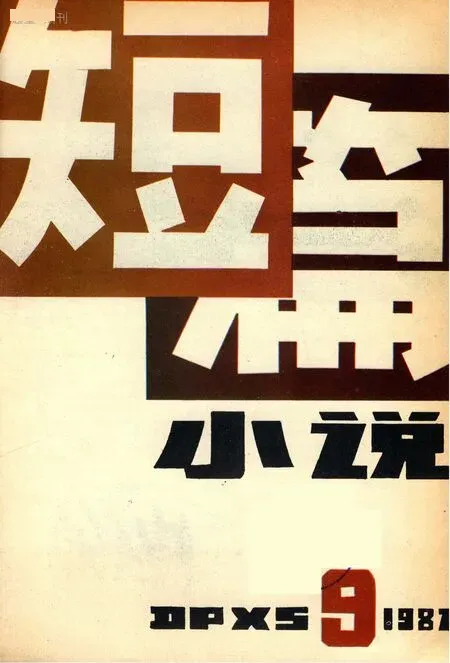一九七六年的爱情
◎小米
一九七六年的爱情
◎小米

一九七六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乡亲们仔细一想,却也认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为什么要这么说?用村里人的话说就是,这一年年初,一前一后,周总理和朱总司令两位极其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去世了,这足以说明,这个国家的根基已经有所动摇。大家都觉得,天地跟人之间,是有着某种神秘的感应的,如此重要的两位领导人都已经去世了,在这个国家,“天”都塌了,地要不震,那才是件奇怪的事情。
我的家乡在这一年也赶热闹似的,在唐山大地震发生的前前后后,不停地,有比较小的地震,连续不断地骚扰着乡亲们。起初,人们不以为然,并不把地震的接连发作当一回事儿。这也不奇怪。家乡在两个地震带的交叉点上,对地震,乡亲们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仅仅是这一年,地震发生得比往年更频繁了一些,震级更大了一些,如此而已。可是,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引起了不知道是党中央还是省委的高度重视,上级要求,必需做好防震工作。没有办法,大家在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的监管之下,不得不防震。
可是,怎么防?
村子的位置,处在古老的地震或泥石流引发山体滑坡之后,形成的一块很大的冲积面上。人们居住得十分拥挤,唯一的可以防震的空地,是村庄中心部位的打麦场。村庄坐西朝东,打麦场的南侧是几十米高的悬崖,悬崖下面是河滩,河滩上是生产队修建的阶梯状的方方正正的大寨田,大寨田既整齐,又好看,只是放水之后,老是渗漏,大约是地的基础并没有打结实。打麦场的北侧就是生产队的仓库。这样的布局是极其合理的。打麦场是用来给麦子、黄豆、荞等需要用碾滚子碾下来或用梿枷打下来的粮食脱粒的场地,也是开社员大会或村里集会的场地,打麦场紧靠着仓库,粮食可以就近入仓。
乡亲们在修房建屋的时候,在屋檐下,都留有一块高出地面宽约两米的长条状空地,称之为台子,台子里侧才分隔成或大或小的房间。生产队的仓库也是房屋的样式,当然,也有台子。仓库是三间屋子,每间屋子的开间与进深,都在一丈五左右,台子的长度,至少也有十六七米。
一九七六年,乡亲们防震的时候,都在仓库的台子上打地铺过夜,每家所占的位置,最多也就是一床被子的宽度,地铺的长度刚好是台子的宽度,约二米。这家的地铺与那家的地铺,彼此连接,一家紧挨另一家,中间没有界限。看上去,真像一个大家庭。
白天,人们分头回家做饭、吃饭,共同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集体睡觉,有民兵轮换着,整夜都在站岗。万一发生了地震,站岗的民兵也好及时叫醒大家,不站岗的人,可以放心大睡,一旦有了什么风吹草动,以为是地震,站岗的民兵就大吼一声,让人们赶紧从屋檐下逃出来,躲到打麦场里去。往往是这样:你睡得正香,迷迷糊糊之中,所有的人突然全都一骨碌爬起来,几步蹿到了打麦场上,地震过了,平安无事了,又纷纷回到自己的被窝里,继续睡。
按说,村里虽只有不到二十户人家,那么小的一块台子,全生产队的人都在那儿睡,再怎么挤,再怎样凑合,也是难以容纳的。事实也是这样。一个家庭,只有大人孩子的,好说,还能将就将就,三代同堂的,比如公公和儿媳之间,女婿和丈母娘之间,还睡在一个被窝里就不方便了。也是因此,约定俗成一般,村里每个家庭的老一辈,只好继续睡在各自的家里,他们共同的理由是:死也要死在自己的炕上。他们说不出口的原因还是台子太小,容纳不下。无论公社干部、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对这些不到仓库的台子上来防震的人,都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在打麦场上露天睡觉肯定是不行的,下雨怎么办?睡在仓库的台子上,虽说不能遮风,好歹还能挡一挡雨。好在到了夏天了,夜里不算太冷,不然的话,乡下的夜晚是很冷的,后半夜就更冷了,如果不是在夏天,台子上也没有办法睡。
打麦场是村里唯一较大而且开阔的平地,是“广场”了,这儿本来就是一个热闹的所在,现在更热闹了。像我这样的孩子,那时还不知道地震的危险与残酷,对这样的生活方式却是喜欢得不得了。几乎大半个夜晚,孩子们都在打麦场上打闹、玩耍,瞌睡得实在不行了,才会钻到自家的被窝里去。大人跟孩子不同,他们干了一天的力气活,累了,天刚一黑,就分头躺在了被窝里,跟左右说些闲话,说着说着,说不了多久,下眼皮就支不起上眼皮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陆续睡了。
睡这样的地铺,几乎是这一家人的前胸紧贴着那一家人的后背,这个人紧贴着那个人,睡前,怎么也得说说话儿,拉呱拉呱,有时还开几句玩笑。这样的生活,真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在这里将要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
一九七六年的防震,改变了牛娃的命运。
家乡方言里,将又呆又傻的所谓傻子,叫做瓜人。牛娃就是一个人们所认为的瓜人。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我并不认为牛娃是个傻子,或者瓜人,恰恰相反,我认为牛娃是个心灵手巧绝顶聪明的人。牛娃没有上过一天学,看上去,也像一个傻子,可他一点也不傻。比如木匠活儿,铁匠活儿,别人登堂入室拜师学艺,也不见得就能学会,牛娃只是看看,再看看,自己就可以动手做家俱,或者当一个铁匠,打铁。牛娃给自己家里做椅子、做桌子、做柜子、做箱子,自己备料,自己配齐了木工用具,不找木匠,自己动手做,是一条龙服务。牛娃也给家里打制农具和其它用具,村里虽然从未有人把牛娃看作一个匠人,因而请他打制过什么东西,可是,牛娃家的农具或铁器,比如锄头、镐头、尖镢、三角等等,在牛娃自己动手做了个铁匠用的风箱之后,从此不曾求助于铁匠。牛娃喜欢这些,酷爱这些,他用农闲时间钻研这些事儿,父母劝不了他,也懒得劝他。
牛娃还研究锁子。谁家不小心丢了钥匙,把牛娃叫过去,牛娃准定可以把锁子给你打开。他开锁,但不毁坏锁子,牛娃帮你将门锁打开之后,还会另外给你配一把钥匙。村里有了会开锁的人,人们普遍会对这样的人有所戒备。牛娃学会了开锁的手艺,但是,村里的任何人对牛娃都是一百个放心的,即使家里丢了什么东西,哪怕怀疑亲朋好友,也不会怀疑到牛娃的身上去。牛娃为人正派,手脚干净,是个正经得不能再正经的人,如果不是有求于他,如果不是看见了他,想起了他,他就像个透明人一样,你可以当他不存在。人们认为,怀疑牛娃盗窃,就跟怀疑自己偷了自己的东西一样,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牛娃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一个傻子呢?这当然与他的日常行为是分不开的。
干活也好,走路也罢,身旁有人也好,无人也罢,无论何时何地,牛娃都是一副微微低头的思考模样。牛娃总是想着事情,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事情,需要他来想。你在旁边干扰他,他也似乎看不见、听不见。他专注于他在想着的事情,不为所动。要是他觉得你很讨厌,打断了他的思路,他也不气恼,而是躲得远远的,继续他的思考。农业学大寨的时候,生产队里放炮炸石头,把牛娃的耳朵给震坏了,除非俯身在他耳边大声喊话,他真的听不见什么了,从那以后,牛娃常常都是一副如醉如痴的思考样子。认为他傻,说他是个瓜人,也不是毫无道理。
牛娃二十六岁了还没有结婚娶老婆,在当时的农村,牛娃是个典型的大龄青年了。
村里有个女子,比牛娃还小一岁。这个女子模样俊俏,耳朵也能听见,不知道怎么回事,却天生是个哑巴。说她是个哑巴,其实并不准确。我很奇怪的是,这个女子的嗓门,一旦呐喊起来,却又大得出奇,但她不会说话。女子在家里排行最小,也许因为儿女众多,她又不会说话,他的父母连名字也懒得给他取一个,就叫她碎女子。在家乡方言里,碎就是小的意思,碎女子,就是小女子。碎女子的父母从小几乎不把碎女子当作一个人来看待。碎女子穿得破破烂烂的,无论衣服还是裤子,都是补丁叠着补丁的样子,她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碎女子吃的也常常是哥哥姐姐碗里剩下的。有时候,连剩余的饭菜也没有了,人们就看见碎女子趴在猪圈里,抢吃猪食。
碎女子大了,是个劳动力了,父母又让她到生产队上工,给家里挣工分。这时候,碎女子的哥哥姐姐该娶妻的娶了妻,该出嫁的出嫁了,老两口身边没什么人了,对碎女子的态度也略微好了些,不再不给她饭吃了,可是,他们不跟碎女子一同吃饭,他们每次吃饭,都让碎女子端着碗,到大门外面,独自去吃。这哪儿像亲生的父母呀,真是连路人都不如。可是,别人的家事,乡亲们也不方便管,只能听之任之。
人们都很同情碎女子的遭遇,他们觉得,这个女子,真是造孽(可怜)。
不用说,碎女子也是真的有点儿傻。
碎女子对父母当然会抱怨,但她从来不违拗,不反抗。父母说什么,她就做什么。她知道他们是她的亲人,父母让她饿着,不让她吃饭,她就恨恨地撅着嘴,躲到屋外去了。碎女子知道人的好歹,父母对她不好的时候,她会用丰富的表情和夸张的手势向过路的人“控诉”父母的不是。碎女子懂得里外,她也明白,她得维护父母的利益,如果父母不在家,她就像看门狗一样,一动不动地守在大门口,她不让任何人进入她家的屋子,更不让任何人拿走属于她家的东西。
碎女子也大了,她的父亲有财想,要是他和老伴都老死了,谁来管碎女子?在父母眼里,碎女子成了负担了。
有个叫做代祥娃的年轻人,对有财提议说,把碎女子嫁给牛娃吧。
不是有财没有这么想过,是他觉得,牛娃跟碎女子,虽然隔了好几代人,血缘关系已经很远了,毕竟还是同宗同族,是同一个先人的后代,这么做,他们觉得不太好,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如今代祥娃这么提议,碎女子的父母不由得心里又动了一动。
她母亲说,牛娃倒也合适,就是木讷了些。
当着代祥娃的面,有财横起脸子来责骂女人说,你也不撒泡尿当镜子来看看,自己养的是个什么货色。
女人就知趣地闭上了嘴,不再说什么了。
有财想了想才对代祥娃说,我知道牛娃家里穷,娶不上个媳妇,你去问问牛娃家里,他们家没什么意见就行,一来,我不要彩礼,二来,他们也不必办什么酒席(举行婚礼)。我让婆娘把碎女子领过去,给他们就行了。有财还说,两个傻不啦唧的人住在一起过日子就算是夫妻了,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人,没有办酒席的必要。
代祥娃找到了牛娃的父母。牛娃的父亲说,我们一穷二白的,能有什么意见呢?碎女子好歹是个女人,能生娃就不错了,就算牛娃碰了天(撞大运)了。
代祥娃说这些的时候,牛娃也在场,虽然耳朵有毛病,毕竟还能勉强听见,他没有说什么,算是默认了这事。
就这么,连好日子也没有挑一个,有财的老婆当天下午就跟代祥娃一起,把碎女子领到了牛娃家。有财老婆简单地向牛娃交待了几句要好好对待碎女子的客套话,扔下碎女子,跟代祥娃一起走了。碎女子就这么名正言顺地成了牛娃的媳妇了。
碎女子却一头雾水,什么也不知道,她既不明白母亲把她领到牛娃家来干什么,更不知道她已经成了牛娃的媳妇。有财两口子就没有跟碎女子商量过,他们连事先给碎女子说一说的打算也没有。当天晚上,天黑了,碎女子认为她应该回家了,死活都要回家去,牛娃不由分说,将碎女子拽到睡房里,闩了门,强行打开她破破烂烂的包装,在碎女子声嘶力竭的喊叫声中,把碎女子“办”了。第二天,碎女子不喊了,不叫了,不哭了,不闹了,她傻笑着穿了一件干干净净的花布衣裳,从睡房里笑盈盈地走出来,去给一家人生火做早饭。
碎女子刚刚换在身上的衣服,是牛娃妹妹的。虽然不新,却也不破不烂,是牛娃妹妹最好的衣服。牛娃的妹妹起初不答应把这么好的衣服让给碎女子。因为事情来得突然,牛娃的父母也没有时间给新媳妇做新衣服,他们也是不得已,才劝牛娃妹妹,让她拿出最好的衣服来,先给她嫂子穿。他们答应给女儿另外做新的,这才说服了牛娃的妹妹。
碎女子一边做饭,一边抚弄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心里美滋滋的。
可是,好景不长。
那几年,时不时的,远远近近的村里,就有山东人或河南人出没,他们在本地娶不上媳妇,于是攒一点钱,专门到遥远的甘肃来,打算花钱买一个媳妇回去过日子。不知道是谁在碎女子的父母那儿瞎起哄,碎女子的父母突然觉得,他们嫁了自己的女儿,却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吃了亏了。有那么一天,有财找上门来,不管碎女子愿意不愿意,也不管牛娃同意不同意,非要把碎女子领回去,说是,牛娃要么拿一份二百元的彩礼给他,然后再把碎女子领回家,要么,他就把碎女子卖给山东人。
牛娃无奈,拿不出彩礼。只能让有财把碎女子从自己家里,生生地揪了回去。
牛娃上哪儿去弄什么彩礼?他家里那时只有六毛钱,连一元钱都凑不够。这个村子里,能够拿出二百元的人,也许是有一个的,但可以肯定,绝对不会有第二个。牛娃也觉得自己白捡了一个媳妇,是有点儿对不起老丈人。他也只能先让碎女子在娘家住着。
天黑了,碎女子要到牛娃家里去睡觉,有财当然不同意。有财也不放心碎女子,怕她三更半夜悄悄地跑到牛娃家去睡。有财在睡觉前,拿绳子捆住碎女子的手脚,第二天早晨,又给她解开。碎女子得了空闲,想到牛娃家去,帮牛娃的家人做点儿什么,有财却不允许碎女子那么做。碎女子只好坐到大门口,独自撅嘴生闷气。过路人用开玩笑的口吻对碎女子说,你咋不到牛娃家去?碎女子就手舞足蹈咿咿呀呀地跟对方解释,她的意思人人都明白:有财是她爸爸,他不让她去牛娃家,她就不能去。
有财明白,牛娃是拿不出二百元彩礼钱来的。可是,转眼要到夏天了,山东人还是音讯全无。有财也在纳闷儿:有个专门说道这种事情的中间人,跟有财都已经说好了,说是过了一九七六年的新年,会有一个山东人来把碎女子带走。有财是真的打算把碎女子卖到山东去,他已经让中间人跟山东人说好了,他要山东人给他二百元,作为这二十多年来碎女子的抚养费。中间人把有财的要求写信告诉了山东人,山东人也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有财的要求。有财这才到牛娃家来,把碎女子领回了家的。
有财心里想的是,摊上碎女子这么个“宝物”,不如嫁得远远的,眼不见,心不烦,还能赚到一笔钱,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在家乡,在那时候,人们都认为这么买卖妇女是很正常的事情,没什么了不起。人们的共识是:男人没有媳妇,就该找个媳妇,女人没有男人,就要设法嫁一个男人,一方想要一点钱,另一方愿意支付,也付得起这笔钱,就是好事情。乡亲们认为,这么做天经地义,理所应当,任何人都无权干涉。
有财天天盼望着山东人会来,可是,他盼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或大或小的地震。
生产队集体防震后,有财两口子每天晚上都到仓库的台子上睡觉,为的是防震,可他们不让碎女子来。有财说是,怕有小偷会偷了家里的东西。他们让碎女子在家里睡,顺带看家。他们说不出口的原因其实是,作为亲生父母,他们都不想跟碎女子在仓库台子上,在大家的眼皮底下,睡同一个被窝。有了这样的想法,有财就不管碎女子安全不安全了,他也不管碎女子是不是会到牛娃家里去,或者,牛娃会不会偷偷摸摸地,睡到碎女子的炕上去。有财想,山东人恐怕是等不来的了。如果山东人不来,碎女子跟了牛娃,虽说不怎么满意,对碎女子来说,却也是条出路。
有财此时此刻的心理,就是这样。
牛娃没有去仓库的台子上防震。牛娃主动要求父母,说是要在家里看家。牛娃为什么这么说?他难道不怕地震吗?牛娃当然怕。但是,牛娃更怕的,是他的妹妹。
牛娃的妹妹也是一个大姑娘了,还没有出嫁。从懂事起,妹妹就觉得这个哥哥让她很没面子,从而在牛娃面前,常常颐指气使,比后娘还凶。牛娃疼爱妹妹,不跟妹妹计较,妹妹以为牛娃怕她,更不把这个做哥哥的放在眼里,记在心上。刚刚打算防震的那天,牛娃到生产队仓库的台子上去给一家人打地铺,地铺打好以后,妹妹前来看了看,絮絮叨叨地埋怨说,这么大点地方,四个人咋睡?牛娃的妹妹回头对牛娃说,牛娃你就别出来了,还是睡在家里吧。妹妹用的是命令的口气,听上去没有商量的余地。牛娃接过话来说,我也想在家里睡,总得有人看家嘛。父母看了看牛娃,不好说什么了。
牛娃知道妹妹嫌弃他,他不跟妹妹计较。妹妹不把他叫哥哥,牛娃还是不计较。牛娃已习惯妹妹叫他牛娃了。
让人想不到的是,碎女子适应了独自在娘家,即使父母不管她,她也不再吵闹着要去婆家了。牛娃呢,除非碎女子回了家,他也是不会去干那些偷偷摸摸的事情的。牛娃的性格就这样,谁也拿他没有办法。
人们纷纷替牛娃想办法。其中一个人,就是代祥娃。他是最卖力的。
代祥娃和牛娃是老庚 (同一年出生的人),是和牛娃一起长大的好伙伴。代祥娃的女人已经一口气给他生了三个女子了,代祥娃还在努力地开垦着他的女人。他一心想生个儿子。可是,在代祥娃努力耕耘自己的女人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关心一下他的老庚。
山东人为什么不到有财家来将碎女子买走?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事情坏就坏在代祥娃身上。找有财的那个中间人,恰好是代祥娃的朋友。有一天,代祥娃到镇上去赶场的时候,遇见了他,那人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把要将碎女子卖到山东的事儿,作为聊天的话题,对代祥娃说了。这时,碎女子已让有财从牛娃家领回去了。代祥娃听了这些,立即冷下脸来,让中间人不要这么做,他对他的朋友说了他跟牛娃的好朋友关系,代祥娃也对中间人摊了牌,他的意思是,碎女子是牛娃的媳妇,中间人要是一意孤行,他不交他这个朋友都可以,也要替牛娃打抱不平,将这件事情干涉到底。最后,代祥娃对中间人说,你赶紧给山东人写一封信,叫他不要来甘肃了,来了也是白来。
代祥娃就是这么对他的朋友说的,他的中间人朋友,只能依了他。即使卖了碎女子,中间人也得不到多少好处,做中间人的人,犯不着因此得罪了自己的好朋友。
这时村里已经开始防震了。代祥娃回到村里,召集了几个关系不错的人,来找牛娃。
代祥娃俯身在牛娃的耳边,高喊着对他说,牛娃,碎女子一个人在家里,今天晚上,你干脆帮她去看家算了。
代祥娃的意思,牛娃当然明白。他想了想,摇摇头说:碎女子已经不是我的媳妇了。牛娃的言外之意是,他不去。跟代祥娃一同来的人都明白,牛娃不是一个心里一套嘴上一套的人,他说了不去,就肯定不会去。于是,代祥娃又俯到牛娃耳边,继续怂恿他:碎女子又没有跟你离婚,你完全可以去,凭什么不去睡她?
牛娃说,她也没跟我结婚不是。
代祥娃说,没结婚,碎女子为啥在你的炕上睡了那么长的时间?
代祥娃不死心,继续开导牛娃:她让你睡,她的父母也让你睡她,她就是你的媳妇。
他不是不让我跟碎女子睡了嘛!他都把碎女子带回他家去了嘛!
牛娃振振有词,不为所动。
代祥娃说,有财不就是要彩礼嘛,你拿不出来,有财也不是不明白,你答应他就是了,十年也好,二十年也罢,你慢慢地给他攒这笔钱嘛,有财也没说不让你跟碎女子睡觉。
牛娃说不出理由来了,他憋红了脸,好久才说,我反正不去。
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
当天晚上,代祥娃叫了几个人,瞒着村里的其他人,去观察牛娃的动静。可是,牛娃没什么动静。天黑,饭也吃了,人们三三两两地往打麦场上走,牛娃的父母和妹妹也分头出了门,牛娃将大门咣当一下,闩了,过了一会儿,牛娃又吹灭了煤油灯,睡了。牛娃家的院子里漆黑漆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代祥娃他们几个躲在牛娃家的大门外面,等了很久,牛娃还是没有出门去找碎女子的迹象。
他们只好往打麦场走,到仓库台子上,睡觉去。
几天以来,代祥娃他们几个,天天都去观察牛娃,牛娃的表现让他们彻底失望了。可是,代祥娃不死心,他认为碎女子要傻一些,好哄骗一些。他又打起了碎女子的主意。代祥娃打算从碎女子身上寻找突破口,促成他们的好事。
代祥娃没有叫别人,这一次,他独自去找碎女子。
碎女子当然在家。确切地说,有财两口子去了打麦场那儿,碎女子却坐在她家大门口,还没有关门去睡。
代祥娃对碎女子说,牛娃叫你到她家去呢。
碎女子连连摇头,她不去。代祥娃问她为啥不去?碎女子就比比划划,她的意思是,门没有人看是不行的,她要看门。代祥娃说,你去吧,我帮你看门,你跟牛娃睡一觉再回来就行了嘛。碎女子知道牛娃跟代祥娃处得很不错,她当然放心代祥娃,可是,她还是不去牛娃家找牛娃。碎女子的理由是,她爸爸不让她去,她就不能去。
代祥娃又没有办法了。他想,总不能把碎女子绑到牛娃那儿去吧?
代祥娃走了。
代祥娃后来想,为啥不能把碎女子绑到牛娃那儿去呢?
代祥娃觉得,没有其它的办法,只有这个办法了。
代祥娃又召集了几个人,他们商量好,等有财两口子去了打麦场,他们就把碎女子绑架到牛娃家。
他们果真这么做了。
天刚刚黑,他们很顺利地,就把碎女子降伏了:用绳子把她捆得紧紧的,还用一块手帕,塞上了碎女子的嘴。代祥娃让另外几个年轻人随后把碎女子抬到牛娃家,他先走一步,骗得牛娃开了门,代祥娃这才示意躲在暗处的另外几人,他们不容分说,把牛娃和碎女子关在了牛娃的睡房里,把睡房门从外面锁了。几个人出了院子,把牛娃家的大门,也从外面锁了。
代祥娃让另外几个人回到仓库台子上去睡觉,假装防震,顺便监视有财两口子,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代祥娃代替碎女子,到有财家去睡,他给有财家看门去了。
代祥娃心里想的是,只要过了这一个晚上,他就跟有财摊牌。他要让有财接受牛娃这个女婿。代祥娃还要替牛娃向有财作出承诺:在三年之内,给有财付清二百元彩礼。万一牛娃到时候拿不出钱来,他就替牛娃还这笔钱。为了让有财答应,代祥娃都想好了,他要以自己的名义,替牛娃向有财写一张欠条。
代祥娃觉得万无一失了,这才放心去睡。
没有想到的是,当天夜里,又发生了地震。
地震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在站岗民兵声嘶力竭的喊叫声中,人们纷纷从仓库台子上,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了打麦场上。人们刚到打麦场上,地震就停了。大家觉得虚惊一场,都乱纷纷地寻找自己的被窝,打算继续去睡。个别有人在家睡觉的人,打算回家去看看。
代祥娃召集的那几个人,没有睡。他们有点儿担心牛娃和碎女子,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他们看到牛娃的父母和妹妹都没有回家打算,就想到牛娃家去看看。他们不担心代祥娃,代祥娃是个灵醒人,他们对他很放心,何况,地震也不是太大。
他们开了牛娃家的大门,又开了牛娃的睡房门,他们把手电筒照射到牛娃炕上的时候,看见牛娃和碎女子赤条条地搂抱在一起,睡得正香,要不是光束刺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还不会醒来。这正是他们几个希望看到的情形,可惜代祥娃不在场。对于发生地震的事情,面前这一对迷迷糊糊却又慌慌张张的痴男傻女,一点也不知情。
大家嘻嘻哈哈打趣了一阵子,打算回到仓库台子上放心地去睡觉。
走了几步,有人提议说,我们去跟代祥娃说说吧。
大家意犹未尽,纷纷说好。
到了碎女子家,他们却怎么也叫不开门。
代祥娃不会睡这么死的。他们觉得有点儿不妙,但是,谁都没有说什么。
有人提议翻墙进去。
碎女子家的围墙是用石头砌的,石头之间的缝隙很大,更未依照常理,用泥巴填塞,虽说有一丈多高,却方便拿捏,是很容易翻墙而入的。这也是有财为什么要碎女子在家看门的另一个原因:家里如果没有人,即使锁了大门,有财还是担心会有人翻墙而入。
正打算翻墙的时候,有人发现,碎女子家的围墙,塌了一个很大的缺口。
天刚黑的时候他们都来过,那时,围墙还是完好无损的,明摆着,是刚刚发生的地震把围墙给掀翻了。
这个人招呼了一声,他们就急急忙忙地,从豁口鱼贯而入。
碎女子的炕上,没有代祥娃。
有财两口子睡觉的炕上,还是没有代祥娃。
再找,别的屋子里,再没有炕了,也不见代祥娃的踪影。
代祥娃睡在什么地方?或者,他到哪儿去了?人们迷惑不解。
有人小声说,会不会砸在围墙下面了?
另一个人立即说,闭上你的臭嘴!
刚才说话的人就闭了嘴,不吭声了。
可是,大家都担心,代祥娃很有可能,就在倒塌的围墙下面。
果然如此。
代祥娃已经断了气了。身子也冷了,僵了。
代祥娃显然是发觉了地震之后,匆匆出门躲避地震,到了围墙跟前,围墙正好塌了,这才将代祥娃砸在一堆石头底下的。代祥娃的脑袋被石头砸得变了形了,瘪进去了,好像泄了气的皮球。
碎女子家的房子完好无损,代祥娃要是不出门躲避,也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他也不会因此丢了命。
世上的事,有时候,就这么奇巧。
葬代祥娃的棺材是牛娃无偿提供的,做棺材的松木是牛娃从山里砍回来的,棺材也是牛娃自己做的,牛娃没有请木匠来做棺材。这是牛娃做的第一副棺材。这一副棺材,牛娃是给他爸爸预备的。提前为家里的老人预备棺材,是有孝心的表现。牛娃没有想到的是,棺材让他最好的朋友背走了。
一九七六年对于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不平常的一年。
就拿国家大事来说,先是周总理去世了,所有的人,臂缠黑纱,戴了一次孝(乡亲们认为这就是戴孝),接着,朱总司令也去世了,大家臂缠黑纱,又戴了一次孝。
故乡的风俗是,只有新故的近亲长辈,人们才会戴孝,而且,戴孝的习惯,也是大大不同。家乡的人戴孝,不是绾在臂膀,而是绾在头上,孝布的用材也不是黑纱,而是白布。人们都觉得这种臂缠黑纱的戴孝方法有些滑稽,显得不伦不类,可是,一想到是为国家领导人戴孝,理应与普通老百姓有所不同,大家还是接受了这种方式。至于该不该戴孝,人们却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就在这一年,迷信的人纷纷议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村里,人们都在私下里说:“朱毛朱毛,没有了猪(朱德),毛(毛主席)还能继续生存吗?大家都认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先后失去了左膀右臂,恐怕也是活不过这一年的了。可是,这样大的事情,这种天塌地陷的反革命话题,谁也不敢公开谈论,只在比较私密的场合,遮遮掩掩闪烁其词地,说那么一说。有了这样的念头或想法,不说一说,实在也是憋得慌,说了,却又不敢痛快淋漓,怕万一有人对自己上纲上线起来,会招来祸端。
好在天高皇帝远,人们的政治敏感性并不是那么强,人与人之间,也不是那么针锋相对,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思想毕竟还是根深蒂固的。好歹都是同一个先人的后代,犯不着搞得你死我活的。也是因为如此,人们才敢如此大不敬,拿最尊敬的毛主席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斗胆说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事儿,甚至斗胆预言,他老人家也有可能在不久的某一天,会离开我们。
在我的家乡,人们无论老幼,一律习惯地,把毛主席不称呼为毛主席,而是叫做毛爷。那种尊敬已经不是装装样子,而是深入到骨头里去了。
村里有人死了,死者的晚辈,当然要戴孝。
代祥娃死后,无论大人小孩,也不管辈分高低,村里人再一次集体戴孝。他们当然是为代祥娃这么做的。一九七六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村里只死了代祥娃这么一个人,而且是个年轻人,是非正常死亡。可是,人们集体戴孝,已经是第三次了。村里人给代祥娃戴孝的时候,都想,集体戴孝在这个村子,在这一年,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吧?
他们想错了。到了九月,他们还要为最敬爱的毛爷,再戴一次孝。
也是从代祥娃那儿开始,这个村子里,凡是重要的人去世了,人们都会集体戴孝。
新的风俗习惯就这么形成了。
碎女子在代祥娃出事的当天晚上就从牛娃家回到娘家来了,办丧事的这几天,她没有去牛娃家,牛娃也没有上门来要求她回去。牛娃跟她的关系,又回到了代祥娃出事前的情形。
代祥娃很有可能是替碎女子死的。有财嘴上虽然不说,心里却有一本明白账,他不跟牛娃要彩礼了,他什么都不要了,他只希望碎女子能够尽快地生一个孩子,最好是个儿子。有财觉得只有这样,这个家才能够尽快地好起来。
代祥娃的后事安排完之后,有财亲自把碎女子送到了牛娃家。
这一次,他没有打发他的老婆去。
责任编辑/乙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