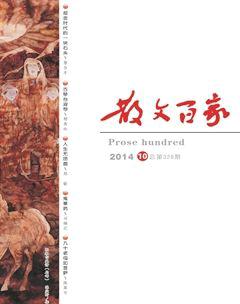一个孝字孝几春
王成均
一
再过一个月,母亲该过八十九岁的生日了,也就是说母亲开始吃九十岁的饭啦。九十岁,我掰着指头算呀算,怎么也算不出母亲走过的路有多长,吃过的苦有多重,付出的爱有多沉。这长长短短、轻轻重重、沉沉浮浮的算法,一次次剥离我的良心和道德。我扪心自问,养儿防老,我的母亲养儿防老了吗?
我痛苦地摇了摇头,回答是否定的,我没有。十年前的九月三十日,七十六岁的父亲选择国庆长假的头天离开人世。父亲去世的那天,我还在市里和团市委副书记刘拥兵一道为推介刘梅的先进事迹报告会奔波着,一场接一场的报告会为市里的孩子送去了一顿顿精神的大餐,而我的母亲正陪着父亲在老家的乡卫生院度过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那一年,母亲七十九岁,比父亲大三岁。
在老家,我和大哥为父亲办了七天丧事,我用数万元工资购买的鞭炮把父亲热热闹闹地送上山。七尺黄土,几块棺木,把我与生我育我的父亲隔成阴阳两半。阴间的路上,父亲有爷爷奶奶、大姐、几十个堂兄堂弟和嫂子们结伴,我相信,父亲一定不会寂寞;而阳间呢,只留下孤独无助的母亲和为了名利奔波的我。
父亲去世的日子,母亲的声音哭哑了,泪水流干了,身子哭垮了。哭了一辈子哭嫁歌的母亲在父亲去世的日子里,时时刻刻握着父亲冰冷的手,不断抚摸着父亲干瘦的脸,诉说着五十七年的相亲相爱。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可她的哭诉让我这个读过三年中文系的儿子听得肝肠寸断,那是五十七年相濡以沫凝结的爱呀。
二
父亲去世后,按中华民族的传统,应守孝三年。可为了升迁,为了博得领导和同事们的口碑,国庆长假一结束,我就把悲伤藏在心底,将悲愤欲绝、生死不离老家的母亲强行“捉”进城,美其名曰怕母亲睹物思人,实际上是怕母亲过度悲伤身体弱了,无法帮我料理家务。
人的自私最怕的是包裹一层漂亮的外衣,让人看不出他的灵魂有多脏、有多丑陋。毫不隐瞒地说,我一直活在生命的忏悔里,活在道德良心的审判里。
母亲进城后,我为了转移母亲的悲伤,借口单位忙,把所有的家务撂给母亲,想让母亲在繁重的劳动中忘记父亲。可在城里,斗大居室的卫生,一日三餐的洗刷,妻子、女儿、母亲和我一家四口人经过洗衣机洗的衣服,对勤快的母亲来说是小菜一碟。无论我们安排多重的活,母亲不用半天就做完了。没事的母亲就站在五楼的阳台望儿子、儿媳和孙女归巢,大半天的时光,七十九岁的母亲等呀等,等出了城市一角儿子不孝的风景。我的家在顶层。妻子看母亲一个人天天站在阳台等,怕母亲站出病来,问我怎么办。我知道母亲在思念父亲,思念家乡的天和地,可我有什么办法呢,家乡的天和地我搬不来。聪慧的妻子说她可以搬来。我不信。妻子抿嘴一笑,她请来一辆手扶拖拉机,不知从什么地方挖来两车和家乡没有什么两样的黄土,对母亲说是从老家拉来的,她和孙女想吃母亲的酸豆角、酸包谷糊。听媳妇一说,母亲眼里多天的忧郁不见了,母亲身上多年的腰酸背痛没有了。母亲用背笼装着泥土,一回回从一楼背到五楼。楼下的人不同意,说阳台是大家的。妻子找了一个漏雨的借口,和楼下的几户吵了七天七夜。为了我的母亲,我那读过大学的妻子学会了骂人,学会了以命相搏的架势,弄得我这个丈夫一次次向邻居赔礼道歉。妻子持久的战争为母亲争回了楼顶100平方米的菜地。母亲用七十九年的经验,种植辣椒、豆角、白菜、萝卜、茄子、西红柿和葱蒜。自从有了土地,母亲干脆住在五楼楼顶,吃住在楼顶。母亲拉下的屎与尿全部成了蔬菜的肥料,母亲还逼着我们也把拉下的屎尿收集起来,她要做肥料。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年,是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了我的农民身份。没考取大学前,父母亲带着我学会了各种农活,认识了各种土地。我知道妻子拖回的土地是贫瘠的土地,种不出蔬菜来。可我没有想到,母亲就用我们一家人的屎尿把黄土变成肥沃的黄黑土。一块块菜地在母亲的伺候下青枝绿叶、绿花翠果,散发出阵阵清香。我三岁的女儿成为楼顶最大的受益者。小小的年龄,她和奶奶一起种菜,一道摘果。加上母亲养的几只母鸡,不知不觉,我们把母亲骗过了一个苦闷和彷徨期。
三
母亲住进城里,一天天忙着,我和妻子女儿一天天忙着上班上学。母亲很快和一些农村捡垃圾的老人认了亲,走在了一起,并且加入了她们的阵营。
母亲每天早上出门,晚上才回家。每天会从废品收购站拿回三元五元的角票不停地数,身上散发着垃圾的臭味。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良心变得麻木,人心变得冷酷的。我一次次撂脸色给母亲看,一次次从母亲手中抢过吃过的饭菜碗自己洗,我觉得母亲脏。我抢过母亲的碗,不让母亲洗,母亲先是吃惊,后是无助,最后是默默地流泪。我也不想给母亲解释,我想让母亲自己想明白。我不知不觉犯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通病:拐弯抹角,绕山绕水,就是不把问题和矛盾直接挑明。
我和母亲的冷战从捡垃圾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开始是愤怒,继而是脸红,最后是无可奈何,我知道我不能因为有一个捡垃圾的老母亲而不认母亲。一个人活在世上,思念可以隔断,孝顺可以隔断,但血缘永远不能隔断。母亲老了,活在孤独的忙碌里,她需要交流,需要陪伴,需要呵护。我看到母亲一回回把垃圾捡回家,垃圾的旁边就是我们的厨房。一次两次吃在散发垃圾的旁边,我还可以坚持。可时间长了,我和妻子、女儿坚持不下去了。我们选择了逃避。我们为母亲准备好一切开销,另起灶具做饭。好吃的,我们会给母亲捎一份。
母亲的话越来越少了,我的话也越来越少了。有时,陪母亲聊几分钟的天,母亲说得最多的是梦中见到了父亲,父亲怎么怎么了。听到母亲的唠叨,我知道这是母亲对我良心无声地鞭挞,我真的无地自容。
母亲的头发由灰白色变成银白色,白发由头顶开始向四周扩展。母亲晚上的呻吟声,因隔着一层楼板,我听不到了。起初,我安安心心地睡了几个好觉,可日子久了,我内心反而不踏实了。一天、两天、三天,长久的不安稳,导致了我的耳鸣,先是一声,后是一阵,最后是数十个小时,甚至数天没日没夜的鸣叫,我懂得这是良心的拷问、道德的审判。我一次次梦见母亲在父亲坟前哭泣,一次次梦见如山的垃圾把母亲的腰压得弯弯的,母亲用一双求助的眼神望着我,我跑呀跑,可怎么也跑不到母亲的身边,有时跑到母亲身边,可怎么也背不起那如山的垃圾。
四
母亲二十二岁和父亲结婚,四十三岁生我。十八岁前,我多病,母亲省吃俭用为我治病。十八岁后,母亲为我上大学、结婚生子奔波操劳。父亲去世后,我把母亲拉进城来,本想让母亲安度晚年,可母亲想到女儿读高中、读大学要的是钱,她要为孙女攒一万元。母亲对考了初中的孙女说,她一天捡垃圾可得五元钱,一个月就是一百五十元,加上五十五元的养老金,一年就是两千四百多元,五年就是一万多元,她一定会活过九十五岁,一定会攒到一万元的。
这是女儿含着泪告诉我的。我的女儿问我,什么是孝,人生的“孝”字怎么写,儿女怎样才能写好一个“孝”字?我无法回答女儿的一连串提问。是呀,人生在世,做儿女的,最难写的字是“孝”字,最难掂量的是“孝”字。我的父母亲生养了我,他们早已把自己的一生押给儿女,他们觉得自己应该为儿女操劳一生,而养儿防老永远只是父母亲的一味精神的良药罢了。
五
作为儿子,夜深人静,茶余饭后,我常常会捂住自己的良心问自己,你为父母做了几件孝顺的事,尽了几年孝顺。
父母亲生养我们,不会算伙食账,不会算尽孝账,只希望儿女活得好,一生平平安安就是他们最大的心愿,他们死后,又把这个心愿带到了九泉之下。为此,我们有什么资格不善待在世的父母亲。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的父母亲一个个过世,面对他们的遗体,我们不悲不哀,认为自己尽到了孝,不用哭泣,那才是真孝。如果我在人前人后、坟前坟后,哭过不停,哀伤不止,我们一定没有尽到全部的孝。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我们做儿女的不能老是用这首古诗在父母亲坟前安慰自己,那是我们对自己的麻醉和欺骗,那是对中华民族传统孝道的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