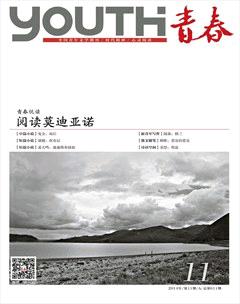走向“地平线”的“海滩人”
周娆
走向“地平线”的“海滩人”
周娆
自1968年发表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起,在莫迪亚诺近五十年的创作生涯里,“追寻”是一个常常出现的主题。可以说莫迪亚诺的小说是相当模式化的,他尝试去写“一些发生在其它背景下的事情”,但是,仍然会“以同样的方式去看事物”,这种恒定不变的看事物的眼光,使得他们这一代人“被迫老是写同样的东西”。很多作家都是按照自我设定的或深或浅的模式来写作的,莫迪亚诺只不过更为突出罢了。细细品读莫迪亚诺的小说,我们可以在似曾相识的莫迪亚诺式元素背后看到其不断开掘与突破。
一般将莫迪亚诺的小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60、70年代,着力于追寻自我,身份就是这个阶段的关键词,代表作品有“占领时期三部曲”(《星形广场》、《夜巡》、《环城大道》)和荣获龚古尔文学奖的《暗夜街》;第二个时期是二十世纪80、90年代,此时作品的主人公不再追问自己的身份,而是追寻已经逝去的青春时光,作者试图从他们当时的生存境遇来揭示人类的渺小性和荒诞性,代表作有《八月的星期天》和《青春狂想曲》;第三个时期是本世纪初,作者开始对人生进行玄学式的思考,在梦幻之重与现实之轻中探寻人的存在意义,《青春咖啡馆》、《夜半撞车》、《地平线》显示出作者本阶段的创作倾向。
受制于同一主题,莫迪亚诺的小说总是表现“同样类型的人物”,此即为贯穿他创作始终的“海滩人”形象。在《暗店街》中,莫迪亚诺借于特之口对“海滩人”形象进行了的界定:“此公在海滩上,游泳池边度过了四十个春秋,他笑容可掬,同避暑的游客和无所事事阔佬搭讪闲聊。在成千上万暑假照片的一角或衬景里,总能看到他穿着游泳裤,混迹在欢乐的人群中,但是谁也叫不上来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呆在那里。有朝一日,他又从照片上消失了,同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莫迪亚诺自己也曾经说过:“这(指他笔下的故事,引者注)也许会发生在一些没有基础的人身上。一些事业进行的不顺利,被环境、家庭、学业所围绕的人,这个阶段,我是经历过的,既不稳定又……”“海滩人”往往漂浮无根,只是一个面目模糊的影子,是别人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点缀。对于世界而言,他们只是偶尔闪现一下磷光随即消逝,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就如海滩上转瞬即逝的脚印一样。
结合莫迪亚诺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海滩人”具有如下特征:
如附骨之蛆的压力
莫迪亚诺的大部分作品是以二战期间法国被德国占领时期为背景,他曾经谈到以这段历史为创作背景的原因:“我力图写出一个没落的世界,而法国被德国占领时期正提供了这样一种气氛。”莫迪亚诺的小说又被称为“氛围小说”,作为战后的一代,他精确地营造出了二战时恐怖、压抑、令人窒息的氛围。莫迪亚诺在访谈中说到:“我总是觉得自己是污浊时代的产物,是战争的产物。人们总是在谈论‘占领时期’,可是对我而言,却并非是无缘无故的。”战争余影始终笼罩着莫迪亚诺,他也将德占时期的压力象征性地投射到他所塑造的“海滩人”身上。他笔下的人物无一不被不安全感死死地追逐,为自己的命运和处境焦虑不已,承受着现实的巨大压力。
《星形广场》中什勒米洛维奇的犹太女朋友达尼娅就是因无法忍受法西斯的噩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夜巡》中的“我”处在两个对立组织的双重压力中惶惶不可终日,希望这种日子早点结束,又害怕自己的身份被识破,精神濒临崩溃。《暗店街》里有一群冒着生命危险也想要逃到中立国的年轻人。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我”常常熄了灯,躲在窗帘后面观察街上警察的动静。就连最近的《地平线》也笼罩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博斯曼斯户籍上的母亲是红发女人,跟她形影不离的是模样像还俗教士的德国男子,而他的亲生父母是否因战乱逃难或是生活所迫将他抛弃?玛格丽特出生在柏林,她的亲生父亲会不会是在战争中阵亡的德国士兵?而她的母亲是不是为了洗刷过去而自愿去德国工作?这些问题,书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但是我们不难根据字里行间作出如上猜测。
《青春咖啡馆》隐含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阴影,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人们对不满十六岁的青少年实行宵禁。因而露姬的夜游充满着被警察抓住的危险,露姬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唤起母亲对她的关注。
《青春狂想曲》表现了战后光怪陆离的法国社会。男女主人公路易和奥迪尔,一个父母双亡,孑然一身,服罢兵役,无处安身,只能浪迹街头,一个生下来就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年少时就有犯罪记录,又被公司解雇,失业在家。这一对青年男女步入社会时就不得不忍气吞声,寄人篱下,在泥沼一样肮脏的社会环境中痛苦挣扎,任人侮辱,正派的艺术家被迫自杀,而流氓无赖却逍遥自在。最后他们选择居住在宁静的乡村,也可以理解为逃离都市的压力。
与惶恐不安的心理状态相适应的是黑色和灰色的作品基调。夜幕下的巴黎才是“海滩人”们的活动场所,躲在窗帘后的“居伊”、夜游的露姬、偶遇的博斯曼斯和玛格丽特穿梭于其间,似乎他们的一生都是耗费在这些幽暗、朦胧的地方。《夜半撞车》更将故事直接设置在了夜晚。那浓得化不开的黑,压得喘不过气的灰,就是这些漂浮者沉重的回忆。
遗失身份
莫迪亚诺是一个喜欢侦探小说的作家,他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悬念,让我们手不释卷地一直读下去。但是他的作品又不同于真正的侦探小说,里面有侦探,有调查,有审问,有死亡,却唯独没有凶手。如果有的话,就是那让人遗失身份的记忆。
《环城大道》的主人公名叫亚历山大,但这只是他在旅馆登记时所用的一个化名,至于他的真实姓名到小说的结尾作者也没有告诉我们。“我”在17岁时看到父亲的一张发黄的旧照片,不畏艰难地踏上了寻父之路。但搞不清楚父亲是黑市走私集团的成员还是被盖世太保追捕的犹太人,为此“我”打入了走私集团内部,最后在父亲被捕时挺身而出。可是父亲是一个只拥有伪造身份证的无根的人,他还企望从儿子的一份中学毕业文凭中得到自我确认。
《夜巡》的主人公是一个双面间谍,同时为法国的盖世太保和地下抵抗组织效力。夹缝中生存的他甚至没有自己的真实姓名,对于法西斯组织来说,他名叫斯通·特鲁巴杜尔;而对于地下抵抗组织而言,他则被称为德·朗巴勒公主。他每天周旋于两个互相敌对的组织之间,他的自我意识也在这种严酷可怕的环境下产生了不确定性,“我”究竟是可耻的法奸还是抵抗的英雄。他的一生纠缠在“叛徒还是英雄”的追问中,最后以死亡来结束自身两难的生存境遇,却仍未能确定自我的性质。
《暗店街》的“我”在二战期间因偷越边境遭遇劫难,受到极度刺激,失去了关于自己过去的一切记忆,侦探社老板于特之所以收留“我”是因为他也遗忘了自己的过去。《暗店街》开始于这样一句话:“我飘飘无所似,不过幽幽一身影”,尽管于特为“我”编造了姓名和社会身份,但是对于失去过去的“我”而言只不过是没有意义的表象,“我”只是一个幽灵般的幻影,“我”可以是千千万万的“我”:于特帮“我”起名叫居伊·罗朗;而在埃莱娜·皮尔革朗的口中“我”则是彼得罗·麦克沃伊,是多米尼加人;但在女友德尼兹的出生证上记着“我”的名字是吉米·彼得罗·斯特恩,国籍是希腊。
《青春咖啡馆》里面更是充满了一群“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放荡不羁”的“流浪狗”,他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真实身份讳莫如深,一旦进入孔岱咖啡馆,他们就以伪装失忆的方式来隐瞒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孔岱这个封闭的空间为这群“大都市的无名者”提供了逃避外部世界压力的契机。她在孔岱咖啡馆得到了新的命名:“扎夏里亚站了起来,装出一副很庄严的口气说道:‘今天晚上,我为你命名。从今往后,你名叫露姬。’”从雅克林娜到露姬,她终于可以与过去决裂,摆脱掉“雅克林娜·舒罗”、婚前姓“德朗克”这一身份,成为一个对任何人而言都不重要的、只是充当配角的“海滩人”。
《夜半撞车》的主人公“我”是一个没有双亲、没有学业、没有社会地位的年轻人,在他的周围总是弥漫着一股乙醚的气味,他总是感觉自己就像一块木板漂浮于水面,任凭自己在河里随波逐流,找不到自己的落脚点。“乙醚”就象征着即将成年的“我”长久以来那种浑浑噩噩的生活,“撞车”则是让“我”清醒的当头棒喝。
磕磕绊绊追寻幸福
我们在莫迪亚诺的小说中常常看到作者穿梭于巴黎的左岸右岸,游走在迷雾般的巴黎各街区。精确的地名和位置赋予作品特别的意义,对于一群漂浮无根的“海滩人”而言,唯一能把他们固定住的就是他们生活的场所,莫迪亚诺如是说:“我一想到什么人,就必须把他放在一个地方,一条街,一栋房子里,地名能让人想起许多事情。但是精确的地址并非服务于一部过于现实的小说,而是为了引发联想。”在《青春咖啡馆》里明确描述了一种“固定点”理论:“女人,男人,孩子和狗组成的人潮像汹涌的波涛,他们攘来熙往,川流不息,最后在长长的大街上销声匿迹,在这些人潮中,我们时不时地希望记住一副面孔,是的,在保龄看来,必须在大都市的漩涡中心寻找一些固定点。”(《青春咖啡馆》,金龙格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第9页)所谓的“固定点”就是记忆的痕迹。寻找“记忆里留下的痕迹”就是莫迪亚诺的写作动机。通过“固定点”,我们可以与过去、与他人建立联系,从而在时间与空间的洪流中确认自身的存在。可以说莫迪亚诺的小说通过记忆与时间的角力展开一场寻找自我、寻找幸福之旅。
回忆总是以永恒的名义与时间作斗争,否定着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和永远向着新的终点前进的单调性。遗忘也是回忆的一种潜伏状态。“遗忘,最终把我们生命中的主要方面,有时,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中间画面都侵蚀掉了……看到这些残缺不全的画面在我们极其混乱的记忆中交相叠印,或者,这些画面在黑洞中央,时而缓缓地相继出现,时而又断断续续,怎么样排出一个最简单的顺序呢?”也许是一张照片,一本电话簿,一个地址,一串号码,一份简报,或是其他什么,唤醒了沉睡的记忆,筑成了通往过去的甬道。
《青春咖啡馆》里为了查明神秘女子露姬的真实身份,四个叙述者(巴黎高等矿业学校的大学生、私家侦探盖世里、露姬本人以及露姬的恋人罗兰)纷纷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述露姬短暂的一生。读完小说,我们可以发现露姬只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年轻女子,她一直想逃离自己之前的人生,“只有在逃跑的时候,我才真的是我自己。我仅有的那些美好的回忆都是跟逃跑或者离家出走连在一起。”露姬同时也是一个极度渴望幸福的人,她渴望遇到某个人或者某件事能够引领她逃离过去,走向幸福:年少时她选择夜游,试图摆脱枯燥无味的生活;她结识女友亚娜特,造访过毒品营造的天堂;她求助于婚姻,但是让·皮埃尔·舒罗给不了她想要的东西;她寄希望于文学,在书籍中寻找精神慰藉;她置身于咖啡馆,混迹陌生人中以摆脱孤独和寂寞。可以说,露姬一直在逃离,也一直在寻找。
《夜半撞车》是年近花甲的“我”对自己“即将步入成年那遥远的日子里”发生的往事的追忆。巴黎的深夜,孤独漫步街头的“我”被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牌轿车撞倒,并与肇事车主雅克琳娜·博塞尔让有短暂的接触。等“我”清醒过来,却只身躺在一家陌生的诊所,这名女子已经不见踪迹,只留下一沓装在信封里的钞票。为了弄清事实,“我”踏上了寻找神秘女子之旅。在一系列调查过程中,“我”关于过去的回忆也被勾起,少年时的颠簸,青年时的穷困,成年前的浑浑噩噩呈现在读者面前。与其说“我”是想弄清事故原委,不如说“我”是想借撞车事件来终结之前浑浑噩噩的生活,“我惟一应该控告的是我自己,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生活得一塌糊涂。而这次撞车事故把这些年的混乱和不确定画上了句号。”当轻纱般的薄雾散尽,“我”终于找到了雅克琳娜·博塞尔,却发现一切都并非我想象的那样。生活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
《地平线》的叙述者让·博斯曼斯在寻找他一生中的“暗物质”,回忆四十年前的一次偶遇。二十一岁时,他偶然结识了出生在柏林的布列塔尼姑娘玛格丽特·勒科兹。玛格丽特从阿讷西逃到洛桑,又逃到巴黎以躲避一个名叫布亚瓦尔的家伙。博斯曼斯则不断变幻住所,以躲避他那红发母亲和样子像还俗教士的德国男子。这两个孤苦伶仃的人因为过去的纠缠没有办法过上正常的生活,无法到达“地平线”。博斯曼斯“从童年时代起一直感到却不知为何感到的犯罪感,以及经常像走在流沙上的不舒服感觉”,玛格丽特则一直担心“在她的一生中,这黑色身影是否会永远把她的地平线遮盖”。一次突然的逮捕,让玛格丽特骤然离开了博斯曼斯,也将这幸福的一年永远地留在了博斯曼斯心中。
《地平线》是莫迪亚诺2010年的作品,从这本书可以看到莫迪亚诺更为专注地思考人类的生存状态,他玄学式提出对于生活而言,时光的流逝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对于博斯曼斯来说,重要的是他与玛格丽特相识相恋的这一年,这幸福的一年在他的记忆力难以磨灭,使得他们分开的这四十年显得微不足道。博斯曼斯一直在期待着能与玛格丽特重逢,漫长岁月里他有过怀疑却从没失去希望,“在怀疑时,至少还有一种希望,有一条逃逸线朝地平线逝去。我们心里在想,时间也许没有完成它摧毁的工作,以后还会有见面的时候”。
首先书名就值得我们注意,地平线是天与地的尽头,一个向着地平线奔跑的人总是充满了对未来和幸福的渴求。而其2007年写作的《青春咖啡馆》露姬试图通过文学书籍来汲取精神慰藉,她出现在孔岱就紧紧攥着一本《消失的地平线》。这本书是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的作品,消失的地平线指的是香格里拉,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在莫迪亚诺小说中,“地平线”就是幸福的象征。
回顾他近十年来的创作,《夜半撞车》已经出现了人冲破朦胧黑夜的萌芽,《地平线》更是首次出现了充满希望的结尾:四十年后,博斯曼斯已经成为了一名作家,他在网上查到玛格丽特·勒科兹在柏林开设了一家名为拉季伊尼科夫的书店,于是就前往柏林去寻找她。小说在此戛然而止,这也是莫迪亚诺一贯的结局,余韵无穷。但相比于露姬的纵身一跳,终结自己追寻幸福的旅程,我们满怀期待地憧憬博斯曼斯与玛格丽特穿越漫长时光的相聚。可以说这个带着金色阳光的结局终结了莫迪亚诺之前作品的阴霾。对此,莫迪亚诺回答说:“年轻时,你对事情的看法会更加悲观,后来,时间一年年过去,你会看到事情不是那样一清二楚。过去使你感到痛苦的事情,你有时会觉得微不足道。”时间也或深或浅地改变着作者,年轻时我们追求一种稳定的身份感,追求与他人建立稳定的关系,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复归平静。人总是带着希望活着的,时光总会慢慢抹平无所归依带来的不安和焦虑。
走向“地平线”的“海滩人”也标志着莫迪亚诺的一场追寻,从个体的苦苦挣扎复归到个体的生机与活力。怀着希望走向地平线也许这才是真正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