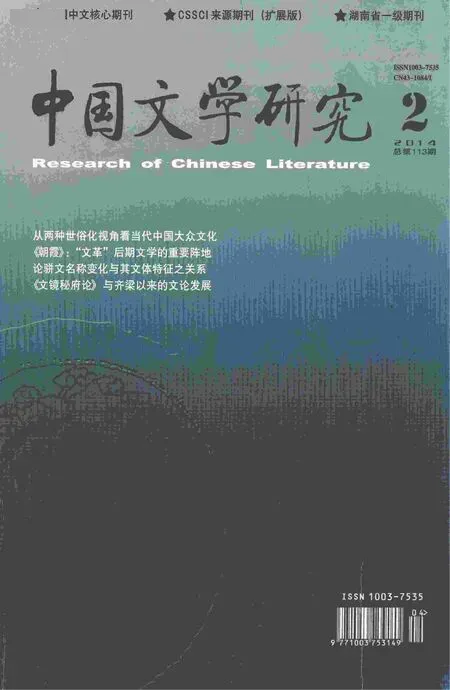大众文化研究的“新左派”范式再考察
肖明华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一
在大众文化几近日常生活化的今天,学界时有大众文化研究成果出现。《日常生活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影像书写——大众文化的社会观察》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当代文化研究网、左岸文化网以及“青年文艺论坛”上,也偶有相关成果面世。这里不拟具体地考辨之,而仅只再考察与之相关的大众文化研究“新左派”范式本身,因为综观其中某些成果,可以发现其言说方式与话语逻辑与这一研究范式颇有渊源。
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已历经三十来年。但大众文化的研究在1990年代才浮出水面。1993年陶东风发表的《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是国内较早的大众文化研究文本。一定意义上,此文正式开启了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历史。自此以后,大众文化研究朝纵深发展。相应的研究范式得以逐渐形成。“新左派”范式即是其中之一。
从文献看,“新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的出现,恐怕是在1995年前后。但作为一种范式被承认,则是1997年的事儿。那一年,《读书》杂志刊发了以“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等“关键词”为话题的一组笔谈。这被视为“新左翼的象征性表述”,“标志着在大众文化研究方面理论运用的一个重要转变”。从此以后,一个可名之为大众文化研究的“新左派”范式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其成果迄今不绝。
“新左派”非常重视大众文化。依其之见,大众文化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它裹挟的“新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构造功能。李陀指出:“大众文化可能正在成为今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藉以建构起来的主要动力和主要机制”。一个人文学者如果不研究大众文化则不能理解变动中的当代社会文化现实,更不可能参与乃至改造社会文化现实,其生产的知识话语恐怕也不具阐释力。基于此,“新左派”学人勇于面对挑战,甘愿经历痛苦的学术转型,主动调整知识结构,建构新的言说话语和阐释框架。戴锦华曾回忆说:“90年代以后我始终处于相当茫然的状态。……我经历了一场‘知识的破产’。自己过去所娴熟使用的大部分理论和方法都在新的现实面前显出了苍白无力。”戴锦华等“新左派”知识人的描述乃当时学人的普遍感受,非常真实。
多年后,历经那个年代的众多学人都有相似记忆。王晓明与蔡翔在一次对话中,还具体提及了1990年代的主导性知识资源从哲学、美学、心理学到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转型的问题。只不过,面对这种转型,有学人依然从事体制内的专业文学研究。而“新左派”学人则跨出学科界限,意欲在大众文化场域中建立“文化领导权”。这说明“新左派”研究者对社会文化事实的观察是敏锐的,同时也说明他们已然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唯物主义”观念,甚至持有有机知识分子的情怀。这是值得肯定的。
二
“新左派”学人从事大众文化研究并非要从中窥视那抽象的审美、道德问题。其目的是透过大众文化来观察1990年代市场经济语境下的“意识形态政治”。诸如贫富悬殊、阶级分化问题即是其主要的观察点。其基本的判断是,大众文化裹挟着一种特有的“新意识形态”,并以一种“隐形书写”的方式展开其实践。在看似与官方或主流的对抗中,又暗度陈仓般地与之合谋,以获取官方的支持,并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对此,汪晖早已指出:“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恰恰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
几年以后,戴锦华也表达了相近的意思:“90年代,大众文化无疑成了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大众文化的政治学有效地完成着新的意识形态实践”这即是说,大众文化在与官方或主流的合谋中,共同书写着这个时代的好生活想象,并实际地构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这个全新的社会结构,其凸显的是各种各样的资本、欲望、消费、享乐等等符号所表征的一种“新意识形态”。这一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在大众文化的参与下,完成得那么自然而然,实乃“绝妙”的“隐形书写”。戴锦华在《大众文化的隐形政治学》一文中,对此予以了较为具体而精彩的分析。她以“广场”这个词为例。广场这个本来具有政治意味,甚至具有革命想象的语词,已然非常普遍而又自然而然的挪用作了商场的代名词,这就“似乎在明确地告知一个革命时代的过去,一个消费时代的降临”。换言之,新意识形态已然合法化了,并主宰了这个时代的想象空间。
在“新左派”看来,“新意识形态”的这种主宰,遮蔽了对底层的生存关切,并且将底层自身的阶级意识和反思能力都消解殆尽。有学者为此指出:“由广告和传媒塑造成形的……这些流行想像已经蒙住了许许多多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经济发展背后的隐患,看不见生态平衡的危机,自然更看不见‘新富人’的掠夺和底层人民的苦难,甚至使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些事情。”那种发展主义及结构性原因导致的社会不平等、非正义问题在大众文化的隐形术中遁入无形。
“新左派”的大众文化批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这个时代的变化有较为准确的把握,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代的症候。它对阶级分化的关注和对新富阶层合法性的质疑,这对1990年代以来的贫富分化现实的确有较强的针对性。其关注弱势群体,批判权贵,为底层说话等等,也有可贵的批判性和人文情怀。这无疑是有道义上的优越感,值得肯定。在资本逻辑几近蔓延整个世界的语境下,它对“新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思考使得其理论研究还带上了一定的国际视野,使得“新左派”的知识话语具有反思全球现代化的意味。这些都可圈可点。
“新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范式的影响力因此并不可小觑。此后,人们在涉及大众文化问题时,不得不考虑“新左派”研究者所考虑的问题。比如,多年后有学者在底层问题的研究上还自觉不自觉地对“新左派”予以了一定的“回应”:“不管存在多少分歧,这一点显而易见:大众文化并非直接抵达底层,表述底层。遮蔽还是敞开?这只能取决于底层与大众文化之间持久的博弈。”此外,“新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彰显了政治经济学的维度,这在后革命时代,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已然文化唯物主义转向的语境下,显得弥足珍贵。
三
然而,“新左派”范式也有其较大的局限性,它集中表现在没有对大众文化做语境化分析。如果说1980年代的大众文化无可争辩地具有反体制特点,那么1990年代的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续了这一特点,它并非一种官方文化,更没有与体制合谋。毋宁说,它伸张了一种社会文化民主的梦想。这一点可以从1990年代最初几年里最具代表性的王朔文化现象看出。王朔以其痞气十足的风格解构了特定时期意识形态政治的权威,这几乎是一种常识。有学者为此非常理性地指出:“中国大众文化以其颠覆性与反叛性,成为‘文革’后解构革命话语的催化剂;中国大众文化用感官愉悦、读图想象代替了传统的宏大叙事与理论说教,使大众文化呈现出有别于主流文化的新特质”。大众文化的这些特质在1990年代中后期也很明显。它在引导个体心性结构与整个社会走向开放、自由与宽容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而如今,大众文化依然还承载着大众阶层实现梦想的功能,它之作为特定生存环境下人们对社会文化的民主化想象之表征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大众文化在特定语境下是具有较强的公共精神及政治意义的。也因此,我们认为要用公共批评的范式去对大众文化进行批评。
即使退一步说,1990年代的大众文化“沉沦”为了中产阶级趣味,但这种“沉沦”也并非简单地表明大众文化与主流权力合谋了。我们要思考的也许是,主流体制提供了多少大众文化发展的空间?是什么样的文化环境使得大众文化放弃必要的担当而在“沉沦”中“娱乐至死”,心甘情愿地戴着畸形的“消费意识形态镣铐”跳舞?我们在批判大众文化局限之时,也应该联系语境去做具体地分析,而不应该抽象地批评大众文化。有学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左派并没有……令人信服地揭示出资本是如何在中国特殊的经济与政治体制中运作的,在资本与权力、市场与原先遗留的政治体制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这样的质疑是切中肯綮的。若能很好地回应这些质疑,“新左派”恐怕就能得出更为合理的大众文化观。
有学者主张用公共理性的视野去对大众文化进行批评,“以推进我们大众文化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公共领域,恢复大众文化‘实质未受损害的文化’”。“新左派”大众文化研究者显然没有此一意愿。这使得其研究范式在批判大众文化局限的同时,遗忘了1990年代大众文化的积极功能,一味地把大众文化“丑化”,甚至视之为一种“敌对”的文化。这则与其思维方式有关。“新左派”的批评者还常常持“意识形态”的冷战思维。不愿承认今日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不肯对实际的社会进行理性地分析。他们完完全全地把作为学术实践活动的大众文化研究变成了一场直接的意识形态斗争。难怪有学人会说:“‘新左派’的真正兴趣根本不在于研究大众文化而是借此骂消极自由者。”虽然大众文化研究难免有自己的倾向,但“新左派”的倾向或也太不自然而然了。如此境况之下,怎么可以得出有说服力的大众文化观呢?比如有论者说:“大众文化已经变为了‘小众文化’,是‘西方式大众文化’,是中产阶级文化,因此要维护人民大众的文化权益。”认为大众文化变为了小众文化的确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恐怕更多的是一种逻辑推理所得。在“新左派”看来,大众文化乃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而中产阶级在中国不占大多数,自然而然就得出了大众文化不是大众的文化的结论。这种把“中产阶级”视为人民大众之外的说法,是一种过度受制于阶级意识的表达。其实,中产阶级也是人民大众。
“新左派”打着人民大众的旗号这一点还是可疑的。在后革命氛围里,人民大众已然不是一个抽象的阶级语词,更不能将它理想化,它也不能成为正义的化身。人民大众与中产阶级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有学者在研究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时指出:“统治系统通过满足人民的需要(无论多么有欺骗性)而‘收买’人民,而左派则在批评资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同时,贬低人民的物质需要本身,而不是寻找更加进步的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这种理论只能建立在下列前提上:人民将抑制自己已经在统治系统中得到满足的需要,遗憾的是,这个前提当然是一厢情愿的。”费斯克所指出的这个非常契合现实语境的问题,是值得“新左派”认真考虑的。人民大众并非一个本质的概念,把它视为铁板一块的做法是不合适的。有学者不无道理地指出:“当代大众文化的表述,断然消解了‘经典’的想像性表述,而大胆凸现感性、即时和碎片化的大众生活经验。这种崭新的城市表述,尽管缺少体现任何具有实质深度的价值持久性,然而它却有可能通过平凡而富有诱惑的欲望叙事,安慰现代大众对世俗幸福生活的‘渴望’,实现大众对理想生活的永恒梦想。”从这个方面说,大众文化其实很人民性的。王朔曾指出:“可以从各种角度批判大众文化,就是不要从‘人民性’这个立场出发,因为那是大众文化本身的立场。”
因为缺乏语境化地分析,“新左派”批评者所指出的大众文化问题即使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真问题,其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不可取的。伴随着1990年代现代化而生的如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即使要“革命”的解决,但“革命”也不应该简单地指那种“均贫富”式的,将目标锁定在生活“必需品”上的低层次革命。依阿伦特之见,那不是好的革命,甚至不叫革命。“只有发生了新开端意义上的变迁,并且暴力被用来构建一种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体,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那才称得上是革命”。阿伦特所言之革命,我们恐怕尚缺乏经验。它之需要与否也尚可讨论。但如果不是此一意义上的革命,恐怕还是“告别”的好。“新左派”学人未加分析就对李泽厚等人的“告别革命”说予以否定,除了其革命观的原因,恐怕也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告别革命”乃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大众文化之所以不大众的缘由。对此,陶东风先生曾理性地指出:“我们既不可能简单天真地鼓吹革命暴动,回到‘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也不可能廉价地(也是完全和乖巧地)宣称‘告别革命’,而是把革命当作认真严肃的学术问题进行反思。”只有理性地看待革命,我们在面对大众文化的所谓新意识形态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出更为合理更为复杂的判断,至少不会简单地二元对立地看待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在否定那种应该否定的“革命”方面是有贡献的,同时大众文化在期待那种应该期待的“革命”方面恐怕也是有担当的。“新左派”大众文化研究者几乎完全忽视了大众文化的成绩。难怪有学人质疑说,“新左派”在言说中产阶级隐形术的时候,是否也遮蔽了不该遮蔽的东西?
四
“新左派”大众文化研究者大多出自文学专业。由此我们不妨顺便提及一下相关的文学理论研究问题。不妨说,1990年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关注大众文化,将之作为研究对象,以此来生产有关这个时代的知识,既而把握时代的脉动,参与到这个时代的公共生活之中,这已然是一个必要的选择。这也是由大众文化的性质以及它在当今时代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因为“大众文化的特征是话题型,而非系统型或逻辑型的。所谓话题型是指大众文化是跨符号系统的,它……打破各种界限,围绕着社会的热点话题或时髦话题而展开,这些话题又同当下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研究大众文化,因此是知识生产者切入现实的一种方式。大众文化的文本为此值得被细读。而因其与“文学性”的关联,以及文学在1990年代的大众文化化的事实,甚至“无论从哪方面看,大众文化都成了当今主要的文学形式”,这就为文学理论研究者涉猎大众文化提供了足够的理由,也因此可成为该学科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方案。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有学者略显模糊但也很是敏锐地,以大众文学为例指出:“新的文学理论也将在与大众文学的相互‘争吵’、‘批判’和‘对话’中显出自己的新貌。”“新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是一种自觉的文化研究。在跨越学科界限,调整研究对象、采用新的研究方法、转换研究目的等方面,都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敏锐和研究自觉。它把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带入了新境。虽然不同的学科背景,相异的理论立场及阐释框架,会影响到这种知识生产的有效性程度,但只要其生产的知识能建立起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的真实关联,只要这种关联多少有助于人们理解这个大众文化化了的文学世界乃至整个的社会生活,既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人性建设,促进共同体生活往更好的方向走去,那就可以成其为一种“文学理论”知识。“新左派”已经让文学理论转型走在了路上。意识到这一点,恐怕并非不重要,因为未来的文学理论研究要走向自觉,就难免要回望并重视这种转型。
然而,多年以后还有学人指出,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的原因之一即是它关注大众文化的力度还不够,建设文学理论要积极介入大众文化。诸如此类的有关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判断,即使在十年后的今天恐怕也依然有效。这难道是由于1990年代的大众文化研究被遮蔽了,因此需要重申?还是由于大众文化虽已研究,并几近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但其与文学理论的关联未曾合法化呢?答案恐怕都是肯定的。由此,我们有选择性地对19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及其研究范式进行回望恐怕是必要的。
〔注释〕
①之所以称之为“再考察”,乃是由于在学界已有陶东风先生做了相关工作。本文对陶东风先生的相关成果有自觉吸收。特此说明并致谢!
②1995年出现的重要文献有:汪晖:《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电影艺术》1995年第1期。李陀:《“开心果女郎”》,《读书》1995 年第 2 期。
〔1〕张贞.日常生活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J〕.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张慧瑜.影像书写〔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3〕谢轶群.流光如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陶东风.欲望与沉沦〔J〕.文艺争鸣,1993(6).
〔5〕陈建华.帝制末与世纪末〔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6〕李陀.“文化研究”研究谁?〔J〕.读书,1997(2).
〔7〕戴锦华.犹在镜中〔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
〔8〕王晓明、蔡翔.美和诗意如何产生〔J〕.当代作家评论,2003(4).
〔9〕汪晖.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J〕.电影艺术,1995(1).
〔10〕戴锦华主编.隐形书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1〕王晓明主编.在新的意识形态的笼罩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12〕戴锦华.大众文化的隐形政治学〔J〕.天涯,1999(2).
〔13〕王晓明.半张脸的神话〔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
〔14〕南帆.底层与大众文化〔J〕.东南学术,2006(5).
〔15〕周骅、黄宗喜.喧嚣与骚动〔J〕.当代文坛,2013(6).
〔16〕肖明华.走向公共批评的大众文化研究〔J〕.山西师大学报,2010(5).
〔17〕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18〕和磊.公共理性视野中的当代大众文化批判〔J〕.文艺评论,2012(5).
〔19〕陶东风、和磊.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0〕马龙潜、高迎刚.人民大众的文化权益〔J〕.文艺报,2005-7-28.
〔21〕陶东风.超越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J〕.学术交流,1998(6).
〔22〕徐国源.‘都市想象’与大众表述〔J〕.江苏社会科学,2012(2).
〔23〕王朔.我看大众文化〔J〕.天涯,2000(2).
〔24〕阿伦特.论革命〔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25〕陶东风.革命的祛魅〔J〕.渤海大学学报,2010(6).
〔26〕刘小新.文化研究的激进与暧昧〔J〕.文艺研究,2005(7).
〔27〕蒋原伦.大众文化的兴起与纯文学神话的破灭〔J〕.文艺研究,2001(5).
〔28〕赵勇.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J〕.文艺争鸣,2004(3).
〔29〕张法.中国文论转型的几个维度〔J〕.思想战线,1994(4).
〔30〕陈传才.当代文化转型与文艺学的重构〔J〕.文艺争鸣,2003(3).
〔31〕李春青.在消费文化面前文艺学何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