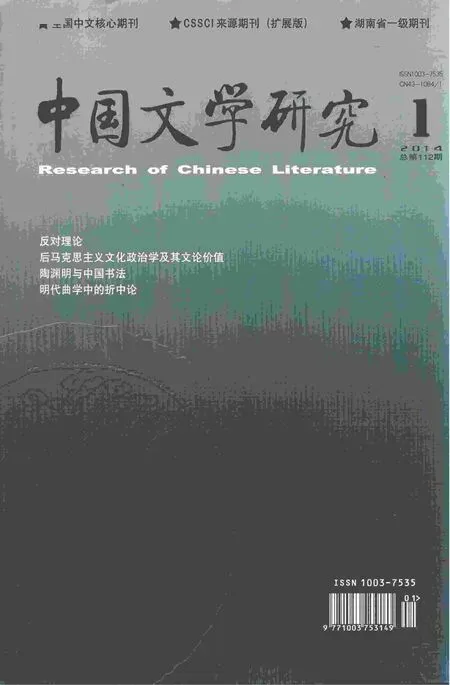论李涵秋“沁香阁”诗
伍大福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无锡分院 江苏 无锡 214153)
近代诗歌,汪辟疆是最有影响的研究者之一,他将之分为六派。“第一是湖湘派,以王闿运为领袖,提倡汉魏六朝诗,和宋诗派相抗衡。第二是闽赣派,即同光派,以陈宝琛、郑孝胥、陈衍、陈三立为领袖,宗尚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兼及李白、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孟郊、梅尧臣、王安石、陈师道诸家,一时羽翼呼应者甚多,成为近代声势最大的一个流派。第三是河北派,以张之洞、张佩纶、柯劭忞为领袖,张祖继、王懿荣、李刚己、严修诸人为羽翼,推崇杜甫,出入韩愈、苏轼,虽然与闽赣派宗旨相近,但一为直溯杜甫,一为取径黄庭坚,又有不同。第四是江左(江浙)派,以俞樾、金和、李慈铭、冯煦为领袖,翁同龢、陈豪、顾云、朱铭盘、周家禄诸人为羽翼,取法唐人,宗风在钱起、刘长卿、温庭筠、李商隐之间。第五为岭南派,以朱次琦、康有为、黄遵宪、邱逢甲为领袖,谭宗浚、潘飞声、丁惠康、梁启超、麦孟华诸人为羽翼,或取法杜甫沉郁之境,或学习白居易讽喻之风,致力于社会变革,多以诗歌咏叹古今,指陈得失。第六为西蜀派,以刘光第、顾印愚、赵熙、王乃征为领袖,王秉恩、杨锐、宋育仁、傅增湘、邓镕诸人为羽翼,诗歌宗尚介于唐宋之间,追求绵远的情韵。这六派覆盖了中国近代诗歌创作的主要地区,也体现了近代诗歌的主要特色与成就。”由于扬州在近代的没落,尽管当时扬州文人的诗社——冶春后社在当地极为知名,诗歌创作也比较丰富,但传播与影响非常有限,基本没有进入同时代人和后人的研究视野。而李涵秋为人特立独行,虽然与冶春后社中不少诗人多有交往,也深得诗社盟主臧谷的称赏,但他并没有加入冶春后社。但李涵秋后来大约是当世扬州本土之外最有影响的一位诗人,其诗自具面目,后期诗作被时人誉为“得陶诗神髓”,其人在辛亥革命前的武汉诗坛被尊为“诗伯”,忽略李涵秋,近代诗歌研究尤其是晚清诗歌研究应该是不完整的。
李涵秋(1874—1923),名应漳,字涵秋,别号韵花馆主、沁香阁主,生于扬州一个经营烟业的小生意人家庭。父亲早逝,自幼家计艰难,年十六即设帐授徒,“岁入修脯,半资家食,半制衣履”(李涵秋《小沧桑志(自十六至二十五岁)》)。光绪乙未(1895)岁试冠军,得补廪膳生。随后放弃举业,立志于诗古文词。自光绪丙午(1906)年始,涵秋应乡人之邀奔走武汉,任观察府西席。此间涵秋除了尝试小说创作外,主要还是进行诗歌创作,直至宣统元年己酉(1909)离开武汉。涵秋之诗虽然有一些诗友唱和、迎来送往、吟风咏月的闲适之作,但诗人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国事之艰,民生之苦,家庭之困,谋生之劳,亲朋的生离死别,诗中也有不少反映。由于涵秋以小说家名于世,他的诗名在后来的文学史中几乎湮没无闻。本文着重探讨李氏诗歌创作,以补学界缺憾。
一、沁香阁诗概说
李涵秋的同乡好友贡少芹曾在《李涵秋》一书中指出:“由十七岁起,以迄三十六岁止,此二十年中,皆有著作,共成十有八册。三十六以后,君一志从事于说部,不复吟咏矣。”涵秋三十六岁(1909)之前共作诗三百四十余题,六百多首,之后就“冗于笔墨,不常作韵语”了;逝后四年,即民国十六年(1927),友人李警众将其十七岁至三十六岁诗作按时序编为两册《沁香阁诗集》,由上海震亚书局出版。沁香阁诗,若以体裁论,近体律绝占大多数,有五百一十多首;古体和歌行体虽然只有一百多首,但呈现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多的态势,且主要集中在二十八岁以后的九年中,多达九十首,这显然与诗人生活经历的丰富、诗歌技巧的成熟与抒情方式的递进有关。单就律绝二体论,律诗尤其组律的写作也呈现出此种态势。二十九岁时(1902),涵秋因家计艰难第一次离开扬州去安庆就馆,此后四年又去武汉,本年也是沁香阁诗诗风发生变化的一年,因此,我们可以这一年为界把他的诗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索之《沁香阁诗集》,前期诗作中提到的诗人:唐代有李白、白居易、杜甫、杜牧,魏晋有阮籍、曹植,清代有王渔洋;后期诗作中提到的诗人除了前述诗人外,又有陶渊明、王粲、苏轼等人。我们当然不能仅仅根据沁香阁诗中所提到的诗人来判断其所学以及其风格,但是至少能说明涵秋对这些诗人熟悉的程度高些,或许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根据涵秋自道以及贡少芹的看法,沁香阁诗早年主要受到白居易和杜牧的影响较大,多“香艳”、“绮丽”之词,诗人衣食基本无忧,又经受了情感挫折,言为心声,难免“曼声绮调”;后来家计艰难,游幕旅食,贫穷愁苦,情感渐转深沉,言词淡远,有时也不乏牢骚激越之词,所以具有老杜、渊明之风致。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清代扬州诗坛生态对沁香阁诗的直接影响。
纵观清诗史,有清三百年扬州并没有产生过著名的大诗人。但是康乾嘉道年间,扬州凭借独特的经济、交通地位,吸引聚集了许多诗人,这些诗人多为因生活所迫而依附盐商、官府的寒士,这些寒士诗作的抒情特征在沁香阁诗中也体现得极为明显。道光以后,太平军兴,盐业衰败,运河阻塞,扬州的区位优势尽失,四方布衣寒士来扬旅食者日少,诗歌多存于扬州民间的不第寒士之口。
清末民初,扬州最著名的诗人团体是冶春后社,该社之所以号称“后社”,是相对于康乾年间的“冶春诗社”而言的。“冶春”得名于顺康年间曾经任职扬州的诗坛盟主王士禛的《冶春词》,涵秋二十四岁时曾作组诗《和王渔洋冶春词江都童大令外课取第三名》,其一云“:两岸疏篱系短舟,落花随水水东流。平山此去无多路,露个青帘即酒楼。”颇饶渔洋山人的“神韵”风致。自王士禛以下,承平时期的历任两淮盐运使多有风雅之举,借冶春诗社而雅集文士,举行红桥修禊活动。道咸以还,扬州屡遭兵燹,其事稍息。直至光绪中,辞官返里的臧谷创立冶春后社,诗友多为扬州本土的不第寒士,其时涵秋年尚即冠,未与其事。扬州自清初直至嘉道间一直是布衣寒士诗人麋集唱和的圣地,冶春后社的布衣寒士诗人进一步平民化市民化,他们的常聚地点只是一家名曰“惜馀春”的小酒店。“平民化世俗化了的寒士诗歌,其生动形象性、客观真实性都是庙堂文字所无法比拟的,它对世道人心的反映,也远比寄迹廓庑的庙堂文学要广泛深刻得多。而在艺术上,正如‘穷’而‘工’之规律所揭示的那样,寒士诗歌独具其感发人心的意味。……以文章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目标之手段,以弥补立德立功之缺憾,故呕心沥血以从事,……而寒士于诗体演进、诗题拓展、语言变化(通俗化、口语化)的贡献,更是不言而喻的。”论者的这一段话主要是针对嘉道年间的寒士诗群而发,而以臧谷为代表的冶春后社的诗人群体的境遇比之更为困顿,“时当清末,变法伊始,或困于资,或狃于习,文人学士,歧路徘徊,不得已诗酒自娱,消磨岁月。其情可悯,其志堪怜”。涵秋虽然没有参加冶春后社,但其诗歌精神与他们是有共同之处的,诗社的活动也经常邀请他参与。其诗继承了寒士诗歌的传统,多用赋比的手法,体征了“诗与人合一”的创作精神。
二、前期多以绮语呈疏狂
涵秋前期诗歌三百余首,不到《沁香阁诗集》的一半,且多为简短的律绝,长篇歌行约十六首,五古四首,诗作的体式选择往往制约了内容的抒写,因此,涵秋前期诗歌多为写景抒情之作。至于涵秋早年写诗的初衷和为诗的旨趣,其十九岁所写诗序颇见一斑:
春光明媚,动草生隋苑之悲;秋雨萧条,唱枫落吴江之句。于以知古人即情写志,对景抒怀,未尝不借佳句之流传,动后人之景慕者也。仆也生当晚近,志在萧骚。游宦何心,门少乘车之客;谋生乏术,家无负郭之田。慕白傅之情多,言言绮丽;羡青莲之志达,故故疏狂。于是月下徘徊,悟三生之夙业;花前沈醉,证一笑之姻缘。鸳谱传来,人拈红豆;鱼书寄去,梦幻黄粱。明知流水东风,都成虚境;无奈浮云皓月,难忏痴心。所由金钥虽严,莫锁怀春之约;况是玉楼深贮,并非没字之碑。乘夜月之苍茫,挑灯握手;忍晓风之凄寂,垂幕谈心。感慨成诗,半属曼声绮调;纵横信笔,未删俚句荒辞。不敢冀人必我知,一点龙睛而飞去;要不过情随境触,稍留鸿爪于将来。是以沁到诗脾,弁一言于冠首;欲说香生齿颊,仍有望于同心。
就这段文字而言,证之于《沁香阁诗集》,我们可以看出涵秋前期之诗的主要风格是“绮丽疏狂”,贡少芹说他“竭力学晚唐”,涵秋自言羡慕李白和白居易,晚唐诗人本有受白居易和温、李影响的两派,因此二人的说法不无相通之处。涵秋二十一岁《题家镜庵二弟<漱香诗稿>》中的两首绝句如此指点其弟作诗:“枯肠镇日费寻思,老却春光总不知。检点闲情入诗句,梨花风雨闭门时。 莫教绮语窒聪明,莫把痴怀苦自萦。可识阿兄方忏悔,一生憔悴误多情。”似乎是说作诗不必在乎“绮语”、“痴怀”,而要关注自然、生活,才能写出好诗。但他二十二岁的《春词有序》又说“绮词靡语,辄移我情”,这就透露出他前期的喜好还在“绮语”。同时代的扬州诗人、冶春后社的成员李伯樵在涵秋二十七岁时曾作《赠涵秋》云:“中唐诗笔元才子,艳雪浓香聚笔花。……为写画图含意思,欲从锦瑟问年华”;《又题涵秋<沁香集>》云:“绮语性空道性灵,屏风隔着有人听。……不分巫山云会散,定情沧海水曾经”。元白并称,绮语感伤本是他们的看家本领,李伯樵指出涵秋前期诗歌的特点由元稹兼及李商隐应属知人之论。
前期沁香阁诗中纯粹直寻眼前景而成诗的并不多,比较典型的如“儿童渡水横牛背,山涧飞泉溅马蹄”(《乡村即事》),“秋揭天光连水白,晚收山气入城青”(《偕李伯樵登南门城观音楼晚望》)等,大多景中有“我”,富于强烈的主体抒情色彩。如果说开始学诗的诗人表现的有“我”之情多为莫名的闲愁的话,那么在经历了一场爱而不得的痛苦恋情之后,爱情就成为涵秋前期诗歌主要融情入景的内容,难免“艳雪浓香”,多以“绮语”出之。如“守礼不教郎暖颊,频来犹累汝煎茶”(《病讯》),但“昨宵花压粉墙低,久坐谈深夜色迷”自能驱散“寂寥”之感,以致诗人不觉“钟声未断又闻鸡”(《无题》)。这些诗句确能表现涵秋诗歌“艳丽深情”的一面。
中国古典诗歌中直现“真我”的大约要算那些名异而实同的《咏怀》诗了,自阮籍以下,代不乏人,前期沁香阁诗中这样的诗作也不在少数。如果说涵秋的恋情诗因为绮语而粉饰了“真我”的话,那么此类诗作就把一个“疏狂”的“真我”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真是白居易所谓“疏狂属年少”了。如《遣怀》写道:“自笑阮郎最萧索,年来赢得一狂名。”这里的“阮郎”恐怕不仅指遇仙的阮肇,应该也有纵情诗酒的阮籍的影子,才显寂寞凄凉,也让“狂名”有了着落。“嫉世酿成孤僻性,学禅难破爱嗔关”(《寓感》)或许道出了造成“疏狂”个性的原因。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涵秋写下了一组《感时》诗。根据诗集的编年,紧随其后的就是一组咏雪诗,这组七律应该作于变法失败之后。
慧愁天忌巧愁人,死后芳心难后身。满地瓦灰前代寺,隔墙花韵别家春。朝廷变法谋生拙,家室遗艰入世辛。后路苍茫思不得,敢云吾亦乐吾真?
烽火迷离近几秋,胪言风听未曾休。豺狼在野城城警,猿鹤无山夜夜愁。夷有文章开圣教,朝无斧钺愧神州。杜陵及见清河北,恐怕萧萧已白头。
小园误启竹笆门,草木侵阶日色昏。粉墨已无人面目,西南新辟鬼乾坤。棋经劫后终残局,酒到醒时又举樽。一把离骚悲壮泪,湘沅来吊屈原魂。
秋水于今久不磨,魂消髀肉太蹉跎。百千万劫偏生我,三十六天都降魔。妇子指星惊彗孛,渔樵何日共烟蓑。旁人莫怪歌喉哑,昨夜声声唤过河。
这组诗把眼前景、身边事和旧典故结合起来,融入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复杂情感,境界阔大,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感伤之情。第一首发句以倒装互文的笔法叙写诗人秉持“疏狂”“真我”陷入了个人生存的危机,天人共忌巧慧之我,身心俱遭死难折磨;落句直陈想到后路,诗人也许被迫放弃“真我”,体现了传统社会对人性的戕害扭曲;颔联直取眼前之景,通过鲜明的对比象征着祖国与列强的现实境况;颈联由国而家,揭示贫困老大的家国谋取新生的艰难。第二首仿佛咏史,借唐代安史之乱寓指列强的入侵,颈联直接切入现实,伴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的洋教势力在扬州以致全国的迅猛发展,令诗人对清廷的无能为力充满愤慨。第三首喻写变法失败,首联以景喻人,写变法失败后光绪帝处境的艰危;中间两联写变法失败,刚刚稍微有点新气象的祖国又陷入破败昏聩的状态,而列强对我国西南的侵略更加深入,面对此种现实,诗人自然想到了为国投江的屈原。最后一首把个人遭遇和国家命运绾合起来,无奈之情渗于其间。发句的“秋水不磨”、“魂消髀肉”表面上写书生文弱,不堪一战,内含自是国家的衰败萎靡;中间两联个人遭受各种磨难,欲求归隐而不可得,国事混乱,民众反应强烈;落句借用北宋抗金名将宗泽临死大呼“过河”的典故,寓指国事危急。这组诗一洗诗人绮丽缠绵的风格,转为沉痛抑郁,颇具杜诗风力,即使放在同时代人的同类诗歌中也不逊色,这又让我们体察到多愁善感的年轻诗人爱国忧世的情怀。
三、后期多以平淡蕴沉郁
大概“诗以穷而工,诗以闲愈多”(《杂咏》),涵秋后期八年的诗作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前十二年,而且诗歌的艺术质量也大大超前,突出表现在诗歌体裁的多样化,尤其长篇古体和歌行体的大量熟练写作,展示了诗人抒情方式的进步;由于生活面的拓宽,诗歌内容也更加丰富多样。
涵秋的学生龚夔石曾作《李涵秋先生诗话》:“苟有所作,亦皆清新俊逸,莫不叹为庾鲍之遗。”涵秋《再答包柚斧》云:“学诗如学禅,须参最上乘。”所以涵秋之诗,从香山、青莲入手,上溯阮、陶、鲍、庾,结穴定在老杜,这在前期诗歌已现端倪,后期诗作多徜徉于陶、鲍、老杜之间。涵秋《题董逸沧<香雪楼集>》云:“感怀班老杜,俯首拜蒙庄。”《暑夕忆镜安弟》也说:“相思不相见,来寄杜陵诗。”涵秋诗风的转变,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绮语”的减少甚至于不作,诗中多次提到“屏除绮语词少作”、“年来绮语噤无声”,后来又说“才子文章惨少作”大约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且看被陈蝶仙誉为“得陶诗神髓”的《咏怀》之一:
炎风烁流云,树影圆新绿。睡起苦烦热,汲泉漱寒玉。纵横二十步,斗室逼如狱。譬似鹤在笼,引吭悲林麓。忆我旧庭除,惜我新花木。团扇让谁人,卧月听风竹。楚语不可学,舌滞声复粗。偶尔出门行,失落难问途。比邻有妇女,妆束与人殊。脚秃紧束帛,乳大垂胸脯。因之忆吾乡,嫋嫋酒家胡。调笑娇不拒,十三才当垆。六月荷花时,秋风瘦西湖。
所谓“陶诗神髓”,主要当指陶诗的平淡自然、朴素真实,而“陶渊明就正是代表了一个‘寒士’的阶层来反对当时半贵族的门第的”。就这首诗而言,时年三十二岁的涵秋在经历了一番贫困折磨之后,初来武汉,生计稍有着落,诗句洗脱绮丽疏狂,纯以平淡朴素表出,在现实与回忆的交织叙写中,我们不难发现诗人对新环境的不适和好奇,对远方家乡的眷恋,诚富淡远之致。
涵秋在《白桃花诗分咏》的序中说:“独风雅一道,所以摇荡性情,抒写物理,可以亘千古而不灭。盖比兴非干禄之具,金石无媚世之术。”《答罗浙波》云:“亡风不亡颂,昔已薄殷周。真士贵性情,纤人工应酬。”董逸沧《香雪楼集》令诗人“反复不忍读”,就在于让他“始识性情正,未妨儿女痴。”《寄李伯樵》自道:“恬退本性情,一旦愧株守。”诗人三十六岁时还写过一首论诗的诗,题名就为《诗》:“小时学诗重性灵,长大为诗重辞旨。性灵生,辞旨死。辞旨死,性灵起。试听隔壁老翁话到明,不及孩婴昵语为可喜。能知此意能诗矣。”这可以看作涵秋对诗歌认识的总结,“性灵”就是“性情”。诗人如此反复强调,可见对“性情”的重视。就“性情”而言,结合沁香阁诗,我们可以分开来看,“性”指诗人个体的“禀赋和气质”,“情”则指由个性触发引起的男女爱情、家庭亲情扩展至山水自然之情和社会上的友朋之情、师生之情、悯人之情、忧国之情等等,表现“性情”的要旨在于“真、正”。
如果说诗人的“真我”个性在前期诗歌中主要以少年“疏狂”的面目出现的话,那么已经饱尝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的诗人不得不对“疏狂”有所修正,转为“恬退”,通过家贫己穷的寒士生活的叙写表达怨愤之情,一方面耻于忧贫,一方面又为贫困所迫而远行依人,直接在剖露矛盾之“我”中见出诗人的“真性”。二十九岁开篇就是送乃弟镜庵离家谋生,“饥躯出门去,相对两茫然”,经过严冬冻饿的诗人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了。当友人也为生计将应官大梁,饯别时却以“尖语”讥刺:“好官不过多得钱,……趋跄拜跪趁腰脚,十年归来金满橐。”坚持“真我”的诗人很快陷入了遭人剿杀的境地,但又必须依朱门而求温饱,“我”的矛盾在浊世中实在难以“全真”,但谁又能说勇于暴露矛盾的“我”不是最真实的“我”。且看《述怀》:
世人欲杀我,我亦欲杀人。杀劫不可开,闭户全吾真。人生寄传舍,飘忽如飞尘。忍抑乞温饱,孤愤安所伸?金风驰素节,芳华凋严晨。檐角铁马语,商夜答吟呻。朱门座上客,笑我长贱贫。何如扶锦瑟,酒肉杂遝陈。但博显者顾,仆辈忘主宾。昂然傲妻子,清夜惭形神。我无逐逐才,遂安闲闲身。拙矣自了汉,遐哉葛天民。
本诗前四句说明自己的处境,也表明自己的立身处世态度,排除世俗的干扰,力求保全我的“真性情”。后四句回应“真”,既然不能象“朱门座上客”那样去为谋求个人私利而丧失“真我”,就只好从容地过自己的安静日子。“自了汉”是佛教要斫胫的只顾自己之人,“葛天民”是儒家理想中生活在自然淳朴之世的人,前者为诗人所轻,后者又远不可及。家室累人,自知逃避不可能,但又不愿太委屈自己,“忍抑”就是最好的选择,中间十六句铺叙自己的现实生活,“惭”字作了自我否定,把人生看作过客又不无慰怀。全诗洗尽铅华,直抒胸臆,用对比的手法揭示“我”之矛盾而不失处世底线,这些都体现了诗人的痛苦。
“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这既是对我国“兴观群怨”的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观的突破,也强调了诗歌抒情言志的主体色彩,成为唐宋以降我国优秀诗人创作的强大原动力。后期沁香阁诗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中国诗歌的新传统,涵秋明言“诗以穷而工,诗以闲愈多。……况乎出语多逆邅,见之忌讳休来前”(《杂咏》),宣称“吾不以文鸣,吾又无以鸣也”(《上武汉报馆主笔愚庵》),更不讳言“吾舌吾所有,宁能媚公卿。岂为遭世忌,兼欲负狂名”(《席中赠报界诸君子,想有同感》)。以致他的后期诗作,友人包柚斧认为有“善骂之句”,女学生葛韵梅谓“多牢骚语”,因为“诗多为恨深”(《遣兴》)。“恨”也是“不平”之一种,一方面源于个体才不堪用怨不得伸的愤懑,另一方面也因为“人生苟可谋温饱,慎勿远行哀别离”(《莫饮酒》)的感伤之情,再就是来自于浑浊衰颓的现实社会给诗人造成的悲悯之感。如写对妻子的思念“最无聊赖是临眠,自展狐裘压衾脚”(《寄闺人柔馨》),写兄弟之情“哀哀兄弟心,天性真不移”(《暑夕忆镜安弟》)。涵秋自幼喜与人通谱,非常珍视友情,尽管曾经受过朋友的欺诈,但是对性情、文字相近的朋友时常眷念。即使自己的境况不好,也还替旧友担心,“来书道是尚无依,乌鹊寻巢绕树飞”(《寄哈蓉村》);互相劝勉多加保重,“各到中年需爱惜,况当少小便同盟。开缄莫当寒暄看,一度临笺一泪倾”(《寄张君赓廷》)。对于真正的文字知己,即使未曾谋面,诗人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激之情:“鑪鞴奇才归锻炼,醉心誉我《咏怀》诗(君论诗甚苛,去秋从汉上《消闲录》见余《咏怀》诗五古三首,遂致专函,谓得陶诗神髓,为当今诗家数一数二之作等语)。只今又是秋风熟(《咏怀》诗中有‘秋风瘦西湖’之句),投报琼瑶已悔迟”(《怀人诗》之“天虚我生陈蝶仙”)。学生新婚,诗人作诗庆贺,不乏幽默感:“被池香软女儿慵,体贴人情我最工。此后读书休早起,莫令小语骂冬烘”(《门人陆仪阁新婚贺之以诗,时仍从余读书》)。“画眉妨了绣工夫,细数年华一笑初。郎十七龄卿十八,由来明月姊称呼”(《贺门人李伯永新婚》)。这些实在是后期沁香阁诗中难得的“快诗”。
涵秋走出了扬州,当然也暂时走出了狭小的自我天地,对现实社会的普遍关注成为后期沁香阁诗迥异前期的突出之处。诗人曾在《劝农民息讼歌(甘邑白朵卿大令校士课作,取第一名)》的序中写道:“自来山讴村笛,流露无心;童谣叟歌,言情最切。本一心之恺恻,思万口之流传。务使雀角鼠牙,迹消囹圄;和风甘露,泽溥闾阎。言之者,朴而不文;听之者,味而弥永。斯为善矣。若夫文人咏物,翻矜刻画之工;学士梨葩,贵称颂扬之体。兹之所撰,亦无取焉。盖不贵杜子美之忧国,寄托遥深;而翻恃白香山之为诗,老妪却解耳。”明言这类诗取法于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他后来创作的“社会小说”大都延续了这一风格。
家庭贫困给诗人带来莫大的痛苦,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现实又给诗人以强烈的刺激,诗人对穷人的无奈和富人的骄横当有深刻的体会。爱憎分明地叹贫嫉富成为后期沁香阁诗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在当时应该具有普遍意义。如《穷士行》:“穷士汝来惜已迟,且留一饭饱汝饥。贵人倦矣请暂息,屏后笙歌鼎沸时。”《贵人行》中贵人的骄横:“贵人气焰高于山,入门下马恣心颜。揉花摘草不称意,欲闯琐闼窥云鬟。”《大风伤覆舟者》对覆舟落水而死者的同情:“低泣长号天下闻,但见涛头一千里。明朝风定江妥帖,上流乱尸多于叶。”《祈雨》讥刺旱魃肆虐、官员不思抗灾、却一心求神的丑行。《陶步兵断指歌》更是直接反映当时的保路风潮,呼吁爱国。
《沁香阁诗集》中这一类直面现实、关心民瘼的诗作虽不多,但在复古风炽的晚清诗坛颇为难得。特别是李涵秋此类诗歌的语言通俗易懂,口语化,命意在于“务使雀角鼠牙,迹消囹圄;和风甘露,泽溥闾阎”,富于教化色彩,体现了诗人的社会使命感,与他后来的小说在创作精神上是相通的。有些诗作浸透传统陈腐思想,体现了诗人的局限性。如《郝烈妇诗》序云:“烈妇萧姓,扬州甘泉西乡人,归同邑郝煦春。郝设豆腐作坊于扬郡南门街。四月染疫,垂死,父持之而泣,烈妇夜祷于庭,愿以身代。祷毕,拥儿于怀,饱乳之,而后越墙出,死枯隍中。”对于这样典型的礼教杀人事件,涵秋缺乏深刻的反思意识,没有揭示事件的血腥本质,却要“志之当贞珉”,这与晚清国门已开、妇女解放的号角已经吹响的时代氛围多么不谐调,我们怎能原谅诗人的麻木?随着时代的发展,涵秋的认识在后来创作的小说中有所改观。
后期沁香阁诗中写景抒情的诗作仍然不在少数,与前期此类诗作相较,不仅写景范围不再局限于扬州,而且诗歌体式更为多样,尤擅古体杂言。如写皖地山水“远山生云云平天,近山过雨雨成泉。在家枉自说登眺,那有千累万叠夐绝之峰巅”(《雨后山行》),写江汉平原“残照堕林木,朔风做刀剪。鹤楼忽俯仰,石塔微明闪。长天一雁过,哀唳寒云卷”(《江口晚渡》)等。
总之,清末民初,李涵秋虽然是与林纾、包天笑齐名的“小说三大家”之一,但他的诗歌创作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取法多途,远绍魏晋,近采康乾,非唐非宋,亦唐亦宋,在晚清壁垒森严、流派林立的诗坛颇有自身特色,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研究清诗史和地域文学富有价值,因此,我们不应忽视对李涵秋诗歌的研究。
〔1〕张宏生.汪辟疆及其近代诗系的建构〔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2(3).
〔2〕贡少芹.李涵秋〔M〕.上海:天忏室出版,明星书局发行,1923.
〔3〕陈玉兰.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4〕杜召棠.惜馀春轶事〔M〕.扬州:广陵书社,2005.
〔5〕龚夔石.李涵秋先生诗话〔J〕.半月,1923(12).
〔6〕林庚.中国文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