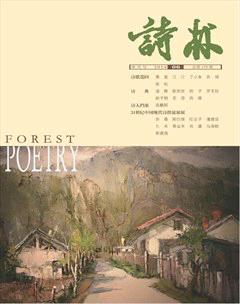在一处公园
文乾义
往上看,往它顶部看,黑榆树每一次分出枝杈,选择方向,自然弯曲,然后再分杈,再选择,再弯曲,那每一个动作都超出想象。
小跑着过来的男人,脸上的紧张像很多男人的脸。
过道边雪地上写着“北国风光”,另一处写着“万里雪飘”。看一眼就大概能猜出是什么年纪的人用树枝写下的。
站在河岸上练发声的那个男的,直到周围高楼里的人差不多都醒了之后才停下来。
几乎每天我都要在这儿走走,坐坐,或者从里面穿过。这些景与物都太熟悉了,难免有时候比我睡醒后更疲劳,但我找不到在附近还有比这儿可去的地方。
明显肥胖的老太太有节奏地用她的腰撞击着靠近河边丁香林里一棵早晨的树。树叶大幅摇动,像是一阵一阵的强风特意从那棵树上吹过。
场所基本固定在挨着人工鱼池的一块空地,时间一般在上午九点,从大街小巷赶来的这群人没有组织者地聚在这儿。他们有时愤怒,有时欢笑,更多时候他们谈论这个不怎么样的世界,以及如何治理或改造这个世界的重大举措。
这个秋天离北门最近的那把椅子常常空着。他坐在那儿的姿势看上去像个军人,或者曾经是。在这个秋天以前,他穿过黄呢子上衣,也穿过北京布鞋坐在那儿,慈祥而冷峻。
几只小花鼠跑过脚下爬上不远的老榆树,它们比老鼠少得多,比老鼠可爱得多。人们驻足的眼神儿都很惊奇,但是后来人们就不了。
老夫妻俩骑在木马上相互挥动手里的帽子,在上面又分别玩了自拍。下来后他们奔向碰碰车场地。
夏天晚上九点以后里面灯熄了,月亮和星星离它更远。
整个上午,笨重的升降车经过过道旁一排黑榆树之后,它们用剩下的“丫”形断肢朝向上方的电线和天空。
胸前挎着相机的成年人,让小男孩儿爬到一段微缩长城上面去,喊着让他站在两个垛口之间招手。那个成年人要给他拍照,他急了说,这是个假的。
大约三四十个老年人组成太极拳方队,统一的装束,在早晨的阳光里很耀眼。动作跟随音乐很慢但很整齐,他们的脖子普遍比较僵硬。
落叶纷纷被秋风追赶。在过道上奔跑的过程中,它们发出的声音像它们求救的声音。
我在昨夜刚下过雨的亭子里看一本勃莱的诗,碰巧遇到我一个诗人朋友也写诗的学生。我说听说你写得不错。他回答,大家都这么说。以后,我们就再没那么碰巧地见过。
一个人在里面走与很多人在里面走差不多。不同的是,有时一个人走,有时很多人走。
他把塑料袋里的葵花子、小米粒放在草坪边上一块水泥板上,还有松子。他说小花鼠爱吃这些,一会儿果然来了几只。
每年柳树的叶子先长出来,然后是榆树的、杨树的。等到榆树的、杨树的叶子落光了,柳树还没开始。
坐在榆树的阴凉里,心想,要是在这儿看一会儿书有多好。
“退了?”“退了。”“怎么样?”“挺好。你呢?”“挺好。”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听出在多年不见的两个声音都把“挺好”这两个字有意放在高音上。
栅栏内几个孩子坐在小轨道车上用手里的激光枪射击吊在木杆上的玩具熊、玩具虎和玩具豹子。票价五元。
我把深秋从里面捡来的带泥土气味儿,有的还带着光芒的树叶,用透明胶带一片一片固定在A4纸上。其中我能认出来的有杨树、榆树、柳树、丁香树、白桦树的。
穿红羽绒衣的男孩儿把眼镜摘下来,给他在雪地上刚堆成的小雪人戴上。
背背包的年轻女人把冰淇淋包装纸放进路边垃圾筒里。跟在她一旁的小女孩儿随后也把冰淇淋包装纸放进垃圾筒。
凉伞下摆放着酸奶和其他小食品的货摊后面,四个在打牌的销售人员招来不少观众。
照在一排老榆树树干积雪上的阳光是白的,照在没有积雪树干上的是黑的。
傍晚,放学的孩子们陆续从公园里穿过,年轻家长或老人们跟在后面,有的背着大书包,有的挎着。
怀抱泰迪的女人被大门口保安喊住:“狗不让进。”女人:“这是我儿子。”
天黑之前几个老人缓慢地离开了那个陈旧的亭子。两个看样子很熟的老妇人沿着长廊聊天。其中一个笑笑,低下头:“咦,一回忆,人就老啦。”她们停下来,停在狭窄的阴影中。另一个摘下眼镜用手擦擦。
骑在大人脖子上的那个男孩儿在“快乐林”栅栏外看见里面有个男孩儿从水泥老虎的嘴里爬进去。过不一会儿,他从水泥老虎的嘴里爬出来。
推销新楼盘的白面小伙儿捧着一叠印制精美的宣传广告站在过道上,他站的位置刚好一伸手就可以把广告塞进别人怀里。
秋天一到,那一小片白桦树就在离北门不远的位置准时举起金黄的集束火把。
穿黄色夹克衫的老人后背上背着一个被风鼓起的包。他领着小男孩儿从恐怖城大门走出来,走向对面的枪战城。
几个人停下来看着一个年轻母亲,她看着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孩子摔了一跤,然后自己哭着爬起来,又摔一跤。
在两排杨树之间打乒乓球那伙儿老年人,平均每天训练时间超过了专业运动员,至少有几个能打到某些国家的前几名,如果不限年龄,进入某个国家的奥运代表队也不是没有可能。
基本上固定的一些人,有拉二胡的,有弹吉他的,有吹笛子的,还有几个唱的,在基本上固定的一座小型欧式建筑门前,从春到秋度过从下午到傍晚的时光。
拎沉重布袋的那个人脱掉了鞋,盘腿坐在椅子上,白袜子露在外面。他点上一支烟,用力吸一口,使看见他的人觉得没有比这还舒服的了。
手推锄草机轰响的马达声过后,很少有机会闻到的一股特别的清香从青草被粉碎的身体里散发出来。
我们可是好久不见了,有五年或者更长。他拎着一塑料袋青菜,我也是。站在一伙儿打牌的人旁边,我们腿酸了。过后想想,我们用一整个下午谈了谈各自怎么“过五关斩六将”那些事。
黄昏,一片晚霞在比它小很多的靠近树林的水池上燃烧。
沿着林荫小路散步碰到一个认识但不怎么熟的人,我抬手做个打招呼的姿势走了过去。
大货车开进积满淤泥的河道里,卸下水泥板,还有地砖。去年有过一次,前年一次。
从楼宇间穿过来的阳光低低地照进林间草坪,树干用它们长长的阴影把草坪分割成大小不等的条块儿。
我走出林间小道时,一个怀抱小孩儿泪流满面的年轻女人问我七十二路车站怎么走。我告诉她出北门右转五十米。等我散了半小时步以后,我看见她坐在过道边椅子上,小孩儿在她怀里睡了,她仍泪流满面。带着一种我希望帮到她的想法,当我有意朝她走过去,她把头埋进了怀里。
天快黑了,面孔在暮霭里隐约。其中一个老人收起小马扎儿,从几个老人中间站起身,说了句:“你们慢慢聊吧。”
戴墨镜穿紫色风衣的高挑女子从南门进来,北门出去。这一路上,眼神儿再怎么不好的,也不放过回头的机会。
一对高大的外国夫妻推着婴儿车,用外语与车上的孩子说话。周围那些“真好看”的赞美,大都与自己的孩子所不具备的“白皮肤、蓝眼睛和黄头发”有关。
美女结队从假山石阶走下来,她们的眼睫毛比假的还不真实。
雪中过道上那些稀疏背影像树干一样缓慢,模糊。
这一天很少有过的一场风从向一侧大幅度倾斜的丁香树上看到了自己强有力的形状。
与一个喜欢自言自语的老人我不止一次擦肩而过。
空地上的那伙儿人在太阳照耀下站了一整个上午。他们慷慨激昂,一直在讨论真理去哪儿了的问题。
有几个人打着伞从不同的街道,从不同方向的门进来,特意赶到那个简易陈旧的木制长廊下避雨。
一个将一串钥匙挂在腰带前面的人走过来,带着金属声响,有时发光。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过这样并持续到九十年代初。
小广场边上,年轻母亲成功阻止了她小时候曾经玩过的她的女儿正在灌木下挖土的玩儿法并蹲下来用湿巾给女儿擦手。
早晨围观的人群在由奶奶或姥姥级组成的操练方队的刀光剑影中一个个微笑着面孔。
园林工用特别响的那种吹风机把堆积在榆树墙下的落叶吹出来,连尘土一起装进手推车,然后把一些工具放在上面,还有后背印着文字的外衣。
坐在椅子上用背部面对过路人的那个女子,她的后脑勺儿在灼热的光芒中颤动。
不清楚原因,这么多树很少有喜鹊或乌鸦飞临。天空中更多的翅膀都是麻雀的,有时它们也在人群里飞来飞去。还有一种很小很小的鸟儿,绿翅膀,黄肚囊,黑亮的嘴儿,尖尖的,偶尔穿过树丛。
昨夜一场雨,灰色地砖新铺的小广场上有几处没有积水返光。
西门口外墙上贴着公园招聘保安员的A4纸打印广告,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广告下方的空白处写着一行潦草黑字:办文凭。并且留下了联系电话。
十几个排练街舞的男孩儿女孩儿在水泥台子上翻来滚去,台下几个老人看一会儿就捂着胸口离开了。
海盗船的牌子换成了神舟飞船,那个戴礼帽儿,用单筒望远镜瞭望远方的古铜色雕像依然站立在船头上。
几乎每天我从北门进来,从西门出去,去那边那个超市。然后再从西门进来,从北门出去。时间一长,我就忘了我这是又一次从里面穿过。
冬天把小火车轨道埋进漫长的雪里。
门票不收了以后最高兴的是那些保安的脸。
自上个夏季以后,有只灰色流浪猫隐现在灌木丛中,只能偶尔看见小花鼠们的身影了。
中午,来这儿散步的周围写字楼里的人与其他人不同,他们一边说话一边点头。
有一次我用手机拍下黑树干和它上面的雪。有一次我拍下后面飘着白云的丁香花。还有一次在我拍行驶在林荫间的红色小火车时,我的手机掉在了地上。
有人夏天抱着老榆树合影,到了冬天没人再抱它。
在枯萎的花池边上,一对老夫妻坐着不说话,戴运动帽儿的老头儿拐杖拄在地上。他们共同望着萧条了的树林后面的天空。
走在雨后路面上清晰的沙沙声听起来让心里干净许多。
躺在过道旁长椅上的男人头下枕着黑色双肩包,脸上盖着一张《参考消息》。一双带泥的胶靴整齐地摆放在椅子下,似乎疲惫不堪。
下雪天,这里任何一处,比如在稀疏的树林里、在贴着封条的冷饮店门廊下、在过道两旁的空椅子上、在四面透风的亭子里,都是那种可以“让我静一静”的地方。不过,时间不能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