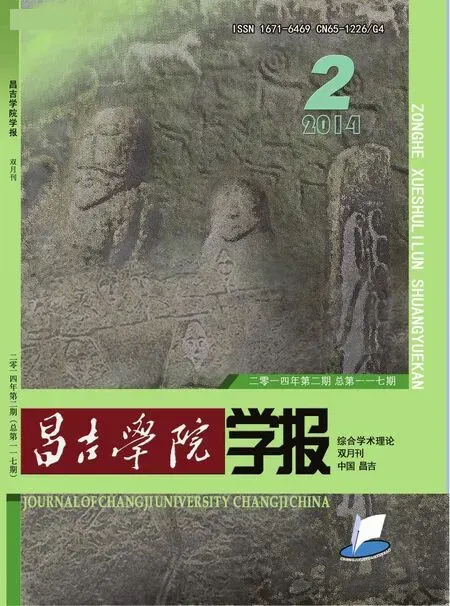文学与考古双重视野中的西域乐舞“胡腾舞”
蔡建东 海 滨
(1.昌吉学院音乐系 新疆 昌吉 831100;2.海南大学 海南 海口 570228)
西域乐舞在唐代流行很广影响很深,诸乐舞中,以胡腾舞、胡旋舞和柘枝舞最具代表性,与此三大乐舞相联系的文学创作情况则比较复杂。现存唐诗等文学作品中,正面描写胡腾舞者仅李端《胡腾儿》、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诗句涉及胡腾舞者仅元稹《西凉伎》与白居易《奉和汴州令狐相公二十二韵》;胡腾舞具体是什么样的情状,唐人在创作中对待胡腾舞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有必要结合传统文献尤其是唐代文学作品和近年出土文物以及敦煌壁画等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还原一个文学与考古双重视野中的唐代西域乐舞“胡腾舞”。
一、文学与历史文献视野中的“胡腾舞”
段安节《乐府杂录》叙唐代舞蹈种类时说:“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健舞曲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软舞曲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团圆旋》、《甘州》等。”[1]胡腾属于健舞,其传入中原时间、服饰道具、舞姿舞容、伴奏乐器等方面有具体规制和特点。除此之外,胡腾舞在笔者查阅的现存文献中的记载共5处,正史1,唐诗4。
正史有《宋史·乐志十七》之记载:“队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儿队凡七十二人:一曰柘枝队,衣五色绣罗宽袍,戴胡帽,系银带;二曰剑器队,衣五色绣罗襦,裹交脚幞头,红罗绣抹额,带器仗;三曰婆罗门队,紫罗僧衣,绯掛子,执锡镮拄杖;四曰醉胡腾队,衣红锦襦,系银 鞢,戴毡帽;五曰诨臣万岁乐队,衣紫绯绿罗宽衫,诨裹簇花幞头;六曰儿童感圣乐队,衣青罗生色衫,系勒帛,总两角;七曰玉兔浑脱队,四色绣罗襦,系银带,冠玉兔冠;八曰异域朝天队,衣锦袄,系银束带,冠夷冠,执宝盘;九曰儿童解红队,衣紫绯绣襦,系银带,冠花砌凤冠,绶带;十曰射雕回鹘队,衣盘雕锦襦,系银 鞢,射雕盘。”[2《]宋史》的记载虽未必能完全反映唐代胡腾舞原状,但唐宋相继,我们还是可以得其仿佛。从这段记载我们可知,在宋代所谓队舞中胡腾和柘枝、剑器等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胡腾队被冠以“醉”字;胡腾舞者之服饰有红锦襦、银 鞢、毡帽等。
诗歌中正面描写胡腾者有李端《胡腾儿》和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李诗曰:
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3]
刘诗曰:
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蒲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槿花西见残月。[4]
诗句中提及胡腾者尚有元稹《西凉伎》和白居易《奉和汴州令狐相公二十二韵》。元诗曰:
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踯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5]
白诗曰:
平展丝头毯,高褰锦额帘。雷槌柘枝鼓,雪摆胡腾衫。发滑歌钗坠,妆光舞汗沾。回灯花簇簇,过酒玉纤纤。[6]
向达先生根据李端、刘言史诗解释道:“就刘、李二人诗观之,胡腾舞大约出于西域石国。舞此者多属石国人,李端诗‘肌肤如玉鼻如锥’,则其所见之胡腾儿为印欧之伊兰种人可知也。此辈舞人率戴胡帽,着窄袖衫。帽缀以饰,以便舞时闪烁生光,故云珠帽。兰陵王、拔头诸舞,舞人所着衫后幅拖拽甚长,胡腾舞则舞衣前后上卷,束以上绘葡萄之长带,带之一端下垂,大约使舞时可以飘扬生姿。唐代音声人袖多窄长,为一种波斯风之女服。因衣袖窄长,故舞时须‘拾襟搅袖’,以助回旋。李端诗‘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大约系指舞人起舞之先,必须略蹲以胡语致词,然后起舞。宋朝大曲,奏引子以后,竹竿子口号致语,李端所云之本音语,疑即大曲口号之大辂椎轮也。胡腾舞容不甚可知,依二诗所言,大率动作甚为急遽,多取圆形,是以‘环行急蹴’、‘跳身转毂’云云。胡腾之腾或指其‘反手叉腰’,首足如弓形,反立毡上,复又腾起而言欤?与胡腾舞伴奏之乐器有横笛与琵琶,酒阑人罢,丝桐忽奏,于是一曲亦终矣。”[7]
二、考古视野中的“胡腾舞”
综合向达先生的推测和元白二诗透露的信息,以正史和文学作品提供的胡腾舞信息为基本依据,以“胡”、“腾”、“舞”顾名思义为基本认识,结合西域胡人的社会生活与艺术民俗等,我们在考古领域中找到了很多可与诗文相印证的实物资料,这些形象逼真的资料从北魏一直延续到五代。
自北魏起,“胡腾舞”形象就陆续可见。
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遗址石雕方砚雕刻着胡腾舞图[8]。1970年,大同博物馆在大同市南郊清理两处北魏遗址,其中东遗址出土石雕方砚一件。[9]方砚上面雕刻几幅图案,其中便有一个胡腾舞的形象,一男子在跳舞,旁有一男子在弹琵琶伴奏。[10]
甘肃庄浪北魏塔塔身雕刻着胡腾舞图[11]。此塔现存塔身局部,其上雕刻有3个男乐伎表演的情形,中间的乐伎在手、臂、腿上挂着很大的铃铛,作腾跃状。
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黄釉瓶腹模印着胡腾舞图[12]。此瓶1970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县的一座北齐墓葬中,扁体,圆口,细颈,肩有双系钮,通体施黄釉,模制。其形状显然是仿照了西域皮囊壶。在瓶腹两面,模印着同样的胡腾舞图。考古简报称:瓶上有一组乐舞图,乐舞人都是高鼻深目,身着胡服的西域人。一男舞者立于莲花台上,头部扭向右方,右臂侧展,左臂下垂,下颌贴近左肩,左肩稍耸,左足踏莲花上;右足稍抬,正欲踏舞。[13]观察照片,尚可清晰辨认:舞者头戴尖顶帽,身穿窄袖翻领长衫,腰系宽带,衣襟掖在腰间,足套长统靴。其右侧立二人,一人执钹,一人弹琵琶。左侧一人吹横笛,一人击掌伴唱。
宁夏固原出土北朝卷草纹绿釉瓶腹绘制着胡腾舞图(图1)。此瓶口已残,瓶腹两面各有一组基本相似的七人乐舞图案,考古简报称:“图案当中一人,头微仰,右臂弯曲舞过头顶,左臂向后甩动,右脚后勾,左脚弯曲跃起,身躯扭动,于莲花座上翩翩起舞。两边舞伎双腿曲蹲,击掌按拍。左右共有四个乐伎,皆双腿跪踞在莲花座上,分别倒弹琵琶、吹笛,击鼓、拨弹箜篌。图中七人均深目高鼻,头戴蕃帽,身着窄袖翻领胡服,足登靴,为西域人形象,乐舞形式似为胡腾舞。”[14]

图1
传世北齐胡人乐舞瓷瓶腹绘制着胡腾舞图[15]。此瓶为故宫博物院所藏,极似固原出土北朝卷草纹胡人乐舞绿釉瓶而完整无缺,中国舞蹈史专家王克芬认为瓶腹所绘也是一组乐舞图:“中一舞人,身穿翻领、窄长袖胡服,右臂上扬,左袖在身后垂卷。左腿向前大跨步,右腿后曲,似正向前奔腾跳跃。动势、感觉均向前,头部扭转回顾,形象生动,舞姿豪放粗犷。两旁四个乐人,左前一人弹箜篌,右前一人弹琵琶,左、右后两人均张臂奋力击掌,表情十分兴奋。比较特殊的是:在舞人头顶左右上方,有两个悬空的乐人,左上一个像在敲击乐器,右上一人吹横笛。……这两个壶(传世瓷瓶和安阳瓷瓶)上舞人的舞姿,都具有《胡腾舞》的某些特点。是我们研究唐代健舞《胡腾舞》极珍贵的形象资料。”[16]西安北郊安伽墓石榻围屏浮雕有胡腾舞图。200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北郊大明宫乡炕底村发掘了一座罕见的北周大型墓葬——安伽墓。墓内石榻围屏内面有贴金浅浮雕图案12幅。其中后屏之一、之六和右屏之二的下部均有胡舞图。发掘简报称,后屏之一为乐舞图,上半部为奏乐合唱图,奏者乐器有曲项琵琶、箜篌等,饮赏者手执角杯、单柄酒罐,帐前置贴金执壶、罐、盘口罐等盛酒器。下半部为舞蹈图,“中部一人身着褐色紧身对襟翻领长袍,襟、袖口、下摆为红色,白裤,黑靴,双手相握举于头顶,扭腰摆臀向后抬右脚……”两侧人或抱贴金带流酒壶,或抱盛酒罐。后屏之六为居家宴饮舞蹈图,主人居亭内榻上,“右侧为四个艺人正在演奏。榻前石阶上立者披发,身着褐色紧身袍,腰系黑色贴金带,脚蹬黑色长靴,弹奏琵琶;后有两红衣人,其中一人抚弄箜篌;右侧一白衣人吹奏排箫。亭前有石阶,庭院内正在表演舞蹈,中间一人身着红色翻领紧身长袍,袍内穿有红色内衣,腰系黑带,浅色裤,红袜,黑色长靴,正拍手、踢腿表演胡腾舞。左侧两人,前者身着白色红花袍,怀抱酒坛;后者身着褐色袍,腰系黑带,双手于头顶托一大盘。”右屏之二为宴饮舞蹈图,其下半部为乐舞图。“舞者居中,身着褐色圆领紧身长袖袍,领、袖、前襟及下摆均饰红彩,红裤,黑长靴,正扭头,伸右手,屈左臂,甩袖,踢腿,表演胡腾舞。左侧圆角长毯上跽坐三乐人,均卷发,中间一人身着红袍,持横笛吹奏;左右两人身着黑色长袍,分别弹奏琵琶和拍打腰鼓。右侧立三人着红或褐袍静心观赏。……舞者周围摆满酒坛、酒壶及叵罗、果蔬盘等器物。”[17]
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石堂北壁石刻有胡腾舞图[18]。史君墓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井上村东,2003年进行清理发掘。史君墓石堂石刻均采用浮雕彩绘贴金图像做装饰。其中石堂北壁自西向东第二部分浮雕图中约略可见胡腾舞舞姿,伴奏者身后立有水瓶或酒瓶。
日本滋贺县Miho美术馆藏北朝石棺床浮雕中有胡腾舞图[19]。1991年纽约艺术品市场上出现了一套中国北朝的石棺床,包括双阙和11帧画像石。后来这批艺术品成为日本奈良附近滋贺县Miho博物馆的“秀明藏品”。其中也有胡腾舞浮雕,一位男舞者在中间挥臂抬腿,尽情舞蹈,两侧乐伎则手持箜篌、琵琶、横笛、铜钹等在伴奏。舞者脚下放置着酒壶。
另,太原寿阳县北齐厍狄回洛墓甬道残存壁画、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安阳出土北齐石棺床图像、山东临朐县博物馆藏北朝卢舍那佛衣服图案、山东青州出土北齐卢舍那佛衣服图案中也都有胡腾舞形象出现。[20]整个北朝,胡腾舞形象主要出现在北方的胡人墓室壁画、浮雕、瓶腹绘画以及佛教造像上。进入唐代,胡腾舞形象出现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承载形态也趋于多样化。
唐苏思勖墓壁画有胡腾舞图[21]。苏思勖,两《唐书》有传。杨思勖,本姓苏,罗州石城人。为内官杨氏所养,以阉,从事内侍省。预讨李多祚功,超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思勖有膂力,残忍好杀。从临淄王诛韦氏,累迁右监门卫将军。开元间,先后四次受诏讨伐安南首领梅玄成、五溪首领覃行璋,以及邕州、泷州等地方叛乱。天宝四年卒,时年八十余。苏思勖墓位于西安东郊,1952年发掘。其墓室东壁有乐舞图,展现了胡腾舞的姿容。王克芬描述道:“站在中间地毯上舞蹈的是一个深目高鼻,满脸胡须的胡人。头包白巾,身穿长袖衫,腰系黑带,脚穿黄靴。两旁是九个乐工,和两个歌者担任伴奏伴唱。舞者高提右足,左手举至头上,象是一个跳起后刚落地的舞姿,很象唐诗中描写的《胡腾舞》。”[22]观察壁画照片,可以看出乐工使用的乐器有筚篥、排箫、琵琶、箜篌、筝、笙、拍板、横笛和钹等。
日本正仓院藏唐螺钿枫琵琶捍拨上绘有胡腾舞图[23。唐螺钿枫琵琶现藏于日本正仓院中,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南仓下”记此琵琶“枫木质,槽之背侧染以芳苏,复于螺钿中交玳瑁,组成花鸟文样,……其捍拨绘《骑象鼓乐图》,山景树下,白象上乘四胡人,胡帽者二人,一击腰鼓,一扬袖而舞,外一吹筚篥,一吹横笛,西域趣味,甚形浓厚。按捍拨上绘骑象图,纯为西域式的风尚,唐时安国乐琵琶,捍拨即画其国王骑象,可知此具乃属于安国式的琵琶。”[24]捍拨,傅芸子释曰,琵琶本有捍拨,捍拨在琵琶面上,当弦,所以捍护其拨者,今琵琶无之。鼓乐图照片上的舞姿与前述胡腾舞相似。
西安丈八沟唐代窖藏出土伎乐纹白玉带铊尾刻有胡腾舞图(图2)。1987年,在西安丈八沟唐代窖藏中出土一付碾伎乐纹白玉带,有方銙十二、圆首铊尾一、银带扣一,玉晶莹,细腻坚硬,为新疆和田白玉制作。“铊尾正面雕一卷发的胡人少年在圆毯上跳胡腾舞,舞者身着开胸紧身窄袖服,腿穿长裤,腰系裙,足蹬高靴,右腿高抬,左腿微屈,头微偏,目下视,双手举起交于头顶,肩饰长带,作腾跳状。”[25]

图2
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鎏金伎乐八棱银杯饰有胡腾舞图[26]。此杯为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银质,纹饰鎏金。呈八棱形,环形柄。柄上焊接两个相背的深目高鼻、长胡须的胡人头像。杯的式样来自西域粟特地区。杯身分为八区,每面饰有一个人物形象,均是深目高鼻的胡人,四人分别执排箫、小铙、洞箫、曲颈琵琶乐器,余四人抱壶、捧杯或作舞蹈状。其中舞蹈者所跳的,“应当就是胡腾舞。”[27]
陕西礼县唐昭陵陵园出土玉铊尾上雕刻有胡腾舞图[28]。1981年陕西省礼泉县唐昭陵陵园出土。此铊尾为白玉制成,温润细腻,抛磨光亮,具玻璃光泽,圆首矩形,两面边缘均削棱,正面雕出一跳胡腾舞的男子。舞者长发卷曲,高鼻深目,面带微笑,上着圆领紧身长袖衣,腰系长裙,裙下摆饰花边,足蹬高筒靴,屈肘扬右手,左手摁于臀侧,双手均藏于袖中,右腿腾起,左腿微曲,肩披飘带,舞于圆毯之上。圆毯周饰垂索。……圆毯正是唐代文献中屡次所讲的‘舞筵’。[29]
山丹县博物馆藏有唐代胡腾舞俑[30]。此俑是著名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捐赠品,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舞俑通高13.7厘米、宽8厘米,圆目钩鼻,阔嘴大耳,头戴高耸而尖顶弯卷的毡帽,身着窄袖紧身衫和长裙,足蹬长筒翘头软靴,背负系挂牢靠的酒葫芦。右臂上扬,左臂下弯,右腿斜踢,左腿直立,长袖甩出,裙角翻飞,舞人单足挺立于垂瓣莲托之上,所跳乃胡腾舞。
陕西西安陕棉十厂唐墓壁画有胡腾舞图。199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陕棉十厂住宅基建工地抢救性清理唐墓9座,其中一座壁画墓壁画保存较好,《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清理简报》称,墓室东壁主图为“一幅8人组成的私家乐舞图。图中部绘一男伶,头戴黑幞头,颦眉低眼,鼻稍高,嘴较小,面庞较大,身穿圆领长袖袍衫,袍上可见残存的淡黄痕迹,腰束黑带,脚蹬黑长靴,上身侧向北略后仰,双手隐于长袖中,耸肩张壁,扭腰踮足作舞蹈状。”伴奏乐器则有琵琶、筚篥、箜篌等。[31其中的舞者“跳着胡腾舞,但舞蹈者和周围的伴奏者都形似汉人。”[32]
陕西五代冯晖墓甬道彩绘浮雕砖有胡腾舞像[33]。冯晖是五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长期掌控北方的朔方军,从唐末一直经历了五代各朝。他的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彬县,在多次被盗扰的情况下,考古部门于1992年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冯晖墓的出土文物中最珍贵的是甬道两侧的50余块彩绘浮雕砖,上面刻画了28名男女艺人分两组演奏的场面,线条流畅,人物神情惟妙惟肖。其中跳胡腾舞者就有6个。演奏者的乐器种类繁多,经专家研究确认的乐器有方响、箜篌、拍板、腰鼓、琵琶、答腊鼓、笙、笛等,堪称一支演奏散乐的小型乐队。
敦煌壁画中,有一个极为壮观的音乐世界,因为壁画中记录和描绘了大量古代音乐表演和乐器的宝贵资料。作为美术作品,这些壁画难免夸张想象的痕迹,但仍为我们研究唐代乐舞提供了形象生动的材料。根据郑汝中先生统计,仅莫高窟就有音乐洞窟240个,乐伎3520身,乐队490组(其中经变画乐队294组),乐器43种计4549件。[34]
这些乐伎之舞容可谓千姿百态美轮美奂,其中也有不少舞姿与我们讨论的三大乐舞的特点相契合(图3、图4),比如我们“可从98窟、112窟、144窟、445窟、112窟、156窟、329窟的经变画中找到‘蹲舞尊前急如鸟’、‘跳身转毂宝带鸣’的胡腾儿在舞蹈时的动律特征。”[35]

图3

图4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胡腾舞形象在唐代南方地区也有大量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起,经过半个世纪的发掘和研究,位于长沙市望城县的湖南长沙窑已被证明是唐代南方重要的瓷器基地和著名的外销瓷器窑。此窑出土的一件印模上,正反两面都刻有舞蹈形象,正面为两个男性中年人各在一小圆花毡上跳舞,单腿屈膝点地,身体倾斜,其中一人手持横笛,反面也刻一位男性中年人立于一圆形花毡上。这些人的形象,尤其是正面两位足踏花毡舞蹈的形象,完全符合跳胡腾舞的特征。[36]石家庄唐孙岩墓出土的长沙窑贴花人物壶,在流下贴有胡腾舞姿的胡人舞伎。[37]长沙窑出土的模印贴花胡人舞蹈纹双耳壶“流下印模贴花纹饰为对鸟团花,耳下纹饰为胡人跳击板胡腾舞。……一个满脸胡须的胡人,身着中式绣满如意云头的服饰,头戴花帽,脚蹬胡靴,一只脚着地,一只脚悬空,动感十足。”[38]
三、双重视野中的“胡腾舞”
综合上述文学与考古资料,我们可以对胡腾舞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胡腾舞至少在北魏时期已传入中原,历代不绝,唐代尤为兴盛。胡腾舞不仅在今陕西、山西、甘肃、宁夏、河南境内流传,而且从北方逐步传播到南方,成为湘瓷印模画的主要题材之一。
第二、舞者、歌者、伴奏者多为高鼻深目髯须浓密的男性胡人;舞者往往戴织成虚顶尖帽,帽或有饰;着窄袖短装胡服,或曳飘带;足蹬软靴以便腾跃;舞者胡语致辞后则环行急蹴、跳身转毂于舞筵之上,运动量极大以致于舞汗沾湿。
第三、舞者往往在酒醉兴奋状态中尽情表演。刘言史诗曰:“手中抛下蒲萄盏”,李端诗曰:“醉却东倾又西倒”,元稹《西凉伎》曰:“胡腾醉舞筋骨柔”,白居易《奉和汴州令狐相公二十二韵》曰:“雪摆胡腾衫……过酒玉纤纤”,《宋史·乐志十七》称“醉胡腾队”,文献资料凡有出现胡腾者皆与酒、醉关联。图像资料亦然,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黄釉瓶、宁夏固原出土北朝卷草纹绿釉瓶、传世北齐胡人乐舞瓷瓶,此三瓶非盛水即盛酒,可能与所绘胡腾舞有关;西安北郊安伽墓石榻围屏浮雕胡腾舞诸图中角杯、单柄酒罐、贴金执壶、罐、盘口罐、贴金带流酒壶、酒坛、叵罗等酒器酒具几乎布满画面空隙;西安史君墓石堂北壁自西向东第二部分浮雕图中约略可见胡腾舞舞姿,伴奏者身后立有水瓶或酒瓶;日本滋贺县Miho美术馆藏北朝石棺床胡腾舞图中舞者脚下放置着酒壶;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鎏金伎乐八棱银杯本身就是酒具。
第四,胡腾舞的伴奏乐器有横笛、琵琶、箜篌、铜钹、筚篥、排箫、筝、笙、拍板、洞箫、曲颈琵琶、腰鼓、答腊鼓、方响等,个别画面中还有按节击掌与伴唱者。
第五,胡腾舞及舞者所出之地应为西域。上述资料涉及到的舞者有唐代九姓胡之石国人——刘言史所谓“石国胡儿人见少”,还有安国人和史国人——安伽墓、史君墓之图版和碑志可互证,即使那个“身是凉州儿”的胡腾者,其路断难归的故乡也在西域。表演者多为西域胡人,观赏者则有胡人、汉人,还有突厥人——安伽墓画像上就有突厥人观看胡腾舞表演。
可以这样说,胡腾舞至少在北朝入华,盛行于唐代南北方,直至宋代犹然不绝。对照胡腾舞诸特点,细读唐人胡腾舞诗,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深刻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既有外在的显性表现,又有内在的隐性契合。
外在的一致性是比较容易捕捉和梳理的,如果将胡腾舞诗与前引材料逐一对比,每一个画面图像和诗歌的描写都有同有异;如果把胡腾舞诗合而观之,再把诸图像材料之相同处抽取集中起来,二者之间则若合符契。诗歌中的胡腾儿来自遥远的粟特邦国,沿着丝绸之路在凉州、在长安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高鼻深目,皮肤白皙,头戴精致的织成虚顶尖帽,足蹬柔软锦靴,身着窄袖胡衫,口操浓重胡语;在夜宴上,他们向座客把酒致语后,踏上从故乡进口的精美舞筵,带着酣酒微醺的醉态,拾襟搅袖做好准备,扬眉动目调整情绪,反手叉腰,腾挪踢踏,上下跳跃,东倾西倒,环行急蹴,在横笛琵琶的合鸣中逐渐进入舞蹈高潮:随着剧烈的腾舞,他们身上的葡萄宝带上下翻飞,珠玉佩饰淙淙作响,夸张的舞姿悍然生风,不仅搅起了舞筵上的长毛,甚至拂动了夜色中的烛光;胡腾儿进入了忘我的表演中,蕃帽偏斜、大汗淋漓却依然如痴如醉,四座的观者则被这精彩绝伦的胡腾舞所折服,瞠目结舌,悄然无语;舞罢酒阑,无边夜色中弥漫着天边斜月的淡淡微光。诗歌的语言启示着我们的无边想象,出土文物和壁画的图像则把鲜活灵动的具体情状充分地展示给我们,二者之间的外在一致性是显然的。
内在的一致性则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和思考。从读诗的感觉而言,华丽的盛筵和精彩的胡腾背后总是带着几分忧伤和怅惘的色彩;从诗句来看,则有“安西旧牧收泪看”、“故乡路断知不知”、“西顾忽思乡路远”的描述和感慨。考察作者的其它诗作,李端尚有《赠康洽》、《赠李龟年》、《送古之奇赴安西幕》、《奉送宋中丞使河源》等,刘言史尚有《送婆罗门归本国》、《观绳伎》、《赋蕃子牧马》、《病僧二首》、《代胡僧留别》等,可见他们与西域胡人、乐部弟子、边幕僚使都有较为密切的接触和交流,对包括粟特人在内的西域胡人生活和中唐后西域军事政治格局的变化还是比较清楚的。河西陷蕃,陇右道绝,曾经叱咤天山脚下的安西旧牧看到忘情起舞的胡腾儿焉能不垂泪;粟特胡人虽兴生贩货,利之所存,无远不至,其乡土观念异于中原,但背井离乡、故园路断的胡腾儿在淋漓酣畅的醉舞中,心头也难免暗生西顾之思。
从胡腾舞图像出现的介质(载体)来看,除了敦煌壁画外,主要是经发掘的粟特人墓室浮雕和壁画以及墓中出土的胡瓶和玉带。唐代中亚河中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粟特胡人,以康国为首组成了城邦群体,以经商为务兴贩于丝路沿途,并逐渐向东形成很多粟特群落,广泛地分布在唐代漠北之胡部、六胡州、河北道以及西州、伊州、沙州、凉州和塔里木盆地一带,在唐代历史上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中,其头脑灵活、善于经营,甘言饴辞、获利颇丰;在其民族和聚落内部则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胡马依北风,狐死必首丘。粟特人在现世获得了巨额的商业利润,其墓室也往往整饬华丽,仔细研究其墓室和随葬品所负载的内容,我们还是可以钩稽这样一些信息:其墓室浮雕壁画内容除了粟特人的祆教信仰、粟特人与外族的交往生活之外,最多的就是宴饮高会,画面中佐酒助兴的就是胡腾舞和胡旋舞;其墓中出土的胡瓶和玉带应该是亡者生前日常所用,其上绘刻的往往也是胡腾舞图。这说明,粟特人无论在现世还是冥世中都把故乡的胡腾舞形象作为长伴身边的重要符号,他们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寄托内心深处的乡思。这种内心的微妙的情愫与胡腾诗中流露的那种深层的伤感之间也是有着内在一致性的。
[1]段安节.乐府杂录.羯鼓录·乐府杂录·碧鸡漫志[M].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28.
[2]《宋史》卷一四二[M].中华书局,1977:3350.
[3]李端.全唐诗(增订本)胡腾儿 [M].中华书局,1999:3235—3236.
[4]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M].中华书局,1999:5354.
[5]元稹.《西凉伎》,《全唐诗(增订本)》[M].中华书局,1999:4628.“胡腾醉舞筋骨柔”冀勤点校《元稹集》正文作“胡姬醉舞筋骨柔”,校曰:“姬,宋蜀本,《乐府诗集》卷九六、《全唐诗》卷四一九作‘腾’。”
[6]白居易.《奉和汴州令狐相公二十二韵》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M].中华书局,1979:528—529.
[7]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66—67.
[8][11][12][23][30]冯双白等著《图说中国舞蹈史[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02,83,84,127,119.
[9]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M].文物出版社,1971:29—30.
[10][27][32]张庆捷.北朝隋唐粟特的“胡旋舞”[A].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C].中华书局,2005:390—401.
[13]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2,(1):49.
[14]马海东.固原出土绿釉乐舞扁壶[J].文物,1988,(6):52.
[15]陈海涛.胡旋舞、胡腾舞与柘枝舞——对安伽墓与虞弘墓舞蹈归属的浅析[J].考古与文物,2003,(3):59.
[16][22]王克芬.中国舞蹈史[M].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13—14,13.
[1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J].文物,2001,(1):4—26.
[18]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5,(3):25.
[19]虞弘墓所谓“夫妻宴饮图辨析”[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1):70.
[20]王克林.北齐厍狄回洛墓[A].考古学报,1979,(3).姜伯勤.安阳北齐石棺床画像石的图像考察与入华粟特人的祆教艺术[A].艺术史研究,第1辑,1999年.宫德杰.临朐县博物馆收藏的一批北朝造像[A].文物,2002,(9).中华世纪坛艺术馆、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北朝佛教造像[C].北京出版社,2002.
[21]张鸿修编著.中国唐墓壁画集[M].岭南美术出版社,1995:150.
[24]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57.
[25][29]北周隋唐京畿玉器——杨建芳师生古玉研究会古玉图录系列之一[M].重庆出版社,2000:58,52.
[26]http://www.ce.cn/culture/more/200607/28/t20060728_7915424.shtml
[28]王光青.唐代玉銙话乐舞[J].文博,2006,(2):58—59.
[31]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2,(1):16—37.
[33]http://tuku.news.china.com/history/html/2006-02-24/2024222_744451036.htm
[34]郑汝中.敦煌壁画乐舞研究[M].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75.
[35]李才秀.从敦煌壁画的舞姿看古代西域与内地的乐舞交流[A].吴曼英,李才秀,刘恩伯.敦煌舞姿[C].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152.
[36]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望城县长沙窑1999年发掘简报[J].考古,2003,(5):61.
[37]石家庄市博物馆.石家庄乐安孙安墓[J].考古,1983,(4).孙启祥.石家庄市振头村发现唐代贴花人物瓷壶[J].考古,1984,(3).
[38]李效伟.长沙窑·大唐文化辉煌之焦点[M].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95.
———史敦宇艺术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