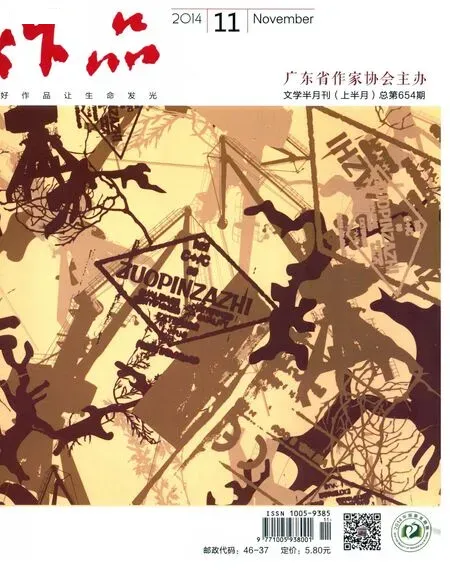小风吹
文/(台湾)王盛弘
有段时期,走路对我来说,是精神疗愈的一个手段。
那些日子里,胸臆常常藏着一团低气压,使我即连呼吸都感觉到吃力;脑中暗暗安了一颗不定时炸弹,眼看着引信就要被点燃。再也坐不住的我遽然起身,夺门而出。
我似乎看到一个就要坏掉了的人,他的躯干些许失衡,脚步忽轻忽重有点儿踉跄,眼眶痠痠的,如果能大哭一场就好了,却偏偏宛如乌云四合、闷雷隆隆低鸣、空气凝固了的午后,雨水迟迟不能落下。
这个人走进了林荫又走出林荫,避不开人群便穿过人群,一条街道紧接着一条巷道,路往哪里开展便朝那里走去,一刻钟两刻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更久,汗水缓缓自耳际浸漫而下,衣衫上印出湿印子,而终于,呼──终于胸口逐渐宽松、呼吸畅顺,步伐重又校准回常轨。走路以自我修复。
走路多半与思考连结,卢梭《忏悔录》里就曾说过:“我只有在走路时才能够思考,一旦停下脚步,我便停止思考;我的心灵只跟随两腿运思。”约翰·泰尔沃在他的《逍遥行》中则有:“至少有一点我可以大言不惭地宣称,我和古代圣贤一样朴素:我在行走之际沉思。”但我走路的初衷,相反地却是为了缓和脑际的运作。
各种思绪参差涌现仿佛一杯混浊的水,我借着踏出一个步伐再踏出一个步伐,机械性、仪式性的简单重复而慢慢沉淀、清空,随之而来的,某些清新的关于创作的念头──也许就是所谓的灵感──便如鲜嫩新芽一般啵啵自皴裂枯败的枝干上萌发。走路是行动的静坐,甚至使我有了新生的契机。
痠,也许逼近于痛,是大量走路的副产品,就像水泥在凝固的过程释放了热,相反地,冰雪融解时吸收热量,而使周遭环境温度降低。
我曾在没有太多走亲山步道──规划得宜的低山山径──的经验下,自观音古道登硬汉岭制高点,下山后跋涉至八里渡船头,搭船到彼岸淡水赋归。钟摆一般,上一个步伐带动下一个步伐,运动T恤湿了又干了又湿,白色薄盐结一圈圈年轮也似的痕迹,自日正当中至月亮高挂,东转西绕地,一趟下来六七小时,累是难免,但精神亢奋,觉得自己可以走得更久走得更远。想要走得更久走得更远。
翌日背痛腰痠,只差没有瘫痪在床,实在是太不知好歹;却同时盘算著下回又该上哪条山径晃晃。
适当的痠痛是锻炼的成果,生命存在的证据。我翻开我所敬爱的小说家柯慈的《麦可K的生命和时代》,直觉可以找到共鸣,果然发现了这样的句子:每当K“在田地里来回走动时,他都感觉到一种来自肉体存在的深刻喜悦”。
这种喜悦来自于礼赞感知身体的原始方式,来自大自然的乡愁,关乎土地与劳动,也来自对都会文明下用进废退、据说人类将演化成只剩一颗西瓜脑袋而四肢终将萎缩的预言图像的反动。
多数时候,“走路”更带有小资情调、布尔乔亚的色彩。
行进间总是左张右望,指认探出墙头的花草,凝视铁窗的花样和锈斑、老房子木头风化后的纹理,扫描街路上一张张脸孔,捕捉能牵引情绪之一瞬如鱼标浮动的物事,多半关乎美。不管美丽的城市与否,总有些因为多情想像而美的星星点点浮凸而出,尤其是生活在他方之际。我不排斥与人偕行,但更钟情一个人上路。
最是迷人的是那些兼收山海之胜、地势高低起伏如小夜曲缓升缓降的城市,旧金山、长崎、香港,乃至于马来西亚新山:我的大马同学领着我爬上马路顶端,放眼对岸是新加坡,眼下为柔佛海峡,海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树的表情是风的表情。
去过许多回香港,渐渐地也就不再迷恋于街市繁华,但总是好期待的是,每到香港要消磨半日光阴的南丫岛家乐径。
可以在中环搭渡轮,索罟湾登岸,经海鲜大街、天后宫,走上家乐径。家乐径地势和缓、路面平坦,虽有人迹但干净、安静,全长六公里,慢慢走约花两个小时可抵达榕树湾。此径前后有芦须城泳滩和洪圣爷泳滩,前者僻静、后者喧闹,端看个人喜爱,不妨逗留片刻。
在榕树湾用过晚餐,天色转暗再搭渡轮,通常忍不住就打起盹来了,当渡轮驶进维港,睡眼中香江最富盛名的夜色层层逼近,惚兮恍兮,是梦的质地。
职场曾举行办公桌布置竞赛,主题乃“梦想中的旅行”。人在路上,心若无余裕,则恒常在赶路,赶朝阳之一瞬、夕照之魔术时刻,赶繁花之易老、烟花之薄命,所以我的旅行,梦想中的旅行,别无所求,只是祈愿不赶路,慢慢走。
京都是宜于慢慢走的城市,有个春天,我准备前往西郊善峰寺,巴士在山径上蜿蜒而行,中途我临时决定下车走走。马路旁休耕的田地里满满盛开著三叶草的小花。宫泽贤治说,只要在傍晚时顺着白花三叶草花朵上所见到的号码一路走下去,便能抵达“波拉农广场”,那是一个没有烦忧扰攘的乌托邦。
暖阳驱走一整个冬季的寒意,空气清净涤洗着胸膛,走着走着,蓦地在爬坡的马路顶点出现一株巨大樱花树,以蓝天为背景盛开一树白色花朵,起风时,花瓣如雪纷纷扬扬。满开时繁华至极,凋零时如梦初醒,啊,比樱花更美的,只有樱花。
徒步至善峰寺时,方才一车旅人都已准备离去。时间不早了,据说由德川家族第五代将军之母亲手栽下的枝垂樱下,我听见一个人说“别偷懒,客人又上门了”,几个娇嫩的声音落错回应“是”,间杂一两句不情不愿的牢骚,又有人说:“忙过花季,就可以休个长假了。”我四下寻找,并无人迹,一阵风吹过,盛开粉红色花朵的枝条款款摆动,摇啊摇啊摇,美人伸了个懒腰一般,最是婀娜多姿。
每日出门,总是为了在书柜找一本适合搭捷运通勤三刻钟翻阅的书籍杂志而举棋不定;不请自来的则是旋律,蓦然附身,顽强地成为当日主题曲。
有个早晨醒来,报到的是“Whoever finds this, I love you!”萧瑟的秋日午后,一个老人踽踽走在荒芜小径上,他发现落叶堆里有一张纸片,拾起一看,泪水泛出眼眶,那是邻近的孤儿院里一名小女孩掷出的瓶中信。因此我有了一个想法,决定当天走路就将目光投向地面,去寻找字纸,有手写字的纸条。
多年前初北上,我曾在一个深夜不小心把自己困在一个废墟也似逼仄的屋子里。洗手间有气窗开往防火巷,但我既非蜘蛛人,也不是美国队长,没有手机没有室内电话,无计可施而又坐立难安之下,我将一张字纸逆着邮件投递孔掷向马路,SOS,Whoever finds this, I need you !
然而那张呼救的纸条,像是没有鱼咬的饵、断线á风吹,一如许多年后,因为一首歌我打算在路途中捡拾字纸却一无所获。
也许这已经不是一个手写字的时代了:与一名初识的朋友临道别时打算留下联络方式,我转身去掏背包,准备找一张纸一枝笔,掏啊掏地到底塞哪儿去了?一抬脸迎来的却是对方错愕的表情。他说你找什么,顺手抄起桌面手机,晓谕我这个手写字时代的遗老:不是有手机!
城市的风景悄悄地在改变──有回通勤途中我蓦然意识到,整个捷运车厢的乘客莫不埋首荧荧发光小萤幕,一个人是一座小剧场,搬演着独角戏;只有我仍翻读着报纸,手上有油墨,彷佛异教徒。
可以等等我吗这世界,以步行的速度。
还好我们仍然走路仍然唱歌,边走路边唱歌。
有段时期,双脚踩踏出的旋律常是,“他沿着沙滩的边缘走/一步一个脚印 浅浅地陷落/他沿著沙滩走 不再回头/他脱了鞋子/喜欢那种冰凉的感受”,在那些挪用周梦蝶的诗句来说,“所有的夜都咸/所有路边的李都苦”的情绪沼泽里,走得有气无力,哼得失魂落魄,少年维持了好长一段日子的烦恼。
演唱会上,有些歌手重唱多年前热门单曲时,会重新编曲,声称是因人事历练、心境转折,便有了不同演绎方法。问题是谁要听这个啊?去听演唱会,就是要听原汁原味原版复刻,带我们重回现场啊。
可是真的耶,一个人好自在时,哼起曾经让人湿了眼眶的失恋情歌时,也好无感;现此时重新唱起“生命中没有多少时候/可以这样沿着什么没有目的地走/也没有什么人规定过/只有十七岁才可以光著脚/十七岁才能为这样简单的事实微笑”,多了轻快少了沉重,多了游戏的趣味,少了钻牛角尖的死心眼。
就这样,走着走着,走过春的气象诡谲,走着走着,走过夏的燠热躁动,走着走着,渐渐地我感受到,感受到了秋日小风轻吹,带走一些躁急的气味,秋阳薄薄,晒褪一些冲动的颜色。我明白了无论如何总会有一条路,等在脚步之前。这是时间送我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