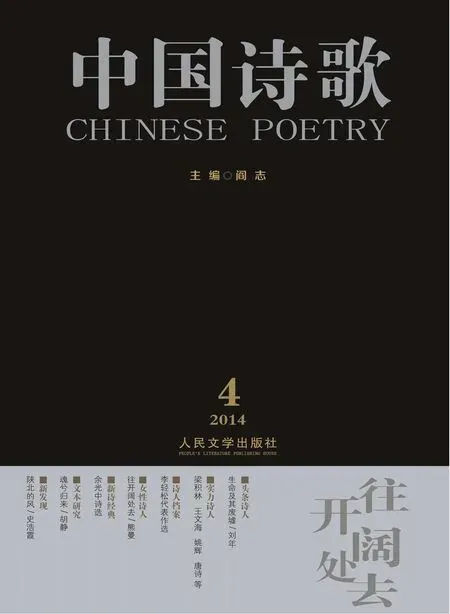生命及其废墟
刘年
·组诗·
生命及其废墟
刘年
刘年是我认识的当代诗人中最具骑士精神的诗人。其诗歌有三个出发地:故乡、路上和现状,在云南时他绕着这三座“雪山”写,去了北京他还是绕着这三座“雪山”不停地写。或卑微如草芥,或灵魂出窍摇身变为大黑天神,或孤独得在出租房里瘦如闪电,支撑他骑士精神的仍然是一个自我流放者、一个文学民工和一个重情重义的赤子的混合体。他的诗歌贴心、动人,温暖而又苍凉,适合在子夜的广场上一个人静静地读,用于个人的祭奠或自救。
初冬
每一天,都当成自己的末日
迟一些睡,早一些起
——雷平阳
默默地辛苦,默默地珍惜,默默地收拾
每天中午,都去收发室看一看
每一次深夜的醒来,都想痛哭流涕
生命(组诗)
1.小秀
小秀想回去了
路边,有一座老坟
她怕,你就去送
回来看到坟,你也怕,她又送你
她回去,坟依然在那里
害怕也依然在那里,你又要去送她
如果不是母亲的帮助
你怀疑,你们会送到天亮
记得那晚,椿树上,结满了星子
有些星子掉在茅草上,会弹起来,变成萤火虫
还记得,一个寂静的下午
大人都修水库去了
在灶房,你胆战心惊地褪下了她的裤子
你的童年,因此有了一条
美丽而又羞涩的伤口
2.苗苗
你最恨的人,是个铁匠
他会钓鱼,打猎,会捉五彩的雉尾鸡
试镰刀的时候,你不止一次
把他勾下的头颅,想象成了高粱
他在你的床上和母亲疯狂地做爱
他让你父亲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他让你母亲走几十里的夜路去追寻他的足迹
那是你一生见过的最深最冷的雪
几十年后,你专程去看他
他的头发,让你再次想到了那场雪
你把钱压在枕头下,嘱咐他,少抽些烟
但不要完全戒。你希望他好起来
你明白,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个人,叫你母亲苗苗
3.阿萍
十六斤重的铁锤
被你高高抡起
两公分厚的钢板
被你当成命运
砸扁,砸痛,砸得惨叫震天
抽烟的时候
你的休息是合法的
所以,你一天抽三包金驼
你把烟点燃,想象
那是生命,在一点点缩短
以烟点烟,把烟蒂踩在脚下
想象那是车间主任
你把另一个烟蒂丢在水泥上
不踩灭,然后,静静地想象
那是一包包50公斤重的烈性炸药
阿萍过来,贼一样
塞给你一样东西
她走之后,有泪水
被你当成汗水,迅速擦掉了
阿萍是车间里惟一的女人
三十九岁,寡妇,车工
略胖,略矮,因为嚼槟榔
牙齿和皮肤一样,有点黄
她像一轮黄色的月亮
挂在暗无天日的灰尘里
她给你的,是一包五块钱的红双喜
你给她的,是二十四年的处子之身
她让你至今都还坚信
女人是宇宙中最接近完美的事物
如果没有月经的话
4.唐子烟
她是你最怕的人
你怕她的名字,怕她的声音,怕她的眼神
连她窗口的蔷薇,都不敢接近
母亲让你许愿考上大学
你却在庙里乞求菩萨,有一天能娶到她
某个清晨,天还没亮,你背着行囊
在她的门口,你压了一张纸条
告诉她,来找你,还附了路线
你知道,她辍学在家,但不知道原因
你知道,她想远远地逃离,也不知道原因
那是你最后的努力,可笑的努力
被脚一踢,被风一吹就会不见踪影的努力
于是,把她塑成了观音菩萨
在内心里,建了一座庙宇
从此,你开始了与孤独的私奔
太冷太累的路上,细雨青灯的晚上
你会进去,慢慢地拂拭,添香
前些天的饭局,有个商人问你
认不认识唐子烟
你淡淡地说,就一河之隔
她家房子卖了,人也不知了去向
她是我初中同学,那时真不懂事,商人道我把她干流产了,又甩了她
商人说话的时候,街上下着大雨
人们朝着各自的方向,匆匆地奔向死亡
但你看到的,却是千亩的冰面和月光
5.二姐
换好床单
你二姐把母亲抱回来
怀里,这个熟睡的孩子般的女人
也曾是村里的一枝花
也曾挑过一百多斤的谷子
也曾和邻村的铁匠偷情
也曾追五条田埂打女儿,用扁担
夜晚,医院阴气很重
走廊上,常有莫名的脚步声
不一定是护士长
害怕的时候,你二姐会服一种叫右佐匹克隆的药片
又来了个脑梗塞病人
下午抬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
这种病真好,要么睡去,要么死去
数完输液管的水滴
你二姐这样发短信给她的朋友
半个月后,母亲竟然醒了
忘了很多事,却还记得女儿
今年41,离过两次婚
有句话,每天都会重复:随便找个男人吧,
生个孩子,我给你带,哪怕是个女儿。
你二姐总是默默地点头,默默地收拾碗筷
一辈子都不生小孩
这样的生命,不值得延续
有次,在和催钱的护士长争吵之后
你二姐这样发短信给她的朋友
女人老成这样子,真难看
自己决不活那么长,45岁就死
有次,给母亲擦身子后
你二姐这样发短信给她的朋友
她说,母亲的乳房,垂至腰际
像两个掏空的麻布袋
养龟记
养只乌龟,在玻璃缸里
于是,办公室里
还有一个生命,比我更安静
周末,带它回家
像个托钵的和尚,走在团结湖路上
于是,城市里,还有一个生命,陪我来,陪我去
陪我到巷子里,配钥匙
从此,出差会有牵挂
这个世界,还有一个生命
离我久了,会活不下去
它搅动着深蓝的夜
似乎想弄出些海浪来
开灯,伸出手指,它立马缩头
我只摸到壳上的伤痕
可怜这个胆小的孩子
它会活得很长
会看到很多我怕看到的
苜蓿花
青菜上有青虫
捉下来,准备喂鸡
你坚持放生
说那是要长翅膀的蝶
不跟你争论
你是个真理的化身
你系着蓝底苜蓿小印花的围裙
喀拉峻
穿一身白衣,骑一匹白马
去喀拉峻雪原,参加一场葬礼
雪并不均匀,有的没蹄,有的没膝
有的背阳处,深达两米,可以直接埋人
薰衣草、芨芨草戴着重孝
远来的风,如丧考妣
生命的底色,是骨白
雪,是那一场葱茏的思念的骨灰
哈木斯提布拉克村
可能啃了马骨头的缘故
走着走着,忍不住跑起来
此时,谁懂得了我的快乐
谁就会爱上遥远、自由和牛粪的味道
谁懂得了我的快乐
谁就不会再害怕孤独和死亡
可能啃了马骨头的缘故
站在草垛边,我像一匹逆来顺受的马
望着苍天,双目柔和而湿润
我愿意驮两麻袋面粉
被一个叫娜依努尔的寡妇牵着
静静地,穿过哈木斯提布拉克村
静静地,穿过白杨林
静静地,走向白雪皑皑的天山
擦皮鞋的人
回去拿东西
路过那间杂物房
里面,已经春暖花开
溪水,树浆,蜂蜜
流淌,泛滥并从砖缝里渗出来
床脚正在发芽
男人像一只快乐的野猪
在丛林里迷了路
女人的声音,失去了节奏
像新剥的笋
青中带白,一掰就断
尖的一头,放进嘴里
一咬,就破
从那以后
每次路过法院门口
我都会留意那两个擦皮鞋的人
一男一女
一左一右
女人四十多岁,肥而矮
男人五十多岁,高而瘦
男人脏而黄
女人脏而黑
两人的皮鞋箱子也大小不同
他们像两个反义词
互不理睬
只有我知道
他们的身体里
各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天堂
鲁迅故居
作为一件礼物
二十八岁的朱安,送给了鲁迅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
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
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可是,现在我没有力气爬了
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
朱安长于针线,烹饪
绍兴话,若耶溪的水一样软
“这辈子只好服侍婆婆一个人了
万一婆婆归了西,从先生一向的为人看
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傍晚,朱安会陪婆婆散步
从鲁迅故居出来,要经过两棵淡白的桂花
“我卖先生的遗物,是因为没有钱过活
我也是先生的一件遗物,你们怎么不管呢?”
婆婆死后,她就一个人散步
放学的孩子都叫她朱安婆婆
小脚的她,走路会像乌篷船一样轻轻地摇
从鲁迅故居出来,直走一百米,就是三味书屋
从鲁迅故居出来
直走,四百米,就是沈园
开荒记
开荒时,不断地犁出人骨
老程一打听,才知道
这里打过仗,死了许多远征军
他把骨头和石头一起,扔进灌木丛
培土,理沟,挖坑,丢种
一片被狗尾草和蚱蜢占领的土地
几天工夫,就被老程夺了回来
看着这片松软、细腻、肥沃的暗红
老程想到了电灯下的姚二娘
一个星期后,老程去锄草
发现有一种黑尾的小雀
把包谷苗拖出来,吃根上的种子
他找了件破衣服,扎了个稻草人
觉得不吓人,于是去灌木丛中
选了一颗完好的人头骨,安在上面
两个月后,包谷长势非常好
每一棵,都有一人多高
在老程面前,像一支雄壮的队伍
六里屯九号院
凌晨三点了,谁还没睡
合上书,开门
月影斑驳,四下无人
靠近围墙的,是棵槐树
那根小臂粗的枝条上
曾吊死了一个十四岁的保姆
有天,男主人喝了酒
看到开门的保姆分外亲切
就把她弄了,当时
女主人在卧房里睡着
后来,男主人又喝了酒
看到开门的保姆更加亲切
又把她弄了,当时
女主人在卧房里,但没睡着
弯弯的枝条在风中
有节奏地摆动着
仿佛下面有个
看不见的人在荡秋千
牛肝菌
称半斤牛肝菌,仔细地削皮,清洗
做菜的男人,手指修长
干椒,蒜头,文火
汤,嫩黄如晨曦
一个人的晚饭,做这么好吃,有些浪费
迟迟不放碗
回忆在亚热带雨林里找不到归路
躺下,往右侧睡
翻《全宋词》,至蒋捷卷
雨声都有韵脚
牛肝菌有很多种,其中四五种有毒
如果一梦不醒
最先来敲门的,当是半年后,催租的房东
从团结湖路到朝阳路
过年,只一个月了,
走出面馆,我想。
喜欢二楼那盏橘黄色的灯。
找房,拨电杆上的号码,
租金是大半月的工资。
挂掉电话,瞪了那只丝毛狗一眼。
我想,能不能买辆厢式货车,
停在公司门口。
下班,钻进车厢就是家。
哪天,看领导不顺眼了,
直接下楼,上车,一路往西,
过青藏,翻喜马拉雅,
到恒河边,一停,就是一个雨季。
报亭旁,有个女人,
像炉边的猫一样,轻轻地唤,
确是冲着我来的。
第二声稍重一些,猫爪般
在我心头抓出了血痕。
等公交的时候,
和一棵老榆树站在一起。
耳朵像两片叶子,
随时,会被风割下来,
明天买顶尖顶帽,我想。
车半天不来,
读一则寻人启事。
男,55岁,脑萎缩,
失踪时,身穿深蓝羽绒服……
剩下的,被撕掉了。
车,依然不来,
我裹紧羽绒服,想
是不是坏了,
像这个城市的星空一样。
胡家寨的牧羊人
寨子里只剩
胡生元和他的四十一只山羊
人走了,草就回来了
羊儿像新月一样,一天比一天肥
为了压寨里的阴气,胡生元
给它们一一安上了熟人的名字
头羊叫胡光宏
那是他的知交,一辈子都想当回官
五年前,在城里扎脚手架时,摔死了
就埋在青枫岭上
那里的草长得特别好
断角的羊,叫木匠老三
他断了一只手,也是左边的
下得一手好象棋
现在在城里摆残局
那只呆头呆脑的,叫杨代课
和杨老师一样,它个子瘦
经常望着远方,不吃草
村小并校后,不知下落
有次卖羊,胡生元看到他在场上卖一堆枞菌
怀孕的黑羊,叫兴华婆娘
羊羔的名字都准备了
公的叫胡健,母的叫胡秋燕
前者,在牢里蹲着;后者,在城里做鸡
最不听话的那只,叫胡兴华
胡生元每天都骂它娘,踢它屁股
他是村里的小组长
不仅搞大了唐玉娥的肚子
还砍了胡生元的两棵核桃
后来跟女儿去了上海,据说学会了跳舞
中秋,胡生元准备亲手杀了它
傍晚,青枫岭乌云滚滚
那只叫唐玉娥的白羊丢了
老胡满山地喊,声音凄厉
像喊一个离开了二十七年的人
林诗诗
一直没告诉她
有次,抚摸的时候
手,在她咽喉停住了
稍一用力,就会听到一声脆响
像藕断,像快门的定格
那晚,月光如瓷
她今年未满12岁
刚刚发育成熟
单独相处的时候
我只叫她一个字,诗
当初只想玩玩
厌倦了老婆的奚落
孩子的哭泣和朋友的酒肉
她像水一样过来了
水一样,任我摆布
水一样,等着我的渴
本以为征服了她
前几天,才发现
真正被征服的,是自己
改变了太多
镜子里,我们有了夫妻相
这个小巫女
送我的围巾,缰绳一样
系住了我的脖子
她耗尽了我的钱财
她带着我,背叛世俗和道德
她牵着我的手
在漫山遍野的油菜花里奔跑
青海的七月
天,蓝得只有一只鹰
我突然站住了
红土路那么直,那么尖
多么像一柄带血的剑
而这个小巫女
依然在跑
她的黄裙子和白衣衫
在风中,多么无辜
多么像我的女儿
长调
暴风雪过后
孤独比天地还要辽阔
牧马的男人,没有带酒
他只有长调
长调很长
比母亲的影子长
比雪原上的破栅栏长
比姐姐的目光长
比地平线长
比冰封的冬夜长
长调,像长长的套马杆
套住了云,套住了奔腾的阴山
套住了查干河
你已经老了
在南方的小城
某个北风呼啸的晚上
你发现
逃得越远,逃得越久
长调的绳索
勒得越紧
致田冯太
田冯太要经过永顺,替我看看父母
有些事情,交待一下
城北两公里,小桥与老树之间
两层的老房子,就是我家
门上贴着春联。父亲有一手好行楷
火塘边,父亲像一只怕冷的猫
告诉他,我很忙,不回家过年了
声音大一些,他耳朵背,特别左边
告诉他,昆明很暖和,我手和脚都没有长冻疮
不要提阿里的事
替我多喝点酒。天麻泡的,不打头
听他说说童年,碾房外,有数不清的鱼
叫他别再拖垃圾,这世界,不是一个老人能打扫干净的
问他疝气好些没有,爷爷的坟什么时候修
给他五百块钱
多坐一会儿,会进来一个人
背着猪草,满头汗水和白发,那是我母亲
告诉她来意。给她五百块钱
不要提阿里的事
致影白
秋深了,保安在写诗
喇叭响起,越野车庞大而庄严
开门,敬礼,对方颔首回礼
其实,你敬的是白杨树上的月亮
诗歌像女人一样,已经走了
揉成一团,扔进垃圾箱
诗稿,比卫生纸要粗糙得多
穿上军大衣,提着手电和警棒,巡逻
城市,是一个巨大的赃物
但月亮,是干净的
电筒打开,光芒雪白
像一柄长剑,你刺向黑暗
只击落一片枯叶
没当过兵,没学过武
三流的保安一流的诗人
但是保安才是你的名片
作为权力的阳具,警棒
显然,比钢笔粗壮得多
一只老鼠在楼脚巡逻
你们心照不宣,互相避开
进来一个鬼鬼祟祟的胖子
你用警棒抵住他胸口
他说他是湘西人,从网吧
写诗回来,声音冻得发抖
你问,为什么不找个正经事做
他说想做保安,和你一起,为人间守夜
他说,想在凌晨五点,用警棒
抵住每一个不睡的人,问
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为了什么,去做什么
羊拉的风
阿明说,拍照,不要站在悬崖边
羊拉的风,力气很大,而且有些变态
阿明说,在羊拉,要学会三件事
第一,要学会同石头说话
第二,要学会钓金沙江的鱼,或者水
第三,要学会喝带着怪味的松子酒
阿明是羊拉的矿工
兼职写诗,穿着脱了毛的皮夹克
两杯酒后,他还原成了牧羊人
用一种神秘的语言和舞姿
又跳又唱。云一片片飘过来
羊群一样,聚满辽阔而荒芜的夜空
第三杯后,他醉成了诗人
吐出的词语很脏,有的,还带着血丝
他说经常去金沙江边,一坐就是半天
他说金沙江水血一样红,没有渡船
他说骑马到县城要四天,寄信要一个半月
一个带卓玛的名字,花生米一样,被他反复咀嚼
他说,女人痴得有点变态
他说,很想逃走,在变成矿石之前
他还提及这里的冬天,以及一人多高的雪
这个晚上我没有睡好
羊拉的风像女人一样,在旅馆下面的篮球场上
大声地哭,半夜过了都不停
第二天,羊拉的草全部黄了
风,不知去向
废墟
所有的铁锁都在生锈,所有的粉刷都在剥落
所有的围墙,都在等待倒塌
于是,我把这片繁华,命名为废墟
一辆漆黑的两轮马车刚刚过去
没有人过问,里面坐着医生还是巫师
于是,我把断柱上那只沉默的乌鸦,命名为孤独
狗尾草已经高过了落日和庙宇
所有的承诺,已经变成瓦砾
于是,我把这座缺了一条腿的石狮,命名为自己
荨麻只长荨麻叶,牵牛藤只长牵牛叶
针茅只开细白的花,枇杷树不结一颗桃子
四季如此辽阔,从容和无微不至
于是,我把这片饱含泪水的大地,命名为爱人
时间和茂盛的言词不足以埋葬一切
一定能找到破碎的瓷器,证明历史的骨头
一定有土拨鼠在挖掘老栗树的根
于是,我把这个静如坟墓的废墟,命名为繁华
世人形容金钱和宫殿的,也可以形容草垛
站草垛上,你看到的是故乡,乌鸦,看到的则是死亡
于是,我把这些金黄的晚风,命名为疼痛
于是,我把那只打开翅膀打开沉默的乌鸦
命名为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