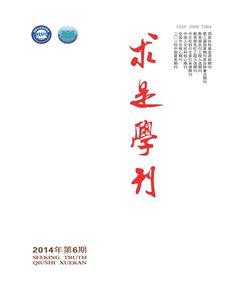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减贫增收效应
范辰辰+陈东
摘 要:以系统的理论分析为基础,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全国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离散选择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等多种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新农保的政策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新农保在全国范围内显著降低了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的概率,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了农民的经济保障能力。进一步地,对不同年龄群体分组检验的结果表明,作为主要目标群体的农村老年人受政策影响更为显著;但是处于缴费阶段的农民并不会因为参保致贫,某种程度上甚至有减贫效果。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减贫增收;缴费阶段;领保阶段
作者简介:范辰辰,女,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农村公共政策研究;陈东,男,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从事农村公共政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财税机制与制度研究”,项目编号:13&ZD03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对新农合实施效果的跟踪研究”,项目编号:14BJY096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6-0062-09
引 言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养老方式以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为主,但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人口老龄化加速、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单向流动以及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小型核心家庭模式逐渐取代了传统大家庭模式,作为家庭保障物质基础的土地保障功能也不断弱化,农民养老脆弱性问题更加突出。在家庭养老模式不再满足农村迅速增长的养老保障需求的背景下,我国不断出台相关制度,以期对传统家庭养老进行转型和替代。2009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试点,农民的养老金待遇由个人账户资金和基础养老金两部分组成,前者源于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是一种储蓄型积累;后者则完全由政府财政负担,具有转移支付性质。新农保的实质是个人储蓄与国家责任相结合的一种社会福利制度[1],其主要政策目标是“实现广大农村居民老有所养、促进家户和谐、增加农民收入”。新农保制度自2009年开始试点,至2012年基本实现全覆盖,制度的短期效应逐渐显现,本文所要关注的正是新农保试点的推行是否在短期内达到了增加农民收入、减少贫困发生的预期目标。
从国外研究成果来看,各国学者对社会保障与公共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颇具共识。例如,House等(1988)发现,社会保障能够显著改善老年人口的生活状况,降低经济贫困的发生概率。[2]无独有偶,Ahmad(1991)亦指出,社会保障应该直接针对收入贫困者,理论上具备显著的减贫效应。[3]究其原因,转移收入可以降低贫困家庭的多元化投资需要,避免其陷入极度贫困。[4]其中,Chen 等(2009)分析了转移支付对中国贫困的长期影响,肯定了适度的增收效应。[5]在与中国国情相似的南非、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社会养老保险的减贫效果也已得到证实。Barrientos(2003)利用巴西和南非的家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养老对老年贫困率的影响,发现两国针对老年人的非缴费型养老金具有显著的减贫效果。[6]Rivera-Marques等(2004)研究了墨西哥城针对老年人的保障计划,发现该项目减少了贫困和收入不平等,但其减贫效果在申请资格被放松时会弱化。[7]Lloyd-Sherlock等(2012)利用2002年和2008年两阶段的南非和巴西数据,动态分析国家和地方两个不同水平的养老金对老年人贫困和福利的影响,结果显示这些国家的养老金制度对于家庭贫困的广度和深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样本家庭的生活满意度不断提高,但影响程度尚不确定。[8]
与国外研究形成对比的是,国内学者对新农保收入效应的研究凤毛麟角。薛惠元(2013)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43个样本县2009—2010年的基本经济数据和湖北省试点县的抽样调研数据,分别从县级和农户两个层面对新农保的减贫效应做出初步探讨,发现新农保在县级层面具有显著的减贫增收效用,但是在农户层面的减贫效果并不明显。[9]类似地,刘远风(2012)利用湖北省50个县域的经济数据,通过构建倍差模型证实新农保具有减少收入差距的效果。[10]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对消费和家庭代际支持的研究也涉及新农保的收入效应,如沈毅、穆怀中(2013)利用2011年全国31个省(市)新农保支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等宏观数据对新农保拉动消费的乘数效应进行验证,发现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发放增加了农村老年人的收入,直接产生消费刺激[11];程令国等(2013)、陈华帅和曾毅(2013)利用2008—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两期面板数据,使用倾向分值匹配基础上的差分内差分方法分别评估了新农保对农村居民养老模式的影响和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12][13],发现新农保提高了参保老人的经济独立性,降低了老人在经济来源和照顾方面对子女的依赖。
尽管部分国内学者或者基于个别省份的调研数据,或者采用农民人均纯收入、新农保支出等宏观数据对我国新农保政策的收入效应进行了分析,但是仍然存在比较大的改进空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 新农保制度的收入效应需要依据新农保不同的参保阶段进行区分。根据新农保政策的规定,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农村居民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新农保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的,只要参保或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参保,不需要缴纳保费每月可领取最低55元的基础养老金;而对于16—59周岁的农村居民,需要选择不同的缴费档次缴纳养老保险费,纳入个人账户,待60周岁后方能领取。因此,新农保制度对处于缴费阶段(16—59周岁)和领保阶段(60周岁以上)的农村居民的影响不同,对新农保效应的分析应区分参保阶段。
2. 新农保的收入效应需要采用全国范围内的大样本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究其原因,由于中国不同县市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异质性很强,若调研地区仅仅集中于一个县市,或者多个地区的单一县市,不仅可能导致样本代表性不佳,而且普遍偏小的样本容量可能无法真实反映总体情况。
据此,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CHARLS)数据,拟使用全国样本分析新农保制度的减贫、增收效应,并且细分不同参保阶段农民群体的收入效应。
一、新农保减贫、增收效应的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看,新农保制度为60周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提供55元/人/月的基础养老金,该部分是独立于个人缴费并由国家财政提供的具有福利性质的转移支付。其一,处于领保阶段的老人每年的收入至少会增加660元,对于完全没有经济来源的老人而言,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其二,如果这部分基础养老金收入能够使接受者摆脱流动约束的困扰,投资于健康、教育等生产性活动,还会产生收入的放大效应。[14]其三,养老金的发放可能会对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金额产生“挤出效应”[13][15],与收入增加相伴的是私人转移支付的减少[16],此时新农保制度对老年人口的增收效果会被削弱。
然而,处于缴费阶段的参保农民则可能面临不同的际遇:除了不能领取养老金,每年还需要缴纳一定数额的参保费用(最低标准为100元/年/人)。虽然地方政府给予不低于30元/年/人的缴费补贴,但要计入个人账户到60岁才能领取,并不构成当期收入。因此,从短期来看,处于缴费阶段的农民一旦参加新农保,就意味着经济支出,相应减少了其可支配收入,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甚至可能因为缴费挤占了其生产和生活资金,给贫困家庭造成经济负担[9],对其减贫增收效应是负向的。当然,政策制定者也考虑到农村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要求地方政府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因此,对缴费阶段农民而言,新农保的减贫效应可能是中性的,甚至是负的。
整体而言,社会养老保险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范畴,新农保制度可以说是一种从增加农村老人收入、提高老人生活水平的角度缓解老年人贫困状况的措施。再加上新农保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模式,社会统筹的财政补贴部分体现为代际的再分配,个人账户部分则为代内的再分配。因此,从理论方面看,新农保制度必然会对农民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数据和研究方法
(一)样本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CHARLS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导的对中国中老年人进行的家户调查,调查对象为随机抽取的家庭中45岁及以上居民,该数据覆盖全国150个县、区的450个村级单位,访问了10 257户家庭的17 708位个人,总体上代表中国中老年人群,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以中老年人为调查对象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微观数据。
就本文的研究问题而言,CHARLS数据具有下列突出优点:一是调查对象与新农保的主要参保人群一致,新农保的参保人群主要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二是覆盖面广,涉及全国28个省区,与新农保全国的开展情况相统一;三是农户样本数量大,以此为基础得出的分析结果具有代表性。进一步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将CHARLS的社区数据、家庭数据与个人数据匹配后,形成了包含28个省区的404个村级单位,共计农村家庭7351户、12 195位个人信息的综合数据集。
(二)变量设定与统计性描述
1.被解释变量
(1)贫困(Poverty)。《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农村贫困标准为人均纯收入1274元,据此,若受访农民的个人收入低于1274元,即为贫困,贫困变量为0—1变量,受访者处于贫困状态时取值为1,非贫困状态时取值为0。
(2)个人收入(Income)。包括个人工资收入、个人获得的转移支付、家庭人均收入,其中,家庭人均收入由家庭总收入(家户农业纯收入、家户个体经营纯收入、家户政府转移支付收入、家庭经济支持)除以家庭人口规模计算所得。
2.关键解释变量
(1)是否参加新农保(Nrpsdummy)。该变量为虚拟变量,参加新农保赋值为1,否则取0。
(2)参保年限(Partyear)。由问卷中受访者的“参保年份”和受访时间计算得出。
3.其他解释变量
根据现有文献和尽可能外生的原则,本文在数据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选取了以下变量:
(1)个人特征:年龄(Age)、是否完成高中教育(Highschool)、是否为女性(Female)、健康状况(Health)、是否已婚并与配偶同住(Married)。
(2)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是否领取政府补助(Subsidy)、家庭人口规模(Hhsize)、人均家庭耕地面积(Gland)。其中,家庭人口规模使用CHARLS问卷中“最近一周,家里几口人吃饭(不包括客人)”的变量替代。
(3)村庄特征:包括所在村庄人均纯收入(Gvincome)、村外出打工比例(Workout)、是否纳入城镇规划区(Cityplan)、村农业人口占比(Agripopu)、村占地面积(m1)、村高中文化程度比例(Vhighschool)。其中,“村农业人口占比”由村常住农业户口人数除以村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数计算所得;“村外出打工比例”由村外出打工人数除以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数计算所得。
(4)为了控制地域的固定效用,还引入了省份虚拟变量。
表1比较了样本中参保农民与未参保农民的基本特征,初步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整体样本中有27.05%的受访者参加了新农保,参保者的平均参保年限为1.96年。全样本中约有48.66%的农户为贫困人口,平均而言,参加新农保的农户中41.72%为贫困人口,平均收入为4617.6元,而未参保的农户中贫困人口则为51.27%,平均收入为3719.84元,相比于未参保的农户,参保的农户贫困发生率较低,收入也高于未参保农民。除了人均家庭耕地面积和村占地面积之外,参保群体与未参保群体的控制变量差别不大,但参保农民所在家庭领取政府补助的比例要高于未参保农民,说明领取政府补助的家庭对政府政策的信任度更高,也更容易参保。
(三)计量模型与方法
1.多元回归
鉴于新农保政策只是影响农民收入的众多因素之一,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引入尽可能多的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以减少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其中,在研究新农保政策的减贫效应时,由于被解释变量“是否贫困”为二值虚拟变量,我们采用Probit模型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而研究新农保政策的增收效应时,农民收入是连续变量,则采用OLS回归估计方程系数。
参考现有文献研究,本文采用以下回归方程对新农保的收入效应进行检验:
其中, 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表示受访者是否处于贫困状态以及个人收入状况,下标 代表受访个体、 代表省份; 为关键解释变量,分别表示受访者是否参加新农保与参保年限, 为其他解释变量; 是省级虚拟变量; 为待估计参数; 为误差项。
2.工具变量法
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时,关键解释变量“是否参加新农保”,可能会因为反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而出现内生性问题。以农户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为例,一种可能是,收入较高的农户由于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来缴纳保费,为了使自己在年老之后更有保障,因而更加倾向于选择参加新农保;另一种可能是,穷人因为更加需要获取新农保的养老金来提高自己的收入,从而更加倾向于参加新农保,此时内生性问题可能导致系数估计值有偏差。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受访者所在村庄领取新农保养老金人口比率”作为是否参加新农保的工具变量,其计算方法为村庄领取新农保养老金人口与村庄常住人口之比。村庄领取养老金的比率与受访者是否参保显然高度相关,因为只有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居民才有资格领取养老金,而且村庄层面上养老金的领取比率对受访者的收入并没有直接关联,也不会与影响农民收入的其他不可观测变量相关,其外生性是可靠的,符合作为工具变量的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当考察新农保减贫效应时,我们面临的是在二值选择模型中存在内生解释变量的情况,忽略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而直接使用线性概率模型的工具变量法将会导致不一致的参数估计量,很容易得到错误的系数估计值[17]。另一方面,由于本文的内生解释变量为离散变量,并非连续变量,因而并不适合采用控制方程估计方法(Control function approach)。参照Dong和Lewbel(2012)的做法[18],我们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Maximum likelihood approach)和特殊回归变量方法(Special regressor approach)来估计存在离散内生解释变量的二值选择模型。使用特殊回归变量方法进行估计时,由于农户年龄变量为连续变量且条件独立于扰动项,我们选择农户年龄变量作为特殊回归变量,因而最后回归结果中并未出现其系数估计。当考察新农保增收效应时,则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
三、新农保的减贫效应
(一)新农保对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的平均影响
新农保对农村居民贫困发生概率影响的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是否参加新农保”对贫困发生率的单变量回归系数为-0.173,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控制个人、家庭、村庄特征及省级固定效应之后,参加新农保的系数为-0.147,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参加新农保对农民陷入贫困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参保年限”作为关键解释变量时,单变量系数估计值为-0.069,引入控制变量后的系数为-0.060,估计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参保时间越长,贫困发生的概率越低。引入工具变量后的最大似然估计(ML)及特殊回归变量估计(SR)结果显示,“参加新农保”的系数分别为-0.569和-0.112,具有负向的显著性。因此,从平均影响来看,新农保具有降低参保人群贫困发生的效果。
其他解释变量方面与现实情形也较为吻合。“年龄”和“家庭人口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对于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村居民而言,年龄的增加意味着身体素质和精力的下降,劳动参与的减少使得贫困发生的概率增加;家庭规模越大,生活的成本越高,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大。“完成高中教育”和“村外出打工比率”的系数显著为负,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主要因素,可以提高生产的能力,从而增加个人收入;寻求更高的收入是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的直接动机,外出务工的比例越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对缓解家庭贫困有积极影响。
(二)按年龄分组考察新农保的减贫效果
表2报告了新农保减贫效应按年龄分组的估计结果。第(1)、(3)列显示,在年龄大于60岁分组下,以“是否参加新农保”和“参保年限”为关键解释变量时,参数估计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第(2)列为引入工具变量后的结果,关键解释变量的估计值在10%的水平上仍然显著为负。这是因为对该阶段的农民而言,无论之前是否缴费,每年大约700元的基础养老金补贴直接增加其收入,特别是对于个人收入较少或者几乎没有收入的农民,这笔收入无疑能够缓解流动性约束,改善生活状况,降低农村老年人陷入贫困的可能性。
表2(4)—(6)列中年龄小于60岁组“参加新农保”和“参保年限”的多元回归估计值均为负数,但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这表明,农村居民并不会因为缴费而加剧其贫困,他们完全有能力承担新农保制度的缴费,不会处于缴费困境[19][20]。该结果同时也说明,政府在公共财政内的适度补贴能极大提高农民的缴费能力,对缴费困难群体代缴部分或全部养老保险费这一制度设计,可以有效避免困难群体因参保而致贫返贫。值得注意的是,引入工具变量后“参加新农保”的估计值显著为负,这一结果与理论预期相悖,究其原因,可能是新农保参保实行“捆绑式”原则,即“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的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该原则使得很多中青年农民参保是为了家中老人可以领取基础养老金。已有研究证明,普惠型养老金的发放会增加参保老人的经济独立性,降低老人在经济来源和照料方面对子女的依赖[12][13]。因此,家中如有老人领取基础养老金,可以减少子女的养老负担,也就增加了家庭中青年人口外出务工的可能,青年家庭获得更多的收入,减少了贫困的发生。
四、新农保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一)新农保对农民收入的平均影响
表3是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全样本回归结果。(1)、(2)列报告了“是否参加新农保”为关键解释变量的多元回归结果,参保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3)、(4)列显示了引入工具变量后,参保变量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新农保具有显著的增收效果,使用工具变量后的估计值比OLS的估计值要大一些,这是因为参加新农保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造成OLS估计中的估计值偏小;(5)、(6)列则报告了以“参保年限”为关键解释变量的结果,其系数估计值同样显著为正,说明参保年限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参保年限越长,农户收入越高。“年龄”控制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即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逐渐减少,与减贫部分得到的结果一致,为确定新农保对不同参保阶段农民收入的影响,本部分将按年龄分组进一步讨论。
(二)按年龄分组考察新农保的增收效果
表4报告了新农保增收效应的分组估计结果。年龄大于等于60岁组的参数估计值在以“是否参加新农保”和“参保年限”为解释变量时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引入工具变量后结果同样显著为正,表明对于60岁及以上的农民而言,参加新农保确实具有显著的增收效果,且参保时间越长,收入增长越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源于个人账户的完全积累性,缴费年限越久,个人账户累积储蓄越多,60岁之后可得的养老金收入也越多;另一方面源于新农保影响的时滞性,其政策效果要在一定时间后才能更好地显现出来。小于60岁年龄组的变量估计值同样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新农保制度收入效应体现在不同阶段,但囿于养老金支付的低水平对中青年人的影响仍不明显。因此,全样本结果表明,新农保的受益者主要是处于领保阶段的农村老年人,并且政策实施的时间越长,老年人的收益越大。
综上所述,本文的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新农保政策对于农村居民具有减贫、增收效果。分组估计结果的差异也证明,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确实存在异质性,即不同参保阶段的农民受益程度有显著差别:处于领保阶段的农民从参加新农保中受益更多,也更为显著,既减少了贫困发生的概率,又增加了农民收入;而处于缴费阶段的农民并没有因为参保费用陷入贫困或增加经济负担,从某种程度上甚至起到了减贫的效果。此外,从结果的稳健性来讲,本文实证部分运用多种计量方法估计的结果一致,证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可靠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理论上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减贫、增收效应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离散选择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等多种计量模型,从实证角度对全国范围内新农保的减贫增收效果进行了评估。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参加新农保显著降低了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的概率,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进一步地,按年龄分组的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主要目标群体的农村老年人受政策影响更为显著,但参保子女从新农保中同样受益。因此,从短期来看,新农保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对提高农民收入、减少贫困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增强了农民的经济保障能力,完成了预期的政策目标。与此同时,新农保对参保家庭代际的影响已经初步显现,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新农保效应的相关问题时,需要考虑到代际的相互作用。
尽管已经证实新农保基本完成了增加农民收入、减少贫困的目标,不过也应该看到新农保当前统筹层级较低,保障力度偏小的短板。农民虽然没有缴费能力风险,但是由于缴费较少造成个人账户累计薄弱,导致养老金保障能力不足,养老金支付水平远不能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与南非等国实施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效应相比,新农保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这是因为目前新农保的养老金支付水平较低,每年660元的基础养老金水平,仅为201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1.15%,而南非2005年发放养老金标准约为130美元/月,相当于人均收入中位数的两倍。若要真正实现农民老有所养,新农保政策仍需在以下方面继续完善:其一,加大财政补助力度,逐步提高养老金待遇。为此,中央财政需要增加支持力度,地方财政根据实地情况适时补充;个人账户方面要拓展新农保基金投资渠道,在确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商业化运营,以提高个人账户基金的收益率。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双管齐下,巩固新农保的养老保障能力。其二,新农保应尽快实现从“制度全覆盖”到“人群全覆盖”。政府应该特别关注贫困农民的参保问题,本文已证明参保不会致贫返贫,且具有普遍意义的增收减贫效果,应吸纳更多缴费困难农民加入,加大对缴费困难群体的倾斜力度,更大范围内发挥新农保作为具有福利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其三,要确保新农保缴费的财政支持机制,充分发挥政府财政补贴的激励效应。一方面,在农民缴费能力的范围内,适当提高最低缴费标准,因地制宜增加可选择的缴费档次,明确多缴多得的财政补贴机制。另一方面,加大新农保宣传力度,积极探索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激励中青年农民群体积极参保、及早参保,以增强新农保制度的稳定性。
参 考 文 献
[1] 赵曼:《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2] House J S, Landis K R, Umberson D:“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health”. in Science, 1988,(241).
[3] E Ahmad, JR Hills, AK Sen: Social secur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1.
[4] Carter M R, Barrett C B: “The economics of poverty traps and persistent poverty: An asset-based approach”. in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6,(42).
[5] Chen S, Mu R, Ravallion M: “Are there lasting impacts of aid to poor areas?”. i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9, (93).
[6] Barrientos A:What is the Impact of Non-contributory Pensions on Poverty?: Estimates from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IDPM,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2003.
[7] Rivera-Marques J A, Morris S, Wodon Q, et al.: Evaluation of Mexico citys safety net for the elderly (preliminary results). Working paper, World Bank, 2004.
[8] Lloyd-Sherlock P, Barrientos A, Moller V, et al.: “Pensions, poverty and wellbeing in later life: Comparative research from South Africa and Brazil”. in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012,(26).
[9] 薛惠元:《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减贫效应评估——基于对广西和湖北的抽样调研》,载《现代经济探讨》2013年第3期.
[10] 刘远风:《新农保扩大内需的实证分析》,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2期.
[11] 沈毅, 穆怀中:《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乘数效应研究》,载《经济学家》2013年第4期.
[12] 程令国, 张晔, 刘志彪:《“新农保” 改变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养老模式吗?》,载《经济研究》2013年第8期.
[13] 陈华帅, 曾毅:《“新农保” 使谁受益: 老人还是子女?》,载《经济研究》2013年第8期.
[14] 解垩:《公共转移支付和私人转移支付对农村贫困、不平等的影响: 反事实分析》,载《财贸经济》2010年第12期.
[15] Jensen R T.“Do private transfers ‘displacethe benefits of public transfers? Evidence from South Africa”. i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1).
[16] Juarez L. “Crowding out of private support to the elderly: Evidence from a demogrant in Mexico”. i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9,(3).
[17] Lewbel A, Dong Y, Yang T. “Comparing features of convenient estimators for binary choice models with endogenous regressors”. i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économique, 2012,(3).
[18] Dong Y, Lewbel:A simple estimator for binary choice models with endogenous regressors. in Econometrics Reviews, forthcoming,2012.
[19] 杨礼琼:《农村养老保险意愿缴费能力因素分析》,载《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3期.
[20] 邓大松, 董明媛:《“新农保”中农民缴费能力评估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试点地区的调研数据》,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责任编辑 国胜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