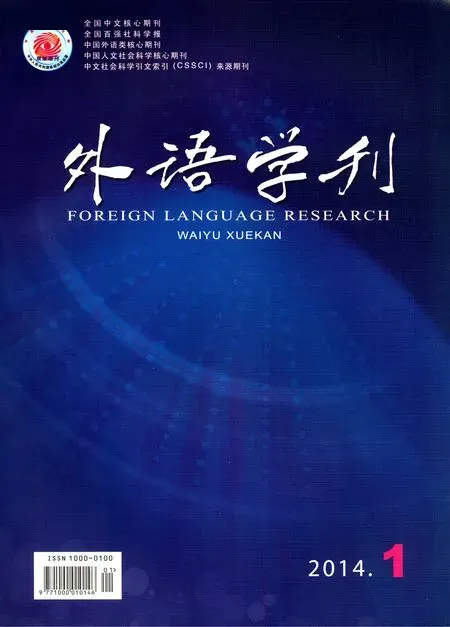从《故地重游》到《去日留痕》凸显出的英国性的转变*
王 卉
(南京大学,南京 210093;大连外国语学院,大连 116044)
●文学研究
从《故地重游》到《去日留痕》凸显出的英国性的转变*
王 卉
(南京大学,南京 210093;大连外国语学院,大连 116044)
被称为“英国性”的英国民族认同在文学中通常以英国乡村庄园为载体,因此英国传统的庄园小说经常讨论英国的民族精神。本研究通过对比《故地重游》和《去日留痕》发现,前者中的本质主义的民族认同通过怀旧的方式被拥有伦理知识的庄园精神继承者承袭;而后者中的非本质主义的民族认同通过对话和沟通的方式被全体英国民众所共享。因此,英国庄园小说中体现的英国性经历着从给定到构建、从本质主义到非本质主义的改变。
《故地重游》;《去日留痕》; 英国性; 庄园小说
1 英国性与英国庄园小说
英国性的研究“实际为民族身份认同的研究,而身份是被区别出来的特性,通常使用筛选、过滤和压缩的方法来研究自己的民族历史,从而使得本民族和他民族相区别”(Langford 2000:14)。认同最早是作为哲学范畴而出现的,其意义就是表示某些事物是相同的、一致的,或者就是它本身。弗洛伊德从心理学意义认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车文博 1988:375)。因此,民族认同作为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认知具有鲜明的群体属性。托宾·希伯斯曾经同时宣称,伦理的核心就是群体(Siebers 1988:202),因此民族认同问题具有重要的伦理维度。
“英国性”的英国民族认同在文学中常常以英国乡村庄园为载体,乡村庄园“是最具英国性的事物。乡村大宅是大英帝国的文化遗产”(王卫新 2010)。弗吉尼亚·肯尼(Virginia C. Kenny)认为,自18世纪以来,英国的乡村庄园就成为美好社会的隐喻。在简·奥斯汀《曼斯菲尔德庄园》的时候,英国的庄园被定位为英国民族精神的重要方面,并且成为体现英国民族身份的重要场所。然而到劳伦斯创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时候,这种传统的庄园小说中构想的民族精神意象却显得模糊和单薄。世界大战、对现代化态度的改变、经济萧条以及再次世界冲突的必然性等因素都逐渐破坏乡村庄园作为民族象征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而伊夫林·沃和石黑一雄都试图复兴传统英国庄园小说,并且作品中的布赖兹赫德和达林顿府都曾经经历过海伦·施莱格尔预见的衰败。因此,乡村庄园作为英国社会的象征,并且能够将社会中各种相互冲突和矛盾的理想融合为统一的民族精神的愿景就无可避免地充满怀旧和乡愁的情愫。《故地重游》和《去日留痕》同时借用英国小说创作中“遗产危机”叙事的传统(Su 2005:120),借助英国乡村庄园的境况反观英国的民族命运。早在20世纪20年代,奥尔德斯·赫胥黎和劳伦斯就分别在《克罗姆庄园的铬黄》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讽刺这种将英国的民族命运和乡村庄园相联系的观点,沃自己也在《一抔尘土》中讽刺这种传统。但是他却在1944年坚持认为,英国祖先们的故园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民族成就”,并且慨叹它们的衰败。可见,沃在《故地重游》中也将英国的乡村庄园作为英国民族认同的象征,并且借助庄园的荣衰来隐喻英国性的发展变化。石黑一雄在《去日留痕》中也偏离以往的创作轨迹,他对达林顿府和管家史蒂文斯的兴趣也有别《群山淡景》和《浮世画家》中对战后英籍日裔移民经历的探究。有学者认为,《去日留痕》展现的是“田园式和怀旧式定位的英国性”,让史蒂文斯陶醉的是乡村大宅和英国风景(王卫新 2010)。《去日留痕》和《故地重游》实则在追溯简·奥斯丁、亨利·詹姆斯和福斯特对英国乡村庄园的兴趣,探讨英国性构成的问题。那么两部相隔半世纪之久的作品所构建出的英国性的异同是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因为它会体现出英国性在历史语境中的变迁。
2 《故地重游》中的民族认同
伊夫林·沃的《故地重游》和石黑一雄的《去日留痕》中英国乡村庄园的衰败自然激发起英国民众对逝去民族荣耀的渴望和留恋。《故地重游》中的布赖兹赫德庄园被征用作抵抗希特勒战事中的临时兵营,庄园中的喷泉已经干涸,里面丢满士兵们的烟头。然而沃却认为,如果乡村庄园正在衰败,整个国家都会因为没能保护自己最伟大的遗产而负有责任;如果英国期待值得向往的未来,那就应该复兴乡村庄园和庄园所象征的民族精神。
《故地重游》中复兴民族精神的任务落在瑞德的肩上,因为他掌握着至关重要的伦理知识(ethical expertise)(Su 2005:122)。柏拉图的对话可以视作伦理知识概念的延伸,而伦理知识是伦理智慧的源泉(Nobel 1982:7)。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性的善是灵魂顺乎美德的活动,同时要以明确的目标为基础,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要顺乎美德地使用灵魂中理性的部分,而伦理知识将是实现该目标的决定因素。但是亚里士多德同时指出,顺乎美德而生活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我们都需要伦理专家的帮助。因此,掌握伦理知识的伦理专家应该存在,从而帮助其他人赢得美好的生活(qtd. in Khan 2005:41-43)。庄园真正的代表者都会拥有某种特殊的伦理知识,这种潜台词几乎毫无例外地写进英国传统的庄园小说(Su 2005: 122)。瑞德的伦理境界和故事中其他角色或骄奢、或荒淫、或空虚的生活形成鲜明对照:马奇梅侯爵在威尼斯的华厦中包养着终身情妇卡拉;貌似虔诚和热情的马奇梅夫人实则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他们的长子布赖兹赫德生性怪僻而虚伪;次子塞巴斯蒂安酗酒无度;而那些以胡柏下士为代表的青年士兵们生活空虚而放荡。因此,如果《故地重游》中构想出的群体能够将布赖兹赫德庄园当做英国民族精神的象征,那么瑞德先知般的声音就是这种精神的唯一定义。
作为民族认同的复兴者,瑞德在故事的进程中逐渐显露出与庄园纷繁复杂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怀念那些马奇梅庄园客厅中发现的东西,并且哀悼它们的消失”(Waugh 1945: 227)。他曾经认为庄园的空间和它体现的民族精神已经荡然无存,然而,故事结尾处小教堂的重新开放迫使瑞德重新考虑自己的结论,而此时能够体现庄园精髓的部分也由客厅转变为小教堂。瑞德同时真切地感觉到教堂体现出的民族精神,因为虽然“昔日那些骑士们曾经看见的、从他们的坟墓中腾起的火焰已经被熄灭”,但是他今朝却目睹“这些火焰在古老的石壁中重新燃起”(Waugh 1945:351)。瑞德有关小教堂是庄园真正的灵魂的发现让他能够将天主教和英国性融合起来,沃在《故地重游》中始终寻求某种价值系统,试图由此拯救日益衰落的国家和民族,而天主教的作用就应该在此种语境中解读。天主教与英国性并非相悖,而是其核心部分,因此天主教的恢复和英国性的复兴实则息息相关。沃在战争和士兵中感知到的英国民族精神的消亡是因为支撑该国家900余年的价值系统被雪藏已久。这种发现也使得他能够再次投身到岌岌可危的战事中,和他的同胞们共同应对当前复杂的任务,虽然他某些战友对布赖兹赫德庄园仍然充满蔑视。此时的瑞德成为庄园的精神继承者,并且守护着历史的记忆。因此,《故地重游》实则借助天主教的思想来满足国家民族复兴的需要。瑞德告诉读者们,“十字军战士们多年前首次目睹火焰,而现在它重新为其他战士燃烧”(Waugh 1945:351)。瑞德选择基督教火焰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承诺,并且将自己比作当今的十字军战士,从而重新投身到为国尽忠的战斗中。英国民族精神和基督教信仰由此融合得天衣无缝。
瑞德领会英国民族精神,成为其继承者的方式便是怀旧。怀旧情结在《故地重游》中的重要性非但仅仅体现在引发瑞德等人回忆过去,而且过往事件的重要意义只能在回溯的过程中被充分认识。当瑞德回顾自己成熟过程的时候曾经暗示到,“新的事实和真理反复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先前的知识也必须由此重新整理”(Waugh 1945:79)。在他的生活阅历中,这种观点也可以视作他与布赖兹赫德庄园以及英国的关系的注释。客厅和小教堂分别体现出的布赖兹赫德庄园精神其实并非相互矛盾;后者体现出的精神更加真实,但是也更加隐性。但是这种事实在当时是无法被认识到的,因为只有那些经历过失落和失去的成熟的智者才能够获得这种洞察力,因此那些以下士胡柏为代表的英国年轻人会迷失方向,屡遭失败。他们缺失文化记忆,缺乏对过去的足够尊重,因此无法体会到怀旧和乡愁的情绪,而该种情绪恰好是感知英国民族精神的前提条件。沃没有在故事中构想出能够扭转历时百年颓废局势的新英国(Gamble 1982:25),瑞德的怀旧情绪使他深陷无尽的反思,而这种反思的过程实则依赖于英国的衰败。他在认识到布赖兹赫德庄园的衰败之前未曾亲眼目睹火焰在石壁中重新燃烧,而恰恰是庄园破败的意象促使他最终意识到,英国的民族精神并非仅局限在庄园的物质结构中,火焰的意象暗示着民族精神的真谛会长燃不熄。因此,瑞德在经历过失落后才认识到英国民族精神的真谛。
因此,此处的怀旧情愫并非仅仅是对过往辉煌的哀悼和追忆,而是使得作者有机会转变有关庄园的记忆。怀旧使得故事中布赖兹赫德庄园本质的承载者由客厅转变为小教堂。这种转变只能在经历过失落后,通过追溯的方式实现。并且《故地重游》中的怀旧情绪能够通过叙事提喻的方式(Su 2005:136),将庄园的某个部分视为庄园整体的代表,从而缓解掉庄园的各种相互矛盾意象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意象所引发的众多民族传统之间的相互抵触。沃将庄园中的小教堂描述为未受到空虚而颓废的时代所侵扰的部分,声称庄园的遗风已经被完整地继承,并且将那些有悖于他想象中的天主教式的英国性的因素消除殆尽。因此,瑞德先是哀悼客厅的损毁以及它所代表的贵族文化理想的消亡,随后便构建起小教堂所代表的精神实质。他无需再痛心地感慨“一切皆是空虚”,而是得出结论认为“小教堂中的火焰必然是为庄园的建设者们重燃”(Waugh 1945:351)。虽然作为物质构造的庄园已经凋敝损毁,但是小说仍然暗示出,瑞德已经继承了庄园所象征的民族精神,并且将它保存在记忆中。
布赖兹赫德庄园的民族精神火焰在福克兰群岛纷争的余波后继续燃烧,撒切尔首相宣称,“英国已经重新点燃世世代代照耀她的精神火焰,这种火焰在今天燃烧得光亮如昔”(Evans 1997:96)。显然,她使用的意象已经回归到沃所描述的“火焰在古老的石壁中重新燃烧”的情景。民族精神的复苏只有在帝国衰落的显而易见和毫无争议的现实中才能够得以实现。正如帕特里克·布兰特林格谈到,撒切尔式的怀旧政治依靠民族起源的神话以及传说中重塑英国性的斗争(Brantlinger 1996:242)。英国和英国性的败落恰好显示出,该国家拥有某种普遍永恒的本质,这种本质能够超越历史的发展和时空的阻隔,不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聂春华 2011:27)。因此,沃在《故地重游》中构建的民族认同是道德层面和本质主义的。
3 《去日留痕》中的民族认同
石黑一雄描述的达林顿府在战后被美国富商法拉戴购买,府中的雇员也由鼎盛时期的18位减员到4位。昔日英国权贵们聚首的地方如今已是空荡而惨淡。石黑一雄同样努力复兴英国传统的庄园小说,但是他却拒绝接受其中的本质主义色彩,虽然这种本质论对沃来说是能够定义英国民族认同的。《去日留痕》同样将庄园的衰败和国家的衰落联系起来,在英国作为世界强权而黯然陨落的时候,达林顿府也出售给美国富商。当达林顿府的很多房间都被关闭,并且落满灰尘的时候,英国的很多殖民地也纷纷获得民族独立。就在英国为夺回苏伊士运河而发动灾难性的军事远征的数月之前,史蒂文斯长途跋涉到英国西南各郡,试图说服前女管家肯顿小姐回到达林顿府。史蒂文斯和瑞德都对乡村庄园的境况和他们的同胞感到深刻的失望,这种失望进而引发他们对伦理道德进行怀旧式的反思,并且最终改变他们的民族理想。但是,石黑一雄和沃的作品却存在本质性的区别,因为前者作品中,复兴英国民族精神的承诺没有出现在的乡村庄园中。虽然瑞德在故事的末尾实现对布赖兹赫德庄园身体和精神上的回归,但是史蒂文斯却在叙述终结时在韦茅斯港口逗留许久。
“空间是强有力的社会隐喻,空间的转换通常喻指着变化”(王晓丹 2012:95),从庄园到码头的物理空间的改变恰好呼应着小说中道德准则的变化。引发这种改变的原因是,石黑一雄对沃推崇备至的、并且弥漫战后政坛的怀旧情结半信半疑。石黑一雄曾经在赫辛格(Kim Herzinger)的采访中谈到,他以写作对抗英国当前“宏伟的怀旧产业”(Ishiguro 1991: 139)。石黑一雄认为,虽然怀旧情绪并无害处,但是它现在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他的话语分明暗示出,他已经意识到英国的政客们正在借助英帝国的神话来美化福克兰群岛冲突、终止联盟和移民限额等政策,而石黑一雄数年后便发表《去日留痕》。历史学家乔尔·克里格尔(Krieger 1986:77-78)也曾说过,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她1979年的竞选中特别注重宣扬帝国主义的怀旧情绪及其暗含的种族主义思想。她提出“伟大民族”的口号而心照不宣地标榜“白人的英格兰”,而石黑一雄却反讽式地将该口号放置在《去日留痕》的中心位置。
《去日留痕》试图挑战和质疑英国特权阶级独占伦理知识的可行性和可能性。达林顿公爵虽然非常老练和世故,但是却恍然无知自己已经成为纳粹德国极权政体的倡导者。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路易斯先生虽然有足够的勇气当众指责达林顿公爵,但是却无法提出有关英国民族精神的可行构想。路易斯使用简单粗暴的手段捣乱达林顿公爵会议的事件恰好反映出,他缺乏基本的智慧。
史蒂文斯和他的同胞们全心全意地服侍那些“伟大的绅士们”,并且坚信自己的服务和信任会取得丰硕的成果。达林顿公爵至始至终都表现得非常冷漠、孤僻和狭隘。他相信,能够拥有象征民族精神的地理空间——乡村庄园,就赋予他代表国家的权力,进而使他对普通百姓的需求和关注了如指掌。这种对百姓的漠视并非为达林顿公爵所独有,其实战后英国的政府普遍持有这种态度。当史蒂文斯踏上拜访肯顿小姐的旅途,英国首相艾登执掌的政府也将国家推向争夺苏伊士运河的冲突,但事先没有征得普通百姓和议会的同意和认可。英国政府背弃普通民众的利益和愿望的借口就是维护殖民帝国的辉煌,而英国的乡村庄园依靠这种辉煌为经济支持。
石黑一雄作品中从庄园到码头的偏离显示出,他试图重新安置英国民族精神的地理空间,从而质疑乡村庄园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观点。当史蒂文斯逐渐靠近韦茅斯码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在修正过去的想法,特别是对那些“伟大的绅士们”的道德权威的盲目崇信。他逐渐远离庄园的行为象征着达林顿公爵代表的伦理智慧慢慢地被弃置。因此,“即使伦理专家现实存在,当自由、自制和差异被封为圣典后,人们对伦理知识的依赖也能够得以缓解和减弱。个体自由的重要性、道德多元化的事实和差异性的积极意义都会撼动伦理知识的地位”(Rasmussen 2005:1)。
史蒂文斯由此开始通过对话和沟通的方式重新商榷英国性的真正含义。因为“对英国性的定义与其说是前言,倒不如说是后记。我们应该设法与英国性相融合,就如同参与谈话那样,而并非是在描述某种既定而永恒的本质”(Aughey 2007:7)。史蒂文斯对英国性的思考同时也呼应着斯图亚特·霍尔的接合理论,民族认同在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作为法则或生活的事实被预先给定,而需要特定的存在条件才出现。它不是永恒的,而是被持续不断地更新,会在某些环境下消失或被颠覆,从而导致旧的连接被消解而新的联系-再接合-被巩固(Hall 1985: 112)。英国的民族认同自然会在后帝国主义时期的历史语境中发生改变,而史蒂文斯在旅途中与英国的劳动阶级偶遇则为他对英国性的构想提供契机。他在行进的过程中因为汽油用尽的缘故被迫暂住附近的村庄,他的民族精神的定义遭到当地的激进主义者哈里·史密斯的质询和挑战。史密斯相信,“尊严”是国家中所有的男女老幼都可以通过奋斗而获得的(Ishiguro 1989:186),而他们都是“伟大”的。史密斯认为,尊严和伟大来自报效国家的行为,并且指出他们村民在战争中贡献卓著。所有的英国公民都可以获得尊严,因为他们都曾经为国家而战,“这就是我们和希特勒战斗的原因”(同上)。史密斯在做出这番论断的同时也表达出对民族认同和民族精神的独特见解,“那种怀旧性和回顾式的英国性通常会向英国的中产阶级严重倾斜,它因为排斥掉英国社会的很多群体而对民族认同无益,以此为英国民族主义的基础显然是反动的”(Blunkett 2005:7)。因此他认为所有的英国公民都能够继承民族精神的遗产,虽然他自由的理念并没有覆盖那些居住在殖民地的民众和后来的英国移民。史密斯对普遍性尊严和伟大的断言是基于英国的劳动阶级在保卫国家的过程中做出的牺牲。所有的英国百姓都未曾享受过乡村庄园的生活,但是“我们在战争中的付出远远超出我们应该做的,远远超出我们应该做的”(Ishiguro 1989:186-187)。他们随后要求分享达林顿公爵等绅士们享有的特权,这说明为国效忠的行为比乡村庄园的物质标志更加适合成为民族精神的渊源。
史蒂文斯没有像瑞德那样在怀旧探索结束后回归原地,《去日留痕》也拒绝将英国的民族精神视为先知和智者的预言,而将它看成对话和沟通的结果。史蒂文斯虽然不情愿理会劳动阶级的意见和声音,但是与他们的沟通仍然改变着他的观点。“村民哈里理想化的畅谈让史蒂文斯意识到自己从前的想法只不过是盲从的理想主义”(刘璐 2010)。由此,“达府那个曾经一味追求有尊严、有帝国身份的男管家变成了一个痛苦地追忆过去生活的反思者”(鲍秀文等 2009)。他意识到自己忽略了尊严问题的重要维度,这说明与现实中和想象中人物的对话带给他片刻的洞察力(Su 2005:135)。这些对话引导史蒂文斯重新解读过去,从而意识到达林顿公爵并非生来拥有尊严和伦理智慧,也意识到自己对达林顿公爵的日益严重的纳粹主义倾向保持缄默的行为实则为同谋。
罗伯特·扬认为英国性本身具有奇怪的空洞性,缺乏文化精髓,并且很难将其赋予实质性内容(Young 2008: 236)。齐泽克(Slavoj Zizek)在分析撒切尔时期的英国时曾经说到,《去日留痕》说明英国性根本就是空洞的能指,用来使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合法化。因为“英国性”这个词汇本身没有任何具体的指代和意义,它可以被用来合理解释所有相关和非相关的目标,正如撒切尔频繁使用该词汇来维护自己的对内和对外政策(Zizek 1991:22)。但是石黑一雄在《去日留痕》只是商榷英国民族认同的概念和定义,而并非怀疑英国民族精神的核心概念。他没有背弃英国性中的“伟大”和“尊严”,只是揭示出“伟大”的意义由该词汇的使用者构成和确定,民族精神无法先于那些构想和定义它的尝试和努力而存在。虽然哈里·史密斯也没有提出任何构想来取代乡村庄园象征的民族精神,甚至对此还颇为向往和着迷。但是,他确实要求英国性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得以发展,从而具有更加宽泛的阶级范畴,乡村庄园以外的阶层也可以成为民族性格法定的拥有者和继承者,因为他们的行为也符合伦理规范。史密斯所向往的那种更加包容的民族精神含蓄地预示着英国的未来,所有的差异和边缘都能够被包容。因此,本质主义的民族认同的否定就说明,民族性格是构建的,而非给定的。
4 结束语
通过前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故地重游》和《去日留痕》两部作品都试图以怀旧为契机,重新想象英国性的真实构成。沃和石黑一雄通过对比英国乡村庄园昔日的辉煌和今日的破败,重构出迥异的民族认同。《故地重游》中借助怀旧情结预示出即将复苏的英国的图景,所使用的语言和意象甚至类似于政治家们的言辞。因此,沃的观点吻合撒切尔首相的怀旧政策,两者最终都崇尚构建本质主义民族认同的策略。虽然石黑一雄对民族主义思想在撒切尔时代登峰造极的现象持有批评的态度,但是他也无法舍弃英国民族认同的概念。《去日留痕》中相关民族认同的新观点也呼应着新世纪时期英国社会学界对英国性研究的最新观点,“重构的英国性应该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质,从而反映出非种族主义和正面积极的英国民族认同,从而将有色的他者群体包容进去”(Hickman 2000:108)。因此,《故地重游》和《去日留痕》这两部作品中体现出的英国性的改变并非偶然,而是暗含出英国民族认同发展的趋势。《去日留痕》中人们聚集在码头等待光亮的意象象征着想象中的国家共同体,那些曾经在民族叙事中故意被抹去和忘记的差异和冲突在这里得到包容和保存。英国民族认同的重构通过空间词汇展现出来——故事的最后部分并非有关庄园,而是有关码头。石黑一雄含蓄地暗示出,如果英国想拥有未来,它就应该接受码头上出现的人物和事物——英国古老的乡村庄园无法在它贵族和精英式的孤立中得以持续保存。这种构想也许不够宏伟和壮观,但是它毕竟为英国提供出未来的设想,使它不再沉浸在当前的衰败和去日的留痕当中。
鲍秀文 张 鑫. 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中的象征[J]. 外国文学研究, 2009(3).
车文博. 弗洛伊德主义原理选辑[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刘 璐. 隐喻性话语和“朝圣”叙事结构——《长日留痕》的叙事特点[J]. 外语研究, 2010(1).
聂春华. 个体言说与“普遍性”神话——从话语沟通看现今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文艺学论争[J]. 文艺理论研究, 2011(3).
王卫新. 试论《长日留痕》中的服饰政治[J]. 外国文学评论, 2010(1).
王晓丹. 空间、身份与命运——《大瀑布》的空间叙事特征与主题[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2(2).
Aughey, A.ThePoliticsofEnglishnes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7.
Brantlinger, Patrick.FictionsofState:CultureandCreditinBritain1694-1994 [M]. Ithaca:Cornell UP, 1996.
Blunkett, D.ANewEngland:AnEnglishIdentitywithinBritain[M]. Londo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2005.
Cornforth, John.TheCountryHousesofEngland1948-1998[M]. London: Constable, 1998.
Evans, Eric J.ThatcherandThatcherism[M]. London: Routledge, 1997.
Gamble, Andrew.BritaininDecline:EconomicPolicy,PoliticalStrategy,andtheBritishState[M]. Boston: Beacon, 1982.
Gill, Richard.HappyRuralSeat:TheEnglishCountryHouseandtheLiteraryImagination[M]. New Haven: Yale UP, 1972.
Hall, Stuart. Signification, Representation, Ideology: 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J].CriticalStudiesinMassCommunication, 1985(2).
Hickman, M. A new England through Irish eyes?[A] In S. Chen and T. Wright (eds).TheEnglishQuestion[C]. London: Fabian Society, 2000.
Kennedy, Valerie. Evelyn Waugh’s Brideshead Revisited: Paradise Lost or Paradise Regained?[J]Ariel, 1990, 21 (1).
Ishiguro, Kazuo. An Interview with Kazuo Ishiguro[J].MississippiReview, 1991, 92 (20).
Ishiguro, Kazuo.TheRemainsoftheDay[M]. New York: Vintage, 1989.
Kenny, Virginia.TheCountry-HouseEthosinEnglishLiterature1688-1750:ThemesofPersonalRetreatandNationalExpansion[M]. New York: St. Martin’s, 1984.
Kenny, Virginia.TheImprovementoftheEstate:AStudyofJaneAusten’sNovels[M]. Baltimore:Johns Hopkins, 1971.
Khan, Carrie-Ann Biondi. Aristotle’s Moral Expert: The Phronimos[A]. In Lisa M. R.(ed).EthicsExpertise:History,ContemporaryPerspectives,andApplications[C].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5.
Krieger, Joel.Reagan,Thatcher,andthePoliticsofDecline[M]. New York: Oxford UP, 1986.
Langford, Paul.EnglishnessIdentified[M]. Oxford: Oxford UP, 2000.
Nobel, Cheryl. Ethics and Experts[J].TheHastingsCenterReport, 1982 (June).
Rasmussen, Lisa M. Introduction: In Search of Ethics Expertise[A]. In Lisa M. R.(ed).EthicsExpertise:History,ContemporaryPerspectives,andApplications[C].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5.
Siebers, Tobin.TheEthicsofCriticism[M]. Ithaca, NY: Cornell UP, 1988.
Su, John J.EthicsandNostalgiaintheContemporaryNovel[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5.
Waugh, Evelyn.BridesheadRevisited:TheSacredandProfaneMemoriesofCaptainCharlesRyder[M]. Boston: Little, 1945.
Young, Robert.TheIdeaofEnglishEthnicity[M]. Oxford: Blackwell, 2008.
Zizek, Slavoj.ForTheyKnowNotWhatTheyDo:EnjoymentasaPoliticalFactor[M]. London: Verso, 1991.
【责任编辑孙 颖】
TheTransformationofEnglishnessfromBridesheadRevisitedtoTheRemainsoftheDay
Wang Hui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The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termed as Englishness is usually carried in the English estate novel which therefore often discusses the English national ethos. By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BridesheadRevisitedandTheRemainsoftheDay, this study finds out that the essentialistic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former novel is inherited by the spiritual inheritor of the country house with the help of his ethical expertise while in the latter novel the anti-essentialistic national identity is shared by the common people in the country by the way of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Hence, the Englishness represented by the English estate novel is now constructed and anti-essentialistc instead of being given and essentialistic.
BridesheadRevisited;TheRemainsoftheDay; Englishness; estate novel
I106.4
A
1000-0100(2014)01-0133-6
*本文系2011年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WJQ2011035)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到达’和‘回归’之间的二十世纪英国移民小说家研究”(10YJC752040)的阶段性成果。
2013-01-13
编者按:本期发表的两篇文章都属于文本分析,但是目的不同:王卉揭示“英国性”的演变历程——从给定到构建、从本质主义到非本质主义的改变;韩璐璐、周振华则发现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本人的自我探究和自我实现之旅以及其创作艺术。其实,文本是人的栖息之所,研究者可以围绕文本中的人及其世界实施多维度、多视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