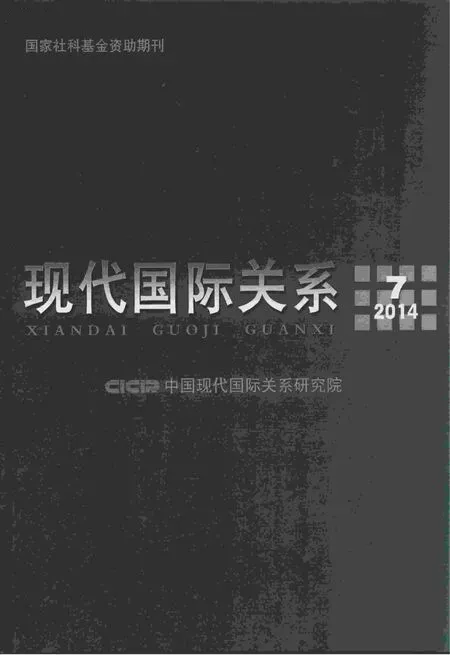对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几点看法
胡仕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与大洋洲所所长、研究员)
当前国际秩序尤其是地区秩序正处于一种将变未变的混沌状态,存在着四大明显特点。首先,中美博弈是催生现有秩序转型的最大推力。中美都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一个是最大的守成国,一个是最大的新兴国;一个是现有制度与秩序最关键的主动设计方,一个是现有制度与秩序最重要的被动获益方;一个是最发达的西方民主体,一个是发展最快的东方威权体;一个希望继续维持其在所有区域的主导地位,一个希望能在尽可能多的领域获取重要话语权甚至主导权。而且,两国都在推动当今秩序转型。美国重在变革那些不能继续服务于其主导性甚至垄断性利益与地位的规则与秩序;中国重在变革那些不能代表其日益崛起之地位与日益拓展之利益的规则与秩序。重要的是,相比其他国家,中美两国更具有带动现有秩序变化的战略需求与资源支撑。两国的博弈也因此具有牵动国际秩序尤其是周边秩序变动的巨大能量。可以说,中美博弈实际上是新旧秩序“破与立”的大博弈。
对美国而言,推动现有国际秩序转型或变化的途径主要有三。一是变革不再能帮助其维持霸主地位的规制,例如对日本摆脱二战后体系的支持与怂恿,以及放弃打破WTO多哈回合谈判僵局的努力等。二是创立利于其巩固垄断性地位的新规制、新高地,最明显者当属其近年大力推进的、旨在超越甚至最终可能取代WTO的TPP和TTIP谈判进程。若其成功,将大大便利美牢固占据未来发展新高地,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垄断性利润,从而极大地强化其维持全球霸主地位的物质支撑。三是削弱甚至破坏那些挑战美国主导性地位的新规制、新秩序的建立。近年通过利用西太地区国家对中国海上维权拓权行动的恐慌心理,美国不断激化地区矛盾,竭力遏阻意在扩大中国地区主导权的新规制、新秩序的建立。例如,美国自身不承认甚至鼓动他人也不承认中国新设立的“防空识别区”;利用南海争端,不断怂恿越、菲干扰中国的南海维权行动;利用亚太国家对经济上过度倚华的疑虑,积极拉拢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加入由其主导的TPP谈判进程。此外,通过怂恿日本激化与中国的岛屿争端、刺激朝鲜南北紧张局势等,美近年大大抑制了几年前呼之欲出的中日韩高水平次区域经贸合作安排,尤其是中断了有可能最终挑战美元霸主地位的中日韩货币安排及自贸安排的相关谈判进程。
对于中国而言,它寻求变革现有秩序的主要途径就是利用其地缘优势、经贸优势和资本优势,推进与周边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如去年提出的“一带一路两走廊”战略构想即旨在提高中国在周边秩序塑造中的主体作用;推动现有国际经贸体制朝着反映中国实力变化的方向发展;推动建立有可能取代现有体制的新机制、新框架。这方面最为明显的努力就是中国不断推动金砖合作机制日益实体化。
其次,大国对周边秩序的竞争远比国际秩序竞争更加激烈。对于守成或新兴大国而言,建立一种支撑其主导地位的周边秩序是维系或提升其全球性大国地位的根本所在。任何大国的崛起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要在其紧邻地区获得秩序主导权;而对于任何守成大国而言,其牵制乃至压制新兴力量崛起的最有效手段也在于维系其在新兴力量毗邻地区的秩序主导权,或动用一切资源干扰新兴大国在其周边构筑新秩序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大国对周边的秩序竞争带有明显的零和性质,一方的破局必然以另一方的失势为代价。也唯其如此,这种秩序之争蕴含相当程度的冲突性。一般而言,大国对周边秩序的竞争不仅易引发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更易在夹于大国之间的第三国或地区引爆冲突,即代理人战争。乌克兰之于美俄和欧俄、日本之于美中、巴基斯坦之于印中、阿富汗之于印巴、中亚之于俄中等,均易成为大国秩序竞争的主战场。同样,印度对于中国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日益扩大的存在也保持着高度戒备,并尽可能干扰中国在其周边投棋布子。一旦中国这种日益显性的存在最终是以取代印度主导性地位为目的,印中之间在南亚及环印度洋区域的战略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同理,中美在西太的博弈也日益呈现出对抗性特征。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即在于最大限度地遏制或尽可能拖延中国在西太地区确立主导地位的步伐。
然而,相比大国周边秩序而言,在全球秩序层面,大国之间,包括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秩序竞争并不如此激烈,甚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协调、彼此磋商地共建新秩序、改革旧秩序。例如,在海上通道安全、全球反恐、北冰洋开发、外太空开发、网络治理、气候变化谈判、贸易自由化机制改革、联合国改革等领域,大国之间,包括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合作远多于对抗。
第三,现有国际秩序的转型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国际秩序的建立与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秩序主要由规则与权力构成。规则主要指秩序的运行框架,权力指维护规则运行框架的主要力量。秩序是在权力互动中通过不断解构与建构规则及其运行框架而逐渐转型或确立的。如果只是权力结构发生变化,而秩序得以运行的规则与框架没有根本性改变,这种秩序就仍未完成转型。只有当运行规则与权力格局都发生根本性变化,一种新秩序才会应运而生。鉴于此,当前的秩序可以说远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权力格局、力量对比本身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维持当今秩序运行的最主要力量仍是美国及其同盟体系;二是支撑这个秩序运行的主要规则与运行框架未有根本性变化,如二战结束后建立的联合国机制未有巨变、主权国家为最主要行为体的现状与法律地位未有巨变、维护自由贸易的国际体系尤其是市场经济体系未有巨变。也就是说,当今秩序之争及其核心部件的规则之争尚未引发现有秩序的根本性转型,以美国为首的守成力量以及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力量之间的秩序之争仍会持续相当长阶段。
此外,作为当今秩序变动的最大推力—中美博弈势将持续相当长阶段。中美博弈不仅是综合实力的博弈,更是两种发展模式、两种价值取向的博弈。美国等西方国家尤其惧怕这种秩序的变动或转型导致其价值体系的崩盘。届时,美与西方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其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更是其数个世纪以来赖以生存的制度根基与价值体系。鉴此,美国等西方国家掌控秩序转型主导权的政治意愿异常坚定,这也意味着这种围绕新旧秩序立与破的竞争既相当激烈,更要持续相当长时段。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全方位超越美国绝非易事,甚至本世纪内尚无力完成;另一方面,即便中美综合实力相互换位,新老大与新老二的竞争还会持续下去。历史上,东亚朝贡体系被不平等条约体系取代经历了数个世纪的拉锯战。同样可以想见,维系美国霸主地位的同盟体系被中国主张的新型安全合作体系所取代可能也需要数个世纪的拉锯战。
而且,在当今世界,围绕秩序转型主导权的拉锯战正使得秩序呈现混沌特性。一方面,旧有秩序仍处在将改未改之际,易反复,甚至易倒退。无论是从G8回到G7,还是从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表示“理解”(赖斯语)到如今美方认为这种“理解”其实是种“失言”,都表明新旧秩序的解构与建构难免出现反复与曲折。此外,从IMF和WB份额与投票权的改革计划至今未获美国国会批准到联合国“五常”对新兴国家“入常”不情不愿,也表明现有既得利益者对旧有制度、秩序有着明显的眷恋与坚守。再如,为维护海洋霸权与现有秩序,美至今都不愿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四,中国在推进国际秩序转型过程中面临三重困扰。鉴于力量格局的变化最终必牵动规则变化以及基于其上的秩序变化,中国与现有地区及国际秩序互动关系的变化尤其具有指向性意义。然而,在推进有利于中国持续崛起的地区与国际秩序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深受三大困扰之苦。一种困扰是,中国对现有秩序是以坚守为主还是以变革为主?是以继承为主还是以创新为主?是以拿来主义为主还是以改良主义为主?这种困扰的产生源自这样的事实:即中国的迅猛发展与崛起主要得益于对现有体制及现有秩序的服从与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成长经历,中国如今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现有体制与秩序的最主要维护者,而主导制订这套体制的美方反而成为企图否定现有体制的最大推手。另一种困扰是,中国如何平衡对周边秩序转型与全球秩序转型的追求。基于相关度的差异性,两种追求不仅在用力方向和用力手段上不能一样,而且最终目标似乎也应有所不同。对地区秩序转型的追求应是中国“治国理政”的一部分,因为周边地带应是大国发展与崛起的战略依托与必然延伸;对全球秩序转型的追求才是中国未来“平天下”的一部分,可以“兼爱非攻”。这就使得相比追求地区秩序转型,中国在追求全球秩序转型时更易寻求与其他各方的协调与合作甚至妥协。再一种困扰是,中国究竟是参与还是阻扰美力主推进的新规制、新标准的确立?也就是说,未来中国是着眼于眼前利益的“止损”而对美力主的秩序转型努力加以干扰,还是着眼于长远的“坐享其成”而对美力主的秩序转型努力予以适当支持、甚至参与,以及乐见其成?这种困扰主要缘自中国的身份困惑。中国当前仍是发展中国家,却是发展最为迅速、利益广布全球且日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是未来绝对的全球性强国。既然美国现今推动制订的新规制、新标准是服务于其全球性强国利益的,那么这种新规则、新标准及其所催生的新秩序不也将服务于中国这个新兴全球强国的利益诉求与秩序诉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