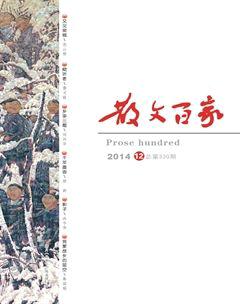千年墨香(外一篇)
郭韵
镇江有一块江中浮玉,是水中一座秀美山峦——焦山。小城人特别是与文化沾上些边儿的人喜欢去那儿踏青赏景,除了山水相依、春有牡丹秋有桂之外,恐怕还是牵挂那山水间浮动的一缕墨香。
记不清多少次走进那缕墨香,每一次归来,心灵都被一种浓郁的文化气息缠绕,如月辉清逸、江风徐拂般挥之不去。
秋风习习,踩着满地金黄柔软的银杏叶,在周遭隐约的香火味里,再次走进焦山碑林,人便走在古老的文化里。这座碑林仅亚于西安碑林,陈列着南朝至清末的263方碑刻。有苏轼、米芾的作品,还有盛世皇帝乾隆的御碑亭……徜徉赏读,千百年前的字迹在21世纪的风中依然儒雅地灵动着。回廊曲径,恬静清幽;真、草、隶、篆,古拙奇峭,秀美飘逸。一方方石刻,似一个个密码,沉潜着古人生命的印迹。历史如白驹过隙,再美好的筵席,最终都将散尽,时间会抹去一切。然而,后世人以焦山碑林,留住了前人足迹、生命韵致。千古墨香弥漫着古老的文明,牵拽回逝去的岁月。我沐一身儒香,亦真亦幻地从南朝走向唐宋元明清。碑林中的六朝石刻《瘗鹤铭》,尤其神秘精美,支撑起碑林的品位。《瘗鹤铭》是石刻主人为葬鹤而作的铭文,与汉中《石门铭》并称为“南北二铭”。
《瘗鹤铭》有一段关于仙鹤之死的传奇。大约一千多年前,有位字号叫“华阳真逸”的隐士,得一只仙鹤陪伴左右,相随云游四方,当他落脚镇江时,一日鹤不幸死亡,这位养鹤人伤心不已,将之用绫缎包裹葬于焦山下,随后写了篇一百六十字左右的祭奠文章——《瘗鹤铭》,抒发养鹤、葬鹤、悼鹤的情感寄托。两晋、南北朝时期,世人将《瘗鹤铭》镌刻在焦山西麓栈道崖壁上,慕名前来观摩游赏的文人墨客思绪奔涌,灵感大发,纷纷寄情诗文。唐宋以来,文人雅士留下许多精美题刻,如唐《金刚经偈句》、宋米芾《辛末孟夏观山樵书》、陆游《踏雪观瘗鹤铭》以及吴琚、方豪、康有为等名家的题名刻石。这些诗文墨迹日积月累形成焦山摩崖石刻群,与焦山雄秀的景致融为一体,吸引了更多的文人骚客、名士清流。从此,焦山充满了神奇故事和可圈可点的诗文墨宝,成了闻名遐迩的“书法之山”。
春秋更迭,墨香携着故事传奇、人文轶事,依山伴江水,和岁月流淌,山水越发秀雅。北宋初期,一日焦山西麓遭雷击,《瘗鹤铭》破碎,沉入江中,江水糅进了墨香,在这儿变得斯文起来。岁月如水般匆匆流去,但人们始终未曾淡忘被风浪浸蚀、泥沙淹没的那一缕墨香,一项浩大的文化抢救工程延续了无数个年头。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至2010年,世人对《瘗鹤铭》的考古打捞从未间断。人们在一次次的希冀中,打捞着历史的碎片,拼接起古老的文明。如今,江中依然沉睡着七十余字的残刻。
《瘗鹤铭》虽残缺不全,犹如断臂的维纳斯、沧桑残破的司马台长城,却一点也不影响其美感和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残缺的东西反而有种神秘感,或许更美,更引人生诗思遐想。《瘗鹤铭》行笔雄健伟逸,苍古奇峭,楷书篆隶行云如水,精美大气。至于它的书者,却是个千古之谜。有说为东晋的王羲之,有说是南朝道教首领陶弘景,又有说是唐朝的王瓒,甚至有人推断是镇江“草根族”的手笔……多年来,众多推测,莫衷一是。其实《瘗鹤铭》为谁所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给后人留下一个隶书向楷书发展过渡时期极为珍贵的实物遗存、一个让历代书家魂牵梦绕的“大字之祖”“碑中之王”,这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坐标意义。《瘗鹤铭》是历代书家、学者赏阅,临摹,研究的文化瑰宝。有了它,就有陆游等人“踏雪观看《瘗鹤铭》”、米芾等人于夏日“观山樵书”, 就有宋代欧阳修的赞语“世以其难得,尤以为奇”和黄庭坚的评价“大字无过瘗鹤铭”,就有了一代代书法大家的横空出世。焦山的墨香千年流芳,似一张儒雅弥香的名片,传播着古城镇江的知名度。
这一缕墨香曾穿越乱世烽火,沾染上硝烟血迹,烙满岁月风尘,始终绕不出小城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大举侵略中国。1842年7月15日,英舰驶抵镇江焦山长江水道,英军企图登岸攻城。焦山守军浴血奋战,英勇保卫祖国和家园,用炮火进行顽强封锁、狙击,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谱写了一曲气贯长虹的镇江保卫战。1937年,日本侵略军攻陷镇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焦山上的雪烦法师为保护国宝,把《瘗鹤铭》推到,反埋在碎石瓦砾之中,躲过日军的刀光剑影和一次次搜寻,最终得以流芳于世,那墨香也就挟带了一缕深沉凝重的意味……
过往已然远去,走在柔和的阳光下,唯有《瘗鹤铭》、古炮台遗址与山风江涛还在身边,倏然恍若梦境,前尘往事在逸香点点的字里行间一一苏醒,翩然起舞,叙说着小城的历史。
秋阳穿过回廊,洒下一抹暖意,淡淡的墨香从两晋、南北朝随风渐近渐浓。迎着山风,和着江涛的节拍,踩着落满墨香的青石板小道,一步步往返于历史与现实,浸润在古老文化和自然景色之中,我沉思,书法、历史、文化、精神,糅铸成独特的小城元素,千百年来,滋养着小城,让焦山的墨香永不黯淡。它,已然成了小城人心底一种不老的情结。
落雪的夜晚
江南少雪,立春已近半月的蛇年正月初九,傍晚时天空飘起了雪,夹珠带粒曼舞,在屋上、窗棂瑟瑟敲打,渐而大珠小珠飘进黑暗,轻轻重重漫无章法地在夜晚演奏。
撑一柄小伞,踩着落雪欢快的旋律,我漫步西行。医政路上,路灯昏黄的光晕在雨雪里洇化开来,湿润地漫漶着暖意。这一带是老小区,我上幼儿园时,父母在此地一所医学院校工作,家就住在这儿。
风过水流,墙头的爬山虎爬着爬着就黄了,日子走着走着也变了样,小区从参差老旧的平房过渡到形态相似的楼栋。这些楼栋像一段段岁月的记忆,静静泊在漫漫的光阴里。我们姐弟前些年一一在他处买了新房,却依然未曾离开这里。也说不清为什么骨子里还是喜欢这儿,或许因晚年的父母不愿搬离,或许是小区平朴里的亲切感,像身边用旧了的物件,有一种复杂而无以言说的气息气场让人难以割舍。人的灵魂和“根”就深深驻扎在几十年老旧的日子里。
小城古来出过多少帝王、豪杰,但每次走在俗世的温暖闲适里,会想,百姓人家的平安日月亦是很好。沿医政路向解放路走去,风雪似乎从过往的日子里飘来,俗常而随意。小时候,医政路南有一条苏医河,河边杨柳依依,田垄整饬,种着各种蔬菜,还有片小树林,树干笔直向天。河对岸是藤柳厂,加工藤椅、藤箱等。矮矮的厂房外有一堆堆青皮柳条,常见工人将一捆捆柳条拖到水边,浸泡在河里。河水清涟,青丝香味在水面浮动,漫过田垄,飘荡在医政路上。河垂直于高出河面的解放路,仰头可见按着喇叭的汽车和打着响铃的黄包车轻悠滑过,视线顺河能看到东面的青山,还可看到一只只蜜蜂和鸟雀。梨花风起,满眼绿色沿河蔓延,蓝色小花在田埂上摇颤,燕子穿过苏医河、小树林飞进它们坐落在附近一所医院屋檐下的家。新蝉唱晚,河边草丛中蚂蚱“蹦迪”,蜻蜓、蝙蝠唱着童谣在水上、田边盘旋。
我们放学后三三两两勾肩搭背流连嬉戏此地,待疯到日隐光暗,才背起地上的书包向家属区走去。暑假,在大人的安排下,我们帮藤柳厂刮柳条皮,加工费除了上交母亲自己也可得到一点零花钱,再相约去路边书摊看小人书,这该算是我们最初打工挣钱的历史了。
太阳天天升起,燕子一拨拨飞过来,又飞过去。不知何日,藤柳厂没了,苏医河没了,田垄和小树林没了,医政路就被两边的楼房夹成窄窄的一条小道,超市、裁缝铺、理发店、包子店、水果摊、烧饼摊等陆续在路两旁落户,车来人往热闹拥挤,那些蜻蜓、蝙蝠飞走了,童年的快乐也远去了。
医政路和解放路交会的那一头,依然是一所医院。这医院依然是那所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儿时心中曾装满对这所医院的仇恨。夏日头生小疖,我常被母亲押往医院打针,“白大褂”们是母亲的同事,趁她们说话的当儿,我一下挣脱跑掉,三番五次,最终还是被“白大褂”制服,药水注入肌肉,伤心的嚎哭就永远留在人生路的那一头。成年后,我曾在这所医院实习,每天对着显微镜细数青春岁月,抬头望见甘露寺,低头看见红细胞,太阳每一天清纯美丽着。
父亲那时是这所医学院校的领导,几十年的岁月中,此地的每一棵树、每一间房、每一个人都成了他人生的一部分,他也见证了学院的成长和发展。那年,医院门诊部外廊相连的低矮平房,被一座楼房取代了,一同取代的还有一代人的风华岁月和情怀。而如今,医院内科大楼那扇窗口的灯火已然成了我们家的一部分。晚年的父亲,住在他工作了一辈子的这所医院的病房里,主治医师是他学生的学生……雪在夜风里扑打着雨伞和树枝,悉悉索索,像往日的细节点击着人的思绪。夜雪飞,岁月走,曾经的日子是守不住的。时光无情地带走了那个诙谐风趣、生龙活虎的父亲,却将他风烛残年的身影留在了病房里。这风雪之夜,我眺望着那盏灯火,痛和依恋在心里穿梭,五味杂陈,周身冷暖炎凉交织流淌,真希望那盏灯火永远为我们亮着,让我们做儿女的朝朝暮暮仍可有个探视陪伴父亲的机会,心中仍有一个完整温暖的家。
顺着医院正门向江边走,风雪将伞掀起,脚下不断打滑,小心翼翼,每一步与艰难为伴。我不由停下站稳,又一次打量父亲的窗口,是他老人家不愿我离开?心里淅淅沥沥也在落雪,雪珠在冷风中悲情滑落。泪,在风雪夜瞬间溢出。
拐上沿江的东吴路,往东行,风安静了些许。路南一栋三层楼亮着灯,楼面新抹过水泥,像披了件新衣,呵护着老旧的骨架和昏黄的灯光。那三角形楼顶,扇形排气窗,还有那窗口的一盏盏灯火,都似曾相识,蓦然心头一暖。多年前,这里是江苏省卫生干部进修学校,我和许多同学曾在此读书深造,这座熟悉的楼房是学生宿舍,当年我住三楼的第三个房间,闲暇时常和同学站在窗口望风景。楼下马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春日浓荫似华盖,夏日阵阵蝉鸣如歌,淡淡的木香远远近近地漫浮。路北的造船厂一直延伸到江边,有大小船只泊在江岸。夜晚船厂的电弧光探照灯似的一遍遍扫过宿舍窗口。深秋时节,船厂里铁锤铁板的沉郁撞击声被江风裹挟又拉长,一声声将清秋里的寂寥冷落送到人的心里头。白天江边吹来轻柔的微风,午休躺在上铺,有船在江里走,小城的阳光在水上闪闪跳荡,那景象是一幅开阔的画面。运载过小城舟楫往来长帆张落商旅繁荣的景象,好像是专门给人留下的遥想空间,年轻的思绪随着江水在五湖四海靠岸……我们四人住十多平米的房间,一盏白炽灯吊在空中,每天下晚自习回到宿舍,上下铺同学依然在灯下读书,读着读着,灯一下就灭了,一片遗憾声中无奈放下书本。那时,人走在春日里精力充沛,多希望每天能有盏通宵不灭的灯火。黑灯瞎火,躺在床上,我们东西南北道山海经,暗暗的楼道里笑声传荡,整栋楼房年轻并快乐着。
雪舞个不停,像当年生机勃勃的学子。周遭一片银装素裹、寒意袭人,可楼上那一盏盏灯火还似当年那般温暖。若干年前,它夜夜陪伴我们,将一段青灯黄卷的风景留在我们人生路上。而今,立于雪中,多少眷恋随风起舞,漫天雪花在那些日子里飘荡,只是我那些曾经的同窗好友,早已像雪花一样无声无息地散落四方了。
离开旧楼,不舍,恋恋。
如今,船厂早已搬离此地,马路也已拓宽,那些可爱的法国梧桐没了踪影。此刻,雪中街道安宁,车辆稀少,行人寥寥。路北就是北固山了。雪,沉静在山上。影影绰绰的山体轮廓染上深深浅浅的白。在夜晚,黑白相间布满神秘。山,冷峻地坐在一幅画里。树丛中几朵灯火被水汽笼罩着由山顶次第而下,似醒似睡,温情脉脉,往事影影绰绰、浓浓淡淡地朦胧在春夜里。雪影中北固楼静守长江,这座楼总叫人想起辛弃疾那首大气磅礴的词:“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这座楼是幸运的,曾经琵琶女因了白居易的诗而出名,汪伦因了李白的诗留名,而北固楼却因了辛弃疾的词闻名于世。建于1934年的老气象台端坐山腰,俯瞰古城,现今这儿是国画院。想来画家们站在景中作画,真是再好不过的画面了。山脚下铁栅栏里,风在竹叶上轻走,翠竹桃林围着的是太史慈墓。这个东汉末年江东军团武将,一生弓马熟练,箭法精良,官至建昌都尉,死时才四十一岁。宋代写婉约词的柳永墓葬也在此山。当年凡有水井处皆有歌柳永词的景象,让柳氏名气家喻户晓。而这位出色诗人的才情最终也尘封于北固山的黄土地里。人散鸟去,春雪落墓清寂无语,黄土地在雪下沉沉地睡了,历史依然在一代代行走,让人沉思,感怀。
小城紧挨金陵城,却未沾六朝脂粉气,拥有着帝王、英雄刚毅之气。北固山浸染过三国风烟,懂得三国的精髓。它经历群雄逐鹿、金戈铁马的场面,走出了江南小桥流水的温婉,多了一份大气,如今又显现出平安日月里的淡定从容。三国英雄的足迹,重叠着一拨拨后来者的脚印,此刻都被一场春雪覆盖得无影无踪。这座山是从诗词中走出的,站在山脚下,辛弃疾、苏轼、陆游、柳永等人的长短句在久远的岁月里吟响,激荡豪迈也好,柔婉忧叹也罢,句句闪着的异光,叫人想到雪地里的寒梅、晓风水月下的舟楫、遥远的烽火狼烟、辽阔的楚天浪涛。时代的风云和心底的波澜,都落在诗人的诗句词章里了。这座山不只是三国英雄和古代诗人喜爱,小城百姓也爱来此地踏青、赏月、游玩。小城生活的慢节奏里有着俗世的温暖闲适,人便与山水走得很近。记得我读一二年级的一个春日来此踏青,返回时为追赶小伙伴跑着下山,哪知越跑越快脚下终于刹不住车,吓得大叫,恰巧迎面遇上一位老伯,他急中生智一把将我抱住,才免遭坠崖之险。儿时,曾无数次登临此山,随同父母,相伴同学,一次次追风追月看景,少年情怀遍洒山间,却未曾读懂此山真面目。
踩着皑皑白雪闲闲地走,就想起作家张晓风的那句话:“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是的,我在,山在,雪在,梦也在,身边的日子便是一如既往的好日子。
雪还在落,纷纷扬扬,在街头路灯的光晕里像无数只小蜻蜓、小蝙蝠扑棱着翅膀嬉戏。那晃动的光晕仿佛亮在梦境里,亮在远远的日子里……凉气从脚下窜上来,被人踩过的地方上了冻。我该回家了。
行至住宅楼下,收伞。其上雪珠抖之不落,撑开旋转,一圈圈依然不落,引我几多怅然:是过往的记忆不忍散去么?无语亦无解,就像这世间许多的人事,你倾其一生就能读懂识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