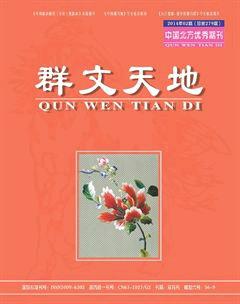“花儿”——河湟谷地的天籁之音
蒲占新
河湟谷地,顾名思义,泛指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交叉地带。其地理范围包括今日月山以东,祁连山以南,今西宁四区三县、海东以及海南、黄南等部分沿河区域。据《后汉书·西羌》载:“乃渡河湟,筑令居塞。”由此看来,河湟之名称,至今也有1000多年了。汉代,霍去病西击匈奴,在此设立西平亭,为有确切文字记载之始,始称湟中。又其族属,称为羌中。甘、青等省大多数“花儿”研究学者认为:它就是历史上古丝绸南路和我国北方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进行茶马交易之地带。其文化圈所处位置,恰好是中原文化圈与吐蕃文化圈、西域文化圈的交界地带。被当代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藏彝民族走廊”的核心区域。
可见,河湟谷地作为中原与周边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伸缩进退相互消长的中间地带,而成为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域内文明与域外文明双向交流扩散、荟萃传播的桥梁地带了。
怪不得在这个地带世代居住着的回、土、撒拉、东乡、保安和部分藏、蒙古、裕固等各民族群众与藏文化相比较,它具有更多汉文化的特征,与中原文化相比较,它又有更多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分。
正因为地理位置的独特性、文化的交叉熏陶使河湟文化既联系两方又自成体系了。当它具备适宜文化发展的条件时,以“花儿”(“少年”)为代表的各种形式的民族民间文化都可以在这里发芽、结果,并形成了得天独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优势。
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点不假。生于斯长于斯的勤劳朴实的各族群众人人都有一副唱“花儿”、漫“少年”的金嗓子;个个都有一副欣赏天籁之音的好心境,去遨游于“花儿”的海洋,尽情地表达着他们对生活的认知和对理想的追求。以至于每一首“花儿”的吟唱恰似与天、地、人之间的一次对话,有多少快慰与忧伤来自这份绵绵的心肠。
“花儿”,民间俗称“少年”,过去人们一般在高山、原野、田间、河边劳动或民间传统集会时演唱。它的曲调以“令”命名,在河湟谷地更是出现了一些以地名命名的作品,如《河州令》、《互助令》、《马营令》、《古鄯令》、《川口令》、《循化令》、《湟源令》、《西宁令》等;以衬词命名的如《溜溜儿山令》、《咿呀咿令》、《尕呀呀令》、《呛啷啷令》等;以音乐特征命名的如《绕三绕令》、《沙燕儿绕令》、《直令》等;以花命名的如《白牡丹令》、《黄花令》、《山丹花令》等;以劳动名称命名的如《拔草令》、《脚户令》等;以称呼命名的如《尕阿姐令》、《三尕妹令》、《尕阿哥令》等;以恋情命名的如《好花儿令》、《尕联手令》等;以相貌特征命名的如《乖嘴儿令》、《大眼睛令》、《水红花令》等;以动植物命名的如《麻青稞令》、《喜鹊儿令》、《尕马令》等;以民族命名的如《土族令》、《撒拉令》、《东乡令》、《保安令》等等。每一种令都有其自身的唱腔和旋律。“花儿”这种“令”的形式还与古典文学中的元曲之曲牌极为相似,这无意中为那些“花儿”研究者开辟了另一片天地。
“花儿”曲令如此的丰富多彩,这就给“花儿”歌手和歌唱家们赋予了广阔的展现才华的平台。当你听到高亢粗犷的“花儿”时,就会想到黄土高原勇敢豪放的汉子;当你听到哀伤悲凉的曲调时,就会觉得仿佛听到被压迫在最底层妇女的如泣如诉;当你欣赏到明朗欢快的“花儿”时,会令你心旷神怡奋发向上;当你听到委婉悠扬的令儿时,你会感到身临其境,定会想起心仪的姑娘,而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
甘肃省的临夏、东乡、和政、康乐、永靖、皋兰、广河、天祝;青海省的民和、乐都、平安、互助、大通、西宁、湟源、湟中、化隆、循化、尖扎、同仁、贵德、共和、门源、都兰、格尔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吉、固原、同心、隆德、泽源、银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昌吉、焉耆等地。这些地方的总面积大约近2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600多万,这些地区都有唱“花儿”的习惯,这在全国及世界各地各类民歌中是十分罕见的。
在西北四省(区)中,世世代代演唱花儿的民族有回、藏、汉、土、撒拉、东乡、裕固、保安和蒙古等九个民族。在中国很多地方,许多民歌的传播范围往往只局限于某一个具有相同特征的小地区,比如“信天游”只流传于陕北,“爬山调”只流传于内蒙的一些地方,其他如白族的“三月街”、瑶族的“耍歌堂”、壮族的“歌墟”等都是在一个地区内流行,而西北地区的九个民族世世代代传唱一种民歌,这就是河湟“花儿”,这在全国乃至世界是没有的。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如藏、土、裕固族信仰藏传佛教,回、撒拉、东乡、保安族则信仰伊斯兰教,汉族信奉佛教和道教,他们宗教信仰不同,生活习俗各异。同时汉、藏、土、撒拉、蒙古、裕固等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有些民族还有自己的文字。尽管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生活习俗有别,穿戴服饰各异,但是唱起“花儿”来,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在“花儿”会上,同在一个演唱圈子里,大家亲如一家,表现了民族大团结的空前气氛。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花儿”大多以四句式为主,前两句以比兴起联,后两句才是主题。它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花草树木、飞鸟走兽、阴阳八卦、民情风俗、传统戏曲、农时节令、服装头饰、烹调饮食、历代名著、山川河流、工农商贾、学堂校园、医药狩猎、棋琴书画、金客沙娃、牧童脚户、三教九流、地区特产、文物古迹、苛捐杂税、反抗封建、褒贬史事……世间万象无所不写,无所不唱,正如民间“花儿”把式们说的:“只要阳世上有的,花儿里就有吼的。”真可谓是祖国民间文学中的一部“百科全书”。
河湟“花儿”的格律,既不像唐诗那样严谨,也不像自由诗那样自由,但它有自己特定的格律。违犯了“花儿”的特定格律,那就不是“花儿”。“花儿”的句式大多数为四句式,但也有五句式、六句式或多句式。如以四句式“花儿”为例,每句由三个词组成,单句为三字煞尾,偶句为双句煞尾。押韵是“花儿”的最基本的要求,有的是全首押韵,一韵到底;有的是交错押韵,隔句对仗;有的是复韵、间韵,全句对仗。这种韵律格式除《诗经》中的某些篇章外,在其他古今中外民歌中,找不到相同的例子,“花儿”特殊的艺术性由此可见一斑。
它的歌词章句如诗,韵律和谐,读起来节奏分明,朗朗上口,唱起来悦耳动听。
这些取自青海本土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的“花儿”,就成了别的西北省区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文化资源。
如:“一绺儿山,两绺儿山,三绺儿山,脚户哥下了个四川。”用一首“花儿”解除了脚户哥的旅途劳顿,一个“下”字使信心顿时倍增;“肉色的袜子条儿绒鞋,穿上了埂子上浪来,远处嫑站了跟前来,心上的花儿哈唱来。”一曲“少年”,一个“浪”字使田野劳动的寂寞荡然无存,内心激起了无限的希冀;“浪头险滩的嫑害怕,黄河的水险上过了。”一个“过”字唱出了筏子客战胜惊涛骇浪时的喜悦心情,道出了请远方的心上人放心的自白;“钢刀铡子明摆下,不死时就这个闹法。”一个“闹”字将青年男女“爱情价更高”的决心表现得一览无余、淋漓尽致;“尕马儿骑上着枪背上,朝林棵打给了两枪。”一个“打”字唱出了牧民的喜不胜收的超凡脱俗之心情,实在是妙不可言。
不经意间,带着翅膀的“花儿”总是在河湟谷地的上空响彻连天;总是在西北大地上和欢乐一起翩翩飞舞,回首间,叫人思绪万千。
早在二十世纪30年代,“花儿”研究拓荒者甘肃学者张亚雄利用在兰州担任《甘肃日报》编辑之便,公开征集流传于甘青宁的一种民歌,在他后来编辑出版的《花儿集》中,他第一次将这种民歌写进书中,称之为“花儿”,并将其特征概括为“汉语、回调、番风”,可谓一语中的。
2007年12月27日,一个名叫朱仲禄的老人在他西宁的家中溘然长逝。老人的去世引起了中国音乐界的高度关注,因为老人是将流传于西北的民间土音“花儿”第一个带进中央电视台的人,并通过央视将自己的作品《花儿与少年》展现给国人,这次契机也使“花儿”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我站在音乐艺术的角度看,朱仲禄的“花儿”,应与梅兰芳的京剧、常香玉的豫剧、白先勇的昆剧相媲美。老人去世时,客厅里挂着的一幅书法作品,就是对这位献身民族民间“花儿”艺术的音乐大师的最好注解:“阅尽歌海千顷浪,踏遍花乡万重山;土墨采尽山乡曲,野腔唱红花海天。”
1956年冬天,为了迎接即将举办的全国专业舞蹈汇演,朱仲禄向作曲家吕冰提供了取自甘、青民间小调的《蓝桥相会》、《四季调》、《五更调》的音乐、舞蹈、服饰、道具等全部素材,并以他最为熟悉的河州型“花儿”格式,写下了“春季里么就到了着……”的歌词,这就是后来誉满神州的“花儿”代表作《花儿与少年》。朱仲禄乘着“花儿”的翅膀,开始进入音乐界的视线。尤其是他和另一位青海的“花儿皇后”苏平把那曲《花儿与少年》带到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以后,“花儿”便张开了翅膀飞向了国内外,从那时起,“花儿”几乎成了西部民间音乐的一张文化名片。
从朱仲禄的艺术生命史来看,他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民间歌手,这种影响既得益于他本人的自然天赋和对“花儿”艺术的无限热爱,也得益于新中国对民间文艺的提倡和弘扬,又得益于“花儿”艺术丰厚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花儿”养育了朱仲禄,时代造就了朱仲禄。朱老对“花儿”艺术的历史贡献和成就说明,他是一个集演唱、创作、研究于一身的三栖式“花儿人”,是他那个时代“花儿”艺术的杰出代表。
“花儿”从“刀刀拿来了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的草根文化特色,历经朱仲禄、苏平、韩占祥、马俊、张海魁、张存秀、索南孙斌、赵吉金、马全、童守蓉、汪黎颖、马文娥等一大批“花儿”歌唱家和歌手的努力,“花儿”作为一种山野小曲,从河湟谷地腾飞,成为了西北民族艺术园林乃至中国艺术殿堂中的一朵奇葩。
“花儿”在河湟谷地根深叶茂,“花儿”在黄河上游姹紫嫣红,“花儿”吸引了喜欢她的人们聚在一起舒畅心意、表达情感,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形成了来自民间的狂欢———“花儿会”,河湟地区“花儿会”的形成一般与庙会、传统节日(如二月二、四月八、五月端阳、六月六等)关系极为紧密。我们所熟知的各大寺院庙观大都依山傍水而建,并且远离尘嚣喧闹。山上草木繁茂,门前溪流潺潺,环境优美,清静宜人。身处花红柳绿、鸟鸣声声的天然会场,不禁使人春情萌动,引吭高歌。到处给人以生命的昭示和体悟,为劳累困顿多时的庄稼汉们平添了一种原始生命粗犷朴野的冲动和豪情。“天不下雨者雷干响,惊动了四海的龙王;浪会的阿哥好声嗓,有心了我俩人对上。”起初彼此都是陌生之人,先用歌喉搭讪相识,若能对上话,感情的距离就逐渐拉近,气氛也趋于宽松:“胡麻花开下的一片蓝,俊不过山里的牡丹;尕妹跟前坐一天,活像是过年着哩。”若此一唱顿生好感,双方一改之前的羞赧,进而坦率大胆起来:“杨柳弯弯弯杨柳,五月端阳的绣球,你和阿哥我当两口,好日子还在个后头。”那份对爱情的渴求与热烈不言而喻,有的甚至达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早晨里邀着个媒人来,晌午里送着个礼来;后晌里借着个驴车来,擦黑儿我把你娶来。”短暂的一天时间,唱词里竟然包含了传统婚礼中的“六礼”习俗,着实让人拍手叫好。如此,两个情投意合的人便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当然其中也不乏失意败北者,不过也不气馁,他们相信“天涯何处无芳草”,况且“花儿会”年年有、处处有,因此没对上歌的人也好聚好散:“五月的端阳没跟上,要赶个六月的会场;这一首唱完再嫑唱,端留个明年的会上。”
尽管日薄西山,倦鸟归林,但更多的年轻人还在纵情放歌,如痴如醉。劳苦的心灵得到了歌声之抚慰,蕴积的心绪得以恣肆的宣泄。那些曼妙的声音带着磁性,歌声飞过的地方便似乎吸引着更多的耳朵倾听、更多的眼睛关注、更多的歌喉介入、更多的文笔创作。
黄河上游的甘青宁地区自然就成了“花儿”怒放的家乡,九眼泉的“花儿会”滋润出诗情画意,孟达天池的“花儿会”泛起阵阵涟漪,老爷山的“花儿会”则成了河湟地区的民间文艺狂欢的品牌,银川举办的全国“花儿”邀请赛、石嘴山市举办的沙湖“花儿”大赛等,更使“花儿”沿着黄河盛开。
青海是“花儿”的故乡,河湟谷地是“花儿”最为流行的区域,一个产于民间的原汁原味的天籁之音,一个被西北地区民间音乐人争相开发的项目,一个旅游时代助阵经济的工程,一个都市音乐低迷时视听上的新亮点,这就是“花儿”在河湟谷地的蓝天下亮出声响后的多重角色。
河湟“花儿”以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丰富的吟咏主题、独特的演唱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优势,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将七里寺“花儿”会、丹麻“花儿会”、瞿昙寺“花儿会”、老爷山“花儿会”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将“花儿”以“中国西北花儿”的名称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此,具有“天籁之音”之称的河湟“花儿”传遍了全国,走向了世界,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花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