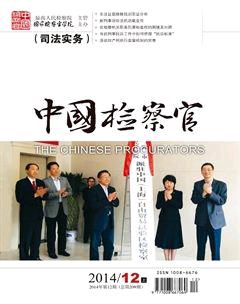由一则案例看“不作为的诈骗罪”
由一则案例看“不作为的诈骗罪”
文◎周海浪*
【典型案例】某日,顾客蔡某到某自行车用品店选购了一款捷安特牌ATX 830系列的山地自行车,蔡某与老板伍某一阵讨价还价后商定好4700元的卖价。此时老板娘洪某正好回到店里。伍某遂将蔡某介绍给洪某:“你给这位顾客开票,4700元,ATX 830。”伍某说罢就在一旁忙着修车。洪某领蔡某进里屋开好发票后便出来忙其他事情,没有收取蔡某应付价款。伍某夫妇其实发生了误会,洪某以为蔡某先前已经收了款,自己只负责开票,伍某却以为洪某开票同时收款,故两人都没有要蔡某付款的表示。蔡某觉察到了两人的不默契,于是大摇大摆地把山地车骑走,伍某和洪某均未加阻拦。待蔡某走远后,伍某、洪某夫妇才感觉事情不妙,原来双方都忘收钱了。后公安机关迅速侦破,将蔡某抓获。[1]
撰写该则案例分析的法官认为应当将蔡某的行为认定为不作为的诈骗罪,但这并非完全没有疑问。例如,蔡某的行为是否就是刑法理论上所认可的“不作为的欺骗”?被害人的认识错误是否需要与该“不作为的欺骗”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回答这些疑问,都需要对不作为的诈骗罪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一、不作为的诈骗罪认定要点
诈骗罪(既遂)基本构造是判断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的标准,不作为的诈骗罪当然地也须符合这一构造要求。常见或典型的诈骗罪都表现为作为形式,从这一构造所勾勒的整个犯罪过程来看,它主要也是在描述一种“作为式的诈骗罪”,那么,不作为的诈骗罪应当如何实现同诈骗罪基本构造的对接呢?换言之,我们应当如何认识不作为的诈骗罪的主要特征,从而判断某种不作为是构成还是不构成诈骗罪、是构成诈骗罪还是其他犯罪呢?笔者认为,将某一行为评价为不作为的诈骗罪,必须把握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单纯的沉默不成立不作为的诈骗罪。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即实施了欺诈行为。然而,单纯的沉默能否认定为欺诈行为呢?我国台湾学者林东茂认为,单纯的沉默并非行使诈术。电影院售票小姐多找零钱,购票者明知而取,由于并未使用诈术,不成立诈欺罪。错找零钱的事实,并非购票者传递不实讯息所制造出来,购票者只是利用了已经发生的错误。[2]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不作为的诈骗罪,必须以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作为衡量标准,特别是关于诈骗罪客观方面的要求(违法性的判断)。犯罪是行为,没有行为就没有犯罪,我们难以将“单纯的沉默”评价为欺诈行为,故而其不具备构成犯罪的前提条件。如果认为单纯的沉默也能成立不作为的诈骗罪,无非就是谴责行为人主观上的恶意,但这极有可能陷入“思想犯”和“主观归罪”的泥沼,与“任何人不因思想受处罚”这一古老格言相背反。因此,“单纯利用对方的错误占有对方交付的财物的,不能认定为不作为的诈骗罪。”[3]
第二,被害人认识错误的产生与欺骗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在刑法理论上,有人完全否认不作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有人完全肯定不作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有人则肯定部分不作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我国刑法理论的主流观点认为:不作为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法律强加的。不作为的原因力,就在于它应该阻止而没有阻止事物向危险方向发展,以至于引起了危害结果的发生。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的特殊性只在于,它要以行为人负有特定的义务为前提,除此之外,它的因果关系应与作为犯罪一样解决。[5]因此,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一结论当然也适用于不作为犯罪。已故刑法泰斗伍柳村教授曾指出:“不作为对于结果之所以能成为原因,其理由不在于负有作为的义务,而在于行为人如起而作为,就有防止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他却不起而防止,结果就必然发生;则这个不作为就是结果发生的原因。”[6]言下之意,不作为犯罪中因果关系的判断可以采用“结果倒推”的判断模式,即如果结果发生的原因是由于不作为造成,那么行为与结果之间就存在因果关系;反之,如果结果的发生不是由于“不作为”本身造成的,那么就不应认定其具有因果关系。这是把握不作为犯罪特征的重要方法之一。据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不作为的诈骗罪中,被害人认识错误的产生应当与行为人具有关联性,如果被害人的认识错误是由于自身原因或其他与行为人无关的原因产生的,不宜认定为不作为的诈骗罪。
第三,不作为的诈骗罪违背了作为义务。就行为所违背的义务性质而言,作为系违背不作为义务。相反,不作为则违背作为义务。[7]那么,不作为违反的义务源于何处呢?国外刑法为了限制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范围,将基于保证人地位的作为义务视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条件。但其理论体系内还存在形式的法义务说、实质的法义务说和机能的二分说等争议。[8]司法实践中大多依据形式的法义务说,从逻辑思考的角度判断不作为犯的行为人是否违背了作为义务,但由于其处罚范围不明确,容易扩大刑罚的范围。实质上,在不作为的诈骗罪中,违反义务的前行为是其作为义务的主要来源,亦即:如果被害人认识错误的产生与行为人具有关联性,那么行为人就负有说明真相的义务;如果被害人的认识错误与行为人无关,那么行为人就没有说明真相的义务。
二、不作为的诈骗罪在评价上的限制
承认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完全可能由不作为构成,并不代表任何不符合作为形态的欺骗行为都可以评价为诈骗罪,换言之,不作为的诈骗罪的评价也是有限度的。就不作为的欺骗而言,在他人已经陷入认识错误的情况下,行为人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使他人继续维持或者强化认识错误,进而处分财产的,成立诈骗罪。例如,首饰店将真金首饰与镀金首饰并陈橱窗中,顾客以为镀金首饰为真金首饰而购买;店员不履行告知义务,以真金首饰价格出售镀金首饰的,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如果他人陷入错误并不是行为人的行为所引起,而且行为人对于他人的认识错误没有说明义务,只是单纯利用他人的认识错误取得财物的,不宜认定为诈骗罪。[9]
首先,根据罪责自负的原则,行为人只对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后果。诈骗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受骗者)产生(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害。在这一构造中,要成立诈骗罪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欺骗行为的实施,即正是由于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才导致后续事件的发生,因此,行为人要对自己实施欺骗行为承担法律后果;二是因果关系的问题,即行为人的欺骗行为与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具有因果关系,如果对方的认识错误不是由于欺骗行为引起的,那么行为人当然不应对此认识错误的产生承担法律责任。
其次,法律不能强人所难,说明义务不能滥用和无限制扩张。不作为犯的成立要求有作为的义务来源,如法律规定的责任、先前行为引起的责任等等。在不纯正的不作为犯的场合,由于义务来源极不明确,有可能被解释者或裁判者随意扩大,这是相当危险的,因而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认定应当极为谨慎。笔者认为,在不作为的诈骗罪的场合,要对“说明义务”进行必要的限制。以买卖关系为例,出卖人与买受人所负担的“说明义务”是不对等的。作为出卖人,他是以出售商品而获取利润,那么他应该详尽释明该商品的相关问题(包括瑕疵),以使买受人能够了解该商品的习性,从而判断是否符合自己的需求。作为买受人,首先他没有义务告知出卖人自己为何要购买该商品,该商品是自己使用还是他人使用,是生活需求还是投资理财都是买受人个人的事情,与出卖人无关;其次,买受人发现出卖人的价格低于市场价时,也没有“提醒义务”,因为要买受人提醒出卖人“东西卖的太便宜”是不符合生活常理的;最后,由“提醒义务”衍生的一个问题就是支付价款的准确性,在买卖关系中,出卖人有收取价款的权利,买受人有支付价款的义务,如果买受人未付款或者出卖人多找了钱,买受人是否有义务提醒出卖人行使权利呢?持诚实信用说的学者认为,市场交易的双方应当诚实守信、童叟无欺,买受人对此应当主动提醒出卖人行使权利。笔者赞同诚实信用说的基本立场,但必须强调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刑法领域的适用不能无止境地扩张;另一方面,要恪守刑法的谦抑性。当今时代的刑法不再是权威主义刑法,而应是自由主义刑法。因此,原则上只有当行为人实施了积极的法益侵害行为才应受刑罚处罚,以刑罚手段强制国民实施一定的积极行为,只能限于特别情形。[10]要求买受人负担提醒义务,实则是以买受人的诚信替代出卖人的疏忽,人为地加重了买受人的义务,难以实现权利义务的对等,实不可取。持诚实信用说的学者实质上是把民法领域的诚实信用原则予以扩张之后课加给了买受人,但是,民法与刑法在诸多问题上是存在差异的。民法学者对诚实信用原则的研究有这样一个案例:法学家昆图斯·穆丘斯·谢沃拉想买一块土地,请求出卖人对他说一个死价;后者这样做了。谢沃拉说,他对土地的估价比出卖人的要高,因此在后者的开价上加了10万赛斯退斯。这个案例说明诚信要求利益的承受人为之付出充足的代价,不得利用对方的疏忽或无经验牟利。[11]这一理念如果泛滥到刑法领域,那么对方在无经验签订合同的情况下,行为人有可能涉嫌合同诈骗罪,这是不可思议的!很明显,民法学者的观点在刑法领域是难以为人所接受的,这也再次证明了持诚实信用说的学者混淆了不同部门法的区别,是滥用诚实信用原则的恶果,实不可取。
再次,认定犯罪的逻辑顺序是从客观到主观,在判断行为违法性时不宜考虑主观的违法要素。有观点在比较不作为的诈骗罪与不当得利之区分时指出:“在诈骗犯罪中,一定要有不法的主观要素的存在,否则便不能构成诈骗犯罪……在诈骗犯罪中,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诈骗行为,其目的产生在先,行为在后,行为是在目的的指引下进行的……在不作为诈骗罪与不当得利的界分中,相对于行为人获得利益的时间而言诈骗罪更强调不法主观要素的先在性,而不当得利并非如此。”[12]该观点的核心思想有两个方面,一是承认主观的违法要素,二是要在区分目的与行为的基础上,坚持从“主观到客观”的认识过程。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一方面,尽管主观的违法要素理论在德日刑法理论中有一定市场[13],但主观的违法要素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概念,因为其极易将判断者拖入“主观归罪”的泥沼,从当前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宜在违法性判断阶段考虑主观的违法要素,仍应坚持“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这一基本共识。另一方面,该观点所主张的目的在先,行为在后,“从主观到客观”的顺序是犯罪发生的顺序,而非认定犯罪的顺序。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对于司法机关来说,首先进入视野的是犯罪行为,因而确定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是定罪的逻辑。只有对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作出肯定性判断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查明该行为是否是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出于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状态所实施,从而为定罪提供主观依据。因而,定罪是一个从客观行为到主观罪过的逻辑过程。”[14]进一步而言,在不作为犯罪中,目的与行为的先后性的区分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不作为是身体的静态,没有(或极少)外观化的表现,目的也是隐藏于行为人内心,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判断目的与行为究竟孰前孰后,所以上述观点实则不妥。
最后,不宜认定为诈骗罪不代表不构成其他犯罪。不符合诈骗罪的基本构造,但行为具有法益侵害性、行为人具有非难可能性时,则有可能构成其他罪名。如根据“机器不能被骗”的原理,行为有可能构成盗窃罪;侵占他人占有脱离物的,有可能构成侵占罪等等。总之,不会导致应受惩罚而未被惩罚的现象出现。
三、对本案的评析
在本文开头的案例中,撰写该案例分析的法官认为蔡某的行为构成不作为的诈骗罪,主要原因是在本案中,被害人伍某、洪某夫妇虽然只是因为彼此的误会(并非由于蔡某的欺骗)而自陷错误认识(误以为蔡某已经付过款),但蔡某正是抓住了被害人之间的不默契,不但不如实告知实情,反倒将计就计成功实施了隐瞒自己尚未付款的“配合行为”并以此强化了被害人的错误认识,进而骗取被害人财产。蔡某实施的(不作为的)诈骗行为与通常情况下犯罪人直接采用欺骗手段骗取被害人财产的(作为形式的)诈骗行为相比,在侵犯诈骗罪保护法益(他人的财产权利)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区别。[15]
根据前文的分析,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笔者认为,蔡某的行为不构成不作为的诈骗罪,而应构成盗窃罪。
蔡某的行为之所以不构成不作为的诈骗罪,是因为:第一,蔡某在该案中只有一个行为,也只有这个行为可能被评价为犯罪,即“将山地车骑走”。单独地评价这一行为,我们难以将其与诈骗罪建立某种关联;综合地评价这一行为,我们也不能将“骑”等同于“骗”,二者是不能完全重合的。第二,本案的结果是“店主财产权益受损害”,这一结果的出现是由于蔡某“未付款而将山地车骑走”造成的,而蔡某的这一行为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应当付款而没有付款,二是未付款就把车骑走。造成本案结果的直接原因是后者,它是一个积极的作为,而非消极的不作为,因此,不能认定不作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三,蔡某在本案中没有实施任何欺骗行为,而店主的认识错误是由于两人的“不默契”造成,与蔡某没有任何关联。所以,蔡某的行为既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也难以认定被害人的认识错误是由蔡某引起的。第四,收款是出卖人的权利,权利的行使须自发、自觉、主动,由于店主两人自己的“不默契”出现了错误,蔡某没有义务提醒其收款。同时,付款是蔡某的义务,未付款而将山地车骑走的行为肯定是侵犯店主的财产性权利的,至于构成何罪,则另当别论。因此,蔡某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也不符合不作为犯罪的基本特征,更不符合不作为的诈骗罪的基本特征,其行为不构成不作为的诈骗罪。
蔡某的行为之所以构成盗窃罪,是因为:一方面,既遂状态下的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别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这一区别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被害人的认识错误是基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而产生;二是被害人有明确的处分财产的意思表达或行为。从本案来看,伍某、洪某夫妇的“认识错误”并非由于蔡某的行为引起,只是由于两人自身的“不默契”造成,与他人无关。原文作者认为“被害人夫妇当时误认为蔡某已付过价款,遂目送蔡某将财物取走而不加以阻止,这种消极的不阻止与通常情况下积极的交付财物都属于“处分”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笔者对此种观点难以认同。法律上的“处分行为”会导致标的物权属发生变动,“交付”则是动产的法律处分的典型外观行为。动产的交付包括现实交付、观念交付、占有改定和拟制交付四种情形,其特点都是积极的行为且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并不包括“消极的不阻止”。消极行为产生处分效力,欠缺当事人明确的处分意思,既没有法律规定,又难以符合社会大众的基本认知,因而不应将其认定为被害人的处分行为。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刑法学者和最高法院的相关法官均认为存在“公开盗窃”的情形,[16]即盗窃罪不以“秘密窃取”为必要条件。这一认识符合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和司法实践的实际,能够严密法网,做到准确定罪。在蔡某未付款的情况下,按照社会大众的基本认知,自行车仍然应该属于店主占有。蔡某将自行车骑走的行为,侵犯了店主的财产性权利,符合公开盗窃的基本构成。因此,蔡某的行为应该构成盗窃罪。
注释:
[1]李方政、张理恒:《不作为诈骗罪的认定》,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12月29日。
[2]林东茂:《刑法综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6页。
[3]周光权:《刑法各论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4][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第185页。转引自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页。
[5]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0-91页。
[6]侯国云、梁志敏:《论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1期。
[7]林山田:《刑法通论》(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
[8]关于保证人地位的作为义务,请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8-101页。
[9]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10][日]山口厚:《刑法总论》,有斐阁2001年版,第77页。转引自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11]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以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分析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12]常磊:《不作为的诈骗罪与不当得利的界分》,载《时代法学》2009年第3期。
[13]主观的违法要素理论实质上在大陆法系仍存在较大争议,自德国学者Hegler、Mezger等人倡导该理论以来,各界对该理论的认识和定位均未达成一致。该理论传入日本后,也形成了肯定说(如西典田之、大谷实)、否定说(如内藤谦、中山研一、前田雅英)、限制说(如山口厚、曾根威彦)等不同观点。
[14]陈兴良:《走向规范的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
[15]同[1]。
[1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法院“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小组办公室:《〈刑法修正案(八)〉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70页。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检察院[6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