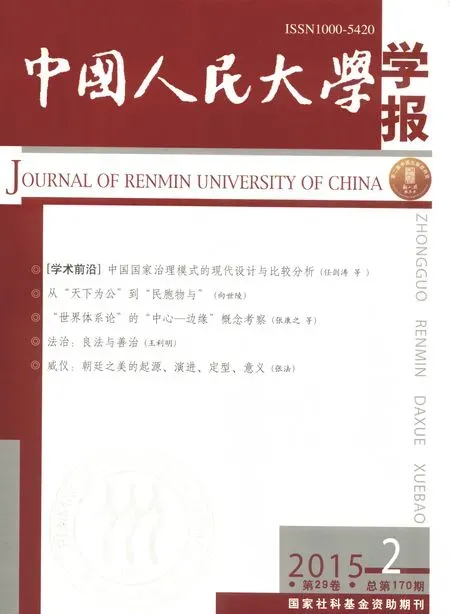现代政治与治理能力的民主化
陈华文
现代政治与治理能力的民主化
陈华文
国家治理是政府、社会与公民在社会公共事务上共同合作的活动。以善治为目标的国家治理需要借重公民的治理能力。由于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事务的具体性及其技艺倾向,审慎的政治判断力构成治理能力的主要内涵。在现代世界,审慎的政治判断至少在下述三个方面可以被民主化为平等的公民能力:作为积极公民的政治能力、作为公共责任的政治判断、作为慎思的政治理性。政治判断是平等的公民治理能力,所反映的正是治理民主与政治民主之间的一致性。政治民主是治理能力民主化的制度保障,而治理能力的民主化为政治民主提供了有效的实践主体。
治理能力;公民能力;治理民主;政治判断;政治民主
国家治理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理念。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统治和管理等观念,它有着新的内涵,使得人们重新思考政府和政治等概念。国内相关文献普遍论及政府的治理能力,但甚少专门讨论作为民主治理或者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潜在前提——公民的治理能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只有在民主政治中才能获得制度的保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包含着治理能力的民主化,也即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否要求平等的治理能力?公民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平等的治理能力?本文将表明,平等的公民治理能力所揭示的是政治民主与治理民主之间的一致性。
一、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民主化:为何需要平等的公民能力
治理是一个全新的理解政府的理念,它与政府统治的不同在于它是人们反思政府作用和重新理解政治的出发点。换言之,治理与统治的区分凸显了治理的主要特征及其意义。不少文献都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也对二者的差异做了细致的厘清。在此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以说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何要求平等的公民能力。
治理与统治最根本的区别是行为主体或者说权威的来源不同。统治的主体是政府机构或者社会上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却不一定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和普通公民。有论者指出:“治理是通过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进行的。”[1](P22)就此而言,治理是一种并不单靠政府来完成的行为。政府不再是治理的唯一权力中心,治理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治理的多元主体中最为核心的是政府、非政府组织与公民,治理活动因而也就是政府、社会与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上的合作。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意味着治理的民主乃至社会的自治。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在统治和治理的视域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在传统政治统治视域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但是,在治理视域中,公民同样也是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不再是被统治者。既然社会组织和公民都是公共事务的主体,治理秩序就不再以政府为中心,而是政府与社会和公民共同治理。可见,治理民主是治理观念的应有之义。若不涉及治理民主,治理与统治和管理的区分也就无法得以彰显,治理作为一种全新政治观念的意义也难以在国家的实际政治运行中发挥作用。
治理民主内在包含着社会自治,或者说治理民主使社会自治成为必要。政府、社会组织治理行为不再纯粹以政府自上而下的权威为中心,也不必完全依赖政府的强制力量。因此,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另一面是社会的自治。“没有政府的治理是可能的,即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规章机制:尽管它们未被赋予正式的权力,但在其活动领域内也能够有效地发挥功能。”[2](P5)这种机制所依赖的是社会的自治。社会自治是政府不在场的情况下社会关于公共事务的自觉的、有效的治理。然而,社会自治从逻辑上讲并没有拒绝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二者共同构成了优化和重建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径。社会的自治能够吸纳多方智识和卓见,民主的治理能够有效促进民生建设。[3]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治理民主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那么,这种能够有效发挥功能的自治机制是如何可能的?社会自治所反映的不只是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变化,其背后隐藏的是公民能力在内涵上的变化。在政治统治的语境中,公民能力主要是作为被统治者的服从德性。而在治理的语境中,既然社会和公民也是治理的主体,那么社会自治本身也就必然要求公民作为公共事务治理者具备治理能力。在治理有效性的问题上,善治对社会、公民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善政是政治统治的理想一样,善治是公共治理的理想,也是公共治理的目标。善政所关注的是传统政治学的核心主题:最佳政体或者好的政府安排,它所要求的是良好的政府能力。较之善政而言,善治有着更多更高的要求。善治的要求既指向好的政府安排,也要求有好的社会治理。“取决于善治的国家治理目标,一个具备善治能力的国家体系,需要同时借重国家权力、市场机制与社会自治积极互动而形成的强大能力。”[4](P17)就此而言,善治本身包含但不限于善政,善治的治理目标需要盘活社会自治的能力。因此,有效的治理在理念上至少应该包括公民的治理能力,而从制度安排上也应该充分释放、吸纳和培育公民的治理能力。
可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包含着社会的自治,而社会的自治则必然对整个社会的公民都提出要求,以善治为目标的公共治理更进一步将良好的治理能力拓展为对全体社会公民的要求。公民的治理能力对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关系到治理民主是否能够切实发生作用、落到实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借重或者说要求公民的治理能力。由于这种要求是指向整个社会和全体公民的,是对于具有公民资格的个体而言的,可以称之为治理能力的民主化。治理能力的民主化指的是公民具有平等的治理能力,治理能力不再只是限于某个群体和某个领域。
二、作为治理能力的政治判断
然而,问题在于公民是否具有平等的治理能力?古今政治理论家对此众说纷纭。在转向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分析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由于本文是从治理主体而非治理制度的角度讨论治理能力的民主化问题,因此对治理能力核心要素的分析也主要侧重于行为主体也即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治理者的政治能力是古今政治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而政治判断又是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古典政治学将政治判断视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智慧或政治能力。柏拉图指出,治理者是深谋远虑的,真正有智慧的。[5](P145-146)亚里士多德持有相近看法:“贤明的统治者就是善良和明智之人,而且一位政治家必须是明智的。”[6](P78)及至近代政治,马基雅维利也明确表明:“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7](P74)在现代政治理论中,相似的论断也不少见。在韦伯看来,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三者之间,判断力又被认为是关键。“激情并不能造就政治家,除非这种献身于‘事业’的激情,也使得对此项事业的责任心成为行动的指南。这方面所需要的,是恰如其分的判断力。”[8](P101)罗尔斯在《万民法》里刻画了政治家的理想,他理想中的政治家能在政治实践中清楚洞见良序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和真正利益,并能够把握应该做些什么。[9](P103)可见,良好的政治判断力是人们对理想政治治理者的基本期许。
政治判断的主要思想来源是政治审慎(political prudence)。政治审慎指的是一种在纷繁复杂的实践活动中对于善的谋划,是一种能够把握理论规范又能结合具体语境予以判断从而正确行动的品质。就其历史而言,审慎一开始指的是那种知道何为其所应得并对求得其所应得感到自豪的人,后来被普遍化为那种在特殊情形下知道怎么下判断的人。[10](P194)政治判断或政治审慎是指在具体情境下,能就何种决定对于国家而言是好的,或者什么最有利于公民福祉这样的问题做出准确把握和辨识的能力。政治判断只是判断范畴中的一种,“判断被假设为我们借以预测具体之普遍(universal of particular)的心灵活动。如果这种活动发生在某种涉及政治本质的普遍与具体的政治处境时,那么我们就有了政治判断的问题”[11](Pvii)。可见,政治判断力指向的是一种在具体处境中做出良好的理解和把握的智慧或品质。在一成不变、整齐划一和抽象的政治生活中,判断是没有任何用武之地的。
实际上,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判断之所以被视为治理者的主要能力或德性,是与治理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密切相关的。
首先,价值指向是治理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治理体系的制度构建至为关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治理体系或治理制度完全没有价值取向。制度的创建和维系应该有着基本的向善性,而不能只是沦为形式主义。关于善的考虑以及价值关怀即使是在现代政治框架中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本杰明·巴伯等对自由民主派的批评虽有待商榷之处,但他指出政治判断力对于“解决各种价值和目的之冲突”的重要性[12](P187)却是有意义的。政治判断或政治审慎的第一要义在于其对价值的关怀和对善的考虑。
其次,治理活动所指向的是具体的公共事务。治理能力的确需要以制度的现代化为前提,但在具体的治理活动中,治理主体所面向的仍然是具体的公共事务。因此,治理能力除了与制度的现代化程度密切相关之外,还与治理制度或体系在具体情境中的适用性相关,与治理主体在具体情境中对具体事务的把握能力有关。政治实践层面的治理能力不仅在当前治理的相关研究文献中阙如,甚至在现实的治理过程中也是一大难题。就此而言,关乎具体情境的政治判断力也理应成为治理能力的主要品质。
再者,治理是一种类似技艺的活动,但它并不等同于工具理性。国家治理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一门精巧的艺术,而近代政治科学对古典政治学的反转却让政治学完全丧失了其重要的智慧。政治判断或政治审慎在一定程度上与技艺相似,都同目的—手段的运行结构有关,是一种善于考虑的能力。但技艺是一种制作的理性,而审慎则是一种关乎实践的理性。它的目的在于行为本身,是一种与善恶相关的品质。[13](P172-173)善于考虑和价值关怀都是政治审慎的主要内涵,根据政治审慎德性而做出的政治判断包含了对目的和价值的双重考虑。而公共治理需要的不只是工具理性,也不只是科学技术。“管理好一个国家所需要的东西,比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知识要多得多。”[14](P61)在这个意义上,审慎的政治判断同时满足了国家治理的技艺性及其伦理性。
因此,判断虽然不是专门属于政治领域的品质,但是政治判断却是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和基本内涵。审慎或实践智慧并不是政治行动所特有的,一切实践技艺都有其关于判断与常识的标准。但这些标准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占有显著地位,政治领导、政治家的治理技艺与公民资格等问题通常都与判断和实践智慧有着重要的关联。[15](P2)政治审慎或政治判断是城邦或国家谋取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真正的治理者必须在基于审慎的政治智慧的指引下,采取合乎正义的行动,尽可能地改善国家和公民的生活。
三、政治判断与公民的治理能力:何种意义上的平等
对政治判断作为一种治理能力不会有太多争议,但问题在于政治判断能否成为一种普遍化的能力,也即公民能否拥有这个意义上的治理能力?是不是所有的公民都可以运用政治判断乃至审慎的能力?
很难设想每一个人都能对自己的利益、对国家的发展总是做出准确的判断,也很难设想人们在每个问题上都有同样的判断力。这个简单的事实也一直是反民主理论的基本点,反民主的理论探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政治学说的传统的确强调审慎是单独属于政治家的德性。即便是在现代,不少理论家也仍然是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讨论政治判断的问题,比如韦伯和罗尔斯。自柏拉图以来,审慎德性就一直被视为政治家治理能力的首要德性。柏拉图将政治家的技艺界定为“照料人”[16](P103),政治智慧首先是统治者可以称为真正政治家的基本要求,而“具有这种知识的人按照自然规律总是最少数”[17](P147)。在柏拉图看来,只有在这种政治智慧与理智引导下的优秀统治者或真正的政治家治理才是真正的体制。亚里士多德更是直接地认为审慎是治邦者所独有的德性。[18](P80)可见,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政治智慧都是政治实践和政治家所需要的美德,而城邦或国家在这种政治智慧的指引下所可能获得的善,则是古典政治思想家判断政治家的唯一原则。这些观点不会令人惊讶,毕竟国家治理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古典思想将政治判断或政治审慎视为一种智慧的主张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古典政治学说关于审慎的政治判断力专属于治邦者的主张,具有非常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尽管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公民都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意愿和能力,但现代世界已经不可能回到精英政治,也不可能忽略公民对于善和正义的把握能力与对公共事务的判断能力。实际上,在共同治理(官民共治)的体制里,好的公民必须学会统治和接受统治,必须具有统治他人和服从他人的德性。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审慎的政治判断可以在下述三个维度上成为平等的可为人人所具有的治理能力。
第一,作为积极公民的政治能力。需要指出,政治判断是属于治理者的能力,而不是专属于职业政治家(或政治—社会精英)的能力。在公民也成为治理者的体制里,审慎或者政治判断也是公民的美德——只不过这并不是公民作为被统治者而具有的德性,而是作为治理者的积极公民所应该具有的能力。
积极公民指的是主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并且能够在政治实践中发挥功效的行动主体。在现代政治世界,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大幅度降低。政治冷漠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这种现代化后果对于公共治理而言是不利的。作为治理主体的公民,应该对如何正确行动做出合乎理性的判断和行动,而不只是简单地表达自己的偏好和个人利益,而这正是政治审慎和政治判断的应有之义。具有政治审慎的人,能够分辨出对国家为善的事物。[19](P173)在古典政治生活中,审慎者需要结合人的自然目的来理解和判断政治生活里的善,但在目的论消弭的现代政治世界里,对于善的把握脱离了人的自然目的,转而与公民和国家自身的安全、发展及福祉相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对善的把握较为容易,具有民主化的可能性。就此而言,慎议民主是其中一条可行的路径:公民应该为了公共利益而展开公共慎思去发展和应用他们的德性。这种要求对于积极公民而言当然是值得期待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复兴审慎的政治判断力,将之作为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的能力是现代政治实践对治理主体的基本要求。
第二,作为公民责任的政治判断。并不是所有公民都有意愿和能力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而且现代政治也不必要求每个公民都是积极公民。但是,公民即便不作为积极公民,也仍然有可能对政治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和功效。现代政治仍然需要政治判断,即使不一定要发展出慎思的政治。
在现代理性主义与工具性的国家权力体系不断挤压公民政治空间的情况下,公民的政治判断力尤显重要。从科层结构的合理性及高水平的技术导不出个人运用理性的意志和能力,事实上,获取这种意志和能力的机会往往被这种合理性所扼杀。[20](P185)纯粹的工具性治理过度强调政治制度的作用,使得政治行为甚少考虑价值关怀和伦理支撑。这种治理方式实际上消解了公民的道德能力,导致公民的公共生活、社会生活也缺乏公共性,带来的是在政治生活中放弃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力的公民。由于国家治理概念源于公司治理,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有效性自然是当前语境下使用“治理”一词的关注点。这本无可厚非,不过正因为治理更多的是一种工具理性上的行为,其伦理支撑和对善的把握就显得更为重要,否则国家治理就只是一种技术理性的政治。纯粹工具性的治理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也已经被普遍认识,比如环境的恶化、道德的腐化以及极权主义的出现,等等。公民对具体善的把握是抵制治理纯粹工具化的有效能力。就此而言,现代公民的基础并不是完全不需要善的理念。
现代化的治理秩序是官民共治,但是共治不只是政府、公民与社会的协同治理,还有彼此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德行的腐化是政治世界常有之事,也是权力的必然本性所致,治理者很难做到坚持不懈地为公众利益奉献。此外,现实政治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康德所批判的政治的道德家,他们可能会利用甚至倡导某种有利于其野心实现的伦理。[21](P136-137)在这个意义上,有责任的公民必须时刻警惕政治家的野心[22](P43),尤其是在政治家将某个个别的有限的目的当做一般的和道德的目的时,公民更应该不断运用良知的自由,对政治家的行为和决定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将政治限制在道德上。大多数情况下,公民的政治判断力所指向的是具体的政策和政治行为,比如针对政治决定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考虑。“我们经常依据判断能力来评价政客和政治家的高下。这对公民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选择,而且还有判断各种选项和可能性。”[23](P187)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政治判断,它不是公民作为治理主体而需要运用的直接参与政治治理的裁决能力,而是公民作为政策的对象,以其判断力对各种具体的政治行为做出评价。
这个意义上的公民能力实际上是公民责任的一部分,也是公民美德的核心内容。这种公民能力有时需要专业的智识,但更多时候需要的是基本的道德能力(如正义感和适宜的善观念[24])以及政治常识。就此而言,回归常识是治理能力民主化的基本指向。
第三,作为慎思的政治理性。这个意义上的政治判断并不是一种罕见的政治理性,也不只是某些卓越的人才具有的能力。实际上,任何人都有可能变得审慎。“我还发现人与人之间更加平等,因为慎虑就是一种经验,相等的时间就可以使人们在同样从事的事务中获得相等的分量。”[25](P92)现代意义上的审慎主要指的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理性能力,但是这种深思熟虑并不是关于人类至善的把握,而是关于完成行动的周全思考。这种能力可以是公民针对公共事务所做的判断,也可以是公民关于自我利益的考虑。就后者而言,这是公民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能力。
公民自我完善的能力是现代治理释放社会活力和达成善治目标的基石。一般意义上的审慎德行可被理解为同一个人自己相关[26](P177),不但没有排斥自我利益,而且在现代政治语境中还要求人们结合自我利益去理解政治。人们对在个人利益上的审慎判断能力误解甚多,认为这不过是对一己私利的追逐,缺乏对公共利益的考虑。审慎的判断能力并不意味着公民完全是出于私人利益判断政治事务的,实践主体实现个人目标的能力与其作为公民所需要的公共精神在逻辑上并不相悖。相反,这种关于个人利益的平等理解能力对公共治理有重大意义,甚至是现代治理能平等考虑每个公民利益的基础。现代治理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每一个政治决定都影响重大。若决策者低估了个体对自我利益的理解能力,那么即便能设计出精致的治理方案,也难以得到良好的实施。只有在充分考虑和重视公民对其个体利益的追求时,治理行为才更具合理性。同时,公民在不被干预的社会领域追求个人目标的能力,是盘活社会自治的根基。公民可以根据个人目标或个人兴趣,在社会领域里积极组织起来,以实现个人福祉甚或公共利益,这本来就是公共治理的主要目标。
综上可见,审慎的政治判断有理由且可以成为人人都具有的治理能力。对公共治理有积极意愿和良好裁决能力的公民,可以运用其作为治理者对于共同利益的判断力,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公民可以运用基本的善能力、正义感和政治常识,对治理行为和政策决定做出正确的判断;公民还可以运用对自己个人利益的理解,在社会领域积极组织起来以实现个人目标、群体目标和公共利益。
随着政治判断民主化而来的是政治判断在内涵上的深化。根据从上述三个维度对政治判断作为一种治理能力的拓展性论述,我们可对政治判断与公民的治理能力做出进一步的分类和梳理。
(1)低位判断与高位判断。在现代政治世界里,政治判断不再是复杂的概念,也不再是高深的智慧,但这并不意味着判断在类别上是没有差别的。不同领域的审慎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审慎,比如善于理家与善于治国是两种不同的事情。即便是在国家治理问题上的政治审慎或政治判断也是如此。对于民族与人类功能的实现、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法律法规的制定等宏观的、抽象的、专业的政治问题,并不是每个公民都有能力做出判断的。但是政治判断并不是很高深的理论,也可以从最根本的问题开始,比如公民可以从是否受惠于权力运作和政策安排,来考虑和判断这些制度及政策的合理性。如果民众没有受益其中,那么任何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治权力的新动作,即便在短期中因运动式权力运作而有风吹草偃之效,但究其长远来看,却是无源之水。这种低位的政治判断标准,在国家治理中反而是根本的,它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回归常识。此外,低位判断与高位判断的区分意味着公民可以针对其能力而参与到不同的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去,而不是一概被排除在治理者的范围之外。
(2)个人判断与公共判断。审慎一般被认为是善于考虑一个人自己的善的能力,而政治审慎是善于考虑有利于国家公共利益的能力。因而,不少论者对政治审慎和政治判断的讨论多是侧重于个人利益的超越,强调政治判断应该以公共利益为对象,从而否定根据个人利益做出政治判断的进路。毫无疑问,民主要求有效的公共判断,但政治判断并不是要完全回避个人判断,毕竟对个人利益的考虑并不意味着个体只能做出自私的判断和行为。治理能力的民主化既包含治理主体善于考虑个人利益的能力,也要求其具有公共的思维方式和理性,并对各种冲突的目标做出判断。
(3)政治判断与道德判断。现代政治的发展以政治与道德的区分为起点,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判断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中没有一席之地。有论者指出:“我们身处的历史情境是基于科学的技术所具有的支配性而带来的连续不断的威胁和危险,公共意见遭受权势技术的操纵,道德和政治导向的丧失,以及损害了那种要求公民做出负责任决定的实践与政治理性。”[27](P174)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以道德为支撑。“政府做出一个政策决定,都应该为设计实现的目标(正义、公平、公正、幸福、健康、生存、安全、福利、平等等)做出一个道德判断。”[28](P60)道德判断是治理能力民主化最根本的内容。由以善恶为基础的判断力所形塑的公民德性,恰是孵化出平等的为人人所具有的现代政治能力的基础。
可见,即便人们总是被告知,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完全一样的治理能力,但是审慎的政治判断作为一种治理能力,应当且可以在多个维度上形塑出平等的治理能力。这种治理能力的平等并不在于每个公民对具体每一项公共事务都有同等程度的理解和判断,而是在于他们作为治理的主体本身就具有同等参与治理的资格和权利;在于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智识和卓见,参与与其能力相应的公共事务的治理;在于他们可以运用基本的道德能力和政治常识对相关的治理主体和治理行为,做出属于自己的应当得到尊重的判断;在于他们能够辨识对于自己而言为善的事物,从而在社会领域努力追求个人目标的实现和公共利益的维护。正如罗伯特·达尔所指出的:“除非在一些非常罕见并受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否则,每一个服从国家法律的成年人都应当被视为有足够的能力去参与民主管理国家的过程。”[29](P64)
四、政治民主与治理能力的民主化
治理能力之所以得以民主化,其背后所依赖的是政治民主的制度保障。政治民主是治理民主的基础。
首先,政治民主保障了公民具有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资格。若公民不能成为潜在的政治家,没有资格或权利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管理,那么就不可能作为治理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公民平等的治理能力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平等,也不是每个公民在任何一项公共事务上都有同等的治理能力,而是公民作为公共治理的主体始终保持有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资格。
其次,公民作为公共权力的赋予者,这使得公民对治理行为的评价和监督具有决定性意义。必须承认,专家在某些领域能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但是“把一些非同寻常的决定委托给专家,并不等于放弃了对最终控制权的掌握”[30](P59)。公民对最终控制权的掌握是指在公民即便不成为治理者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民的治理能力得到了最根本的表现: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是公民治理能力在组织形式上的表现。就此而言,治理民主并不意味着对代议制民主的排斥。
再者,政治民主对权力的限制是公民能够在社会领域形成有效自治的前提。社会的自治需要有足够自由的空间,公民的自我完善能力只有在不受任意权力干预的领域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发挥作用。一个不断被国家权力挤压的公共空间,并非公民德性运行之处。因此,现代民主政治只有在多个维度上限制权力的边界与规范权力的运行,使之不能随意侵入社会领域以避免损害公民的自由,才有可能释放和培育公民良好的政治判断力与积极的治理能力。
可见,治理民主预设了政治民主,或者说治理民主需要以政治民主为基础。就此而言,治理能力的民主化本身就要求政治民主。若缺失民主的制度安排,那么治理民主也就无从谈起,更遑论治理能力的民主化。因此,民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31]不仅治理能力民主化需要政治民主为其保障,治理能力的民主化反过来还可以为政治民主的落实提供稳定的基础。
国家治理必然要求国家决策以“内在平等”为合理原则,也即“政府在决策的时候,应该对那些受决策约束的公民在物质和利益上给予平等的考虑”[32](P54-55)。平等对待每一个公民是一种道德判断,也是政治民主的内在之义。但是,“内在平等”的主张并不只是民主政治的诉求。传统政治学说(尤其是在柏拉图那里)所主张的是具有政治智慧的政治家竭尽所能为国家带来福祉,也即罗伯特·达尔所力图反对的“监护政治”:“把权力交给专家,后者致力于为普遍利益而实施统治,并且知道如何实现这种利益。”[33](P58)可见,在贤能政治或精英政治的主张里,“内在平等”也是重要的内容。但是,相对于这些理论而言,强调平等的公民能力的政治主张更能实现“内在平等”原则。审慎能力并不是一种孤独的考虑,它会让公民遇到与自己有着同等能力和同样欲求的他人,并且明白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单独决定所有的治理政策以使之只考虑自己或与自己相关者的利益。这种理解向所有人发出告诫,相信自己高人一等是一种最糟糕的骄傲,而这种骄傲使人们无法进入有序的政治社会[34],无法组织社会生活,也无法做到平等对待其他公民。因此,承认公民具有平等治理能力的治理模式,更能够保证决策者考虑到与此相关的每一个公民的物质和利益需求。
治理能力的民主化还有利于提升公民参与治理的能力,形成共同治理的模式。一个充分肯定公民具有平等治理能力的社会,更容易调动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从而可以一方面强化公民的主体意识,一方面进一步增强公民实际的治理能力。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促进公共利益的达成。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治理能力的民主化对于政治民主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治理能力的民主化为政治民主的具体落实提供了有效的实践主体和群众基础。因此,治理能力的民主化实际上是通往政治民主的道路。
概而言之,对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而言,公民能否运用自己洞察一切不当的审慎能力,并站在理性的一边做出良好的判断力和采取积极的行动,是这个国家能否为其长治久安夯实道德基础从而实现善治的重要保障。因此,国家治理应该规范权力的运行,限制权力对社会领域的任意干预,释放而不是限制公民的政治判断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开辟出有利于培育具有独立判断力的公民人格的公共空间,提升社会自治的能力,进一步夯实政治民主的基础。
[1] 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 罗西瑙等编:《没有政府的治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3] 王浦劬:《以治理民主实现社会民生——我国行政信访制度政治属性解读》,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4] 任剑涛:《国家的均衡治理——超越举国体制下的超大型项目偏好》,载《学术月刊》,2014(10)。
[5][17] 柏拉图:《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6][1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9] 罗尔斯:《万民法》,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10] 麦金泰尔:《追求美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11][15] Peter J.Steinberger.TheConceptofPoliticalJudgment. 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12][23] 本杰明·巴伯:《强势民主》,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13][19][26]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4][28][29][30][32][33] 罗伯特·达尔:《论民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6] 《柏拉图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0]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1]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2] Howard Williams.Kant’sPoliticalPhilosophy.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83.
[24] 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5][34] 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7] Richard J.Bernstein.BeyondObjectivismandRelativism:Science,Hermeneutics,andPraxis.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5.
[31] 俞可平:《民主法治: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之路》,载《团结》,2014(1)。
(责任编辑 林 间)
Political Judgment and the Democratized Ability of Governance
CHEN Hua-we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Public governance entails the participation and autonomy of citizens, good governance thus depends on citizen’s ability of governance. While political judgment based on prudence is considered as the foundation of ruling, it is also credited exclusively to statesmen or experts by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theory. However, political judgment or prudence could be democratized to the ability of citizens in three ways: as the ruling ability of active citizen but statesmen or experts, as the judgment of spectators and as the deliberative reason about political affairs. The democratization of ruling ability actually connects to the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such a connection provides new understandings of governance and democracy. Democracy makes the democratized ability of governance possible, which in turn paves the way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political judgment;ability of governance;citizen;democracy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主政治语境中的政治家与公民美德研究”(13CZX074)
陈华文: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