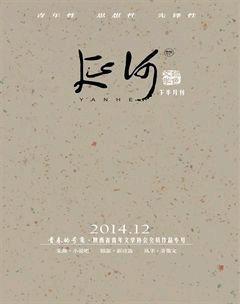庄稼人
郑升
一
庄稼人一年中最重要最辛苦的时候是夏收季节。
当天气越来越热,当一声声“算黄算割”的布谷鸟开始一遍又一遍地穿越麦田上空的时候,庄稼人的神情就会越来越凝重。麦子和天气成了大家最为关心的事。平日里嬉戏打闹的孩子们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许多,都回到自家屋里忙乎着:抬水、喂牛、喂猪、放羊、烧火、带小孩或者拾麦穗。大一些的就要跟着大人们去地里割麦子。
记得自己第一次割麦子是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烈日当空,热浪滚滚,麦杆脆生生的。我提着镰刀跟着父亲到了地里。父亲做了几个示范后,让我先割几捆看看。其实割麦子并不难,打一个结实的麦腰却不好学。父亲打麦腰又快又结实,麦捆扔来扔去都不会散架。我打的提不了几回就散开了,父亲让我只管割最后由他来打麦腰。那时候,我个头和麦杆差不多,可以直着腰割。这样到最后,我与父亲的差距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大。从中午1点多一直到傍晚8点多,我们父子俩居然将3亩多的麦子割完了。那一次虽然汗水湿透了背心,麦穗划伤了胳膊,两手磨出了大泡,但心里却是乐滋滋地。
即使这样,要割的麦子还有许多,而不下雨的天气却只有那么几天。包产到户后各家少的也有十一、二亩地,多的会有二、三十亩地。亩产少,只有广种。这样,好多人家断断续续要从五月底一直忙活到八月中旬,那真是焦人。
后来就有了越来越多的麦客。麦客基本上都是甘肃人,在这里割完麦子,他们拿上工钱回去正好赶上自家的麦子黄了。
第一次跟着父亲叫麦客是到镇上。叫麦客要赶早,父亲说。我们凌晨4点多就出发了,走了近3个小时的山路赶到镇上。人已经很多,街道上,屋檐下,戏台上,甚至学校的园子里也都是人。那时的人们朴实,麦客要价不高,主家砍价也不狠,谈好价就走人。父亲很快就找到了四个人:三个中年人,一个年轻人,每亩价3块,管吃管住。后来割麦的价格一直在涨:4块、6块、8块,到90年代一度涨到40多块。随着平塬上的收割机越来越多,价钱又开始降了。麦客只有去更远的山里才能揽到活。听说这几年山里退耕还林,也不需要麦客了。
麦客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我还记得。
第一次叫的麦客至今有两样事记忆深刻:他们好像已经许多天没洗过脸,洗过澡,脸上黑乎乎的,身上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我直皱眉头但什么也没说,因为一直很爱干净的母亲也没说什么,她显得很有耐心。给麦客们做的饭也是白面多一些,比我们平时吃得还要好一些;给麦客们安排的睡处也总是打扫干净,末了还要再铺上一层干麦草。每天中午日头最红的时候,妈让我去给地里的父亲送水时,再加一罐给麦客。有一回我终于忍不住问母亲为什么这样?母亲沉默了一会,摸着我的头说:以后你长大了就知道了。答案在1996年我读张承志的作品知道什么是西海固地区,什么是甘肃的窖水时开始明了。2006年4月底我坐车路过兰州、定西、陇西、柳园时有了更深地明了:甘肃太旱了。麦客们爱水胜过爱自己,比如自己的脸面。那一次透过车窗,目光所及的地方除了黄色的山塬沟壑,还是黄色的山塬沟壑。已经4月底了,这里没有一丝绿色,大地干裂地没有一点生气。手伸到窗外,有一些清凉。但你的鼻孔里,眼睛里,心里却分明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灼热。
另一样事是这些麦客饭量大的惊人。他们的中午饭要吃两大碗“燃涡面”(不带汤的热面),再加一个大馒头(四两),然后是一大碗面汤。记得上高中时,长身体,同学中饭量大的也就是两大碗面,或者一大碗面一个馒头也就饱了。麦客们吃饭快而仔细,碗里的饭吃完后要再舔一遍碗才交给你,吃得很干净,一点不剩。他们特别爱吃馍馍,临走时主人若能送几个馍馍,他们会高兴得不行。麦客们有时也向主人要一碗开水,从他们随身背着的布袋里取出一个小布袋,抓出一两把灰色、黄色或者黑色的干面粉,泡着吃或者就着水干吃。后来我知道那是甘肃人一种特殊的吃面法:吃炒面。这种面是将黄豆、黑豆、豌豆和在一起磨成粉,再和玉米面、高梁面或者麦面放在一块炒,加盐,加水,直到焙干。这种面放在袋子里,不易坏,是出门远行很方便的干粮。但吃起来呛喉咙,上火。我头一次吃,呛得直咳嗽,眼泪都快出来了。但麦客们吃得很香,很仔细,手指上沾一丁点,也会用嘴小心翼翼舐掉,然后心满意足地点上一根纸烟走向麦田。他们衣衫破旧但背影却像山一样厚实。
这是没水喝的人,饿过肚子的人对待水和粮食的态度,偏执而又真实。他们是一群麦客,让人隐忧让人幸酸又让人敬重的麦客。
现在老家收麦子都用机子,已经没有麦客了。但是,就像一条河流,虽然干涸甚至消失,可是受之影响的人们又怎能轻易忘记呢?又怎能不去追忆而眼睛湿润呢?
我想:会的,即使是在记忆中……
二
当割回的麦子可以堆成一个小落子(麦垛)的时候,紧张的碾麦子就与割麦子同时进行了。
最初是套上牛,用石滚子碾;后来是用打麦机打,就改叫打麦子而不叫碾麦子。
碾麦子那会,早上九点以前就要把麦子摊到麦场上,到中午12点多麦杆被晒得脆生生的,就可以碾了。给牛套上牛笼嘴(防止牛吃麦子),再用绳子套上石滚子,然后大人们赶着牛在麦场里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膨松的青麦杆被压的扁平光滑。这中间我们小孩子一般要坐在场边,有两个事做:给牛喝水和接牛粪。这两样事要动作快,不能让水洒在麦草上,不能让牛粪落在麦杆上。碾完第一遍,就要马上翻场,也就是将麦杆翻过来,再碾一遍后,就开始起场了。
起场主要是将已经碾得很薄很明亮的麦杆(也叫麦草)用木杈挑起来,堆到场边。这是个细致活。用木杈挑麦杆,不能戳到地皮,不能将麦粒卷走。要一边挑一边抖,一边翻一边堆,一气呵成。在木杈的一挑一抖中,厚而软的麦草纷纷散开、落下,散开、聚拢,然后被堆到场边,与此同时,金黄色的麦粒纷纷落下,像天女散花一般,又像大珠小珠落玉盘,灵巧而动人。我喜欢看大人们起场,有时自己也上去试一把。
起完场,就剩下满场夹杂着麦粒的麦草末(又叫苡子),这时全家人一齐要用推把把这些麦草末团到一起,等待扬场,才能稍稍喘一口气。endprint
扬场也就是将麦草末和麦粒分开的过程。父亲是扬场的好把式,经常被村里人请去帮忙。慢慢地,我发现父亲扬场有两个地方与其他人不一样:一是他沿着麦草末堆走一圈,就能辨出风向;二是其他人扬完场,麦粒呈棒槌状。而父亲扬场时,迎风挥动木掀,自胸前一直挥到身后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厚厚的麦粒最终在场里像一道彩虹静静地铺展着。在晚风和余晖中,大人们终于长舒一口气,我们也开始欢呼雀跃,为一场新麦子的诞生。然后我们围坐在彩虹的不远处放心地吃起晚饭。吃完饭,歇上一支烟的功夫,就要忙着将麦子装进袋子,扛进屋倒进麦包,忙碌而又紧张的一天才算结束。即使碰上好天气,这样的日子一般也要持续20天左右。
后来好一些,不用牛碾麦子,用打麦机一次完成,强度却大了许多,一户人家山一样的麦垛一个晚上就打完了。我只打过一次麦子,但印象深刻。
那一次和另一户人家合作,先打我家的。从下午4点多一直打到凌晨5点多。大家各有分工:有拆麦垛的,有拆麦腰递麦子的,有挑麦草、推麦子、装麦子的。每个人都要手脚麻利,才能跟上机子的速度。那真是紧张:顾不上擦汗,顾不上掸掉帽子上、肩膀上厚厚的麦尘。那一年我上初二,是个小大人了,也觉得撑不住了。有好几次一边推着麦子,一边打着盹,手上磨出的泡也不觉得疼了。
终于打完了,我一扔麦杈,靠在离自己最近的麦草垛上,很快就沉沉地睡去。直到11点多醒来眼皮还在打架。大人们的眼睛也都红红的,布满了血丝。
庄稼人的农忙生活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简单而又复杂,紧张而又艰辛。后来收割机越来越多,后来我也不再参加夏收。但是每到夏收季节,特别是下雨天,庄稼人那种焦虑、苍老而又无奈的神情就会浮出记忆的河,让我想起唱着“算黄算割”的布谷鸟,想起烈日当空、挥汗如雨,想起那句充满了焦虑的俗语:龙口夺食……
三
收完麦子、碾完麦子、嗮完麦子、打包入库后,整个夏收就算结束了。然后就是一段雨季,就着雨季,庄稼人们终于可以歇上一口气。雨停之后,差不多就到了8月中旬、9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直至11月份,整个渭北乡村是轻松的、开阔的又是忙碌的。
没有了大片大片金色麦子的土地先是露出了它本来的颜色,没有麦秆遮掩只有低矮麦茬的土地在广袤的蓝天、白云下面显得开阔而又错落有致,我特别喜欢这个时候的渭北乡村,不再焦虑不再炎热,我们骑在树梢爬上坡顶迎风高呼,声音传得老远,时常在山的那一边就会有人也向我们呼喊;我们沿着庄稼地畔或者直接就在庄稼地里撒开脚丫追逐、奔跑或者点燃麦茬,跟着火苗和火龙大喊大叫;我们抓蛐蛐追兔子拿起弹弓射向野鸡麻雀或者天空飞过的不知名的鸟儿;我们跟着大人们看着他们锄地或者犁地,有时候我们也会拿着自己的小锄头上去试试,也会在大人犁地的时候负责送水倒水或者在前面拉着牛缰绳或者一人一个拽着牛尾巴蹲在磨地的犁耙两端。随着站在犁耙中间大人们的吆喝与皮鞭的响声,两头牛拉着犁耙飞快的跑起来,我们一起欢呼身后便留下一道道平滑的辙印,几轮下来,高低起伏的麦地平整了许多好看了许多。锄地主要是用锄头在麦茬地里间隔挖出一个个地窝来,然后在里面点上玉米、高粱、红豆、豌豆或者黑豆的种子,然后再小心翼翼地盖上土。不用多久,一望无垠的麦地里又突然冒出玉米、高粱、红豆、豌豆或者黑豆的小苗,放眼看去,有高有低,有红有绿,错落相间,像一幅斑斓多姿的水彩画。
几天后,这些小苗好像不约而同都长高了许多,尤其是玉米和高粱。大人们接着就要在每株玉米或者高粱的根旁松土,除去杂草,撒上一把化肥然后再掊上土用铁锨或者锄头拍几下。过不了多久,大人们就要在夜间点起篝火就要在庄稼地里巡查,吓走兔子野猪野獾什么的;过不了多久,大人们就要准备掰玉米棒子扔进肩背上的背篓里,用镰刀砍下高高垂下的沉甸甸的高粱穗子,用镰刀或者锄头砍下玉米杆、高粱杆,挖起它们的根,然后一捆一捆背回家或者用架子车拉回家;过不了多久,大人们就要串起玉米棒子挂在窑洞里或者屋檐下,或者搓出玉米粒晒干装包,或者在院场里举起一捆一捆的高粱穗甩向石碌子,一任高粱粒在头顶或者身上飘落,洒满一地直至像小山一样堆起来。
庄稼人就这样似乎有干不完的伙计:割草、打糠、养鸡、养鸭、放羊、喂猪、喂牛、犁地、锄地、种麦、割麦、收麦、秋种、秋收、交公粮、买化肥,到了冬天又要忙着施肥或者给麦苗盖上一层土,忙着挖地窖藏白菜洋芋红萝卜,忙着杀猪宰羊赶集买年货,忙着给孩子们买新衣服忙着孩子们的生活与学习忙着弹棉花缝被子贴窗花蒸一锅又一锅的馒头擀一案又一案的面条,忙着上坟烧纸钱砍松柏赶庙会在大雪飘飞的时候走亲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