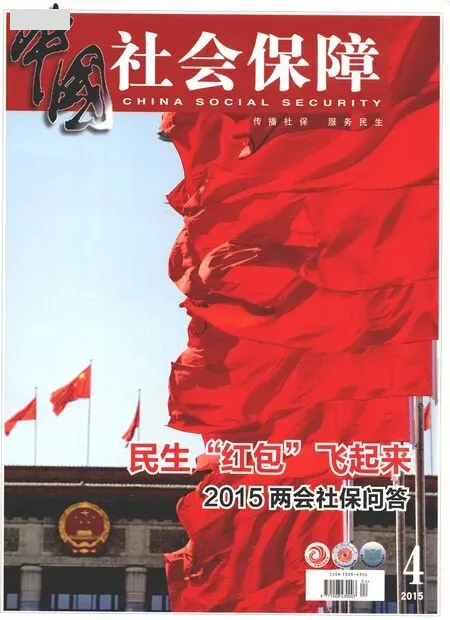金融危机后福利国家新转向
■编译/张占力
金融危机后福利国家新转向
■编译/张占力
未来10年,对欧洲社会公平的威胁不是激进的制度变革,而是福利国家固步不前、“制度化”地拒绝改革、患上“欧洲硬化症”。西欧地区在迈向社会投资型和充满活力的社会保障征途上仍有很多障碍,政治决策者们仍需要在有效地组建持久的改革联盟、打破零和博弈、促进代际团结上作出卓绝努力,唯此或可找到破题之道。
福利模式的变化
过去30年间,对于福利国家与全球化、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相适应的质疑声日益高涨,自由主义怀疑论者尤甚。其依据有三:一是福利国家扭曲劳动力市场,毁灭了工作积极性,致使社会抚养率畸高;二是人口和社会变化,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福利国家财务难以为续;三是全球化对各国政府财政支出施加约束机制,迫使政府减少社会保障支出以增强国际竞争力。2008年金融危机中公共财政表现得不堪一击,也一度证实了怀疑论者观点的“正确性”。但争论很少明晰区分内外变量的影响,尤其对福利国家内在主动调整以应对新风险和需求的关注度不够。
欧洲福利资本主义并无单一、显著的模式,艾斯平·安德森将其分为三种模式,即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北欧)、保守主义福利国家(大陆)和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盎格鲁-撒克逊)。保守主义模式侧重于财政支出,而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则是服务密集型模式,福利供给中市场化占比非常低。艾斯平·安德森强调“路径依赖”,认为不同群体和利益集团会竭力维持现状,使政府只能保持现有福利待遇和服务模式,这反过来进一步强化现行福利供给,如此循环往复。应注意的是,欧洲福利国家也存在“再分配悖论”,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福利国家虽对全体国民进行普惠式待遇发放,却比仅仅针对贫困者的再分配更能有效地减少贫困和不公。
福利模式三分法拥趸众多,反响广泛,但也存在异议,比如没有将地中海沿岸国家和中东欧国家考虑进来;较少关注社会政策对男女性别不平等造成的影响;福利模式划分主要以失业和养老支出界定,而对教育、医疗、家庭服务考量不够等。
欧洲福利国家近年面临两大系统性挑战。挑战之一来自于国家的财务危机。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速放缓,生产力下降,去工业化进程加快,加之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泥沼难以自拔,财务紧缩政策成为未来10年福利国家的优选政策。第二个挑战则是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与不断出现的社会新风险之间存在割裂。传统社会保障安排难以快速地适应劳动力市场结构性调整、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中工作富裕者和穷忙族等新兴社会不公平也在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中难以得到有效化解。在此背景下,社会投资型福利国家模式颇受人们所重视。
社会投资型福利国家模式有其自身特点,如强调劳动力市场的灵活保障以及实施就业激活政策,这与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所提出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保障概念密切相关。社会投资型福利国家模式内容丰富,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危机,建立服务为基础的知识驱动型经济等。目的即是“学习型经济与社会”,通过员工持股形式不断提升其知识和技能。目前该模式已经得到欧盟决策者的支持与认可。莫瑞尔、帕尔梅等人认为,理想化的模式具有一些基本的特征,如普惠式的儿童照看、高质量的学校教育、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倡导终身学习、主动减少失业尤其是青年失业,以及实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等。因此,社会投资型福利国家模式更强调资本主义经济体公平与效率的长期平衡。
政治环境的约束
福利国家植根于其政治构造,并受民主制度的约束和选举力量的左右。过去30年促生福利国家膨胀的因素不断削弱,这不仅体现在工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影响力减弱上,也表现在战后合作主义制度体系逐渐瓦解的进程中。二战后福利国家富有弹性的观点也被一系列社会现实所证伪——如撒切尔政府时期由新自由主义者发起的紧缩政策难言成功。尽管终止现有社会供给模式并对其重构不失为解决政治上不受欢迎之良方,但很少有富有影响力的政治联盟会劝说投票人,福利国家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地步。上述种种原因造就了福利国家政治上的谨慎小心,仅对福利制度的外围修修补补,而不敢对制度核心内容来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中右翼政府更乐于安享现状。
关于政府失灵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福利国家由于受公共部门和个人群体等既得利益集团的牵制而难以改变。大量研究也强调政府而非国家立法机关在福利国家决策中的作用。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中产阶级在许多国家已成为社会保障制度最大受益者,导致养老待遇和现金转移支付难以施惠于老年群体。最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福利国家多为“原地踏步走”的发展,使诞生于50年前、本就难以应对未来挑战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僵化,政治和选举参与度的差异也将这一现状推向更加恶化的境地。随着年轻群体和社会弱势群体选举参与度的下降,老年群体和富裕阶层在政治进程中更具影响力。
民众态度的转变
关于民众态度定量研究调查数据的样本来自于欧盟三个成员国,即英国、丹麦和法国,各代表了三种福利模式中的一个类型。调查的目的在于衡量民众认为福利国家需要进行多大程度的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再校准又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共识。金融危机后财务紧缩政策让欧洲居民逐渐意识到财政资源优化配置、重建新型社会契约的必要性。然而,投票人仍相当“保守”,拒绝改变的迹象增多。与此同时,民众对福利国家态度不断转变,他们不仅仅关心财政紧缩和财政赤字的合法性以及相应的财政政策选择,更注重金融危机后政府角色的定位:鉴于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以及人口和社会的压力,政府未来应该进军哪些领域,又要在哪些领域淡出,或提供方式上应如何不同于以往。确切地说,政治家们不仅要有短期计划以解决公共赤字,也要对未来国家结构有一揽子战略安排。调查相关结果如下:
第一,欧洲地区对集体福利供给需求依然强劲。为保护个人免受不可预见的风险,提供老年收入保障等传统福利供给仍然很受拥护,“福利末日”预言亦不攻自破。事实上,对社会保险缴费原则的普遍支持也让人大感意外,英国在此方面表现尤为明显。数据显示,失业保险方面,49%的英国受访对象支持缴费原则,法国为57%,丹麦为43%;养老方面,对缴费原则支持者占比英国为48%,法国为44%,丹麦为20%。而对由普惠式、社会连带主义福利制度向以贫困群体为对象的自由主义福利制度转变的动力不足,制度缴费者应该平等地获得福利待遇和社会服务已深入人心。
第二,强调缴费原则或有助于巩固福利国家的地位。如果公民认为自己缴费与所得之间缺乏关联,远离了贝弗里奇报告所确定的缴费原则,那么他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拥护力度更会减弱。北欧地区如丹麦由于奉行福利共享主义传统,缴费原则淡薄。贝尔和加夫尼认为,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如果加强缴费与受益的关联,能够解决由财政紧缩和人口快速调整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一些主要矛盾与问题,“充分的缴费”和“有义务的权利”二者融合与建立福利国家的目的之间关系密切。尽管如此,调查结果却反差甚巨:为减少公共赤字,大多数民众认为应该采取减少对富裕阶层的支出、针对性地投向贫困者等措施,而非遵循缴费原则,两者占比结果对比情况为英国54%∶24%,法国62%∶17%,丹麦60%∶13%。但也有令人欣慰之处,财政紧缩背景下,民众更加强调对社会保障核心内容——如养老、医疗保险等缴费项目的投入,削减生育津贴、儿童福利等非缴费性项目支出。如丹麦额外财政支出用于学前儿童照顾(12%)、儿童津贴(4%)和产假津贴(3%)的支持者占比较低。这也说明社会公众对扩大福利外延、应对新社会风险的态度较为冷淡。
第三,转向社会投资型国家的支持力度有所削弱。调查结果显示,失业、养老、疾病和残疾已成为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58%的法国人、51%的英国人认为失业金充足性不够;68%的法国人和58%的英国人认为养老金的充足性有待提高;53%的丹麦人认为疾病和残疾的保障不够充分。与此相反,社会民众普遍认为家庭保障(如儿童津贴等)已较为充足,这一占比丹麦为92%、法国为80%、英国为78%,这种认知现状给欧洲福利国家向社会投资型方向发展设置了巨大障碍。此外,欧洲老年人口占比大,投票参与度高,其关注重点主要集中于养老和医疗方面,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决策。与养老和健康照顾支出相比,当财政发生赤字需要削减待遇时,教育、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家庭救助等支出更易首当其冲。由于受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影响,欧洲社会投资型支出占比已近历史低点,如不加以矫正,将对欧洲未来长期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削弱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力,并带来个体生命周期内及代际之间的不公平。
从上述分析可知,社会投资型福利国家模式与充满活力的社会保障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公众对国家应该承担新型社会风险的态度比较冷淡。欧洲国家福利资本主义在制度遗产、目标以及社会投资方面存在“三元悖论”。首先,福利国家仍广受欢迎,但主要投票群体也出现拒绝改变福利国家的倾向和一定程度对现有制度的保守偏好;其次,福利国家的支持与缴费原则之间虽有共鸣,但金融危机下投票者的目标(如减少富裕阶层支出)却会损坏长期公平;再次,公平与效率需要由收入维持和传统社会风险到新兴风险转变,但投票者仍倾向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国家原有安排而不想作出改革。(文献来自《国际社会保障评论》Patrick Diamond and Guy Lodge “Dynamic Social Security after the crisis:Towards a new welfare state?”)■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