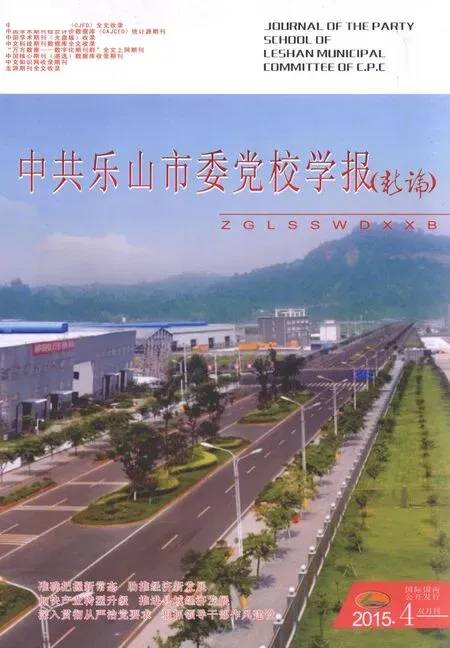浅谈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
梁有存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400074)
恩斯特·布洛赫(1885 年—1997 年)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成名作《乌托邦的精神》发表于1918 年,其哲学宗旨是以乌托邦为武器,唤醒人们内在的精神力量,达到自我超越和人类救赎。布洛赫之所以专注研究乌托邦精神,是因为他洞察到现代人的根本困境,即精神的萎缩,或者说是超越维度的丧失。他认为人之为人的根本不在于人的过去、人的历史,而在于他对未来乌托邦的追求,也就是达到自我的超越。他在《乌托邦的精神》一书中,明确回答了如何唤醒人们内心的乌托邦精神的问题,指出乌托邦精神的唤醒包含着两条道路:内在的道路和外在的道路。通过内在的道路达到自我面对,再把内在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外在的,同外部世界的种种敌人战斗,使世界成为我们的家园。布洛赫唤醒乌托邦精神的外在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强调通过实践来改造世界,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谋而合。他的乌托邦思想不仅为我们理解人的存在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理论视角,更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内涵提供了重要指示。
一、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
布洛赫一生致力于研究乌托邦思想,在他这里,乌托邦不是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笔下一个虚构的世外桃源,而是一种巨大的隐匿力量,它深藏于人类的内心深处,驱动着人们的灵魂世界,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一)乌托邦的精神实质
布洛赫在《乌托邦的精神》的开篇就写到:“一个新的开端被指出了,尚未被丢失的传统又重新占有了自己;那光在遥远的内心深处闪耀着,它不是懦弱的 ‘好像’,不是毫无意义的评论;在所有的伪装和死去的文明之上升起的是它,永恒的目标、预感、良知和救赎:它从我们的心中升起,我们的心虽然经历了所有的一切却仍然没有破碎,从内心的最深处,即我们的正在觉醒的梦的最真实的部分。”这里所说的“那光”、“最真实的部分”就是人们内心的乌托邦的精神,它是“永恒的目标、预感、良知和救赎”,也就是我们追求自我的永恒目标,对未来越来越好的预感,以及我们内心所保有的良知和对自我的救赎。布洛赫之所以在这里强调乌托邦精神的重要,是因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的生命遭到了严重的威胁,精神饱受摧残,生存状况受到挑战,人们开始迷失自我,造成了精神的枯萎。正是由于布洛赫看到了人类正在丢失自己,走向精神的死亡,他试图通过唤醒乌托邦的精神,帮助人们重新获得自己,拯救人类,回归到走向完满的道路上来。
那么,为什么说人的精神的枯萎就意味着人的死亡呢? 在布洛赫看来,人之为人的根本就在于精神,在于对乌托邦未来的希望中体会自我,超越自我,即人的存在的超越的维度。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精神,那便如同动物一般,成为了行尸走肉,空壳一样的存在。布洛赫叙述了现代人的生存体验:我活着,但却感到前途渺茫。在“货币经济”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一旦堕入铜臭,精神就枯萎了,再也听不见内心的激动。知识分子尽管谈吐优雅,但他们的灵魂、伤感体验、行动中的道德感统统坏掉了。那么,我们内心最本真的东西究竟为何? 更进一步地说,现代人都被物质利益、权利欲望等虚假的东西所蒙蔽,成了它们的奴隶,丧失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人们离本真的自我越来越远,内心的精神已经被物欲、爱欲等重重迷雾所遮盖,人类已沦陷为追求利益的动物,崇拜权利的动物。
(二)乌托邦精神的超越性
布洛赫对于真正的人的理解在于人的超越性上,对自我内在的超越和对外部世界的超越。自我内在的超越也就是对死亡本身的超越。人人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如果死亡意味着一切结束的话,那么人的生活意义、人的历史意义都将被抹掉。通过他人死亡的经验中人们可以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在死亡的压力下,人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对此前人生种种做出再评价、再选择,回归本心,达到自我升华,在那一瞬间,死亡也不能阻止人对于内心灵魂世界的追求。同时,对于那些尚未受到死亡威胁的人们来说,超越死亡就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超过本身的存在价值,那么死亡将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毫无意义,来时的人与去时的人对他们自身的存在并无贡献。想要成为真正的人,超越死亡本身,人类就要在有限的生命活动中发挥出无限的生命意义,贡献出大于本身的存在价值,到那时,人们不再惧怕死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布洛赫在这里谈到,如若人们不能超越死亡,那么这一代人活着便对下一代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历史意义,人类一代又一代只能是机械的、麻木的繁衍过程,不能保证各代之间的连续性与总体性,死亡使得人类变得虚无。只有当我们主动去迎接死亡的挑战时,我们才能超越人的有限性,达到永恒,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我们内在的灵魂力量,冲破一切虚假和罪恶。到那时,死亡不再意味着一切的终结,我们最终成为了真正的自己,即布洛赫所说的灵魂的转世。
在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超越性的丧失上,布洛赫就曾提到现代人或者是物质利益的奴隶,或者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奴隶。外部世界的虚假与罪恶正在统治着我们、腐蚀着我们,我们的一部分意识已经屈从于它们,开始自我欺骗,满足现状,把外部世界看成是万能的,受制于这些虚假和罪恶,放弃反抗与抵制,使得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相互牵制的张力消失了,最终成为了外部世界的奴隶。要想打破这种物化状态,把人从外部世界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最根本的是要重建人的存在的超越维度。唤醒沉睡于人们内心的乌托邦的精神,赋予人们强大的精神力量,完成内心世界的准备,再把内在力量转化为外在的,对外部世界进行改造,使外部世界成为我们的。
二、唤醒乌托邦的精神
布洛赫在《乌托邦的精神》一书中着重回答了如何唤醒乌托邦精神的问题,他分两部分对此问题作出了回答,第一部分叫《自我相遇》,这部分主要讲的是人从内在道路对乌托邦精神的唤醒;第二部分叫《卡尔·马克思、死亡和启示录》,在乌托邦精神的引领下使内在的东西成为外在的,变革世界,让世界成为我们的家园。
(一)内在的道路
布洛赫试图通过对音乐和艺术的大篇幅描绘让人们与内心深处的自己相遇,他坚信人们心中还保留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用艺术的真谛、音乐的美妙来感染越渐麻木的人们。他相信人们内心正沉睡着乌托邦的精神,虽然人类正在因为精神的枯萎而走向死亡,但死亡绝不是人们唯一的出路。他在书中写道:“与此同时,拥有着数百万无产阶级的西方还没有发言;与此同时,在俄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共和国;与此同时,那些关于我们的灵魂,关于我们的宗教良心的问题依然在燃烧着,依然没有熄灭,没有被压服,它们的绝对的要求还没有被实践。更重要的是,我们至少已经从一个世纪前的马克思对现实的看法中学习到了很多。”从这里可以看出,布洛赫认为,我们还保有人之为人的根本,我们的精神还没有完全死亡,我们的灵魂还在燃烧着,我们还有走向未来、改造世界的机会,因为我们已经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这种方法,那就是实践。在自我面对的历程中,我们首先要战胜的就是当下的黑暗,布洛赫描述人存在的黑暗状态:“我甚至体验不到我自己,我不拥有我自己。”他一再强调我们无法真切地体验当下的瞬间,只能将刚刚过去的作为我们的体验对象,确切地说:“我们活着,却体会不到自己活着;从来没有进入意识的东西也不会进入无意识。”相反,希望会带来我们冲破黑暗的力量,希望就在黑暗之中。布洛赫认为人只有攻破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才能获得重生的力量,才能拥有自己,感受自我的存在,回归到完满的道路上来,并在乌托邦的希望指引下,同外部世界战斗,使世界成为灵魂的世界。
(二)外在的道路
在达到自我面对之后,就要把内在的变成外在的,因为只有这样,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过真正属于人的生活。要达到这种状态,就必须把内在的精神力量转化成外在的行动,找到变革现实的力量之源,对外部世界进行改造。布洛赫说,我们生活的周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虚假的意识形态,它们正在侵噬我们的灵魂,这迫使我们必须将内在的自我释放出来,同外部敌人作战,战斗的主要场所就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此时被唤醒的乌托邦的精神在变革社会中就有了革命的使命,它不但必须是外在的,还必须与现实世界保持一定的张力,因为只有与现实世界相互作用,才能既达到改变现实世界的作用,并且这些改变还合乎我们内在的灵魂世界。也就是说外部世界的任何一个小的改变都与我们密切相关联,我们的实践活动对生活的周围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再通过乌托邦的精神回到我们本身,产生比原来更大的作用。至此,通过内在的道路与外在的道路结合,布洛赫对乌托邦的唤醒就完成了,但必须注意,对乌托邦的唤醒是一个长久的、持续的过程,在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坚韧的意志,才能达到最终的完满。
三、乌托邦的哲学本质
在对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进行梳理之后,可以发现他的哲学逻辑是这样一条路径:现实的人—真正的人—革命的人,其哲学思想带有浓重的人本主义色彩,突出强调人的内在本质的重要性。他把人看作是一切的起点,企图通过唤醒真正的人来改造现实世界,将人的重要性放在了至高点上。布洛赫乌托邦哲学的特点是对自我的不满和批判,对人的内在世界的敏感和超越。在他那里,一切社会的变革和改造都必须由真正的人来完成,没有经历过内在自我超越的人是不可能为人类的进步做贡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布洛赫乌托邦思想的核心就是人的内在精神,即乌托邦精神。与之不同,注重于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则坚持的是对外部世界的超越性,力图通过对现实世界的美好改造,提供给人类一个成为真正自己的乌托邦,也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上文中提到布洛赫唤醒乌托邦精神的外在道路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密切,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正是帮助我们获得对外部世界一切虚假和罪恶的敏感性的,他的实践哲学是人类自我面对之后与外部世界斗争的有力武器。在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又是革命的乌托邦,革命是因为它在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批判的基础上有所行动,而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上;乌托邦则是因为它的最终归宿也是到达一个理想的国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布洛赫这里就是把现实世界改造为通往灵魂世界的工具。马克思主义与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就是“理性”与“希望”的统一,是“寒流”(对现实的批判分析)和“暖流”(对乌托邦未来的希望)的交汇。
[1]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M].trans.Anthony A.Nassar,Stanford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Meridian,2000.
[2]夏凡.社会革命与灵魂革命的神圣相遇——恩斯特·布洛赫《乌托邦精神》的文本学解读[J].东南学术,2006,(02).
[3]张双利.乌托邦与我们——论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的现实意义[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