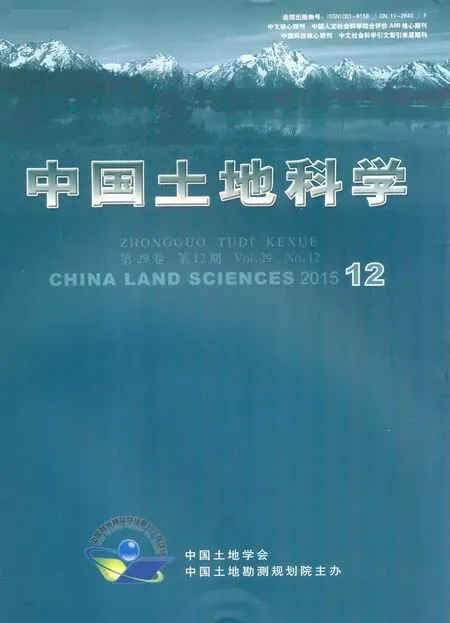关于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土地(系统)”定义的讨论
冯广京
关于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土地(系统)”定义的讨论
冯广京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北京100035)
研究目的:改变土地科学学科没有反映学科特征的“土地”概念定义的状况,提出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概念定义。研究方法:针对土地科学学科长期没有形成能够反映学科特征的“土地”概念的状况,搜集土地科学界和相关学科有关“土地”概念定义的研究文献,研究分析土地科学界有关“土地”概念定义存在的问题,指出土地科学学科缺失反映学科特征的“土地”概念的严重性,根据土地科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和内涵,提出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概念定义。研究结果:(1)土地科学学科现有“土地”概念的定义主要体现了地理学等自然学科的特征,不能反映土地科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和内涵;(2)由于没有学科视角的“土地”概念的定义,导致土地科学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研究范围等重要方面难以反映土地科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和内涵,引致土地科学学科体系构建困难。研究结论:(1)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概念具有以土地权籍理论为核心和基础、权籍可及性、人力可达性及土地一般属性的重要特征;(2)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是“一个人类可以设置并行使土地权籍的地球陆地表层(包含内陆水域、海岛和沿海滩涂)的时空系统”,简称为人地关系权籍时空系统;(3)由本文提出的“土地”概念定义,推出“土地科学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地球表层土地人地关系权籍时空系统中出现的一切土地现象”;(4)作者提出的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概念定义体现了学科的本质特征和内涵,反映了人类开展土地利用活动不可或缺的视角,构成了土地科学学科发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学科建设;土地科学;土地;人地关系权籍时空系统
1 “土地(系统)”概念是土地科学学科的元概念(meta-concept)
1.1两个基本概念
(1)本文讨论的“土地”,有两种概念的意思,一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土地,具有土地的一般性质;另一种是指学科视角下的“土地”,具有某一学科的特殊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土地,对于研究有关“土地”的学科而言既是最基本的概念,也是至关重要的概念,具有决定性意义。为了表达学科视角下的“土地”概念的重要性,笔者将其视为一种“元概念”。“‘元'在此表‘本原'、‘根本'、‘统领'之意。元概念占据着阐释西方文化共时性展示和历时性演变的观念制高点,是统领诸多一般性具体概念的具备统括能力的本原性概念,内置潜在的可延扩指对功能。”[1]
(2)“土地”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词的问题,在涉及研究“土地”的学科中,它是一个有关“土地”时空变化的系统[2],是由多因素构成和时空关系决定的系统。为了强调这种“土地”时空系统的概念,笔者在本文中使用了“土地(系统)”的概念,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有关“土地”一词的讨论。需要读者仔细区别“土地”和“土地(系统)”的概念。
1.2“土地(系统)”概念对于土地科学学科的重要性
土地科学学科是一门系统研究有关“土地(系统)”变化的科学学科。它有三个关键词:“系统研究”、“土地(系统)”、“科学学科”。其中,“系统研究”是利用系统思想、观点和方法,从整体上研究土地时空系统的变化;“土地(系统)”是构成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一个整体时空系统的土地,而不是狭义的土地;“科学学科”是系统研究土地时空系统变化的“知识体系”。在这三个关键词中,“土地(系统)”是核心,是土地科学学科开展研究的起点和研究对象,也是土地科学之所以能成为学科的根源。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没有这一“土地(系统)”,也就没有土地科学学科存在的必要了。
因此,首先需要科学认识和把握这一“土地(系统)”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才能准确认识和科学研究土地科学学科的问题,也才能明确和坚持应当以什么样的科学方法研究这一“土地(系统)”,从而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有关这一“土地(系统)”的“知识体系”[3]。这一点对于认识和研究土地科学学科十分重要。
1.3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有关“土地(系统)”概念存在的问题
由于“土地和土地利用是多学科的研究领域”[4],也“是多学科的研究对象”[5],同时又是这些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素,因此凡涉及土地的学科都要在确认土地的基本共性的基础上,首先定义其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概念,以确定各自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角度,这就导致了有关“土地(系统)”概念的多义性,而这种多义性恰恰反映和体现了不同学科的差异性和存在的客观性、必要性。土地科学学科也不例外,大部分研究者和大部分研究专著都从“土地(系统)”的概念展开各自的研究。
然而,当笔者通过梳理、总结和分析土地科学界有关“土地(系统)”的概念后,发现土地科学学科是一个例外,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准确反映自己学科本质特征和内涵的“土地(系统)”概念,较多使用的是地理学定义的“土地(系统)”概念,小部分使用的是其他学科定义的“土地(系统)”概念。这导致了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土地科学学科难以从这些“土地(系统)”定义的概念展开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角度,引致与其他学科的重叠性,使得很多人不能把握土地科学学科的核心任务和研究内容,把其他学科的研究内容当成了自己的主要研究内容,难以体现和开展土地科学学科自己的独特性研究,从而又使得土地科学学科缺失了“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的建构;第二种结果是将一般意义的“土地”概念混同于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概念,从而认为“土地(系统)”这一概念不科学,“没有指出土地科学的本质”[6],从而放弃对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概念的界定,使得土地科学学科缺乏了生长和生存的逻辑基础。这也正是涉及土地问题的学科都要做出符合各自学科视角的“土地(系统)”概念定义的原因所在。
当前,在土地科学学科的研究和发展中,出现的很多疑难问题以及由其引致的很多分歧,根源都在于对于这一“土地(系统)”的认知和研究的差异。因此,本文将集中讨论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概念问题。
2 有关“土地(系统)”的概念梳理
2.1多学科有关“土地(系统)”的概念
每一门研究有关土地的学科都有其特殊的“土地(系统)”概念。
从自然学科整体的角度分析,有关“土地(系统)”的概念是,“土地是地球表面的一个特定区域,其特性包括与这一区域上下垂直的生物圈的相当稳定或可以预见的、周期循环的所有属性,以及过去和现在人类活动的结果。”[5]因此,自然学科属性的学科基本上都以此“土地(系统)”概念为其定义的“土地(系统)”概念的基本内核。
比如,地理学有关“土地(系统)”的概念是,土地是地球表面的某一特定的区域,既是一种自然资源,又包括人类生产劳动的产物[7]。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FAO)1976年出版的《土地评价纲要》(Framework for Land Evaluation)将土地定义为:“土地是比土壤更为广泛的概念,它包括影响土地用途潜力的自然环境,如气候、地貌、土壤、水文与植被,还包括过去和现在的人类活动成果”。受此影响,1995年出版的《中国自然资源丛书》(综合卷)定义“土地是由气候、地貌、岩石、土壤、植被和水文等自然要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自然综合体及人类生产劳动的产物。”[8]近些年来,地理学视角下的“土地(系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人类家园的地球表层、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等在时间和空间中变化的一切地理现象”[9],但是,由于其中众多的关键概念也造成了“缺乏核心的困惑”[10],因此近些年来逐渐认识、提出并将其重心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转移,认为:“‘人地关系'维系着‘环境变化'、‘景观'、‘发展'、‘风险'等人类—环境地理学的关键概念,而‘地域系统'凝聚了‘空间'、‘时间'、‘全球化'、‘区域和地方'、‘尺度'和‘系统'等空间—分布地理学的关键概念”[11]。可以明显看出,地理学对地球表层即“土地(系统)”的研究实际上已经明确为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而其他学科对“土地(系统)”的概念也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
经济学有关“土地(系统)”的概念是,土地即自然,“是未经人的协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劳动对象,作为一切活动的一般空间基础”[5],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比如美国的伊利(Richard T· Ely)和莫尔豪斯(Edward W· Morehouse)在《土地经济学原理》中指出:“但土地一辞的含义,就经济学的术语来讲,不仅限于土地的表面;它包含一切天然资源——森林、矿藏、水源等等在内”[12],“它的意义不仅是指土地的表面,因为它还包含地面上下的东西”[13]。而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Marshall)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帮助人类,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所赠与的物质和力量。”[14]
政治学有关“土地(系统)”的概念是,土地是立国的要素。一个国家的土地或者称为‘国土',它和人民及主权共同构成立国三要素。因此一个国家的土地是与其“国土”相同的[15]。基于这样的概念出发,国土经济学提出了国土是某个国家的人民赖以生存的场所,因此将某个国家地域范围内的全部国土资源定义为国土[16],因此,国土经济学视角下的“土地(系统)”实际上就是国土。
法学有关“土地(系统)”的概念是,“土地是指地球表层的特定空间(包括地下矿产),中国民国时期《土地法》称土地谓水陆及天然富源。”[5]“1939年《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规定:‘本条例所称土地,包括农地、林地、房地、荒地、山地、水地及一切水陆天然富源。'瑞典民法典谓:‘本法所称土地为:①不动产;②不动产登记簿上登记的独立而且持续的权利;③矿山;④土地公有关系所有部分。'”[17]“法律上的土地并不是地理学上所指的整个陆地表面,而是人们能够利用、控制的土地。人力难以控制利用的陆地,还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土地”[18]。因此,在法学的视角下,“土地(系统)”是由具体法律条文规定的,其大小由法律条文所规定。
系统论有关“土地(系统)”的概念是,土地是由耕地、林地、牧地、水地、市地、工矿地、旅游地和特种用地等子系统组成的大系统,是由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共同组成的,并借助于能量与物质流动转换而成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19]。
景观学有关“土地(系统)”的概念是,土地即景观,在景观学家们的眼中土地和景观是同义语。“依据景观生态学原理,景观就是地面上生态系统的镶嵌,景观在自然等级系统中是一个比生态系统高一级的层次,景观就是自然和文化生态系统载体的土地”[20]。
由这些不同学科对“土地(系统)”的定义可以看出,不同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具有各自学科的特殊规定性,从而构成了学科上的层次性、差异性和区别性。
2.2土地科学学科现有的“土地(系统)”的概念
土地科学学科有关“土地(系统)”的概念和定义也有很多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马克伟主编的《土地大辞典》中定义,“土地指地球表层的陆地部分,其中包括内陆水域和沿海滩涂。”[5]
王万茂认为,“可将土地分为狭义土地和广义土地,进一步细分为平面土地和立体土地,最终归结为土地资源和土地资产。”其中,从土地资源角度上仍然是将土地定义为地球表面的一定空间,从土地资产角度上则强调了资产和土地权属的价格[20]。
毕宝德认为,“土地是一个由地球陆地一定高度和深度范围内的土壤、岩石、矿藏、水文、大气和植被等要素构成的”,并“综合了人类正反面活动成果的自然—经济综合体。”[21]
梁学庆认为,“土地是地球陆地表层的总体,它是由地貌、土壤、植被、地表水、浅层地下水、表层岩石、矿藏和作用于地表的气候条件组成的综合体,是自然历史的产物。”但是“在社会生产中,它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宝贵的自然资源。土地是不同于地球其他部位的相对独立的自然—经济复合系统”[22]。
林增杰认为,“土地是人类社会活动和使人类劳动过程能够得以全部实现的基本条件与基础”,“为地球表层的陆地部分,包括海洋滩涂和内陆水域。”[23]
刘黎明和林培认为,“土地是由地球陆地表面一定立体空间内的气候、土壤、基础地质、地形地貌、水文及植被等自然要素构成的自然地理综合体,同时包含着人类活动对其改造和利用的结果,它又是一个自然—经济综合体(Physical-Economic Complex),具体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含义:1)土地是由土壤、气候、地形、岩石、水文、植被、等自然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构成自然综合体,有其自身形成、发展演变规律……2)土地是一个垂直系统,具有一定立体空间……3)土地的性质和功能(如土地适宜性等)取决于各自然要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4)土地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条件,具有社会经济属性……。”[24]
张占录和张正峰认为,“土地的本质是由自然要素和人类活动成果组成的一定范围的空间。更简单地说,土地是一定范围的空间,这个空间的组成要素是土壤、大气、光照、岩石、水文、动植物及人类活动成果。”[25]
李元、马克伟、鹿心社认为,“如果大家认同把土地的利用、配置、保护、地权和收益分配作为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去重复研究气候、水、地貌、生物、地质矿产学科已在研究的东西,或者研究由这些因素组成‘综合体';只是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分别研究单个环境因素和综合研究若干主要因素对土地利用、质量和地价的影响,为探索土地利用、地权和地价的规律和制订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则可考虑暂把可以设置管辖权和所有权的地球陆地表层(含海岛和内陆水域)作为土地学科研究对象的土地概念。”[26]
以上的观点基本代表了土地科学界有关“土地(系统)”的概念定义,无需更多一一列出了。
可以看出,土地科学学科有关“土地(系统)”的概念体现出来两种明显的特征,一种是其所定义的“土地(系统)”主要还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土地”的概念,并以这种普通“土地”的概念代替了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概念;另一种是较多地体现出了地理学和其他一些学科的“土地(系统)”概念的特征,强调土地是地球表层上一定范围的空间,它是自然形成的,同时其上又凝聚了人类的劳动。但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别,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它们研究的角度不同,研究的侧面有所不同”[27]。土地科学学科有关“土地(系统)”概念表现出来的两种特征,前一种导致了土地科学学科在研究土地问题的学科中丧失了自己的特殊学科视角,难以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而后一种导致了土地科学学科现有的视角主要反映和体现了地理学科和其他一些学科的研究视角,地理学和其他一些学科的语言和理论替代了土地科学学科的主导语言和主导理论,土地科学学科丧失了自己学科的独特主导语言和主导理论,从而使得土地科学学科丧失了自己学科的“相对独立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笔者看来,李元、马克伟、鹿心社2000年提出有关“土地(系统)”的思考,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土地资源利用和管理实践遭遇了阻碍其发展的较大瓶颈问题,比如土地资源利用和管理实践应当以什么内容为主要任务、核心目标和发展方向以及如何协调相关行业部门的关系等,迫切需要土地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突破的支持,但遗憾的是土地科学界在实践需要理论支持的时候,并没有能够通过实现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给予土地资源利用和管理实践的有力支持,理论研究大大滞后于实践的发展。同时,这一结果实际上也影响了后期土地科学学科的发展,长期没有认识并提出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概念定义,使得土地科学界也难以准确提出能够反映自己学科本质特征和内涵的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研究范围、研究任务和研究目标等,进而引致土地科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困难,导致目前有关土地科学学科发展方向的混乱和矛盾。
2.3土地科学学科现有“土地(系统)”概念的问题
上面有关“土地(系统)”概念的讨论,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1)不同学科领域对“土地(系统)”概念的讨论,都具有自己学科的特殊规定性,因此有关“土地(系统)”的概念是有明显区别的,带有明显的学科视角特征。这恰恰表明了这些学科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2)无论哪一门学科视角下的“土地”都是一个系统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狭义的单一概念,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构成因素,每一门学科都是从自己的学科视角研究“土地(系统)”。(3)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也是一个有关“土地”的系统,也不是单一因素的狭义土地。这一点对于认识和研究土地科学学科及其核心理论十分重要。
但是,土地学家们并没有形成能够准确反映土地科学学科本质特征和内涵的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概念,而且多数人提出的“土地(系统)”的概念也只是从土地本身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的角度展开的,带有比较强的地理学特点,特别是受到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1976年出版的《土地评价纲要》中有关土地的概念影响较多,因而表现出与地理学家们有关“土地(系统)”的概念十分相近。这样的结果不仅没有使得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有关“土地(系统)”的概念反映出土地科学学科的特点及其学科的特殊规定性,反而导致了与地理学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概念相似的结果。
这一概念决定了地理学(也不止于地理学)把研究土地的自然形成过程和机理、景观和空间,以及人在其中的作用和关系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土地科学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呢?可以肯定的说,一定不是地理学(不止于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否则,只要地理学(和已有的研究土地的学科)就足够了,完全不会也不应该出现和发展土地科学学科了。但是,已有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都已证明,土地科学学科对于人类开展土地利用活动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还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一定不是现在使用的地理学或者其他相关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概念。
地理学和其他相关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概念只体现了地理学和其他相关学科自身的特征,并没有体现土地科学学科的特殊性。由地理学或其他相关学科的“土地(系统)”概念出发去构建土地科学学科体系,不仅使土地科学学科总是带有某些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似性,而且随着近些年来老一代土地学家们逐渐的自然退出和多学科研究者的逐渐进入,使得土地科学学科也逐渐出现了一种倾向,即一部分人越来越倾向于把土地科学学科的研究重心转向其他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领域(比如试图将土地科学学科由主要研究非生产性土地利用而间接提高土地生产力的方向转向研究生产性土地利用直接提高土地生产力的方向),而越来越弱化土地科学学科自己的学科独特性(比如逐渐弱化土地科学基于“人、地、权”三位一体的视角研究人地关系及其之上的人与人开展土地利用活动关系的特性),结果不仅导致土地科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土地科学学科发展方向上的迷茫,也使得科学界的人们更难以认识土地科学的学科独立性了。
土地学家们对“土地(系统)”没有形成一致的概念的结果,势必会导致土地科学学科对“土地(系统)”认知和研究的矛盾性与局限性;而土地学家们不能形成能够准确反映土地科学学科本质特征和内涵的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概念,又势必会导致土地科学学科与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混淆,影响土地科学学科的发展。
3 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概念
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的概念应当是什么样的呢?
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既不可能是其他单一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也不可能是包括所有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的集合。如果土地科学视角下的“土地(系统)”完全是其他某一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则表明土地科学学科毫无存在的价值和必要,也与土地科学学科不断发展壮大的现实相矛盾;如果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是所有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或若干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的集合,从现阶段发展来看,土地科学学科既不可能也无能力“包打天下”。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一定是带有明显的土地科学学科的特征和特殊规定性的“土地(系统)”。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的,“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门科学的对象。”[28]
因此,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一定是一个具有学科特征的特殊系统,应该完全不同于其他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这一道理十分浅显,如果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和另外一门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是一样的,那么土地科学学科一定不是一个独立学科,而且也不可能发生和继续发展。
事实上,土地科学学科35年前就已创立,而且现在还在快速发展,这说明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独特的“土地(系统)”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以是否被人们显化所改变。但是,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概念长期不能发现和提出,也造成了目前土地科学学科定位和发展的困惑与困难。这种情况如果继续长期发展下去,非常不利于土地科学学科的发展完善。
3.1土地科学不是研究土地某个单一特性的学科,也不是研究直接提高土地生产力的学科,而是研究实现“人、地、权”关系系统最优化的学科
已有研究指出,土地科学通过独特的“人、地、权”三位一体的研究视角,研究协调人地关系及其之上的人与人开展土地利用活动的关系[28]。人类早期与土地的关系起于土地利用活动[2],由此引出了有关土地利用的两个方向上的“知识”,第一个方向是有关“怎么具体利用土地”的“知识”,第二个方向是有关“怎么保障开展具体利用土地”的“知识”。土地科学学科属于后者,即“怎么保障开展具体利用土地”的“知识”,这就决定了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的特殊性。
第一个方向是最容易想到和理解的“知识”,即有关人类如何在“土地”上开展具体土地利用活动的“知识”,比如如何在土地上种粮食、如何在土地上放牧、如何在土地上盖房建城、如何在土地上采矿和冶炼等等。这类知识都是将土地当作具体土地利用活动中的“基本材料”即“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的前提下,主要研究人类如何在“土地”上或者借助“土地”来开展具体土地利用活动从而直接改善生存条件和提高生产力的“知识”。所以很容易发现,它们基本上都是有关土地怎么“用和建”的“知识”。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发展,最终演进成为现在那些有关主要以直接提高土地生产力为主的科学,比如有关提高农林业土地生产能力的农学、林学等,比如有关提高工业土地生产能力的建筑工程、道路交通工程、采矿工程等,比如有关提高生活用地生产能力的房地产开发、生态修复、湿地保护等,它们基本上都是通过对土地实施工程和技术等手段来实现服务人类生存和发展目标的。这类有关“土地(系统)”的知识和学问主要是通过作用于土地的方式来直接提高人类利用土地的程度和质量,因此其作用较为直接和明显,受人类的关注程度较高,发展速度较快。
第二个方向则是有关“怎么保障开展具体利用土地”的“知识”。它是由第一个方向“怎么具体利用土地”引起的“知识”。由于土地具有数量的有限性、空间的固定性、质量的差异性、利用的排他性、利用方向改变的困难性、土地报酬递减性、利用的社会性等多种自然和社会经济特殊性的存在,使得人类在第一个方向上的有关土地利用的活动逐渐受到上述土地特性的制约,即使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土地也不能再随意地开展土地利用活动了,有关土地的生产关系开始逐渐发展成为制约人类开展具体土地利用活动的限制因素,人类不得不面对土地生产关系的制约,逐渐开始认识和研究解决这些影响开展具体土地利用活动的问题,最先形成了有关土地权籍的理论和制度——地籍,并在其基础上逐渐积累起有关如何保障人类能够开展具体土地利用活动的“知识”,比如针对土地数量短缺、质量差别,逐渐形成了兼顾数量和质量的土地配置(份地)的分配方法;比如针对由于土地质量差异引起的生产力不同形成的物质产品数量和质量的差异,逐渐形成了地租理论;比如由于土地空间位置的固定性和宜用性的差别,逐渐形成了土地适宜性评价和土地规划布局的理论和技术;比如针对土地数量和质量的差异、土地利用的排他性和社会影响性等因素,逐渐发展完善了土地权籍理论和制度;比如针对土地数量和质量的差异、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土地宜用性等因素,逐渐形成了土地开发、改良、复垦等改善土地立地条件的工程技术手段和方法等。这些“知识”都体现出基于土地权籍理论的基础上,减少或减弱有关土地特性形成制约人类开展土地利用活动的影响,为第一方向的具体土地利用活动提供改善土地利用条件、保障土地利用效益和维护土地利用秩序的特征,即使采用工程技术等其他手段和方法,其出发点、目标和结果也都是以达到更有利于开展第一方向的具体土地利用活动为目的的,而不是直接开展第一方向的具体的土地利用活动。它与第一方向的有关“土地(系统)”“知识”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主要服务于如何提供更高质量的可利用土地、更合理的配置可利用的土地、更有效的调整土地生产关系,从而能够有利于更大程度的提高土地生产力。很显然,现代土地科学学科就是这里所讨论的第二种有关“土地(系统)”的“知识”的积累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土地(系统)”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其研究重点是基于土地权籍基础上,通过对“土地(系统)”采用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多种手段,改善和协调人地关系及其之上的人与人开展土地利用活动的关系,消除或减少土地特性形成的制约人类开展土地利用活动的因素,保障人类有序有效开展直接提高土地生产力的土地利用活动,而有关“土地”的形成、机理等方面的自然属性虽然也是土地科学学科研究的内容,但都不是土地科学学科的研究重点。这是土地科学学科与研究其他具体开展土地利用活动的相关学科的根本区别,而它在土地权籍基础上能够采用包括工程技术在内的多种手段来实现调整土地关系的特征又使它明显区别于从其他角度研究调整人地关系的学科,这才是从最初的地籍经过数千年的科学发展和演进仍然不能被淹没反而发展成为现代土地科学学科的根本原因。
很显然,这些决定了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一定是具有可协调人地关系及其之上的人与人开展土地利用活动关系的土地系统。
3.2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以土地权籍为核心和基础
调整人地关系及其之上的人与人开展土地利用活动的关系,是土地科学学科的核心内容和显著特征,是与其他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最明显的区别[29]。而调整人地关系及其之上的人与人开展土地利用活动的关系,依赖于以土地权籍理论为核心和基础构成的土地科学学科理论体系和方法[30],它们共同规定了人类利用土地的秩序、程度、空间范围、处置、收益等所有利用土地的方法和权力及权利,从而规范了有关人与土地的关系,进而又规范了人与人开展土地利用活动的关系,使得人类利用土地的活动变得有序与有效、人类利用土地的程度变得可控与有利于代际平衡、人与人开展土地利用活动的关系变得有序与合理。由此可以看出,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是一个以土地权籍为核心和基础的人地关系及其之上人与人开展土地利用活动关系的系统。这就决定了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具有了第一个重要特征,即它是以土地权籍理论为核心和基础的“土地(系统)”。
3.3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具有权籍可及性
以土地权籍理论为核心和基础构成的土地科学学科体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知识体系,也是研究和协调人类开展土地利用活动引起的人与地的关系及其之上的人与人开展土地利用活动关系的专用理论体系,没有土地权籍理论就难以研究清楚和合理调整人与地及其之上的人与人开展土地利用活动的关系。换一种说法就是,如果没有可以设置土地权籍的“土地”,也就失去了研究和协调其上的人地关系及其之上的人与人开展土地利用活动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这样的场域中土地科学学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前提。这就决定了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具有了第二个重要特征,即能在其上设立土地权籍的条件。
3.4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具有人力可达性
土地科学学科主要研究的是人与地的关系及其之上的人与人开展土地利用活动的关系,很显然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的核心是人及人可利用的土地,人或者是已经存在于那一“土地”上,或者即将可以存在于那一“土地”上,如果在目前人力暂不能达到的“土地”,也就意味着不能在其上设置土地权籍,而没有土地权籍的“土地”,土地科学学科也也就失去了根基。
这又决定了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土地(系统)”具有了第三个重要特征,即人力可达性。
3.5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具有土地所有的一般属性
由于土地科学学科研究人与地的关系及其之上的人与人开展土地利用活动的关系,因此有关人类开展土地利用活动对象的土地,其各种特有的属性都会影响人类开展土地利用的活动,研究利用土地各种属性和消除各种影响人类开展土地利用活动的因素,为人类开展直接提高土地生产力的第一方向的土地利用活动提供良好的土地利用条件,是土地科学学科的核心任务,因此,这又决定了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土地(系统)”的第四个重要特征,即它是一个具有自然性、社会性、经济性、技术性等所有一般属性的“土地(系统)”。
4 结语
综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土地科学学科的视角是基于以人为核心和主导的调整人与土地关系及其之上的人与人开展土地利用活动关系的视角,这一视角下的“土地(系统)”具有如下的特征:①以土地权籍理论为核心和基础;②具有权籍可及性、人力可达性和土地所有的一般属性。
(2)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概念可以定义为:它是一个人类可以设置并行使土地权籍的地球陆地表层(包含内陆水域、海岛和沿海滩涂)的时空系统。简单说,它是一个有关“人、地、权”关系的“人地关系权籍时空系统”。在这一“人地关系权籍时空系统”中,人们通过制定并遵循“秩序”(土地权籍),寻找并利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的各种“方法”,协调和规范人与土地及其之上的人与人开展土地利用活动的“关系”(调整土地生产关系),从而追求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土地生产力)。由此,可以推出:土地科学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地球表层土地人地关系权籍时空系统中出现的一切土地现象。
(3)本文提出的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概念定义,充分体现了土地科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和内涵,形成了土地科学学科的特殊“土地(系统)”概念,更重要的是这一“土地(系统)”反映了人类开展土地利用活动不可或缺的视角,构成了土地科学学科发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4)本文提出的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的“土地(系统)”概念定义,既是自然属性的“土地(系统)”,也是社会属性、经济属性、法律属性和技术属性的“土地(系统)”;既包括土地生产力的问题,也包括土地生产关系和土地权籍制度的问题。但是,土地科学学科并不是单一研究这一系统中的某一个方面的“知识体系”,而是研究这一系统间各因素的关系最优化的“知识体系”。研究这样的一个“人地关系权籍时空系统”,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的知识,也需要社会科学的知识,而且还需要技术科学的知识,这又使得土地科学学科成为一门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的复杂的系统交叉学科。但是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土地科学学科本质上是属于调整人地关系及其之上的人与人开展土地利用活动关系的学科,所以无论是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还是技术科学的手段都是为调整这种关系而展开的,本质上还是有关土地利用的第二个方向上的“知识体系”而不是第一个方向上的“知识体系”,即它并不是以土地为“材料”通过施加人类活动而直接提高土地生产力的“知识体系”。这对于认识和把握土地科学学科的独立性至关重要。
(
):
[1]陈中梅. 词源考——兼论西方文化基本结构(BSWC)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上篇)[A] .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2013春夏卷)[C]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241.
[2] 冯广京. 土地科学学科独立性及学科体系研究框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六章.
[3] 同上书:第三章.
[4] 王万茂. 论土地科学学科体系[J] . 中国土地科学,2002,16(5):4 - 9.
[5] 马克伟主编. 土地大辞典[M] . 长春:长春出版社,1991:802.
[6] 林坚,刘文. 土地科学研究对象和学科属性的思考[J] . 中国土地科学,2015,29(4):4 - 17.
[7] 李元主编,马克伟、鹿心社副主编. 中国土地资源[M] .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0:2.
[8] 孙鸿烈、石玉林主编. 中国自然资源丛书·综合卷[M] .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
[9] 蔡运龙,陈彦光,阙维民,等. 地理学:科学地位与社会功能[M] .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2.
[10] 同上书:9.
[11] 同上书:10.
[12][美]伊利,莫尔豪斯.滕维藻,译.土地经济学原理[M]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3.
[13] 同上书:第19页。
[14] [英]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上卷)[M]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57.
[15] 李元主编,马克伟、鹿心社副主编. 中国土地资源[M] .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0:1.
[16] 杨树珍.国土经济学[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2.
[17] 李元主编,马克伟、鹿心社副主编.中国土地资源[M] .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0:1 - 2.
[18] 王万茂主编. 土地利用规划学[M] .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4.
[19] 同上书:5.
[20] 同上书:6.
[21] 毕宝德主编. 土地经济学[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
[22] 梁学庆主编. 土地资源学[M] .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8.
[23] 林增杰主编. 地籍学[M] .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3.
[24] 刘黎明主编,林培主审. 土地资源学[M] .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4:4 - 5.
[25] 张占录、张正峰主编. 土地利用规划[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 - 3.
[26] 李元主编,马克伟、鹿心社副主编. 中国土地资源[M] . 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0:3.
[27] 钱学森. 论地理科学[M] .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96.
[2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98.
[29] 冯广京. 土地科学学科独立性研究——兼论土地科学学科体系研究思路与框架[J] . 中国土地科学,2015,29(1):20 - 33.
[30] 冯广京. 土地科学学科独立性及学科体系研究框架[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三章、第五章.
(本文责编:陈美景)
Discussion on the Definition of Land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Science Discipline
FENG Guang-jing
(China Land Surveying and Planning Institute, Beijing 100035,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lt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extant definition of land does not reflect its discipline's characteristics and to put forward the definition of 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science discipline. The research methods go as follows: Firstly, it collects related literatures about the definition of land from land science domain and relevant disciplines in the context that the definition of land reflecting the discipline's characteristics has not come into being in land science discipline yet. And then it points out the severity of lacking the definition of land reflecting the discipline's characteristics. At last, it comes up with the definition of 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science discipline accordingto land science discipline's substan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extant definition of land in land science discipline mainly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nature science disciplines e.g. geography but it cannot reflect land science discipline's substan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s; 2)without the definition of 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discipline, some vital aspects of land science discipline, i.e. research object, perspective, scope and so on, cannot reflect this discipline's own substan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s, which leads to the difficulty of land science discipline system construction.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1)the definition of 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science discipline has several key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aking land cadaster and property right theory as the core and basis, land cadaster and property right accessibility, human accessibility as well as common attributes of land;2)land is a kind of spatio-temporal system based on earth's land surface that human beings can set up as well as perform land cadastre and property right, referred to as the spatio-temporal system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based on cadastre and property right; 3)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land put forward by this paper, the object of land science discipline is all land phenomenon that occurs in spatio-temporal system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based on cadastre and property right on earth's land surface; 4)the definition of 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science discipline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not only expresses this discipline's substan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s but also reflects the indispensible perspective of land use,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premise and basis of land science discipline's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land science; land; spatio-temporal system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based on cadastre and property right
F301.2
A
1001-8158(2015)12-0001-10
10.11994/zgtdkx.2015.12.001
2015-11-05
2015-11-17
冯广京(1957-),男,山西阳泉人,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政策。E-mail: fenggj@139.com
- 中国土地科学的其它文章
- 《中国土地科学》2015年(第29卷)总目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