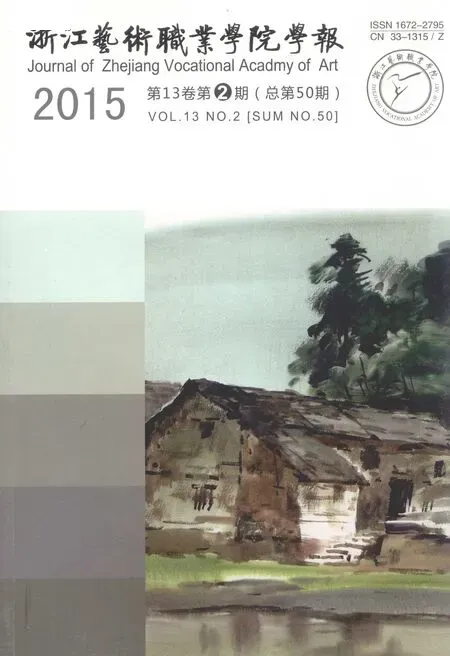深闺有愿作新民——传奇《六月霜》的秋瑾形象与当时女性的文化心态
孟 梅
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六日,即公元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六日),鉴湖女侠秋瑾就义于浙江绍兴轩亭口,终年32 岁。
秋瑾遇难之后,社会各界以各种形式开展追悼活动,仅戏曲,就出现《六月霜》(1907)、《轩亭冤》 (1907)、《轩亭秋》 (1907)、《轩亭血》(1908)、《碧血碑》(1908)等近十部作品。其中,署名为“古越嬴宗季女填词、南徐香雪前身正拍”的《六月霜》传奇,是现知唯一一部女性书写秋瑾的戏曲,也是明清女性戏曲创作中唯一一部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作品。
《六月霜》全剧共十四出,写秋瑾与丈夫志向不同,因出国留学致使夫妻反目。秋瑾东渡归来,在明道学堂任教,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她遭人陷害,含冤入狱,被斩于轩亭口。除了首尾“蓉谪”、“返真”两出之外,《六月霜》按照真实的线索叙述了秋瑾出嫁、离婚、东渡求学、归国任教、含冤被杀、朋友祭奠的过程。据自序云:“属吾乡秋瑾女士之狱起,申江舆论,咸以为冤,几欲万口一词。而吾乡士夫,顾噤若寒蝉。仆窃深以为耻。会坊贾以采摭秋事演为传奇请,仆以同乡同志之感情,固有不能恝然者,重以义务所在,益不容以不文辞。爰竭一星期之力,撰成十四折,匆匆脱稿,即付手民。”[1]作者自称为秋瑾的“同乡同志”,可见亦属与秋瑾志向相同之新女性。剧本正文前又有作者与宛溪双玉诗媛、苏台桂宫仙史、初云女史、乌云女史等六人的题词,虽然真实姓名已不可考,但根据署名,当知皆为女性。大概是出于对秋瑾的性别认同感,《六月霜》在有意无意间成为完全由女性参与的“女性戏曲作品”。作者的性别视角和社会角色决定着她对剧中人物的评价或态度,从《六月霜》传奇对情节撷取、人物塑造、叙事手段等方面的解读,能够透析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晚清进步知识女性的文化心态。
一、流俗旧弊——对时代背景的描摹和批判
秋瑾被杀之后,当时舆论界的共同倾向是为秋瑾“鸣冤”,认为秋瑾是没有证据、口供的情况下被诬以“革命罪”杀害,属于冤狱。秋瑾的义姐吴芝瑛在第一时间撰文力陈秋瑾只是主张“男女平权之革命,而非政治种族之革命”[2]。戏曲作品则以代言体的方式陈述秋瑾之“含冤被屈”: 《轩亭冤》①《轩亭冤》全名《中华第一女杰轩亭冤》,署名萧山湘灵子。成稿时间为丁未年(即1907年)农历九月九日。见阿英辑《晚晴文学丛抄·传奇杂剧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七出《喋血》中秋瑾反复申明自己并非革命党:“(旦)哎呀!你你你这糊涂东西,竟把侬认作革命党了!兀的不痛杀人也!”“(哭介)糊涂糊涂,你这个糊涂狗官,竟把我认作革命党了。苍天呀!苍天呀!我秋瑾今日死得好不瞑目也。!”《六月霜》第八出《鸣剑》中,叙述秋瑾游学归来,义姐吴芝瑛见秋瑾所配倭刀,有些忧虑:“得不惧鸡鸣偷度,错疑君是革命的女孩儿。”秋瑾“笑白”:“男女革命与政治革命宗旨则一,办法各异,姊故知吾非新少年之侈谈革命者流也。”。在第十二出《对簿》中,又由秋瑾之口说出她和徐锡麟只是“数载前在海上曾经一面,近年来并书札亦绝往还。”当被问及“你不是主张革命的吗?”秋瑾回答:“余所主者,男女平权之革命,而非政治种族之革命。”这种种对秋瑾“革命党”身份的辩解,皆以吴芝瑛《秋女士遗事》为底本,虽然被后人批评作“对秋瑾的曲解”,然考虑到当时清廷对革命者的严酷镇压,吴芝瑛意在“以身家性命保秋氏家族,望当道负立宪之责任者,开一面之网,饬属保全无辜”。出于保护秋瑾家人的目的,自然不能大张旗鼓地张扬秋瑾的“革命事迹”,只能通过塑造一个蒙冤的秋瑾来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唤起民众对清政府的愤怒。
可贵的是,《六月霜》在为秋瑾“鸣冤”的同时,以秋瑾的人生经历与“蒙冤”过程为线索,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秋瑾的丈夫作为京官,每天想的是“但愿主恩偏,一日九迁福章换。”在秋瑾苦劝他为国出力之时,他振振有词:
夫人言之虽也有理,但是家国的兴衰,民族的消长,大抵皆是天运使然,非人力所能强挽。况朝廷大事,自有当局者主之。你看那一般儿天潢的、贵胄的、当朝的、元老的,尚都得过且过,燕雀处堂。何况区区一个卑官末秩。委实平生志不及此,敬谢不敏。
京官如此,下面的绍兴知府和会稽县令更是以投机为业,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时而花面逢迎,时而翻脸无情。作者通过徐锡麟刺杀恩铭案后“查抄徐党”为线索,塑造出陷害秋瑾的“群丑图”:先是丑扮乡绅上台,自述为求提拔,曾经“狗颠屁股筛介”去巴结徐锡麟,而在官府要“清查徐党”之时,为了洗脱自己,“想得一个脱身之计,移灾害人,只有倒咬介秋竞雄一口,就说俚(她)是徐党,要想搭介阿徐同谋造反”。而绍兴知府则自我介绍:
咱们本是内务府的一个包衣出身,何尝知道什么新名词,何尝知道什么种族界。满人现做皇帝,我固不妨杀人媚之,万一汉人掌了大权,我也何妨反颜事之。……其实区区方寸之地,只有升官发财的四个大字而已。
为了升官发财,他们派人“以手枪纳旦手及怀中,旦撑拒不受,众强置旦足下”,极尽栽赃陷害之能事,并说“杀一秋瑾,何足为奇!”、“借她颈血斑斓,染得我顶儿红矣”。通过对群丑的刻画,深刻揭露出晚清官员的残忍贪婪,在这样的官衙内,秋瑾的冤狱成为一种必然,也成为具有代表性的象征:秋瑾之狱案如此,可见芸芸民众受屈多矣!
作者不仅对官府的腐朽做了揭露和批判,又通过秋瑾东渡求学在船上的见闻,刻画了那些只想捞取政治资本的留洋学生嘴脸:
(生白)我是官费到东的留学生,这一趟儿,元是怀挟着金钱主义和功名思想来的,拼着稍微吃一两年的苦,将来还要做大官,娶西妇,前程万里不可限量。今日虽然是客边暂时在船上,倒也不可妄自菲薄,被外人看轻了。好在有的是同胞汗血的钱,替我代惠,又何妨慷他人之慨呢?我要做头等的舱。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一方面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逐渐由封建社会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西方文化思潮的引进使传统观念包括“男女内外有别”观念受到严重冲击,许多女性开始放眼看世界,走出闺阁创作“闺思、伤时、咏物、写景”的窠臼,有意识地将个人命运的荣辱置于国家和社会大环境中考虑,作者借秋瑾之口叹息:“看着那一桩桩恼人的邻国事,又加上这一般般羞人的留学弊……可地将心愁碎。”反映出晚清知识女性已然感受到大厦将倾的民族危机,希望能尽一己之力,呼吁民众觉醒,建构一个崭新世界。与秋瑾和古越嬴宗季女同时代的女作家吕碧城有诗云:“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有愿作新民”,可以为这一时代女性的文化心态作一注解。
二、侠骨柔情——对秋瑾的形象塑造
可以说,在那个思想与社会同样激烈动荡的年代,秋瑾是以实际行动打破自己与“旧时代”的联系、完成从形象到内心的自我重构的。秋瑾的放足、练习击剑、体操、骑马、参与演讲等行为,都对塑造晚清新女性形象起到了率先垂范作用。文艺作品中对秋瑾的塑造从她去世到现在,从未间断过。塑造一个什么形象的秋瑾,恰可与创作者个体和所处时代相互影响、彼此参照。
“雄姿豪骨,气搏风云”(《轩亭冤》),是秋瑾形象的主要基调。然而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伸冤”的目的,大多数戏曲作家还是力求通过展现秋瑾的“女性气质”,激起观众对秋瑾的同情,从而引发对冤案制造者的愤恨:啸庐的《轩亭血》第一出即为秋瑾带着两个孩子游园赏花的场景,首先呈现秋瑾“良母”的温柔形象[3];萧山湘灵子的《轩亭冤》则在秋瑾被捕时反复以“旦一路哭介”、“伏地泣介”,试图表现秋瑾的“女性柔弱”,引发观众的怜惜;而《六月霜》则在以“负笈”、“试剑”、“凤仪”等折展现秋瑾“欲挽中衰”的豪气的同时,以秋瑾的夫妻“情感”为切入点,描写秋瑾的“柔情”。
《六月霜》十四出的戏中,有《梅嫁》、《恤纬》、《典钗》、《雀飞》四出是全力描写秋瑾与丈夫关系问题的。并在传奇之始的《前提》中有《沁园春》一阕:
秋雨秋风,南望仄身。有怀故都,痛离魂倩女,冤同精卫,浮云夫婿,忍甚秋胡。彩凤随鸦,明珠弹雀,乐府凄凉咏采芜,偶才妇教飘零至死,薄幸知乎?
定场诗则写到:“芙蓉城谪仙降尘世,苧萝村越女破天荒。天壤郎随鸦惜彩凤,人间世打鸭惊鸳鸯。”可以看出,作者对秋瑾的家庭、婚姻和个人情感的关注。
《六月霜》中的秋瑾最初对丈夫充满期许和温情,希望夫妻同心,自己宁愿做孟光和桓少君那样的“贤妻”:“女子宜家所同愿,便侬也有情未免,宁不愿风肆好月长员(圆),乐融融悱恻缠绵,堪媲美孟和桓。”。她在劝告丈夫积极进取为国出力时,说“莫怪妾忠言进谏,既做个男儿当自贤,断不该贪苟安。博得个万千秋留名汗简,便是妾也与有荣焉。”这番言论,虽然表现出秋瑾的报国志气,却也流露出“夫荣妻贵”的传统观念。一番肺腑劝谏之言,换得丈夫恶言相向,并告诫秋瑾“卿若要我和卿琴瑟两相调,须索把此怀全遣。”然后“拂衣竟下”,秋瑾也只是“掩泪下”,哀叹丈夫不理解自己的苦心:“怎拒我比肩人药石良言。”当丫鬟劝告秋瑾:“只恐俺爷怪伊雌伏雄飞。”秋瑾赶忙说:“非是咱英雌忽有雄飞志,道的咱似醉如痴,只为他丈夫身却少男儿气,以故将言相劝伊……”与《轩亭冤》中秋瑾坦然宣称:“侬家不甘雌伏,漫想雄飞”截然不同,《六月霜》中的秋瑾一再声明:“非是咱英雌忽有雄飞志”,无疑这是作者从个人体验出发,对秋瑾婚姻生活的摩想与假设。
秋瑾遵从父母之命出嫁,出嫁后发现自己所遇非偶,时常对家人感叹:“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4]“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5]然而即使如此,秋瑾依然在王家度过七八年,生下一儿一女,这不能不说明秋瑾也一度对现状是无奈而屈从的,古越嬴宗季女作为秋瑾的“同乡同志”,对当时女性的家国观念、社会地位当有深刻的了解,剧中出现的秋瑾柔情劝夫、暗地洒泪、到最终无奈离开家庭,虽不一定是秋瑾的真实生活,也必然是众多女性由闺阁走向社会过程中的必然经历,这些情节设置让观众意识到晚清新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传统与革命之间一度徘徊无措的现实心态。
但是《六月霜》中秋瑾在离婚之后,依旧说:“谢君家留别词,是自家人何须客气,总是妾不贤,敢愿君弃遗……” “裙钗琐琐亦何奇?君是大丈夫,不患无妻,祝新人胜故,清娱得意交替,妾从此蘼芜罢采,君尽把素缣互比。明知道旧恩已断,临别尚依依。”便有刻意逢迎旧传统之嫌了。剧作呈现给大家的竟然是一个逆来顺受的秋瑾:“前日因商议游学日本一事,和相公争执了数言,此事若在男女平权文明之国,妇人有志求学,思助藳砧,为夫婿者,方且求之不得。就是意见偶左,也尽可含容,不意他盛怒难回,竟写离书,促吾归去,这也是无可如何之事。”语气的无奈、离开时的留恋和祝福,使《六月霜》中的秋瑾成为一个“弃妇”的形象。“蘼芜罢采”、“素缣互比”的典故出自汉乐府《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 “新人从门入,旧人从阁去。” “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6]
作者把这个典故借秋瑾之口说出,传递的思想和情绪都是与现实不符的。秋瑾的离异是她先行离家,后提出与王子芳断绝关系的,并不是如《六月霜》所言,其夫首先提出“休妻”。并且从留下的信件诗文中可以看出,秋瑾在离异问题上表现得十分坚决:“无使此无天良之人,再出现于妹之名姓间方快。如后有人问及妹之夫婿,但答之死可也。”[5]“妹近儿女诸情,俱无牵挂,所经意者,身后万世名耳,不则宁湮没无闻,断不欲此无信义者有污英雄独立之精神耳。”[7]可见,“明知道旧恩已断,临别尚依依”这样多情的话语是绝不会从秋瑾口中说出的。作者这样写无疑是想塑造秋瑾的“温柔贤良”、集传统美德与进步意识为一身的审美形象,使她更符合传统女性的审美特征,从而能够引起读者的更大同情,增强后来含冤被杀的悲剧性效果。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在为女性立言、在呼吁“男女平权”的同时,却不自觉地依然运用传统文化的男性话语完成对秋瑾形象的建构。
三、神仙谪世——传统叙事方式的承袭与创新
出于对良善忠勇之士的哀悼与祝福,中国传统的小说、戏曲中经常赋予主人公“神仙”的身份——或忠义之士成仙得道,或神仙下凡为忠义之士,其中尤以神仙贬谪为了断前世因果的故事为多见,如岳飞与秦桧、西施与范蠡、水浒传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临世……这种叙事皆是有所寄托,给悲剧故事赋予美好的神话色彩。
《六月霜》的作者也承袭了这一传统叙事方式。戏曲一开场,秋瑾便以“手执芙蓉花”的仙子形象出现,她眼见“今五洲风紧,四海尘飞,小仙以是因缘,常滋感愤,生成傲骨,特标不二法门,发愿舍身普度大千世界,不辞下辄,欲挽中衰。”遂毅然与灵芝仙子、菊花仙子相约下凡,欲以“纤纤素手,志扶半壁之河山;磊磊丹心,誓洗六朝之金粉。”及至含冤被杀,作者特意详细交待秋瑾脱离凡尘回归仙界:“场上放烟火,旦换仙装,手执白芙蓉花一枝,扮芙蓉仙子上。”不得不承认,这种谪仙叙事方式使读者(观众)马上从秋瑾被杀的悲剧情感中脱离出来,冲淡了原事件的悲壮惨烈,然而由于叙事主体的文化背景和革命意识的影响,使《六月霜》的“谪仙”叙事蕴涵了鲜明的时代精神。
同样将秋瑾塑造为“仙”的戏曲还有啸庐的《轩亭血》传奇:在“楔子”中,秋瑾以“拂尘仙装”的形象开场,自述被杀之后,“啸俦命侣,更多海外英流”,遂邀请西施、费宫娥、罗兰夫人等中外女性英魂去观看“秋瑾戏”。也就是说, 《轩亭血》中的秋瑾是去世之后英灵不灭,并未指明她“已经升仙”或者是“神仙下凡”,从剧场设置来看,“仙装秋”瑾起到的是“副末开场”的作用,由她介绍前因后果,点出《轩亭血》的作者及家门大意,戏曲才正式开始。而《六月霜》中秋瑾的“芙蓉仙子”身份是凸显秋瑾以家国为己任的重要素材。秋瑾是自愿下凡的,和传统叙事中的“谪仙”故事不同,她并不是因为“触犯天条”被贬下人间以示惩罚,也不是“宿有旧缘,致令增此一番孽案”[8]。她完全可以守在和平安静的天界,不问人间事务,然而她却“懒做白日升天的谢自然,却愿作青史留名的曹大家。”剧中的“芙蓉仙子”没有神仙谱系中的等级制度管辖,决定和她同行的灵芝仙子(吴芝瑛)和菊花仙子 (梁爱菊)也只是因为和芙蓉仙子志向相投,她们下凡不用经过“请示和批准”,也不受前世因果的制约,这是“谪仙”叙事与女性意识相结合的结果,既反映出女性投身社会洪流的自觉主动,又是当时女性冲破枷锁追求自由意志的体现;
其次,神仙道化的叙事方式一般是用宗教来消解现实中的无奈,主人公升仙之后,大多表现为对尘世种种的“幡然悔悟”,从此一笑斩断情缘,专心清修。作于1908年的《碧血碑》杂剧是写秋瑾去世之后,她的好友吴紫英 (当为吴芝瑛化名)在墓前哀悼,并应女尼要求,将秋瑾的遗照供到佛堂,“朝夕供养”,并说“待小阁花磬响,再把那妙金经日诵两三行。细自想,代他好忏悔些生前魔障,我端整真诚一片礼空王。”便是试图用宗教的“清净、忏悔”化解秋瑾殒身的惨烈。而《六月霜》中的秋瑾返回“仙界”,依然关注尘世间的事: “便脱胎换骨、成佛生天,难解眉间皱。”她追忆往事,叹息婚姻失败的叹息,想念年幼的儿女,对国家民族更是萦系在心:“愿则愿,中华政党无新旧,日夜馨香悼祀求,俺一片痴心尚未休!”可以说,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升仙之人”,她没有“忘情”,生前未了之事完全被她带入“仙界”。换言之,作者清楚地知道秋瑾未竟之事业并不能随着她的成仙而了断, “升仙”并不是圆满的结局。她借“返真”之后的秋瑾之口呼吁女性觉醒,继承“振兴女界”、“力挽中衰”的先烈事业。
综上所述,《六月霜》在对秋瑾事件进行书写的同时,也融入了作者的主观艺术创造,作为晚清新女性的生活体验、人生经历和家国观念等渗透于剧本之中,建构了一个处于新与旧、闺阁与社会、革命与保守交替冲击下的“秋瑾形象”。虽然作品借秋瑾之口大力倡导男女平权、女性自强的思想,也通过秋瑾的见闻经历对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做了深刻的揭露,但在情节安排和语言上依然不自觉地流露出或浓或淡的男权思想,在秋瑾形象塑造上依然有意识地迎合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审美期待,这与现代女性文学创作还有明显的距离。但《六月霜》毕竟是中国女性戏剧史上第一部以重大历史题材为背景、反映女性觉醒的剧作。作品中既有传统女性的心理折射,又有初步觉醒的近代女性的精神特质,正可以视为古代女性创作向现代文学的过渡和发展。
[1]古越赢宗季女. 六月霜[M]. 上海改良小说会光绪三十三年刊行本.
[2]吴芝瑛. 秋女士遗事[M]. 六月霜:附录. 上海改良小说会光绪三十三年刊行本.
[3]啸庐. 轩亭血传奇[J]. 小说林,1908 (12).
[4]秋瑾. 谢道韫[M]. 秋瑾. 秋瑾集. 北京:中华书局,1960:72.
[5]秋瑾. 致秋誉章书其二[M]. 秋瑾. 秋瑾集. 北京:中华书局,1960:34.
[6]郭茂倩. 乐府诗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3:32.
[7]秋瑾. 致秋誉章书其三[M]. 秋瑾. 秋瑾集. 北京:中华书局,1960:37.
[8]方成培. 雷峰塔传奇[M]傅惜华. 白蛇传集.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