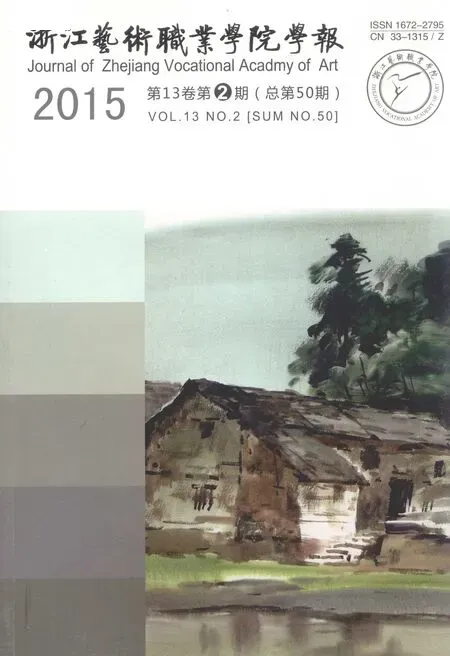歆舞界舞蹈的精神内涵——以《双城》为例
张 星 苏仲霓
一、歆舞界发展概况
2009年初,史晶歆女士创建了歆舞界—艺术实验室(XIN-ART-LAB),该实验室致力于中国当代舞蹈与多媒介融合的探索。史女士12 岁进入上海市舞蹈学校,毕业后考取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继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习,并留校任教至今。早年,史女士曾游历新加坡、美国、比利时、巴黎、泰国、柏林、尼泊尔、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英国、荷兰等诸多国家,受到编舞家陈维亚和邓一江的教导,并在法国编舞家苏珊·伯居(Susan Buirge)和美国先锋戏剧大师理查·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的门下研习,博采世界大师的真传。2007年,史女士被亚欧基金会(Asia Europe Foundation)点名入选“点对点” (Pointe to Point)第五届亚欧舞蹈论坛,在中国舞蹈家协会的资助下,积极地投身于舞蹈创作,并广泛进行国际交流;2008年成为了第29 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导演组最年轻的导演;2010年和2011年先后获得“国家艺术类人才培养特别项目”和北京舞蹈学院的资助,并受邀参加美国舞蹈节- 国际编舞项目(American Dance Festival:International Choreographer Residency)的创作与交流。史女士是一位多产的舞蹈编导,创作作品有: 《圆明园》 《面具的世界》《空城》《NOTHING IS REAL》 《水墨游》 《BOW》《夜愿》《身体博物馆之人类动物园》《记忆-时间-碎片》《活着就好》 《霞谐帛瓦:觉、白、梵三部曲》《日子》等多部作品。除却在实践方面的耕耘,史女士也涉足舞蹈研究领域:出版艺术散文《身体笔记》,在《中国艺术报》(舞蹈专刊)上发表特约专栏《纽约访学记》,与《舞蹈研究》合作专栏《歆舞界—欲说舞言》等。
歆舞界—艺术实验室是一个勇于求新和求异的团队,歆舞界的作品绝不是简单的舞蹈动作的叠加,而是致力于为观众带来多元化的享受。主要元素——舞蹈动作变成了一个链接工具,它把实验音乐、环境空间、戏剧表演、声音文本、纪实影像、舞台装置等不同的媒介融合在一起,正顺应了当下中国当代舞的发展趋势——随类赋彩,变化多端。2014年,歆舞界致力于“身体建筑师”训练方法的研发与建材录制,开设了初级、中级两个班,这不仅是一门舞蹈类的教学课,更是一种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鼓励人们塑造自己的身体,帮助舞者和生活对话,与生命共舞。作为中国当代舞蹈的一支主力军,歆舞界以其新颖的表现方式和独特的舞台效果吸引着一大批舞蹈从业者和业余爱好者,在业内外的影响广阔而深厚。然而,道具和服装,舞步和舞姿,内容与形式,这些都只是歆舞界作品的表象符号,若是基于这些基础的元素来欣赏歆舞界的作品,并不会理解其中的真谛。舞蹈语言作为史女士创作的手段,作为她与观众沟通的媒介,帮助她在头脑中积淀着强大的精神力量,舞蹈剧场承载着这些天马行空的创意,然后整合它们,并把思考的种子赋予每个走进剧场中的观众,使他们徜徉在编导、演员,以及自我的精神世界中。毫不夸张地说,史女士是用舞蹈的方式在思考。
二、新颖的创编模式
2015年,歆舞界—艺术实验室五岁了, 《双城》——歆舞界的经典之作上演于中华世纪坛小剧场,精神之旅永不停歇。北京舞蹈学院青年教师、歆舞界艺术总监史晶歆和歆舞界的舞蹈家、艺术家们再次和观众相聚一堂,呈现舞蹈剧场力作。精湛的表演,细腻的台风,深刻的内涵,无尽的联想,庞大的信息量,这些都使得《双城》在中国舞蹈界独树一帜。歆舞界的舞蹈作品对当今的中国舞坛影响颇深,其作为一种新颖的舞蹈现象,不仅推动了舞蹈语言的开发和创造,丰富了舞蹈作品的呈现方式,加深了舞蹈作品的内涵意蕴,为无数先锋、新锐的编导示范出一条崭新的创作之路,更用优秀的作品证明着舞蹈的无限可能——开发身体、重塑心灵。
熟悉歆舞界的人都知道,演后谈环节是歆舞界的传统,而演出前对演员的介绍却并不是每场演出都能有幸看到。在《双城》开始前,中华世纪坛小剧场的白色投影布上播放了歆舞界的简介、《双城》的简介以及演员对作品的感悟,图像和文字把观众的心拉向平静,找到沉心思考的方向。《圆明园》和《活着就好》两个部分组成了《双城》这部作品,分别讲述史女士对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的感悟。史女士早年曾在新加坡艺术展演中观看过实验室作品,感动之余为之吸引,对实验室作品的思考使她以两座城市为主题展开创作。2009年,《圆明园》诞生了,随即展演于北京现代舞周、广州现代舞周;而《活着就好》则创作于2011年,史女士受到新加坡艺穗节的邀请,委约创作舞蹈剧场作品《活着就好》,并得到美国先锋戏剧大师、纽约大学终身教授查理·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的指点。《双城》把《圆明园》和《活着就好》整合起来,两座城市,两种风格,两种文化,两个时空,信息量极大。在第一部分《圆明园》中,演员的服装是亮点之一,女演员身披宽松的白色布袋,宛如圆明园中价值连城的玉器,又似废墟中破土而出的重生的灵魂;男演员上半身赤裸,下半身围裹一匹金色和古铜色相间的棉布,硬朗的配色透出浓郁的力量感,象征着阴暗、强大的西方列强。《圆明园》的情节以火烧圆明园的历史为基础,史女士把火烧圆明园事件用肢体语言还原出来,在假想中进行回忆,随着演员的舞动,时间倒退,历史重演,破败残缺的历史惨象震撼着观众。舞台左前方的一抹灯光之下,作曲家李铁桥现场伴奏,随着身体与音乐的不断碰撞,追忆出北京城的历史之殇。
史女士赴纽约访学回国后创作了《活着就好》,即歆舞界—艺术实验室“城市”系列的第二个作品,上海成为了主角。讲述了一个城市与个人、奶奶与孙女、青春与迟暮的故事,体现了隔代人之间的观念冲突与情感变化,城市的建设和时间的流逝都不会停止,人们在城市中思索和感悟,了解他人也反观自己,最终找到人生的真谛。以城市为主题是《双城》的创新点,也是其区别于其他舞蹈作品的特征所在,这里的“创新”就是指艺术的“个性”。“这种‘个性’的产生来源于舞蹈编导个体生命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在创作中必然呈现舞蹈形象的个性色彩,正是这种个性色彩,使舞蹈形象具有了更为强烈的个性魅力。”[1]每个人都有关于城市的独特记忆,每个人都能够被舞蹈激发出思考的欲望,被自己的思维所笼罩,这正是《双城》要为观众带来的精神世界。
三、独特的表达方式
走进剧场,就走进了史晶歆女士的意象世界。朱光潜先生曾说:“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在舞蹈中,美感无处不在,意象也无处不在。意象是一种思维空间中的加工形象,是主体对客体传递的表象信息消化、整理、加工后形成的记忆痕迹,这个记忆痕迹既是舞蹈家的灵感摇篮,又是欣赏者的想象源泉。这些意象被编导用肢体语言重塑,变得或抽象或夸张,“象征能力,实际上是一种初级抽象能力。从诸多生活原材料演化为某种抽象图案的情形来看,不管其高级还是初级,抽象过程中都含有夸张、变形等因素。”[2]《活着就好》的故事情节比较复杂,但演员在交代情节时非但没有显得捉襟见肘,反而把故事讲得清楚明了,把叙事的任务交给了无数的碎片化细节,细节不仅仅包含舞蹈演员的肢体动作,其中一大部分是剧场内的其他物件、声音、光线等等,比如红色短裤、电视机、扩音喇叭、凳子、老式电视、灰尘、光束、黑板、图画、演员的朗读、旁白、洗脚盆、抹布、扫把、传单等等。这些细节源自生活,但又不是以生活原型呈现于舞台,而是经编导之手的解构和重构,饱含着编导对它们的理解,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如果道具是静态的、实体的碎片化细节,那么声音和光线就是动态的、虚幻的碎片化细节,动静结合,虚实相生,每一个细节都代表着一个或多个意象,这些意象充斥着观众的头脑,引领观众走出程式化的叙事手法,在碎片化细节的带动下进入舞蹈、感受舞蹈、思考舞蹈。“舞蹈创作的根本就是要善于运用舞蹈语言,辩证地结合虚拟空间与实境空间,运用虚实相生的原则,营造特有的舞蹈空间,引领观众进入到想象的世界,从而完成由生活形象到舞蹈意向、由心理空间到心理效应的遨游旅程。”[3]对于一个舞蹈编导来说,意象是其所追求的,却也是很难把握的,史女士炉火纯青的手法值得称赞,她把对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回忆通过意象的形式保存在头脑中,通过意象到碎片、碎片到舞蹈、舞蹈又到意象的方式传输给观众,其实这种方式是大多数编导在编舞时的目标,但有新意地达到这种目的则很难,史女士以意象为工具,不仅抓住了观众的眼睛,更抓住了观众的心。这种编舞方式增强了歆舞界作品的延展性,舞蹈不再单纯地只表达编导的个人意志,也可以扩大观众的思维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个走进剧场的观众的个人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对舞蹈的感知直观且具体,丰富且深刻,从走进剧场的那一刻开始,意象就像一根无形的绳子牵引着观众的思绪,促使着观众不断进行思考。
走进剧场,就走进了史晶歆女士的生命世界。很少会有艺术家像史女士一般如此炽热地爱着舞蹈,她不求回报,不断探索、追寻、攀登和超越,很难想象她娇小的身躯下竟有着如此庞大的力量,是她的坚韧、执着和无私成就了歆舞界的今天。舞蹈对于史女士来说,已超越了谋生技能这一层面,而变成了生命必需品,在史女士的舞蹈世界中,肢体运动有情感、有思维、也有记忆,可以诞生和消亡,也可以沉闷和生机勃勃。因此,欣赏史女士的作品就仿佛徜徉在她充满激情和力量的生命历程中,时而赞叹,时而反观自己。仍然以《双城》为例,第一部分《圆明园》略带晦涩,抽象难懂,史女士并非要把圆明园被烧毁的历史事件详尽地描述清楚,而是要借发生在北京这座城市的故事来呈现强与弱的对比。男舞者表面上看是西方列强,实际是现实生活中的强敌、挫折和诱惑、人们心灵深处的躁动、绝望和迷茫;女舞者表面上看是圆明园中的瓷器,实际是现实生活中的祥和、美好和安宁、人们心灵深处的平和、希望和笃定。第二部分《活着就好》的结尾处,经历一世沧桑的“奶奶”和心智成熟后“孙女”分别站在舞台的两侧,旋转,静止,相望,伸出双手渴望着拥抱对方,却始终无法触及,在不断地重复之后幸福相拥。此处对结尾的处理点明了舞蹈的主题——纵使生命中充斥着不幸和无奈,但只要永葆一颗乐观的心,就总会迎来幸福的一天。正如史女士在演后谈环节中说的那样:“奶奶给了我一件最珍贵的礼物——希望。”这种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带给观众独特的审美体验。
欣赏歆舞界的过程,是踏入一段充满奇遇、反思和遐想的精神之旅的过程。史晶歆女士带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欣赏肢体语言时的满足感,而是以舞蹈为对话的媒介,与观众共享记忆、一同思考。“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总是要寻求最适合表现自己的艺术手段,而一个历史阶段审美崇尚的变化则主要在于顺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符合当时审美艺术发展的特点,所谓‘变者时也’,势也。”[4]期待着史女士能永葆对当代艺术的热忱和理想,让这份强烈的、灿烂的追求继续走下去,更期待着歆舞界—艺术实验室能够在当代艺术的洪流中蓬勃发展,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1]周宏. 论舞蹈创作的审美个性[J]. 延边大学大学学报,2014 (1).
[2]吕艺生. 舞蹈美学[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9.
[3]周宏. 论舞蹈的空间营造[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3).
[4]金浩. 新世纪中国舞蹈文化的流变[M]. 上海:上海音乐,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