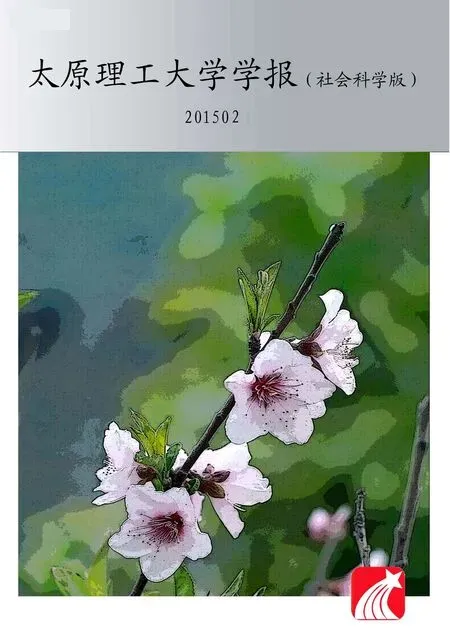文化沙漠里的心灵绿洲:索尔·贝娄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和《院长的十二月》解读
文化沙漠里的心灵绿洲——索尔·贝娄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和《院长的十二月》解读
籍晓红
(天津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222)
摘要: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和《院长的十二月》是索尔·贝娄对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的一种完美阐释。两部小说的主人公赛姆勒和科尔德对人生理想与人类终极真理的追求体现了贝娄对人的“物化”现象,以及“成功”情结的反拨,揭示了贝娄小说的一个永恒主题——“求索”,即人类在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沙漠中对心灵绿洲和精神家园的不懈追寻。
关键词:索尔·贝娄;文化沙漠;心灵绿洲;终极真理
中图分类号:I106.4
收稿日期:2014-11-26
基金项目: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10zd&135);天津科技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 (20110410)
作者简介:籍晓红(1973-),女,山西长治人,天津科技大学讲师、文学博士, 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当代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创作生涯中后期的几部小说在对物质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揭示了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后工业社会里人们所产生的精神危机,刻画了人们在物欲的驱使下迷失生活方向的困境,展现了后工业荒原社会中的文化沙漠现象。值得肯定的是,贝娄力图在一片文化沙漠中为人们营造一方心灵绿洲。如果说,他对物质主义的批判是对社会现状的一种解构。那么,他对心灵家园的寻找则是对人类理想和终极真理的一种积极的建构。贝娄对困境的表述可以以“物化”、“异化”和盲目地追求“成功”等概括。贝娄写于1970年的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和写于1981年的小说《院长的十二月》,虽然在写作时间上相隔11年之久,但这两部小说都完美地阐释了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赛姆勒和科尔德对人生理想和终极真理的追求,均体现出贝娄对后工业社会人类的“物化”现象和“成功”情结的反拨,深刻地揭示了其小说的一个永恒主题——“求索”,即人类对心灵绿洲和精神家园的不懈追寻。
一、贫困时代的荒原景象
海德格尔曾经对荷尔德林在哀歌《面包和葡萄酒》中所展现的贫困时代的景象作出过如下解读:“……上帝之缺席意味着……不光是诸神与上帝逃遁了,而且神性之光辉也已经在世界历史中黯然熄灭。世界黑夜的时代是贫困的时代,因为它一味地变得更加贫困。”[1]281与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贝娄在其小说作品中也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了一幅后工业社会“贫困时代”的荒原图景:“荒凉被留在了身后,那是茫茫无边的废墟”[2]184,“感情得不到报答,心灵找不到慰藉。无边无际的虚假;无边无际的欲望;无边无际的可能性……这是现代荒原”[3]227。
贝娄意在说明,在这个后工业“贫困时代”的荒原世界里,社会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即精神让位于物质、科学君临于艺术、哲学屈从于现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贝娄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道:“我在芝加哥已经呆了约半个世纪,可以说我对美国的商业化民主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我知道艺术并非广大美国社团的兴趣所在,艺术不是他们事业核心的内容,他们不是要创造一个‘更为高尚的人生’,他们追求的是稳定的经济繁荣、中等的生活条件、个人自由的保障,以及大致的公正,也就是一种体面的精神麻木状态”[4]215。他曾经直接或间接地说过,美国的城市里到处是丑恶、可怕的事情,充满了“混乱和精神麻痹”[2]185。他认为,人类“向强大的空虚投降”[2]335。《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和《院长的十二月》这两部小说典型地表现了贝娄对人类精神、文化沙漠的隐忧。概括起来,这两部小说主要揭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时代问题。
二、一切受人尊敬的东西“翻了个个儿”
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的译者汤永宽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残垣断壁之境况由复苏走向繁荣发展的阶段。美国因处于战争的后方,社会财富大量涌入,也使得其空前的富裕起来,但在精神文明、道德思想上却是惊人的空虚与贫乏。人们对性的疯狂和对金钱的贪婪充塞了整个社会[3]3。关于这一点,贝娄写于1987年的另一部小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的主人公、俄国文学家肯尼斯·特拉奇登伯格曾作出过精辟的概括。肯尼斯在谈到1913年的圣彼得堡和今天的芝加哥之间的相似之处时指出:“日益明显的是很久以来支撑着伦理秩序的形而上学已经走向了崩溃、瓦解。”[5]44这一现象在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和《院长的十二月》中得到了更加深刻的表达。
贝娄在1975年曾经说过,我认为20世纪60年代将被作为疯狂的、暴乱的年代而被人们记住,这个年代与文学和艺术无关。我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作家、画家、知识分子政治化的年代(政治化这个词在这里是个贬义词)[6]248。贝娄认为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的灵魂丧失了,社会“正在将人们的灵魂夺走”[6]248。他意识到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时代引发的重大悲剧——“情感的消逝”表达了对传统丧失、信仰崩塌的担忧:“是不是所有的传统都已走到穷途末路?信仰是否已经破产?……这是不是毁灭前的最大危机?道德沦亡、良心堕落,对自由、法律、公德心等等的尊重,都已沦为懦怯、颓废、流血——这种肮脏的时刻难道已经来临了么?”[6]1891990年11月,贝娄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们正在失去对作为一个人和拥有一个灵魂意味着什么的感知”,“我们的人性正处于危机中”,他提出警告,“在本世纪生命的神圣感已经消逝”[5]47。
在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贝娄以美国纽约为背景表现了西方文明的衰落。他写道:纽约使人想到文明的崩溃,想到索多玛和蛾摩拉*索多玛和蛾摩拉是两座古城,因居民罪恶深重而被上帝焚毁,参见《圣经·旧约·创世纪》。,想到世界末日。[3]301小说的主人公赛姆勒是一位波兰籍老派犹太知识分子,他是从德国法西斯灭绝犹太人的集中营里逃出的幸存者。他那饱含着思索和批判力量的内心独白,对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的社会风貌、政治经济和家庭生活都进行了广泛的揭示。像他的小说主人公赛姆勒一样,贝娄也“被美国社会的混乱吓倒了”[6]247。
小说中赛姆勒的亲戚格鲁纳之子华莱斯和女儿安吉拉,一个忙于投机钻营,另一个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姐弟两人在父亲垂危之际,他们不是陪伴在父亲身边,也不管他的死活,而是一心惦记着父亲藏在家里的一笔钱,姐弟俩为了争夺父亲的财产而互相心生芥蒂。华莱斯担心父亲死后,如果安吉拉继承了那所房子,这样他就会失去拿到那笔钱的机会。安吉拉则想请赛姆勒替她在父亲那里说说情,她担心父亲会把她的名字从遗嘱里去掉,更担心父亲把钱捐给慈善事业。华莱斯甚至为了找到父亲藏起来的那笔钱,不惜拆毁家中顶楼的水管,造成跑水,使住宅成为一片汪洋。而当小说的另一个人物苏拉发现华莱斯家的坐垫里藏着这笔钱后,就想把这笔钱独自吞掉。贝娄通过描写华莱斯、安吉拉姐弟及苏拉他们自私、丑恶的嘴脸,表现了道德解体、人性堕落的社会现象,以及他对这种现象的忧虑。
《院长的十二月》中的主人公科尔德不仅关心社会问题,而且还关注传统的衰落问题。科尔德想对他外甥梅森敞开心扉,告诉他按现在的阐释方法人们都是相互间的影子,影子中的影子……是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影子毁掉了我们传统的阐释方法[2]94。无独有偶,《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主人公赛姆勒也在沉思,“人们今天在证明懒散、愚蠢、浅薄、混乱、贪欲是正当的——把往日受到人们尊敬的东西翻了个个儿”[3]12。赛姆勒心痛地看到过去人们信任的东西,今天却被包围在无情的嘲笑之中[3]12。他对安吉拉说道:“体谅、爽直友好、善于表达、仁慈、体贴、同情——人类的所有这些优美的品质,由于舆论的一种特殊的转变,现在全给看做是见不得人的活动了。对罪恶公开坦率似乎要轻松得多。”[3]299-300赛姆勒还说,眼下科学人道主义,对一个解放的未来的信心、理性、文明的信仰已经不流行了[3]209。他在感叹:是我们人类发了狂了?[3]93
三、艺术被边缘化了
在后工业社会这一精神贫困的时代里,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矛盾冲突显得尤为突出,这种冲突成为索尔·贝娄笔下一个永恒的悖论。贝娄的研究者葛兰代指出,《院长的十二月》等小说涉及“科学对人的腐蚀作用”[7]99。贝娄本人则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对艺术家有着无法克服敌意的科技时代。因此艺术家必须为生活而斗争,为自由而斗争,和其他每一个人一样——为正义和平等而斗争,因为这二者已经受到机械化和官僚化的威胁[8]439。贝娄在诺贝尔奖金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中引用历史学家埃德加·温特在《艺术与无政府》中的话说道:黑格尔很久以前就说过,艺术不再吸引人的主要精力。如今吸引这种精力的是科学——是从事“理性探究的不懈精神”,艺术已经退居边缘[9]457。贝娄强调人文科学的价值,他曾经说道:没有艺术,现实就不可能得到解释。艺术和语言的衰落会导致人类判断力的消亡[7]1。他还说道……技师、专家、知识分子缺乏人道主义传统的“音调”,他们仅仅为“巨大的噪音”增加了不和谐的音色[5]48。正如特雷·伊格尔顿所说,人文学科包含着很多价值、意义和传统的内容,富于种种智慧和经验[10]202。人文学科也庇护了某些被日常社会所粗鲁摈弃了的可敬的、高贵的价值,培养了对于我们现行生活方式的一种深切的批判[10]243。贝娄试图恢复人文学科在后工业社会中的地位。
美国作家爱伦·坡在十四行诗《致科学》中曾经提出了科学及其“凝视的眼睛”的“沉闷乏味的现实”与奉献和诗人的梦想之间的冲突[11]385。麦考利在1825年写道:“我们认为,随着文明的进步,诗几乎必然会衰落。”[11]383托马斯·坎贝尔发出感叹:“原本是多么可爱的幻想,现在却受缚于冷漠的物质定律!”[11]385
英雄所见略同。贝娄的小说表现了这样一个主题,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中,艺术被边缘化了。“艺术在科学面前总是卑躬屈膝。”[3]136历史和文学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而数学和物理科学则“立于不败之地”[2]37。科学从部分人类那里获得了认识深层次事物的全部能力并垄断了它,而把其他人都留在了非常虚弱的状况之中。虚弱中的人们于是写诗、绘画,搞点人文学科,雕虫弄术——太白痴了[2]161。在这个实用主义至上的社会里、在人们心目中,自然科学的功用要远远大于文学和哲学等人文科学。诗人作为艺术的代表遭到和艺术同样的被遗弃和冷落。小说《院长的十二月》中主人公科尔德认为,在美国,诗人从来没有真正地受到过喜爱。科尔德对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言论“一个好校长胜过二十个诗人”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最需要想象力时我们只有“特殊效应”和矫揉造作[2]307。这表达了贝娄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及他对想象力的推崇。
贝娄的小说常常用两个彼此差异很大的人,比如一对夫妻,或者两个朋友,来隐喻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矛盾。米娜和科尔德院长就是这种对立的写照,他们的结合是“一个超清晰的头脑与一个梦想家配成了一对”[2]286。科尔德院长和他儿时的伙伴杜威(贝娄用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名字给他命名也是用心良苦)之间的关系也是这种对立的缩影。科尔德的那些严肃问题不能向杜威提及,例如,精神和自然的结合(已被科学分裂了)[2]141。杜威对那些高谈“精神”的作家、那些远离当今物质实际的知识分子毫不客气[2]141-142。
在那个重实用、轻艺术的时代,芸芸众生随波逐流,他们往往沦落为失落了灵魂家园的精神流浪者,《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所描写的印度科学家拉尔就是其中之一。拉尔小时候是个爱哭的男孩子,他离不开父母,离不开家,离不开小朋友。在他家里,每当客人要走的时候,他就会大哭大闹。一切离别对他来说都是感情上的磨难,总会让他难受一场。他用他“内心深处的分子”来感觉离别,他身上亿万个细胞核都会为之颤抖。但是自从他开始从事血管方面的生物物理学研究工作以后,他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他相信“行为是诗,是隐喻的秩序,是形而上学。从大脑皮质网膜十几分之一毫秒的高频反应到最显著的生态学现象,这一切都是崇高的隐喻用神秘的代号印出来的图像……”[3]220-221。他从一个“感情的动物”,变成了一个“科学的动物”。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拉尔这个人物所折射出的是在这个时代,人们丢弃了古老的价值观,失落了灵魂,成为了“无根”的人。小说中华莱斯对赛姆勒说道:“生根?生根不是现代的想法。这是农民的概念,土壤和根茎。农民就要消失了……我当然没有根……真正的事是遥测技术,是控制论。”[3]244一班工作人员,操纵着世界的机器……计算精确到了十亿分之一度……这些醒着的天才。这里所说的那些睡着的笨蛋,一些做梦的空想家[3]252。那些操纵世界的“醒着的天才”是实利主义者,是科学家们,而那些“睡着的笨蛋”是理想主义者,是艺术家们。赛姆勒也曾经加入了这些“睡眠者”的行列。《院长的十二月》中也曾写道:芝加哥还有摩天大楼里的商业活动,有雄伟不朽的银行业,有计算机化了的电子联合体[2]184,唯独没有了艺术、梦想和爱。
科尔德的儿时伙伴杜威也是如此,少年时代的杜威酷爱奥斯卡·王尔德,喜欢阅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李尔王》。而现在在他心目中,老芝加哥已经很遥远了——林肯公园已时过境迁,莎士比亚和柏拉图引起的激动……《荒原》的背诵、《权力意志》的争论及虚无主义的真正意义,所有这些,还有老伙伴们都是童年时代的事了,人们必须摆脱那一切(科尔德自己还没有摆脱)[2]265。
相反,科尔德们则始终依恋、支持旧的哲学,价值观和文学艺术。他的思绪常常回到少年时代,回到那些他和杜威他们一帮男孩子揣着诗人和哲学家的作品徘徊在林肯公园……与苏格拉底和里尔克神交意往的日子[2]140里。科尔德在后来写的短文里也总体现出一种“诗意”的流淌,一种他年少时吸入自己的血液之中的真正的激情[2]201。他放弃了真实世界,在哲学和艺术中寻找避难所[2]56。他相信,“现代成就、飞机、摩天大楼、高科技是对智力的极度耗费,尤其是对判断力的极度耗费,最重要的是对个人判断力的耗费”[2]287。
科尔德心地脆弱,却是个真正爱思考的人。他无法把握世界变化,去处理人类事物发展的新技术、新因素,去了解后工业社会的权威机关做出决定的分析图表的全部含义。……当他再次出来看一看目前的社会政治舞台时,他震惊了。他独有的人道主义标牌无法使他对他在街上、在摩天大厦里看到的东西作好思想准备[2]331。他总是具有一种“不合时宜的高尚情怀”[2]179。在科尔德的外甥梅森看来,舅舅现在正“与一种难以捉摸的哲学调情”,并极想“与不存在的美德有染”[2]95。在梅森看来,科尔德的“不真实,脱离了现实”[2]95。教务长威特也觉得科尔德身上有某种东西是“无法被教育”的,是一种“情感障碍”[2]200。
赛姆勒和伊利亚·格鲁纳医生也是如此,他们都“根据的是一种旧体系”,“珍重某些旧感情”[3]298。伊利亚有着强烈的家庭情感,他认为赛姆勒有一种不寻常的力量,或者说魔法,可以确认人类的联系[3]270。伊利亚能这样看待赛姆勒,并且在经济上帮助赛姆勒父女,就如同“文物工作者发现文物”一样[3]78。赛姆勒生活在内在的方式里[3]257,他是一个不合潮流的人,不是一个跟得上时代的人[3]135,他被视作一个旧的世代的遗留物。赛姆勒感到自己有点“与同类分离了”,这是由于他“专心致志于那些太不相同和太遥远的事物,在精神方面专心致志于同当前太不相称的那种柏拉图式的、奥古斯丁的十三世纪的东西”[3]47。“如果大多数人好像是被符咒迷住了似的,像梦游者那样,被微不足道的、神经过敏的琐细的目的所约束、所掌握而兜来转去的话,那么,对于像赛姆勒这类个别的人就只有一往直前,他注意的不是目的,而是周围环境美的消耗。”[3]48
四、结语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引用了雪莱文章中一段经典的话,指出诗人雪莱对功利主义进行发难,并将这种病态归咎于科学的发展与人类诗的想象与道德想象的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调。雪莱是这样写的:
科学已经扩大了人们统辖外在世界的王国的范围,但是,由于缺少诗的才能,这些科学的研究反而按比例限制了内在世界的领域;而且人虽然已使用自然力做奴隶……,但是人自身却仍然是一个奴隶……当由于过度的自私自利和计较得失,我们外在生活所累积的资料,竟超过了我们同化能力的限量,以至于不能依照人性的内在定律来消化这些资料,在那个时期,我们最需要诗的修养。[11]412
雪莱在这里指出了科学与诗的对立,以及诗歌对人类精神的重要性。艾布拉姆斯认为,这段话的精妙之处在于对我们这个崇尚技术和物质、渴求知识的社会所作的经典性责难。应该指出,贝娄作出的“艺术家受到机械化和官僚化的威胁”[8]439的论断是和这些观点一脉相承的。他在《院长的十二月》和《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中,将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沙漠现状揭露无疑,同时又试图重新绘制一幅新的人类心灵绿洲的地图。
参考文献:
[1]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索尔·贝娄.院长的十二月[M]//宋兆霖.索尔·贝娄全集.陈永国,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索尔·贝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M]//宋兆霖.索尔·贝娄全集.汤永宽,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马修斯·鲁戴恩.索尔·贝洛采访记[J].郭廉彰,译.国外文学,1988(3):214-228.
[5]Eugene Hollahan.Saul bellow and the struggle at the center[C].New York:AMS Press,1996.
[6]John Jacob Clayton.Saul Bellow:In defense of man[M].Bloomington&Lond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
[7]Michael K,Glenday.Saul bellow and the decline of Humanism[M].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90.
[8]索尔·贝娄.思考者的荒原——谈谈小说家的职责[M]//王宁.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9]索尔·贝娄.在诺贝尔奖金授奖仪式上的讲话[M]//王宁.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0]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M].鹂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A Spiritual Oasis in the Cultural Desert——An Interpretation of Saul Bellow’s NovelMr.Sammler’sPlanetandTheDean’sDecember
JI Xiao-ho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TianjinUniversityofScience&Technology,Tianjin300222,China)
Abstract:Saul Bellow’s two novels Mr.Sammler’s Planet and The Dean’s December are perfect illustration of the journey of men’s search for their spiritual home. The protagonists Mr. Sammler and Corde’s pursuit of their life ideal and ultimate truth embodies Bellow’s antagonism to the phenomenon of human “materialization” and “success” complex, which reveals the eternal theme of his novels—“pursuit”, that is, the incessant pursuit of an oasis of soul as well as the spiritual home in the cultural desert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Key words:Saul Bellow; cultural desert; spiritual oasis; ultimate truth
(编辑:陈凤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