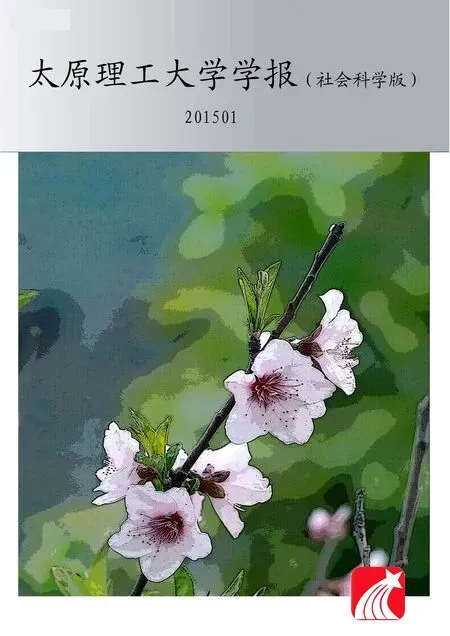论“民心”在秦汉变局中的作用——向张秋升教授请教
刘 巍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论“民心”在秦汉变局中的作用——向张秋升教授请教
刘巍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导致秦汉之际政局变动的因素有很多,这些因素共同发生了作用,并推动了秦亡汉兴的历史进程,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暴力战争。在这一过程中,民众的作用不应被高估,“民心”的价值更不足为道。在中国历史上,“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表述只是儒家的价值判断和官方的政治宣传,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切忌“脸谱化”,绝对意义上的“善恶忠奸”并不存在。
关键词:民心;起义;暴力;儒家;政治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珍贵遗产,其中对于“民心”重要性的强调,也成为中国历代政治术语中的重要闪光点,并被后人津津乐道。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秋升教授发表在《人民论坛》的文章《民心向背与秦亡汉兴》,就以秦末的历史典故为例,对“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一传统说法进行了论证,并将其肯定为“颠扑不破的真理”[1]。张教授此文言辞精彩,大气磅礴,但文章的中心观点与几处表述似有商榷的余地。笔者作为后学晚辈,不揣浅陋,略陈管见,恳请批评。
一、论刘邦与项羽的历史形象
历史人物的形象是复杂的,需要从多角度进行研究,“脸谱化”的人物评价标准并不准确。张教授对于文中所提到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似有不当。他认为,“与项羽相比,刘邦则是一位宽厚长者。……与项羽的杀、烧、刚愎专断形成了鲜明对比”[1]。
在中国古代的争霸战争中,阴谋诡计、尔虞我诈贯穿始终,最后都以血流成河而收场,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仁主贤王注定会被淘汰。他们或许可以做守城之君,但很难当得了开国帝王。历史上那些具有“妇人之仁”的“宽厚长者”,如宋襄公、张鲁等辈,莫不以失败为终。刘邦虽有“约法三章”之举,但从整体上看,他绝非宽仁之人,这是学界的公论。无论是打天下还是坐天下,其阴险狡猾、背信弃义的行为都有很多。鉴于此,后人对刘邦的负面评价不少,晚清郭嵩焘在《史记札记》中就谈道,“高帝以匹夫有天下,……其心惴惴焉,惟惧人之效其所为而思所以戮之”。
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刘邦一系列的政治举措都以行政安全为视角。他常遭后人非议的一项行径便是对开国功勋的屠杀。据《史记》记载,韩信死前便哀呼:“狡者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种过河拆桥、诛杀功臣的行为,不仅没有宽仁之风,反而体现了法家的实质。“在法家看来,唯一可信的是法(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术(通过分权制衡驾驭群臣的权术)、势(严刑峻法形成的高压)。”[2]178秦之覆亡,常常被看作是法家执政理念破产的明证。其实,这种观点并不准确。此后的历代帝王,谁也没有抛弃法家,反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3]195。
同样,张教授对于项羽的评价也不甚准确。我们今天从典籍中看到的项羽的形象,其实并不是其真实面目。人们对项羽的印象,来源于史书的记载。但治史者因为身处的环境,并不能真正做到秉笔直书和“不以成败论英雄”,相反,为胜利者歌功颂德,对失败者抹黑栽赃,成了传统史学中的通行法则。“汉代史官司马迁与班固‘妖魔化’项羽,目的是为刘氏政权合法化提供法理依据。……项羽形象和行为经过汉代官方史家精心‘妖魔化’,已经真伪参半。汉代史书中项羽形象的书写与评价,是胜者意识支配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结果。”[4]
因此,项羽留给后世的印象,其实是经过后人粉饰乃至假造的一种历史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人群体的文饰与臆想充斥其间,使得历史记忆也往往距离事实越来越远,最终“墨写的谎言”定格在历史的时空中,成为了所谓的“史实”。当然,这并不是说项羽就是菩萨心肠,他和刘邦都是打天下的军事集团的首领,他们都有过杀人放火的残暴行径,只是二者之间充其量只是量的差别,而非质的不同。史家的这种曲笔,其目的恰恰在于制造“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假象。而我们如果从史家有意制造的假象出发,便正好落入其陷阱之中,难以摸清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政治变局与“民心”价值
无论是先秦诸子还是后世学人,都对“民心”的作用有过不少论述。例如,“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民心”(《美芹十论》)。张教授也感叹“民心的作用为何如此之大”,他认为,“支配人民行动的是民心,心的凝聚从来都有感天动地的力量。所以,问题的关键在民心,民心向背之所以能决定一个政权兴盛衰亡的秘密就在这里”[1]。
对此,笔者颇有疑问。也许在儒家的理论构建乃至统治者的政治宣传中,民心的确应该发挥重大作用,甚至成为天下兴亡的关键。但是,历史事实却与此相悖。从学理上来说,中国古代的政权和皇位无不是通过战争或者是以暴力胁迫而获得,从未有过民众授权的例子。既如此,民心向背如何能够决定天下的归属呢?
张教授在文章第一部分就谈道,民心“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想法,是百姓的情感倾向,是人民的意愿和要求”[1]。对于这个定义,笔者表示赞同,但民众的这种情感,对历史进程又起了多大作用呢?
在中国历史上,“民”通常是指平民百姓,他们承担官府的赋役,社会地位较低,属于被统治阶层。官府在“编户齐民”制度下对民众进行管理,推行“族刑连坐”,从而将大规模的群体性反抗行为消弭于无形。平民百姓出于生存策略的考虑,在一般情况下往往处于一种平和安定的状态。这种状态的特征就是:并不过分关注皇位的归属;对于捐税赋役有较强的忍耐力;基本上处于一种得过且过、随遇而安的生存状态。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道家式的生存理念。“如果不是就道言道,而是就诸家互动形成对国人行为的综合影响而论,则道家(主要是在庄周以后的形态中)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润滑油,具有很浓的犬儒色彩。”[2]184这就是说,只要官府压榨得不是太过分,老百姓一般都会保持着一种顺民姿态,不愿意介入到政局纠纷之中,更不愿意用身家性命作为赌注与官府直接对抗。因为百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民,“‘安土乐天’、和平主义的生活情趣,更是直接从农业文明中生发出来的国民精神”[5]127。他们依靠土地而生存,对自然灾害、兵荒马乱等外界变化的应对能力很弱,因而渴求安定,希望自保。所以,在政局相对安定的时期,民心向背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来,老百姓没有造反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朝廷感恩戴德,官府“得民心”与否是难以说得清楚的。
而当苛捐杂税忍无可忍,特别是在水旱天灾等特殊情况的作用下,老百姓有可能会揭竿而起,奋起一搏,投身于求取活路的斗争中。不过,历史上民众的类似行为,大部分都被官员通过镇压或者招安而化解。而且,这种反抗行为也不能一概认定为朝廷“失民心”,因为,历史上通过烧房子、抓壮丁等行为裹挟民众参与造反斗争的情形并不少见。民众的造反行为并不意味着他们与朝廷不共戴天,往往只是被迫的选择。
对于上述之论,笔者曾经总结如下:“在大多数时候,民心可能并不表现为一种‘非得即失’‘非黑即白’的状态,而是处在二者中间的灰色地带。因此,民心很难用得与失来表述,也无法具体考量和定性。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相比‘民’之于‘官’的弱势,在强权与暴力面前,‘民心’更是显得单薄与无力,民意的表达也常常被扭曲”[6]。
因此,笔者认为,“民心向背”往往缺乏一个真正客观的衡量指标。即使是像造反这样的极端行为,有时候也不是出于本心。民心与民众的实际行为之间并不能划等号,没有付诸于行动的民心往往用处不大。退一步讲,即使是民众的武装行动,也多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集体行动的决策和展开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个体民众之间目标不一致的时候自不必说;即使是有着共同利益时,也往往容易出现“搭便车”的情况,难以形成合力;一旦势力壮大,集团内部也容易出现内讧,进而削弱整体实力,瓦岗寨内讧和太平天国的“天京事变”就是实例。历史上那些真正通过农民战争起家并一统华夏者,只是极其个别而已。所谓“得民心”与“失民心”,都是一种通过“事后诸葛亮”的方式而总结出来的。这是因为我们可以从胜利者的历史中发现惠民之举,也可以从失败者的过去中寻到恶政的踪迹。其实,历史上打天下的军事集团,为了胜利都是无所不用其极,善恶手段兼而用之。李自成不仅开仓放粮,也烧杀抢掠,对于这种既得民心,也失民心的案例,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呢?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并不是完全否认民心的作用,也不是完全否定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定位,但是,过分夸大所谓“民心”的作用,也是对历史的错误认识。
三、再论“秦亡汉兴”的历史进程
下面具体到文中所谈案例——秦亡汉兴。张教授谈到了民心向背与秦汉历史进程的关系,在他看来,这是秦亡汉兴的根本原因。对此,笔者有着另外的解释:秦末的战乱与统一,归根到底是由暴力层面的竞争决定的,夹杂在其中的所谓“民心”,在暴力面前不仅抽象而且弱势,根本无法起到左右政局的作用,试述如下。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中原已经分裂了几百年。位于西戎之地的秦国,因变法而国力强盛,并通过武力战争吞灭六国。在这期间,“民心向背”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三晋和齐楚之地的民众也并不认同秦国。但是,战争的胜利还是压过了民心的力量。作为刚统一的政权,秦朝不可能在短期之内获得六国之民的认同。而在反秦战争中,真正的核心力量也恰恰来自六国故地。陈胜首义之后,他们趁势而起,开始复国,严格来说,六国之民从来就没有对秦政权产生过认同,他们一直都是秦政权的离心力量。
走投无路的陈胜、吴广被迫揭竿而起,这可以被看作是朝廷失民心而导致的起义。可是,民变并不意味着“失天下”。陈胜、吴广很快就被政府军通过武力镇压,这恰恰是“民心”在暴力面前脆弱的真实写照。六国复起之后,他们对秦政权的争夺,在一定意义上重演了战国争雄的故事,只是这一次秦国败亡,决定结局的依旧是暴力战争。客观说来,导致秦之覆亡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权力纷争、兵力分散等等,但最终的结局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因素的缺失或变化,都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汉初贾谊长于政论,他在《新书·大政(上)》中谈道,“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然而,这种说法未免太过天真,“秦朝灭亡的原因是汉初儒生总结的,这些人在秦朝过得很不如意,他们的看法带有很强的倾向性”[7]。
随后的楚汉之争,更是暴力军事集团之间的争霸。双方争雄四年,互有胜负,垓下一战,刘邦大捷,而项羽又负气自刎,最终成就了大汉的天下一统。总结战争,我们不难看出,“运筹帷幄,用兵千里”才是决定胜利的根本。选人、用兵乃至时运等因素决定了战争的最后结局。在这其中,我们似乎看不到平民百姓的身影,更不用说抽象的“民心”了。
“约法三章”曾经被认为是刘邦“得民心”的证据,这一举动也为后世所传颂。即便真的如此,这种所谓的“得民心”之举与最后的战争结局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呢?关中百姓纵然爱戴刘邦,甚至“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史记·高祖本纪》),可这又当如何呢?关中只是天下一隅,其他地方的民心又是何取向呢?刘邦的地位和名号来源于任命或者是自封,并非来自下层百姓授权。百姓们情感支持的实际作用并不大,因为这种爱戴如果不能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话,往往并没有实际意义。退一步讲,即使老百姓真的对刘邦心悦诚服,甚至愿意赴汤蹈火,其作用恐怕也不能高估,单个民众的能力有限,集体行动又面临重重困难。
项羽在很多方面“失人心”固然已成历史的铁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失人心”并不等同于“失民心”,概念上的混用往往会导致推理进入误区。背弃项羽的范增和投靠刘邦的韩信,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分子,他们即使出身贫贱,但是一经卓拔任用,成为谋士和统帅之后,便不能等同于普通大众了。项羽被他们抛弃,却并不意味着被广大民众抛弃,最后带兵击败项羽的正是不被其重用的韩信。客观地说,项羽在用人方面的失误的确左右了最后的结局。然而,这一切与普通百姓关系并不大。尽管张教授认为项羽“好战嗜杀,迷信武力,刚愎自用,无好生之德,……这些所作所为使得已经极端厌恶残暴的百姓对其失掉信心,自己最终落了个乌江自刎的悲惨下场”[1],但这种说法的因果联系其实并不相关。
综上所述,秦末的历史呈现给我们的是赤裸裸的暴力色彩,民众的作用微乎其微,我们根本无法得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结论,相反,只有战争胜利者才能得天下。这种成功意味着取得了统治百姓的资格,继而掌握话语权,进行“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宣传。
因此,笔者斗胆猜测,张教授可能是因为预先存有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观念,才去搜寻史料以证明之。“对于过去发生的事实而言,记忆常是扭曲的或错误的,因为它是一种以组构过去使当前印象合理化的手段。”[8]48面对着刘邦得胜的既定事实,回溯并搜寻与结果性质相符的材料并不困难。而如果先研究真实史料,再进行分析和总结的话,可能会得出相异的结论,即为了战争胜利而不择手段者才能得天下。历史的事实与儒家的美好理想之间,相差何其之大!
四、结语
结合上文的分析,笔者对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中“民心”的作用的观点表述如下。
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暴力层面的竞争是决定性因素。旧政权的某些恶政,即“失民心”之举,可能导致民间的反抗行为。绝大部分情况下,政府会恩威并施,化解这种对统治安全构成威胁的挑战;在个别时候,由于镇压或者招安不利,这种行为也会呈现出扩大化趋向,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导致天下大乱。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朝廷首尾不能兼顾,镇压能力减弱,相继而起的各路诸侯,往往并非是因为饥饿等被动原因,而是怀着觊觎天下的野心。其起兵反叛旧政权的行为并不能视作旧政权丧失民心的证据。而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在乱世之际的生存策略,主要是守土保身、流浪讨饭、化身盗匪、当兵吃粮等,这一切行为,都是基于生存目的的选择,与“民心向背”关系不大。
而当从军征战成为一种生存方式之后,行为主体并不需要对军事集团的首领有过高的价值认同。暴力集团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或投诚于朝廷,或互相兼并,其行为均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身处战乱之中的老百姓,其利益往往很难得到保证:败落的散兵游勇乃至割据势力,都会为了眼前利益而对平民百姓肆意搜刮,竭泽而渔,力图在短期内增加兵饷,扩充军队。在这个意义上,爱民行为往往不如害民行为更有效果,这时的乡野呈现出土地抛荒、流民遍地的景象。最终,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军事战争的胜利者问鼎天下,改朝换代,进行新一轮的专制统治,同时,招纳流民,进行农业生产,以之作为皇粮国税的基础。
根据上述之论,我们不难看出,秦汉之际的历史变迁无法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表述,更深一层说,甚至在中国历史上,都很难找到与儒家这种表述相契合的例子。历史上的专制帝王,将儒家的仁义道德高挂嘴边,可是谁又真心相信“得民心者得天下”呢?更何况“得民心”是一个难以量化的概念,究竟怎么做才算是得民心呢?对于古代专制社会的统治者来说,一切行政手段的根本目的无非为了政治安全,只要能够达成这一目标,他们往往并不在乎平民百姓的具体感受。对孟子民本思想深恶痛绝的朱元璋不仅得到了天下,还开创了大明王朝两百多年的基业。其子朱棣在“靖难之役”之前,也曾担心“民心向背”,结果被谋士姚广孝说服,后来通过军事战争,从侄儿手中夺取了皇位《明史·姚广孝传》有如下记载:“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朱氏父子两代的经历恰恰印证了民心的真实作用。
因此,笔者认为,儒家的美好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儒家主张行事手段正义性,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达成目标,行为主体往往“王道”“霸道”兼而用之。不仅如此,在历史进程中,诱发事件和决定结果的因素也有很多,各种偶然性因素的作用使得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其特殊性。一般来说,掌握军事实权的政客可以通过“逼宫”等方式改朝换代,乱世之际的政权更迭则是通过军事战争决一雌雄,民众在其中的作用并不大,更遑论“民心”了。所以,“得民心者得天下”这种表述过于简单,也没有认清历史进程的真实脉络。
参考文献:
[1]张秋升.民心向背与秦亡汉兴[J].人民论坛,2012(9):78-80.
[2]秦晖.传统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4]阎盛国.项羽被“妖魔化”的历史学考察[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86-90.
[5]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 中华文化史:第3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6]刘巍.民心何足恃——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的一个解释困境[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81-84,91.
[7]陈菁霞.学界热议“秦是否亡于法家”[N].中华读书报,2013-06-26(1).
[8]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编辑:张文渲)
On the Function of “Popular Suppor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Qin-Han Period
——Asking Professor Zhang Qiusheng for Advice
LIU Wei
(DepartmentofHistory,AnhuiUniversity,HefeiAnhui230039,China)
Abstract:There were many factors leading to the change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hich promot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decline of the Qin Dynasty and the prosperity of the Han Dynasty by their joint action and among which the decisive factor is violent war. In the process, the function of the masses should not be overestimated, much less the value of “popular support”. In Chinese history,the statement that “one who get the popular support will conquer the world ” is only Confucian value judgment and official political propaganda,so the appraisement of historical characters should never be “formularized”. “Good and evil, loyalty and treachery” in the absolute sense don’t exist.
Key words:popular support;revolt;violence;Confucianism;politics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5)01-0060-04
作者简介:刘巍(1986-),男,安徽蚌埠人,安徽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经济史、经济思想史。
收稿日期:*2015-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