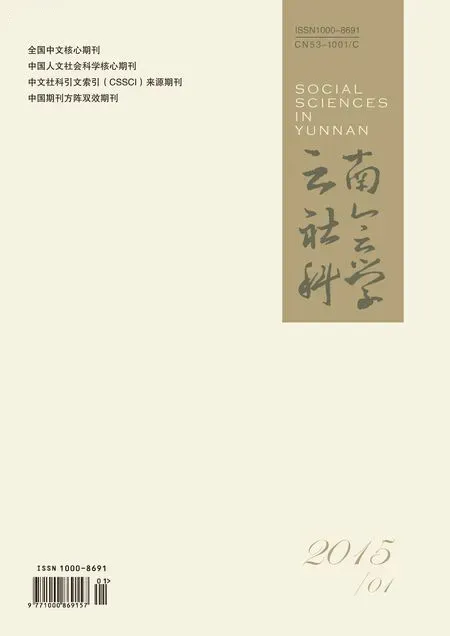从社会到群体:1949年以前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概念与视角的学术史梳理
卢成仁
对概念的建构、应用及其变迁过程进行梳理和分析的概念史研究,已成为历史学特别是学科史研究的新兴方向,其为历史过程及学科史分析所带来的新视角,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和重视。对于人类学学科史的梳理特别是1949年以前的学术史陈述,大多侧重于研究对象、方法和人物的阐述*参见胡鸿保:《中国人类学逸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美]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对于学科本身的研究概念、视角较少进行集中的分析和讨论*王铭铭教授主持的团队曾以“民族”和“文明”概念为中心,对1949年以前人类学研究文本进行了解读和分析(参见王铭铭主编:《民族、文明与新世界: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叙述》,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人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的著作、论文、文档,不仅是学科史的基础性资料,也是这个学科自身的“心史”,即学科自身研究概念、视角的建构与应用过程,代表了学科发展的内在机理。对于1949年以前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概念、视角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之分析范式进行梳理和讨论,不仅可以丰富学科史的写作和实践,也可以为当下多元化的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建构新分析概念、视角提供历史经验和逻辑基础*关于早期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著述与调查活动,王建民教授有详细的履列与阐述(参见王建民:《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2期)。本文对过往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分析与评述,以公开出版的民族志文本为主。。同时,1949年以前的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与中国人类学研究有着重要的重合(一定层面上,西南人类学研究的展开也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发声),对于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概念、视角的分析和讨论,可以满足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史进行新理解、新解释的需要。本文应用概念史的分析方法,以1949年以前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概念、视角的建构与转变为核心,尝试进行这一新的梳理和讨论。
一、作为概念与思维方式的“社会”和“群体”
与“文化”一样,“社会一词是社会学家词汇中最不明确和最普通的名词之一”[1](P347)。即便是在严肃的学科辞典上,对其的定义和范围也因作者与论述方向的不同,在异彩纷呈的基础上,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1](P347~348)、[2](P640~641)。不过,就社会一词作为研究概念的意义而言,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论述较为系统和精到,并在相当意义上使社会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研究概念被认知和使用。本文所讨论的社会,主要就其研究概念的意义而言。
在涂尔干的成名作——《社会分工论》中,他认为只有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系;他以分工为基础,透过对法律与惩罚的精细研究,将社会连带分成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两种,从而把一种以分工为底座的社会结合过程系统地呈现出来[3]。在这一论述体系里,涂尔干将社会看成是一个整体,同时也是一个异常真实的存在。而透过涂尔干对于社会事实的论述,我们能够深入地了解社会这一研究概念所具有的真实力量。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现象,“是存在于人们身体以外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同时也通过一种强制力、施以每个人”[4](P5),具有外在性、强制性和普遍性的特征[4](P1~60)。之所以会具有这些特征,是因为社会与个人是两种不同的状况,社会独立于个人发生作用,并不会随着个人意愿而改变或消失,有其自身独立的发生、发展和影响的轨道[4](P3~38)。因而,涂尔干所论述的社会,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整体,具有其独立且特别的规训性力量发散在千千万万的个体之间,一切社会现象的产生、发展及其研究、解释,只能回到社会本身中来。作为现代社会学三大奠基人物之一,涂尔干对于社会这一学术概念的深刻论述成为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基本研究概念之一,而社会这一概念带来的认知方向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也使之成为社会学、人类学基本的学科思维方式之一。
不过,社会与群体究竟有什么区别呢?笔者对比了诸多社会学、人类学辞典,注意到辞典中对于社会和群体概念本身的解释中,二者的同质性大于差异性*如“社会:一群人作为一个实体实活着,有自己的文化;一个由遵循特定生活方式的、时间上持久的、并有群体意识的人组织起来的集合体”;“群体:构成社会的重迭的基本单位。一般具有泛人性、也就是独立自主的存在,超出其组成成员的支配”(参见吴泽霖主编:《人类学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第634、275页;)“社会: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群体:人们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的相对稳定的集体”(参见张光博主编:《社会学词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0、335页)。;而这其中最核心的差异是:由群体组成社会,即社会大于群体*参见陈国强主编:《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75~276、500页;程继隆:《社会学大辞典》,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第249~251、526页;蔡文辉、李绍嵘:《简明英汉社会学辞典》,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2年,第83、221页;参见邓伟志主编:《社会学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3、19页。。因而,对群体与社会概念差异的梳理,需要回到群体概念本源上去。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提出Gemeinschaft与Ge-sellschaft概念,前者一般译为共同体、社群、社区,后者一般设为社会、社团。Gemeinschaft指的是人群共同体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家庭为中心,多数人彼此认识并有着亲密的人际关系和团结感,受传统所约束注重群体行为、利益、活动的一致性,对异常的行为主要以非正式手段(如闲话、个别规劝等)进行控制。同时,在对Gemeinschaft这一研究概念的应用中,并不将之仅限于有固定区域的人群共同体(社区),也包括跨越区域的人群共同体(社群)[5]。虽然,涂尔干吸收了Ge-sellschaft并推演出社会的概念,但从群体与社会概念的形成过程上看,可以发现强调人群的同质性多过于异质性,强调以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组合人群大过于刚性的法律和功能交换,强调人群的自组织大过于组织本身的系统性与严密性,是群体与社会最主要的差异。
不过,“社会”作为人的科学分析概念类别中的“国王”,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崛起、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概念和超强势话语[6](P315)。而随着近现代中国对于西方社会科学学说的吸收及现代学术研究体系在中国的建立,对于有异于汉人社会的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无疑议的是,社会这一研究概念也随着人类学调查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的展开,被借鉴和应用。不过,社会这一概念,在进入在西南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体系中,是如何被讨论、如何被看待?对于社会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从社会到群体,是如何发生转变的?这不仅是一个需要深入考察和思索的学科史问题,更是一个概念史的问题。
二、从社会到群体:转化的过程
1928年,杨成志先生较早开展了对西南少数民族的人类学调查,对凉山彝族、巧家与永善的青苗和花苗、河口瑶族的社会制度、语言、历史与风俗及歌谣等进行了研究[7],从而将社会的概念初步引入了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在杨成志于1937年发表的对广东北江瑶人的论文中,将家族、乡村与会社群体,视为“社会生活或文化”;换句话说,在这里杨先生将家族、乡村与会社群体,视为社会的基础(参见刘昭瑞编:《杨成志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9~91页)。。在王同惠、费孝通先生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中,透过对广西象县(今金秀县)地区花篮瑶的家庭、亲属、村落、族团及族团间关系的分析,来看其社会组织与社会运作,认为社会组织的各个部分之间有其微妙的搭配,也有其自身独特的功能,如此一个社会才能顺畅运作[8](P422~497)。这与当时功能论对社会的理解和观点比较一致。1935年在怒江进行了实地调查的陶云逵先生,虽然以文化来统领调查事项,但在文化之下分为“物质、社会、精神方面”,而社会方面则包括了男女社交、姓氏与部落、战争与武器、政治与法律等部分[9](P373~392)。在陶云逵的论述中,虽然没有明确侧重于对社会或者对群体进行讨论,但在调查中社会这一研究视角被应用到调查事项中,则是比较明显的。庄学本先生在1934年对四川的羌族和嘉戎藏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历史源流等进行了考察和分析[10];在1938~1939年间,他又对彝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其眼中的社会,是由物质基础、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心理生活组成的,庄学本所认知的社会包括了阶级、法律、战争、年节等[11]。1937~1939年间,马长寿先生在凉山彝族的调查中,将社会的概念落实在彝人的社会组织上,认为在家庭、家族、阶级三个组织中,以血缘的家族和政治性的阶级为核心,同时婚姻与继嗣规则、宗法制度等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12]。马长寿对于社会的理解,与一般社会学对于社会的解释几无差别。与此观点相近,曲木藏尧认为凉山彝族社会组织纯为“部落阶级制度”,而“打冤家”行为是促进社会组织进步的动力[13]。虽然,以上诸先贤对于社会的理解,与研究概念意义上的社会有一定的差异,但在他们的调查中应用了社会这一视角,是非常明显的。
不过,随着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渐次深入、研究作品的不断增多,群体这一既可称之为研究对象,也可称之研究视角的概念,慢慢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换个角度看,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伊始,社会的概念就相对要弱;而随着田野调查,特别是时人所言之“社区调查”的深入开展,群体的概念就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当时基础性的学术话语。。凌纯声、芮逸夫先生的《湘西苗族调查》[14],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15]、吴泽霖与陈国灿等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16]等著作,大多将调查对象作为一个人群共同体进行叙述,对其群体行为也多有讨论。江应樑先生在1949年前于云南傣族地区的3次调查中,详细叙述傣族经济、政治、宗教、习俗等情况后,对傣族的家庭与亲属群体作了较为深入的说明[17]。不过,在许烺光先生的《祖荫下》之后,情况似乎发生了转变。他以祖先为主轴,来描绘大理喜洲人的家庭、家族群体的日常生活及其文化建构[18],从而使群体这一研究概念和视角在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中被突出出来。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将大摆、公摆中6种摆之仪式背后的群体作了条分缕析的细致阐述,并将作为群体行为的“摆”与村落的自然环境、社会地位、人情往来、社会组织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19]。同一时期的魁阁作品《云南三村》,如果换一种视角来看的话,事实上是以土地所有权、家庭手工业与作坊工业、农田种植与蔬菜经营的差别,将村落中人口分为贫富两大群体,而这两大群体的互动及其行为的移易正是乡村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之一[20]。在此影响下进行的尾村经济行为调查,也以地位、婚姻、政治、职业过程为中心将村落人群区分彝汉两大群体[21]。林耀华先生的《凉山夷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对凉山彝人的家族与氏族群体所做的深入讨论[22]。同一时期,林耀华在对西康北部藏族的调查中,将贵族与平民的阶级制度、地域性的村落群体及幕营群体和血缘性的家族群体,作为西康藏人社会组织的背景与基础进行论述[23](P408~432)。1945年,林耀华又对嘉戎藏族在双系基础上的家族及其婚姻过程与规则进行了详细调查,这一调查重在以婚姻为基础形成的嘉戎藏族家屋(家族)群体[23](P408~432)。这些调查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随着西南人类学研究渐次深入,对于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理解,对于社会、群体的研究概念与视角的认识和理解,存着一个不断深化及转化的过程。
与此同时,不仅是西南中国人类学的民族志作品涉及对群体的讨论,《江村经济》《金翼》《山东台头》这三本1949年以前出现的经典民族志作品中,也都涉及了群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如马凌诺夫斯基所说的《江村经济》是一个土地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过程的研究[24](P16),费孝通晚年时也承认这一研究是一个“农户家庭再生产的过程”[25](P327)。因而,《江村经济》可以说是以经济生活为基础,来看长江流域汉人家户群体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林耀华的《金翼》,通过对地域社会中家族群体兴起与流变的梳理,来考察地方社会在大时代背景下的变迁[26]。而《山东台头》则通过对初级群体、次级群体及村落层次群体及跨村落群体的细致描述,将一个乡村社会的生计、政治、信仰作了深度呈现[27]。不过,在对这三本经典民族志文献的分析中,联系之前所陈述的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社会这一研究概念进入中国学术体系以后,不同的地区、人群,是如何看待和理解社会的?这既涉及到研究对象是如何看待社会的,在他们眼中社会是怎么样的,更涉及到研究者对社会的理解和阐释的问题。群体的研究概念、视角的出现,似乎可以看成是人们对于所研究、所讨论之西南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本身特殊性的思考和反应。不过,相应地也就产生另一个问题:在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中,为什么群体的概念会被渐渐突出?该如何来理解和解释这一问题?原因如下:
首先,涂尔干对于社会这一研究概念的梳理和论述中,始终有一个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的二元结构性视野在里面。同时,涂尔干对于社会这一概念的论述,是建立在对西方社会发展过程的理解上,以西方社会为蓝本建构的理论概念。这样的理论概念一旦尝试于与西方社会组织原则和结合性质迥异的少数民族社会及汉人社会时,就会产生一个适应与对话的问题。其次,少数民族社会自身特殊性的问题,西南少数民族在社会组织的性质上,相对于涂尔干的“社会”,强制性要弱一些。进一步说,血缘、地缘特别是血缘与“社会血亲”[28](P24~34)、拟制亲属[29](P126~146)等因素,在其社会组织与结合过程中往往具有基础性作用。因而,由这一类别与关系所确立的群体,往往是这些社会中常态且基础性的存在。再次,中国人类学研究在起步时,就非常强调“社区研究”,并以此作为实现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的切入点[30](P122~158)。在一个微型的社区中进行调查,群体的行为及其结合过程,是比较容易被观察和看到的[31](P478),也是相对容易操作的研究对象、研究概念和视角。因而,从概念建构自身、本土社会特殊性及本土研究体系对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过程本身的建构上,大体上可以理解为什么群体的研究概念会在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中逐渐被突出。
三、何以成群:概念史的形成及其比较
上述与群体相关的大部分研究,并没有直接说明在研究过程中对社会与群体之间关系的问题是如何来考虑的?对群体这一概念和视角本身,又是怎样来理解和思考的?这一问题,事实上涉及到如何理解早期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方法论及其研究逻辑。对于群体的论述中国社会古已有之,如荀子的“人之生,不能无群”[32](P143)等,而群体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和研究视角的理解、接受与论述,则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因而,有必要对在西学东渐的近代化过程中,人类学学科先贤们对于社会、群体关系及群体本身内涵的思考做一个回溯。这里将以严复、潘光旦、费孝通三位先生的思想作为回溯的目标,不仅因其是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具里程碑式意义的人物,而且他们在接受西学的同时,也都有建基于本土文化传统及个人智识上的创见和新论述。
严复将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译为《群学肄言》,认为群学所建基之基础——群体,“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33](P38);也就是说,群体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个人的性质决定了群体的性质。如果说“群者谓之拓都(Aggregate),一者谓之么匿(Unit)”,“独么匿之所本无者,不能从拓都而成有,么匿之所同具者,不能以拓都而忽亡”[33](P38~39)。因而,在严复的论述中,群体是个人为了某些需要汇聚而成,个人的品性决定了群体的品质及其功能与作用。而潘光旦认为,形成群体存在着“品质的同异”、“同异之辨”、“同义辨别的自觉”三个基本条件[34](P147),即强调个人的差异性是群体形成的基础[34](P148)。潘光旦以分合、聚散、鼎革为社会学研究的前提,特别强调对类别的分析与把握;因而,他认为,以个人的差异性与能动性是群体、社会关系建立或者说是群体形成的前提[34](P146~150)。综合来看,在群体问题的思考上,严复虽然认为群体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但其论述方向以群体本位为基础;而潘光旦则将论述重点转向群体中个人的差异性和能动性,可以说是个人本位的论述。这两种论述方向都代表着中国学术界与学人对于群体这一问题的思考与探索的过程。
费孝通晚年在将自己一生的学术历程,放入到个人、群体、社会的视角下进行回溯和反思时,认为自己是在严复的群体观中入门社会学的[35](P469),但在《生育制度》中,他认为群体并不仅由个人所组成,而具有自身的力量、影响轨道的群体实体论观点(即与涂尔干的社会实体论相似)。并以自身在“文革”经历的过程为例,将这两种不同的群体观点进行综合的思考、比较和讨论,认为群体实体确实具有巨大的力量,但同时也一直有一个具思想和感情的个人或“自我”与之相对抗。在这一基础上,费孝通重提潘光旦早年对他的批评——只看到社会、文化、群体,忽视个人在其中的基础性作用[36](P73~111),认为自己确实在某些方面没有注意到人的能动性[35](P467~490)。同时,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这三位先生的论述中,虽然认为由不同群体汇聚而成社会,但他们的群体指向与社会是可以互相指代的。
从群体本位到个人本位,再到群体实体论观点的出现,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对于群体概念的本土理解,事实上与西方社会概念的发展过程存在着一个相似的路径,即从作为具像的群体走向作为研究概念的群体。但以1949年以前本土社会对于群体的概念史建构过程来反观同一时期的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可以看到在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过程中,对于群体概念的应用主要采用严复的群体观点来考察自身的研究对象、建立自身论述的逻辑基础。因而,在这一时期的西南中国人类学论述中,大部分情况下只看到某一族群(人群)的“群相”,而不见群中之个体。同时,费孝通在西南地区完成的《生育制度》中,将群体视为具无所不在之规训性力量的独立实体之群体实体论观点,并没有在这一时期的西南中国人类学实地研究中进行深入应用和拓展。与本土群体概念形成过程中其与社会概念可相互指代的特征相似,在1949年以前的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中,既将群体或群体性存在视作某一族群社会(或西南区域社会)的基础,也将对群体的论述与社会相互指代。因而,从研究概念本身的建构、应用过程来看,1949年以前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中,对于群体这一概念的应用和理解,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具像的群体,而不是将其作为研究概念本身来进行分析和讨论。换言之,从作为具像的群体到作为研究概念的群体之转变过程,尚未完成。
在所谓的人类学中国化问题上,虽然论者深刻分析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可行性路径、代表性人物等,却基本上没有对研究概念的建构、应用及变迁的过程进行讨论。由早期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概念史梳理,来回望和反思被长期关注的人类学中国化问题,可以发现在中国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对研究概念、研究视角本身的理解和应用,而没有对研究概念、视角本身的深入理解,并在实地调查和研究过程中进行应用和再讨论的话,人类学中国化过程本身就会存在着偏差和失衡。过程的不完整,同样也会造成中国化目标达成的困难。如果说在学科史的梳理过程中研究方法、对像是显层次的问题,那么研究概念、视角的建构与应用就是深层次的问题。
当下西南中国,处于市场经济背景的“新常态”之下,与以往历史时期迥然不同。面对由市场而来的人的流动过程,个人意识、个体主义蔚然成风,如何讨论新历史背景下群中之个体,成为当下研究必然要面对的课题。正如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言,当市场机制“脱嵌”时,必然会对社会组织基础形成深刻的影响[37],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原先以血缘、地缘、信仰等为结合基础的群体,会否发生变化?又该如何理解和分析这一变化?同时,西南中国跨境民族众多,市场化背景下的跨境民族问题,成为这一地区醒目的社会现象。在这一背景下,群体本身的规训性力量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它又是如何在境内、境外两个不同场域中存在的?同时,群体作为一种超社群、国境的文化-政治单位,是否仍然发生作用?而对于早期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研究概念和视角的梳理,不仅可以为当下新分析概念的建构提供历史经验和逻辑基础,也可以对具体研究本身进行定位和创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