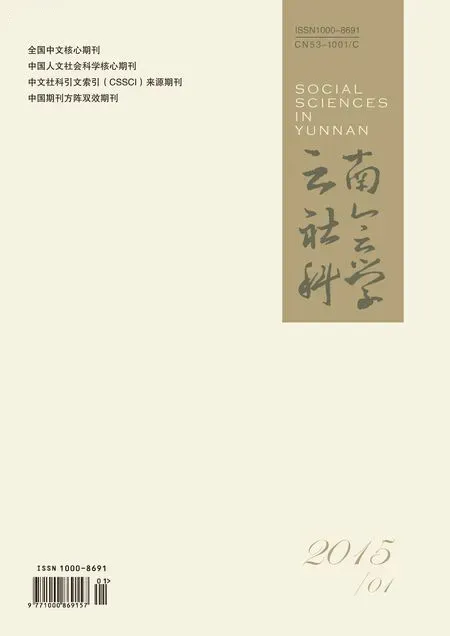南宋遗民诗人的心理认同与诗歌创作
谢 丽
在中国历史上,每逢江山易代之际,总会出现一个独特的士人群体。这些于鼎革动乱中持志守节、隐遁草莽、不仕新朝的士人,不仅以高尚的志节捍卫了民族与自我人格的尊严,而且还为当时的文坛书写下璀璨的篇章。对于这类有着特殊社会身份的士人,往往被称之为遗民*本文关于“遗民”的具体所指来自张兵先生的《遗民与遗民诗之流变》一文。该文认为:作为遗民,首先必须是生活于新旧王朝交替之际,身历两朝乃至两朝以上的士人,且在新朝不应科举、不出仕;其次,内心深处必须怀有较强烈的遗民意识。。国学大师钱穆曾说,遗民的出现是“世变时代不可或缺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现象”[1](P120)。于是,在宋元易代、蒙汉异质文化剧烈碰撞冲突的社会背景下,亦产生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士人群体。他们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或遁迹山林、笑傲江湖,或卜卦为生、以死明志;或避居草野、著书立说,或狂饮买醉、以诗言志……这就是心怀黍离麦秀之悲、矢志守节、隐居不仕的南宋遗民诗人。
南宋遗民诗人是历代遗民中颇具特色的一个文人群体。他们亲身经历了家国沦丧、改朝换代的风云变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少数民族文明彻底征服华夏文明的历史,并由曾经享有优渥待遇的文人雅士沦落为最下等的亡国之奴。民族的灾难与动荡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南宋遗民诗人的人生道路。独特的遗民身份和苦难的经历,则使他们的文化心理呈现共同的趋向,并进而凸显出这一诗人群体的创作共性。探讨南宋遗民诗人的心理认同与诗歌创作,既是研究宋末遗民社会现象的必要环节,也是剖析中国遗民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鉴于此,本文拟从创作群体心理认同的角度切入,考察南宋遗民诗人的诗歌创作,以期推进现今对南宋遗民诗人研究的深入思考。
一
宋末元初是一个山河巨变的时代,伴随着彪勇强悍的蒙古铁蹄的长驱直入,摇摇欲坠的南宋王朝最终彻底覆灭。这次鼎革之变迥异于以往历代政权之更迭在于:自诩为正统的泱泱华夏民族被“蛮夷”的少数民族取而代之,蒙古族成功地实现了“以夷变夏”。显然,蒙古族的入主中原给予了以华夏正统自居的儒家知识分子致命的一击,使他们思想中曾经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理论,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对于南宋遗民诗人而言,宋元易代也就并不仅仅意味着单纯的朝代更替,它更意味着“以夷变夏”带来的奇耻大辱,意味着在异族异质文化统治下汉民族文化面临的断裂之忧。于是,新旧易代不仅使这一批士人转变了人生观、价值观,而且也促使他们的心态和诗歌创作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么,深受夷夏文化观念与程朱理学思想影响的南宋遗民诗人,是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时代的沧桑巨变的呢?
面对家国的沦丧、民族歧视的屈辱以及个体的严重失落,以谢翱、林景熙、谢枋得、汪元量、郑思肖等为代表的南宋遗民诗人,皆无法达成对元朝新政权的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于是在共同的社会历史与文化氛围中,怀着离乱亡国的巨恸和自身失落的哀戚,他们产生了趋于一致的心理认同,这就是鲜明的悲愤忧患心理与隐匿遁世心理。
作为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遗民群体,悲愤忧患心理无疑是南宋遗民诗人最具趋同性的一种心态。这种心理认同既是宋末元初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下遗民诗人们炽烈之民族情感的普遍反映,也是其激昂之爱国情怀的显著体现。面对亡国之恸、家国之恨,这群满怀忧国忧民之思,却壮志难酬的遗民诗人,纷纷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悲愤之情与忧患之心。他们或坐卧不朝北,或登西台恸哭,或扮乞丐收拾帝王残骸剩骨,或画兰不画土,或屡辞征召……就这样,作为宋元易代这一动荡的巨变时代的参与者,他们表现出了拳拳的爱国情怀与故国忧患意识。遗民诗人谢枋得曾慷慨激昂地说:“宋室孤臣,只欠一死”[2](P1)“某愿一死全节久矣”[2](P11)。因此,当被元朝政权强行征召北上时,他是以绝食抗争、以死殉节来表达对元廷统治者强烈的抗议,亦表现出华夏士人豪迈的英雄气节。其他遗民诗人虽然并不都是谢枋得这样视死如归的英雄,但却仍然是有着铮铮铁骨的忠臣义士。他们对灭其宗国的蒙古政权有着强烈的愤怒,对已不复存在的故国怀着深深的眷恋。例如诗人林景熙就是出于民族义愤,冒着生命危险拾取并掩埋宋帝遗骨;士人郑思肖在南宋灭亡后,即改名思肖,字忆翁,号所南,并隐居吴下,匾其室曰“本穴世界”,暗寓思念故国、不忘大宋之意。*“思肖”,取“肖”从繁体字“趙”的偏旁之意;“忆翁”,表示不忘故国;“所南”,表示以“南”为“所”;“本穴世界”,移“本”字之中的“十”置“穴”中,即为“大宋”二字。其实,无论是绝食殉难的谢枋得,抑或不顾自身安危冒死收葬宋陵骨骸的林景熙,还是听人讲北方话即掩耳疾走的郑思肖,他们不同的举止行迹表现出的是南宋遗民诗人强烈排斥异族政权、深深怀念故国旧君的一致心态。当然,除了以自己的言行来宣泄蕴藏于心中的忧愤苦恸外,遗民诗人们还借助诗文表露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在诗文中,他们或书写故国沦亡后的悲愤,或控诉蒙古贵族野蛮的侵略行径,或表达对民族命运的强烈担忧,或理性反思国家灭亡的原因,或抒写“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3](P265)的沉痛……虽然恢复宋室的热切渴望已无从实现,但南宋遗民诗人持志守节、不屈抗争的姿态和努力,体现出的是他们坚贞忠烈的遗民气节与悲愤忧患、誓不屈从的群体心态。这种在家国危难之际勇于抗争的悲愤忧患心理,正是南宋遗民诗群区别于以往遗民群体最显著的心态之一。
此外,隐匿遁世心理则是南宋遗民诗人另一突出的普遍心态。宋末元初改朝换代的政治动荡,不仅使得遗民诗人无法成就自我的功名事业、实现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且在异族的统治下,他们根本找不到自我的归属,既不能继续效忠于宋朝,又矢志不仕于元朝。就这样,他们被无情地抛在了宋元易代的历史夹缝中。不过,虽然国已破、家已亡,但士人的忠贞却始终未曾改变,这是宋末遗民诗人最基本的坚持。于是,遗民身份成为这一群士人唯一的选择,而隐匿避世心理也随之成为他们共同而普遍的心声。因此,放弃用世之志,以出仕元朝为耻,以逃离遁世、浪迹山水为尚,成为他们心理上共同的情感倾向。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宋亡后,遗民诗人谢翱退隐浙东、林景熙隐居家乡、郑思肖避地苏州、谢枋得曾入建宁唐石山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南宋遗民诗人的避世心理与历史上那些高蹈出世的逸民隐士有着本质的区别。这诚如方勇先生所言,南宋遗民诗人“无论是放浪山水、啸傲田园,还是寄身佛寺、栖隐道观,隐逸抗节是他们的共同特征”[4](P198),他们所“呈现的高蹈飘逸的表层形式,哪里能掩抑得住其深层结构中的愤激情绪呢!”[4](P205)的确,宋末遗民诗人的隐退避世具有时代的独特性,诗人们逃匿避退的表象,实际上是对新朝不合作与抗拒的深层心理的反映。对南宋遗民诗人而言,在确认元朝政权一统天下的现实无法改变,自己也无力改变时,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着手自救。于是拒绝与新政权合作、避世隐居拒不出仕、守护自我人格尊严,成了他们共同的选择。就这样,在特殊的时代境遇中,南宋遗民诗人以特有的隐匿遁世方式证明了自我的存在与价值。因此他们的隐逸避世,既是坚持民族气节的自我救赎,也是对新朝的一种自觉反叛。而这种倾向于“政治性退避”[5](P85)的隐匿避世心理,显然有别于以往士人悠闲飘逸的隐逸之风,它是南宋遗民诗人又一独特之群体心态的表现。
由上可知,宋末元初的易代之变给南宋遗民诗人以巨大的心灵震荡。强烈的内心体验与深沉的遗民情怀,使他们显现出悲愤忧患与隐匿遁世的群体心态。诗人群体的这种心理认同使得他们的命运更显苍凉与悲怆,当然也使他们的诗歌显现出有别于以往的特质。因为,正是在这种悲愤忧患与隐匿遁世的心态激发下,诗人们在诗坛前贤杜甫与陶渊明的精神世界与诗文世界里找到了与其相通的契合点。于是,宗杜与祖陶式的诗歌创作成为宋末遗民诗人忧愤痛苦和逃匿避世心迹的外化,并进而带来了他们诗歌创作迥异于前朝的新变。
二
南宋遗民诗群突出的悲愤忧患心理,使诗歌在他们笔下不再仅仅是自我性情的吟咏与表达,而是一种表现亡国之哀痛的记录、一种对已覆灭之政权的追念反思,以及反叛现状的宣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汉民族文化代言人的宋末遗民诗人,将激赏的目光投向了在艰难时势中仍“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6](P19)的唐代诗人——杜甫,宗法杜甫也因此成为宋末遗民诗人共同的师学指向。
作为诗人群体,南宋遗民诗人虽然各具特色,但相似的经历与遭际却使他们无一例外地将忠君爱国的杜甫作为师学的首选对象,无不表现出对杜诗的钟爱仰慕之情。如烈士诗人谢枋得称誉杜诗“辞情绝妙,无以加之”[7](P197);追慕杜甫的林景熙说“天宝诗人诗有史,杜鹃再拜泪如水”[8](P43526);自称“大宋孤臣”的郑思肖诗云“突然骑过草堂去,梦拜杜鹃声外天”[9](P225);即使是少时不解杜诗佳处的汪元量,在宋亡后再读杜诗时亦曰“斯时熟读之,始知句句好”[10](P121)。此外,谢枋得还在《谢张四居士惠纸衾》中云:
独怜无褐民,茅檐冻欲偾。
大裘正万丈,德心欠广运。
天下皆无寒,孔孟有素蕴。
愿与物为春,衾铁吾不愠。
显然,这正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博大之儒者情怀的体现。可见,宋元易代之变所带来的宗社种族及个体的巨大不幸,促使遗民诗人与生逢乱世、在颠沛流离中仍念念不忘国事、天下事的杜甫产生了共鸣。诗人们纷纷认识到心怀忧国忧民之思的杜甫与充溢着诗史精神的杜诗的可贵价值。于是,在表达对杜甫的钟爱、尊崇之余,他们还自觉秉承起杜甫“以诗存史”的创作精神。一股宗杜学杜的热潮在当时的诗坛蔚然成风,师法先贤杜甫便成为风行一时的群体创作行为。
在这股宗杜的诗学热潮中,遗民诗人尤为看重的是杜甫诗史的创作精神。因为,他们知道元朝的官修史书在记载宋末元初这一段历史时,必然会抹杀前朝的诸多事迹。于是,不容青史尽成灰的遗民诗人便赋予了诗歌记忆的功能。诗人郑思肖曾这样阐发诗与史的关系:“夫天下治,史在朝廷;天下乱,史寄匹夫……史而匹夫,天下事大不幸矣。我罹大变,心疢骨寒,力未昭于事功,笔已断其忠逆。所谓诗,所谓文,实国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系焉。”[11](P196)这种“亡国谁修史,遗民自采诗”[12](P40963)的创作理念,使南宋遗民诗人如实地用诗歌记录了国破家亡的重大史实,记录了人民离乱的不幸生活,记录了元代统治者残暴野蛮的侵略行径,以及对故国故君的深深眷念等。比如郑思肖的《陷虏歌》:
德佑初年腊月二,逆臣叛我苏城地。
城外荡荡为丘墟,积骸飘血弥田里。
城中生灵气如蛰,与贼为徒廿六日。
蚩蚩横目无所知,低面卖笑如相识。
诗人便用饱含血泪的文字真实记录了苏州沦陷后,元朝统治者杀戮生灵的暴行,其悲愤忧患之情与忧国忧民之心与杜甫如出一辙。另如谢翱的《过杭州故宫》:
紫云楼阁宴流霞,今日凄凉佛子家。
残照下山花雾散,万年枝上挂袈裟。
则如实书写了宋王朝覆灭后昔盛今衰的凄凉现状,真切抒发了诗人故国黍离之悲音。像这样以纪实的笔法书写亡国之恸与表达爱国情怀的诗作,在南宋遗民诗人中比比皆是。此外,深受杜甫诗史精神影响的林景熙,记录其收葬宋陵遗骨的诗歌《梦中作》,则被时人比之为杜陵诗史。他在《杂咏十首酬汪镇卿》中所云:“何人续迁史,表为节义雄”,表露的亦是以诗歌存录易代之际忠臣义士之节义行为,以补正史之缺的创作理念。就这样,宗法杜甫的南宋遗民诗人,用诗歌承担了“官修史书由于权力话语的遮蔽而无法记录的史实的责任,实践了‘史’的真正意义”[13]。而在这股以诗为史的宗杜潮流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诗曰“我更伤心成野史,人看野史更伤心”[14](P37)的汪元量。
宋亡后,汪元量由于其特殊的琴师身份,随宋室三宫北迁,滞留燕京十余载,终以黄冠道士身份南归。由于这段特殊的经历,他得以见证了南宋政权覆灭的全过程。作为这场时代巨变的受难者与见证者,汪元量秉承杜诗“诗史”之创作精神,以诗的形式和史的笔法,真切记录了南宋亡国这一段“伤心野史”。他的诗作《湖山类稿》以七绝组诗的方式,将正史多未记载的元军入城、宋室投降、三宫北迁及其抵达燕京后的不幸遭遇等完整记录下来。钱谦益称其诗歌“周详恻怆,可谓诗史”[15](P1764)。其诗作中,尤为人称道的则是最得杜诗创作精髓的98首《湖州歌》、20首《越州歌》及10首《醉歌》。这众多的组诗皆以杜甫联章体的创作形式,如实记录了南宋覆亡前后的史实。它们犹如一幅幅规模宏大的诗史性画卷,从不同角度还原和揭示了宋元易代那段真实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真可谓亡国之诗史也。而汪元量的以诗写史,恰是对杜甫诗史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如上所述,南宋遗民诗人宗法杜甫之诗歌创作,是诗人们出于以诗存史、保留宋室覆灭事迹的目的。但实质上,这种取法杜诗诗史精神的诗作,在赋予诗的记忆功能的同时,更是宋末遗民诗群悲愤忧患之群体心态的反映,是一代遗民的泣血心史。当然,这种宗杜式的诗史性书写在为身历易代之变的遗民诗人,提供宣泄其忧患悲愤心理的渠道和抚慰其痛苦心灵的同时,也促成了宋末诗歌不同于往昔的新变。这种新变主要体现在:南宋遗民诗人重在纪实的诗史性创作,彻底颠覆了宋季诗坛原有的以才学为诗、以诗为戏的诗学理念。它一反当时诗坛气骨孱弱衰敝的诗风,而新变为风格沉郁、内容充实的遗民诗风。诚然,正是这种新变之后的诗史性文本,使得南宋遗民诗歌成为“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16](P772)的最佳注脚。
三
在宗杜学杜潮流成为鼎革之际南宋遗民诗国极为独特的诗学景观的同时,有着强烈隐匿避世心态的遗民诗人又将“古今隐逸之宗”——陶渊明,奉为师学指向的另一楷模。
改朝换代之际,家国覆亡的惨痛现实促使不愿屈节出仕新朝的宋末遗民诗人,把终老山林、退居江湖作为人生道路的必然选择。师学陶潜,便是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独特之心理体验的一种反映。显然,窘迫的现实生存环境与隐逸避世的心理态势,都将遗民诗人的价值取向导向了传统文化中出世的精神世界。这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就和诗圣杜甫一样,成为南宋遗民诗人争相尊崇效仿的又一典型。他们或仰慕陶渊明别有情致的田园生活,或激赏他退隐守节的气节情操,或爱慕他真淳自然的人格品行……因此,正是其共同的隐迹遁世心理,促使这一批士人把隐居守节、不仕二姓的陶氏视为追慕的对象,在宋末诗坛尊杜学杜的同时,亦掀起了一股尊陶学陶热潮,并由此凸显出诗人群体又一鲜明的创作共性。在这股祖陶的诗学潮流中,遗民诗人们创作了大量咏陶、和陶之作。比如谢枋得的《庆全庵桃花》:
寻得桃花好避秦,桃红又见一年春。
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
诗中清新可人的自然景致,犹如陶潜笔下的桃花源世界一样让人沉浸与向往,而飘荡回旋于字里行间的无疑是遗民诗人们共有的那份遁迹避世的隐匿情怀。另如宋亡后隐居家乡的林景熙所做的《薛德之之江东简熊西玉诸公》:
乍逢还又别,龙竹葛陂阴。
野水流春远,江云入暮深。
新知满湖海,遗老在山林。
解后如相问,凭君道素心。
该诗则借江云入暮、野水流春、龙竹葛陂等自然景色,道出了诗人对素心自居的隐逸生活的钟爱之情。再如郑思肖歌咏陶潜的《桃源图》中“有耳不闻秦汉事,眼前日日赏桃花”,谢翱《二月十日》中“独拟寻鸡犬,云萝挂葛巾”等诗句,都无不表现出遗民诗人面对安顿自己灵魂之所在的自然山水、日常生活事物时的那份沉醉与逃逸式的忘情。正是如此,宗法陶渊明式的隐逸之歌成为当时响彻南宋遗民诗坛的另一时代主旋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南宋遗民诗人浓浓的隐匿避世情结,促使他们从山水自然中去寻求精神的抚慰与心灵的慰藉,一起深情地吟咏起祖陶之歌,但亡国的深恸巨哀却时时刻刻啃噬着他们的内心。因此即使是仰慕并宗法陶渊明,但踯躅于残山剩水间的遗民诗人,实质上是无法真正创作出陶渊明那种物我两忘、冲淡自然的山水田园诗的。事实上,他们祖陶式的隐逸遁世之歌体现的是一个特殊时代的诗人群体,对自我生存境遇与人生道路的思考和选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退居山水林泉的遗民诗人齐声唱起的咏陶、和陶之歌,就仅仅是秉承了陶诗山水田园之貌,而陶诗之怡然世外、遗世独立的内在神韵则被遗民诗人所忽略,取而代之的却是一股潜藏于隐匿旋律之下不屈抗争与表白心迹的暗流。例如郑思肖的《陶渊明对菊图》:
彭泽归来老岁华,东篱尽可了生涯。
谁知秋意凋零后,最耐风霜有此花。
在歌咏陶潜的背后,赫然掩映的是在特殊时代语境中隐匿抗争的遗民诗人对不屈之民族气节的诚挚呼唤。再如林景熙的《答柴主簿》:
山林未遂鹿麋性,风雨空愁葵藿心。
老气十年看剑在,秋声一夜入灯深。
诗人虽身已隐居山林,但亡国之巨恸难以忘怀,那颗忧愤沉痛的心始终难以平复。可见,在宋末诗坛响彻耳畔的咏陶、和陶声中,尽管诗人们沉醉于“眼前日日赏桃花”的自然美景,忘情于“独拟寻鸡犬,云萝挂葛巾”的农家生活,但这些却都与陶诗和谐静穆的人生境界、恬淡自然的美学世界无关。遗民诗人更看重的是陶潜忠于晋朝、义不二仕的高洁品质,是陶诗关注一己之心灵建构的真情书写。所以,与他们遁迹不仕的心理认同相契合,遗民诗人以隐匿避世的生存方式和祖陶式的言说方式,意欲表达的不过是其故国覆灭的哀思、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以及对新朝的不满而已。就这样,陶渊明笔下原有的山水意象在遗民诗作中被赋予了特别的意蕴,它们成为遗民诗人抒发亡国之惨痛记忆的诗性代码。而遗民诗人就用这种祖陶式的隐逸之歌、并以一种隐匿避世的姿态,证明自己仍旧属于南宋。
综上而论,国破家亡后,南宋遗民诗人在悲愤忧患与隐匿避世心态的激发下,不约而同地将杜甫与陶渊明作为吟咏效仿与精神寄托的对象,宗杜与祖陶亦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两种典型范式。如果说作为悲愤忧患心理之外化的宗杜式诗歌创作,承载了遗民诗人以诗存史的恢宏志向,那么作为隐匿遁世心理之外化的祖陶式诗歌创作,则暗含了在乱世中自持秉节的遗民诗人欲借自然山水慰藉心灵与表白心迹的创作动机。当然,这两种由诗人群体特有的遗民心理所生成的诗学范式并非截然二分,它们往往相互杂糅、并行不悖,出现在同一个诗人的笔下。而这种反映一代士人忧愤沉痛又隐逸避世之复杂心理的遗民诗作,则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这恰如钱谦益所言:“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17](P800)由此可见,宋元易代不仅改变了大宋王朝的命运,改变了士人的心理,也改变了诗歌的发展轨迹。因此,南宋遗民诗人的心理认同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有力诠释了“客观存在决定诗人心态、心态特征影响诗歌创作”[18]这条基本的文学创作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