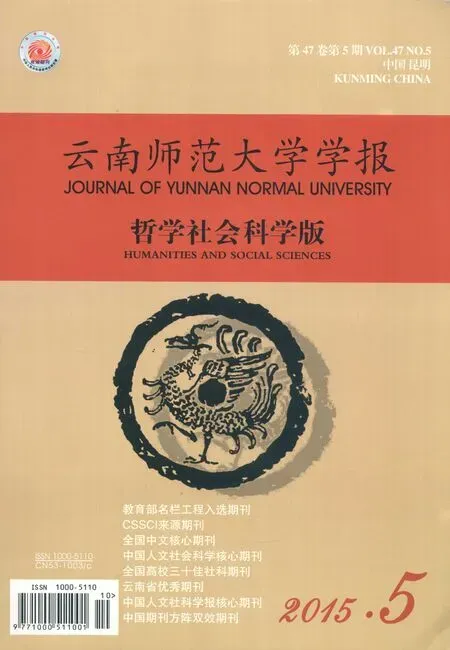地方性知识及其反思
——当代西方生态人类学的新视野*
罗 意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少数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乌鲁木齐830054)
地方性知识及其反思
——当代西方生态人类学的新视野*
罗 意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少数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乌鲁木齐830054)
【主持人语】本栏目为3篇生态人类学论文。第一篇《地方性知识及其反思——当代西方生态人类学的新视野》以国际生态人类学的前沿视野评述地方性知识研究的问题和进展。在当代环境问题突显、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遭受严重威胁的情势下,生态人类学继承其学科传统——专注于地方性知识的研究和利用,使其更加贴近时代脉搏。由此带来的问题——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与局限、与现代性和普遍性之关系、与自然保护之关联、与现代科学之“糅合”、知识产权和权益分配、在全球与地方政治中发挥何等作用等,成为绕不开的理论难题。本文梳理当代西方生态人类学地方性知识研究的转型及研究进展,对地方性知识进行深度剖析与反思,并联系国内相关研究进行探讨,颇具启示。第二篇《云南新平傣族生计模式及其变迁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以云南新平县戛洒镇大槟榔园傣族村落为田野点,应用生态人类学的文化适应理论,分析该村传统生计模式变迁及其对生态文化的影响。在现代化、城镇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此典型案例研究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在继承传统生计模式的基础上,该村村民能以较为主动的方式融入经济市场中,积极适应新环境,努力创建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复合型生计形态,颇具借鉴意义。第三篇《德昂族仪式性茶消费:物质消费边界的跨越》,是不可多得的以茶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论文。当下茶及茶文化的研究十分热闹,然而真正的人类学著述并不多。本文着眼于人类学经典话题“仪式性消费”,研究德昂族的茶,发现了德昂族对茶具有4类仪式性消费形式:生命周期仪式对茶的仪式性消费、生命危机仪式对茶的仪式性消费、家庭做摆仪式对茶的仪式性消费、年度仪式对茶的仪式性消费。通过对4类仪式消费的分析研究,得出仪式性消费是一个超越物质消费边界的文化生态体系,其文化生态性维系和保障着人类的生存安全和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同时展现出传统生态文明的地方性与实践性的新颖结合。
(学科主持人简介:尹绍亭,男,云南梁河人,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生态人类学、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保护等。)
最近20年,西方生态人类学地方性知识的研究发生了深刻转变,包括三个方面:现代性语境中地方性知识的边缘化与再发现,生态上的“高贵野蛮人”神话之颠覆和迈向实践领域的地方性知识研究,地方性知识的限度、权利及与全球和地方政治关系之反思。文章对这一转变和地方性知识最新研究进展进行评述,重点对地方性知识的反思进行剖析,并阐明这些研究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启示。
地方性知识;反思;生态人类学
生态人类学对地方性知识有着一种天生的迷恋,这既是对人类学专注简单、原始或无文字社会的文化、习俗、实践和制度的传统之继承,又是对区域和全球性环境问题之回应。①AndréBéteille,The Idea of Indigenous People[J].Current Anthropology,Vol.39,Mo.2,1998.不管研究区域或问题有何差异,生态人类学家都认同学科肩负两大使命。其一,收集、记录和拯救那些独特的处理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使之免遭现代化和全球化之破坏;其二,从各种地方性知识中获取教诲,开启人与生态相和谐的另一种可能。最近20年,西方生态人类学对地方性知识的研究发生了重要转变,主要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地方性知识与现代性之关系为何?与生态环境的平衡是地方社会有意识保护自然的结果,还是地方性知识在各种条件下实践的结果?地方性知识有何价值,又有何不足?地方性知识在全球与地方政治中扮演着何种角色?本文对当代西方生态人类学地方性知识研究的转型及研究进展进行评述,重点对地方性知识的反思进行剖析,并阐明这些研究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启示。
一、边缘化与再发现:现代性语境中的地方性知识
现代性既助长了地方性之流行,也对地方性形成了威胁。①Michael R.Dove,Indigenous People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35,2006.一方面,西方科学知识之确立及全球扩展导致地方性知识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当西方科学知识面对全球环境危机表现得虚弱无力时,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解释和解决危机的可能再次被发现。
地方性知识已经成为人类学话语体系中最为人熟知和引用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尚未有关于概念的明晰界定。主要原因是“地方性与非地方性”具有很多高度特殊的区域与历史内涵,这些内涵并不总是适应于其他民族志的情境,导致比较归纳相当困难。②Roy Ellen and Holly Harris,Introduction,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Criticl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C].Edited by Roy Ellen,Peter Parkes and Alan Bicker,Harwood Acdemic Publishers,2005:2.因此,概念的阐释就成为一连串的特征归类。它是地方的,口传的或通过模仿与示意传承的,镶嵌于更大文化传统之中的,重复性的,在群体内分布非均衡的,变迁的,被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的,被发现与遗失并存的,也是日常生活实践的产物和一种经验性的知识。③Roy Ellen and Holly Harris,Introduction,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Criticl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C].Edited by Roy Ellen,Peter Parkes and Alan Bicker,Harwood Acdemic Publishers,2005:4~5.这些特征是与科学知识相对而言的,不同地区的地方性知识也具有相对性。地方性知识包括三个层次:其一,经验性的知识,涉及对动植物的认知,以及利用它们的目的与方式;其二,知识的范式——理解,即对经验观察进行解释,并将之置于更大的情境之中;其三,制度性知识,指知识镶嵌于社会制度之中。④Arne Kalland,Indigenous Knowledge:Prospects and Limitations,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Criticl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C].Edited by Roy Ellen,Peter Parkes and Alan Bicker,Harwood Acdemic Publishers,2005:320:321.
地方性知识也是被误读最多和引发争议最多的词汇之一,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视之为“普遍性知识”的对立面。格尔茨对此做了回应,指出“这种对立不是‘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的对立,而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比如神经病学)与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比如民族志)的对立”。⑤克利福德·格尔茨.烛幽之光:哲学问题的人类学省思[M].甘会斌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124.与来自民族志的地方性知识相对立的,是随着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全球扩张所带来的科学知识。罗伊·艾伦等人指出,科学知识植根于西欧传统民间知识及其整合,事实上也整合了亚洲与美洲的一些地方性知识。但在这一过程中,其他地方性知识被置于科学性实践的对立面。⑥Roy Ellen and Holly Harris,Introduction,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Criticl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C].Edited by Roy Ellen,Peter Parkes and Alan Bicker,Harwood Acdemic Publishers,2005:6.现代制度的“脱域”机制将话语从地方情境中抽离出来,使其在无限的时空中得以表述,这与强调地方与历史情境的地方性知识难以相容。⑦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18.科学范式方法论上的化约主义和价值评判将地方性知识贬斥为“非科学”。20世纪全球科学内在的民族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又使科学家很难接受民间尚存任何有价值的知识。①Roy Ellen and Holly Harris,Introduction,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Criticl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C].Edited by Roy Ellen,Peter Parkes and Alan Bicker,Harwood Acdemic Publishers,2005:11.伴随着西方科学知识的崛起及其全球传播,各种地方性知识被边缘化。
当代环境危机和科学主义范式的衰落,为地方性知识的再发现创造了机遇。阿恩·卡兰指出,科学主义范式建立在笛卡尔式的世界观基础之上,强调主体与客体、身与心、文化与自然、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之二元分离。他呼唤一种人与自然不再分离和对立的、有机体与环境成为各自内在组成部分的范式——这正是大部分非西方社会的固有特征。②Arne Kalland,Indigenous Knowledge:Prospects and Limitations,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Criticl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C].Edited by Roy Ellen,Peter Parkes and Alan Bicker,Harwood Acdemic Publishers,2005:318.人类学家将目光转向被边缘化的地方性知识,记录和整理它们,使之系统地保留下来以供发展规划与实践者所用。在这个过程中,浪漫主义者发现了与自然保持平衡的“高贵野蛮人”,狩猎采集民、传统农民、游牧民、渔民等被重新想象为富有文化的、具有自然智慧的人群。实用主义者发现了丰富实用的地方性知识,认为它们可以成为更成功发展干预的基础。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也送来橄榄枝,将地方性知识纳入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的项目之中。
在实证研究中,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与环境的关系是核心问题,涉及栖息地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维系两个层面。狩猎采集民与渔民采取一种“控制短期收益,以保障长期收益”的策略,游牧民根据“水草资源”非均衡分布的特征选择周期性移动的策略,长久有效地保持着资源的可持续性。③Lore M.Ruttan and Monique Borgerhoff Mulder,Are East African Pastoralists Truly Conservationists?[J]. Current Anthropology,Vol.40,Mo.5,1999.传统农民发展出了保持土壤肥力更新、控制水土流失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甚至将有用的野生动物整合进资源管理体系之中的实践策略。④Alcorn J,Ethnobotanical knowledge system:a resource for meeting rural development goals.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development: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C].Edited by D.Micheal Warren,L.Jan Slikkerveer and David Brokensha,London: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1995.这些地方性的资源利用也有助于生物多样性之维系,证据来自4个方面:1)在人类历史上,对物种之威胁并不来自小规模原住民人群;2)丰富的地方性知识;3)基于这些知识的特殊管理实践,涉及动物与植物种群的维系;4)关于动植物之信仰与仪式性利用,确保原住民致力于保护这些物种。⑤Benjamin S.Orlove and Stephen B.Brush,Anthropology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5,1996.这些研究揭示出,地方社会依托地方性知识长期保持着与生态环境的平衡。
再发现地方性知识的动力来自4个方面:首先,宏观理论在解释第三世界国家中政府主导的发展之缺失的失败;其次,对现代性反文化与反自然的学术回应;第三,反映了工业化世界的人们对西方科学范式和经济发展计划的怀疑;最后,反映了一些原住民人群及其组织在国家与国际场合发声能力的增长。⑥Arne Kalland,Indigenous Knowledge:Prospects and Limitations,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Criticl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C].Edited by Roy Ellen,Peter Parkes and Alan Bicker,Harwood Acdemic Publishers,2005:316.4个动力同时存在,彼此互动。查尔斯·哲尔纳提供了印度尼西亚摩鹿加群岛中心区一种名为“赛”(Sai)的制度之再发现和再发明的经典个案。“赛”是一种仪式性保护资源的安排,禁止在资源生长和再生产周期内获取资源。该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式微,但非政府组织和环境部门将之重塑为一种环境制度和习惯法体系,认为有助于可持续发展、自然保护和社会公平。“赛”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资源管理和保护形式——被称为“人民的科学”,进一步被整合到国家的发展计划中,甚至在国家层面作为一种仪式被庆祝。①Charles Zerner,Though a Green Lens:The Constructions of Customary Environmental Law and Community in Indonesia's Maluku Islands[J].Law&Society Review,Vol.28,Mo.5,Symposium:Community and Identity in Sociolegal Studies,1994.
总之,地方性知识摆脱了“非科学”的形象与被边缘化的宿命,以富有生态智慧的面貌重新进入全球环境话语体系和公众视野。
二、建构与颠覆:生态上的“高贵野蛮人”之争
在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中,存在着生态上的“高贵野蛮人”之争。一种观点认为,与自然之平衡是地方人群有意识追求的理想与目标,被文明剥夺的“原始社会”通过地方性方式与自然保持和谐,只是现代社会的愚昧和无知才对之视而不见。②Roy F.Ellen,What Black Left Unsaid:On the Illusory Images of Green Primitivism[J].Anthropology Today,Vol.2,Do.6,Dec,1986:8.与西方工业社会相比,这些社会是生态上的高贵野蛮人。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社会可持续利用与资源、栖息地的管理是普遍的,但生物多样性之保护或提高、栖息地拼图之创造更多是一种间接结果。③Eric Alden Smith and Mark Wishnie,Conservation and Subsistence in Small-Scale Societies[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9,2000.
生态上的“高贵野蛮人”之证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关于环境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文化对动物、植物和物质资源的深刻认知,擅长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利用它们以满足日常生活之需,④Virginia D.Mazarea,A Viewed from a Point:Ethnoecology as Situated Knowledge,Ethnoecology:Situated Knowledge/Located Lives[C].Edited by Virginia D.Mazarea,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99:1~2.也可能利用这些认知有意识地保护和培育植物。比如,采集民精心照料分散的、可食用的和药用的野生植物,游耕民选择在耕地中培育生长快的树种以加速森林恢复;其次,广泛存在的尊重自然世界之精神、文化上传达保护之意的伦理和关于动植物之宗教信仰——视之为社会性生物;⑤Eric Alden Smith and Mark Wishnie,Conservation and Subsistence in Small-Scale Societies[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9,2000.最后,公共资源的管理规则界定了与资源相关的集体行为,让个体愿意牺牲资源的短期收益以保障集体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包括获取、排除、管理、监督、惩罚、仲裁等几个方面。⑥Arun Agrawal,Sustainable Governance of Common-Pool Resources:Context,Methods,and Politics[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32,2003.澳大利亚的阿兰达人通过图腾信仰将保护各类动植物的责任和义务按氏族划分,并以各自的仪式强化氏族与保护物种之关系。一旦某一特殊物种下降,人们便会责怪那些负责这个物种的氏族没有正确地表演仪式。⑦凯·米尔顿.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对环境话语中的人类学角色的探讨[M].袁同凯,周建新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63.因此,地方社会被认为与自然保持着一种田园诗歌般的和谐。
然而,上述证据很容易为经验事实所反驳。首先,一些社会并没有意识到人类保护环境的责任。印度的那亚卡人、马来西亚的巴特克人和扎伊尔的姆布人认为,环境无须任何回报或尽任何义务就能够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⑧凯·米尔顿.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对环境话语中的人类学角色的探讨[M].袁同凯,周建新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47.其次,与生态相平衡的资源利用策略与生态上的“高贵野蛮人”假设相悖,而与“最优觅食理论”相符。狩猎采集民的生计策略更多受到“终值定理”之影响,即单位时间内获得最大回报。当任何一片区域的回馈率下降到迁移到其他区域的回馈率时就会转移,之前的区域就留下了相当一部分未采集的东西。①Eric Alden Smith and Mark Wishnie,Conservation and Subsistence in Small-Scale Societies[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9,2000.亚马孙狩猎者捕猎老、弱、病、残的动物并非为了保护物种,而是因为捕猎的难度更小。当一个地方捕猎难度增大,就会转向其他区域;②Michael Alvard,Intraspecific Prey Choice by Amazonian Hunter[J].Current Anthropology,Vol.36,Mo.5,1995.第三,具有生态保护功能的宗教信仰可能并非出于“保护”之目的。东南亚北部及中国西南的“建寨始祖崇拜”被视为保护生态之信仰,但研究表明,这一信仰之目的在于实现有效的人力管理与控制;③F·K.莱曼.建寨氏族崇拜与东南亚北部及中国相邻地区各族的政治制度[A].王筑生,杨慧.人类学与西南民族[C].郭净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194.最后,地方社会在资源利用上具有持续性,但并不意味着这是有意识管理之结果。与生态环境的平衡更多的是人群无力导致资源退化的结果,是低人口密度、有限的技术和消费需求所致。④Raymond Hames,The Ecologically Moble Savage Debate[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36,2007.
显然,生态上的“高贵野蛮人”是基于地方性知识而建构的一个神话,那么这个神话是如何产生的呢?适应、能量流动、系统平衡、结构与功能等概念,使地方社会与其所居住环境保持和谐的宣言在生态人类学中找到了理论支持。借助这一宣言,地方社会被误读为“自然的保护者”。问题在于这些社会是否真的存在“自然保护”的观念。为回答这一问题,可以先从“环境”一词谈起。蒂莫西·卢克指出,“环境”一词是随着工业转型带来的“生态议题”上升而建构的话语。沿着福柯的进路,环境不应被理解为生态过程的给定空间,而是被公开建构的历史产物。⑤Timothy W.Luke,On Environmentality:Geo-Power and Eco-knowledge in the Discourses of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ism,The Environment in Anthropology:A Reader in Ecology,Culture,and Sustainable Living[C].Edited by Mora Haenn and Richard Wilk,Mew York University,2006:261~236.换言之,“环境”是我们想象中值得争议的发明,“自然保护”同样如此。⑥Paul Robbins,Political Ecology:Critical Introductions to Geograpgy[M].Blackwell Publishing,2004:109.谢巴德·克雷奇曾对两个问题做过调查:美洲土著是生态学家吗?他们是自然的保护者吗?令人惊奇的是,第一个问题之答案普遍是确认的,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大部分是否定的。⑦Shepard Krech,The Ecological Indian:Myth and History[M].W.W.Morton,1999.纳达斯蒂认为,自然保护是一种西方的观点,带有偏见的、评判式的和西方建构的色彩,外在于美洲土著的信仰体系。⑧Paul Madasdy,Transcending the Debate over the Ecologically Moble Indian:Indigenous Peoples and Environmentalism[J].Ethnohistory,Vol.52,Mo.2,2005.
神话一旦颠覆,就须另辟蹊径去解释地方社会与生态环境之平衡关系,涉及三个层面:首先,地方社会都有人口密度低的特征,避免了资源压力造成环境退化。弗雷德里克·巴特在巴瑟里游牧民的研究中指出,与生态的短期平衡取决于移动和冬季的分散,实质是根据不同草场的季节性承载力调整草场利用强度。长期平衡则取决于人口增长率、疾病和课税等因素。⑨Fredrik Barth,Momads of South Persia:The Basseri Tribe of the Khmanseh Confederacy[M].Oslo University Press,1961:113.换言之,地方性知识在生态平衡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与资源之关系;第二,这些社会获取资源的技术与形式不足以造成资源退化。狩猎采集民、游耕民和游牧民都通过移动来利用范围较广区域的资源,这决定了对任何一片区域资源之利用在时空上都是限定的,这为资源再生创造了机会。移动性也是一项社会原则,必须保持简单的技术和小规模的社会组织,将资源利用维持在较低水平;最后,这些社会的经济目标是有限的,他们是为了“使用而生产”而非“为了交换而生产”。这决定了这些社会的资源利用必然以满足生计为目标,而不会为了利润过度利用资源,并表现为低度生产结构。⑩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M].张经纬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95~96.
已有研究揭示出,如果历史上的资源利用是以可持续为基础,但变迁发生了,比如外部需求(毛、皮和羽毛贸易)增加,土地减少或是更具优势的技术(火枪)引入,资源就不再具备可持续基础。①Raymond Hames,The Ecologically Moble Savage Debate[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36,2007.因此,地方社会与自然的平衡是人类活动和其他因素造成的一种偶然性结果。②凯·米尔顿.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对环境话语中的人类学角色的探讨[M].袁同凯,周建新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43.必须指出,颠覆神话并非否认地方性知识在生态平衡与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的功能,而是将地方性知识的研究引向实践领域。
三、限度、权利与政治:地方性知识之反思
当前地方性知识的研究出现了三种更具反思性的新趋势,即对知识的价值和限度的探讨,对知识的产权及其商业化利益之分配的分析,以及知识与全球和地方政治关系之揭示。在这个过程中,限度、权利和政治成为地方性知识研究的核心话语。
(一)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与限度
地方性知识的价值看起来是不证自明的。首先,地方社会拥有处理与不同生态环境关系丰富的经验性知识;其次,地方社会拥有与科学范式相异的对经验知识的解释范式;最后,地方社会拥有值得借鉴的资源管理体系。③Arne Kalland,Indigenous Knowledge:Prospects and Limitations,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Criticl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C].Edited by Roy Ellen,Peter Parkes and Alan Bicker,Harwood Acdemic Publishers,2005:317.然而,对地方性知识价值的关注不应只是简单地重新发现知识与管理实践,而是要更好地理解规约体系中的哪一部分传承了下来,知识与实践在什么条件下才可能成为发展策略的另一种可能。④Paul Robbins,Political Ecology:Critical Introductions to Geograpgy[M].Blackwell Publishing,2004:13.
因此,在重新发现地方性知识的同时,要洞察其局限性,在知识的运用中保持理性。首先,任何一种知识都有文化根基,整理和记录地方性知识以为发展与环境保护项目所用时必然要对知识“去情境化”。对知识的提炼、分离、存档和转换存在被简化或过度归纳的风险,也可能因为“脱域”机制而无法发挥原有功能——西方科学知识为人诟病之处;⑤Roy Ellen and Holly Harris,Introduction,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Criticl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C].Edited by Roy Ellen,Peter Parkes and Alan Bicker,Harwood Acdemic Publishers,2005:13~16.其次,地方与超越地方知识体系之间断裂的观念并非是社会科学的中立态度。霍恩博格指出,当把地方与超地方的分割问题化,地方性知识的观念就掩盖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⑥Michael R.Dove,Indigenous People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35,2006.以及两者“糅合”的可能性。地方性知识也通常被等同于“传统”,给人以静态而非动态发展的印象,这会强化关于地方社会简单技术、低经济复杂性和与世隔绝的形象。
“糅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需要超越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的二元论范式,以一种更为宽泛的视野将两者在地方情境中进行糅合。国家和国际组织所引入的资源管理体系,因缺乏地方性知识的基础和过度关注生物性与经济性,使其非但未能有效解决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在一些地方还加剧了资源退化和引发了新的社会不公等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未理解自然资源管理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关系,也未考虑地方社会文化因素。因此,必须形成一种当地社会结构和当地人优先的管理制度,并应充分体现在地方性知识的各个层面。也要记住生态系统是复杂和可能发生不规则之变化的,这需要保持管理制度的机动性,使之可随着环境之变迁而调适。①Arne Kalland,Indigenous Knowledge:Prospects and Limitations,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Criticl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C].Edited by Roy Ellen,Peter Parkes and Alan Bicker,Harwood Acdemic Publishers,2005:325.
(二)知识产权、利益分配与人类学家的伦理困境
过去几十年,地方性知识的记录和整理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地方发展与环境保护项目和生物性资源的商业开发之中。到1989年,以自然产品为基础的药物已经形成了年均430亿美元的销售额,这预示了生物勘探潜在市场之巨大。到1994年,基于传统作物多样性的种子产业也已达500亿美元的规模。地方性知识中的生物和文化多样性已经成为一些国家最具价值的资源。②Fredrik Barth,Momads of South Persia:The Basseri Tribe of the Khmanseh Confederacy[M].Oslo University Press,1961:33.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达成,呼吁获取并保护传统技术与知识,以及对技术和知识开发产生利润的更广范围之分享。然而,因为这些技术和知识为地方社区所有人所共有,无法确定其产权归属。这导致知识与技术商业化的利润不断增加,而它们的拥有者几乎没有获利。商业机构将这些知识注册,不仅剥夺了利润,还窃取了知识与技术的产权。
产权问题将人类学家置于了两难的伦理困境之中,因为这些知识和技术主要由他们所记录和整理,并以民族志的形式发表。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大学与科研机构占据了地方性知识生产和传播网络的各个节点。地方性知识已经嵌入了“知识—权力”群之中,而记录和整理它们的人类学家无力控制这个网络。③Arturo Escobar,Does Biodiversity Exist?,The Environment in Anthropology:A Reader in Ecology,Culture,and Sustainable Living,Edited by Mora Haenn and Richard Wilk,Mew York University,2006:244.同时,人类学家的记录也可能为其他利益主体有意识地误读,以实现其自身目标。皮特·布若瑟斯提供了这方面的经典个案。在其民族志记录中,马来西亚佩纳人(Penan)“马龙”(molong)一词为“保有”之意。个人可能发现某棵树尚未被人宣称“保有”,就以自己的方式做上标记以为将来所用,先祖“保有”之树可传递给子嗣。环保主义者将这一记录转化为一种保护伦理,即佩纳人认为所有的树都是神圣的。佩纳人在耗尽一片区域之西米后,会留下数年的恢复周期,在布若瑟斯看来这是一种管理方式。环保主义者将之表述为精神信仰要求佩纳人以可持续的方式来利用资源,体现出一种神圣的责任。布若瑟斯强调,要区分人类学家与环保主义者的地方性知识,后者附加了过多的政治性话语和权力维度。④J.Peter Brosius,Endangered Forest,Endangered People:Environmentalist Representations of Indigenous Knowledge,The Environment in Anthropology:A Reader in Ecology,Culture,and Sustainable Living[C].Edited by Mora Haenn and Richard Wilk,Mew York University,2006.
(三)地方性知识与全球和地方政治
误读或建构地方性知识显然可能是蓄意而为,生态上的高贵野蛮人就是最好的例子。雷蒙德·哈米斯指出,着重突出现代欧洲面临之问题,指出一条不存在上述问题的生活方式,生态上的高贵野蛮人就成为批判现代欧洲的一种政治工具。⑤Raymond Hames,The Ecologically Moble Savage Debate[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36,2007.在全球和区域政治中,生态上的高贵野蛮人具有两个政治面相:一方面关注土著人群如何利用这一概念来确认其文化和世界观的一些基本特征,以及这一概念如何在他们为了自决和平等之斗争中被赋予政治性;另一方面关注自然保护组织利用土著人群以拓展其组织议程,以及当前他们与土著群体之间的争斗。⑥Raymond Hames,The Ecologically Moble Savage Debate[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36,2007.
康克林和格雷厄姆提供了亚马孙土著与环保主义者结盟以实现各自利益诉求的经典个案。历史上,印第安人之诉求集中在人权与文化生存权两个方面,但各种原因使得这些诉求在国内难以实现,在国际上也难以获得理解。20世纪80年代,环保主义者发现了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和与土著结盟的政治价值,并与媒体一道塑造了“生态印第安人”,将之作为扩大环境政治影响的武器。印第安人则将“生态印第安人”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并借用环保主义的话语将自己塑造为“雨林卫士”,最终在国际上赢得支持,在国内获得土地与自然资源的自主权。双方结盟基于这样的假设:印第安人关于自然的观念和自然资源的利用与西方环保主义的原则相一致。如上所述,这一假设与印第安人社会的真实不相符,注定了结盟之不稳定。原因有三:其一,环保主义者之目标在于“无人类干扰”的环境保护,而印第安人之目的在于获得土地和资源自主权。印第安人在市场经济中出售或开发资源获取利益为环保主义者谴责,本土活动家则意识到了西方价值与土著社区世界观之差异;其二,环保主义者视土著领袖为印第安社会无可争议的代言人,忽略了这些社会的平等主义规则。当一些土著领袖陷入贪污丑闻后,就动摇了其在印第安社会的支持;最后,国内民族主义者视印第安人为外国经济帝国主义之帮凶,这给印第安社会带来了新的政治风险。①Beth A.Conklin,Laura R.Graham,The Shifting Middle Ground:Amazonian Indians and Eco-Politics[J].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97,Mo.4,1995.
人类学家也开始反思地方性知识研究中地方社会主体性的缺失问题,反对将地方社会视为同质性的群体,转向以知识为中心的地方政治研究。②Arun Agrawal,Sustainable Governance of Common-Pool Resources:Context,Methods,and Politics[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32,2003.保罗·罗宾斯提供了印度坤布哈噶钦(Kumbhalgarch)地区森林管理的经典个案。该地区的森林由5个种姓或阶层群体所利用:传统精英、大土地所有者、放牧者、无权和被边缘化的农民与居于森林的部落民。各群体围绕森林如何管理,因何而变等问题争论不休,并与国家森林管理者群体结成了不同的利益同盟。精英和大土地所有者强调森林中的木材和建材,通过相同种姓与社会背景的中低层管理者行贿获取木材贸易机会,视过牧与燃料获取为退化首因,反对成立村落森林管理委员会。边缘群体和女性群体认为森林提供了饥荒食物和药用植物,放牧者认为森林提供了饲草。他们无力行贿,认为森林退化乃伐木所致,因此支持成立村落森林管理委员会。地区长官则负有改变森林退化之使命,深知伐木是退化之元凶。他一方面与社区精英、土地拥有者和中低层管理者斗争,另一方面与边缘群体结盟。还有少部分受教育者则强调森林是“树之空间”,这与国家知识相一致。对森林用途认识的差异反映了不同人群地方性知识的差异,社区中的斗争之实质是地方性知识表述的竞争。地方性知识因此与政治相结合,与种姓、阶层、性别因素相杂糅,决定了自然资源的管理政策,并主导了景观的变化。③Paul Robbins,The Practical Politics of Knowing:State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Local Political Economy [J].Economic Geography,Vol.76,Mo.2,2000.
反思地方性知识的实质是“去魅”,将地方性知识进一步从各种“高贵”形象和神话中解放出来,并将之置入全球化与地方世界的场域中,最终迈向知识的“本真”。
四、反思国内地方性知识的研究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生态人类学在地方性知识研究中的新进展有助于推动和反思国内相关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人类学界逐步开展对地方性知识的调查、记录和整理。在边疆民族地区更深度地卷入现代化与全球化浪潮的时代,文化多样性(包括地方性知识)和生物多样性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则呼唤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和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文明理念。地方性知识的研究就被赋予了拯救和保护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径的使命。最近十多年,国内地方性知识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一批具有经验性和理论性的研究成果,但仍隐藏着诸多问题亟须探讨。事实上,这些问题正是西方生态人类学最近20年着力解决的问题。文章最后,我从3个方面简明地探讨国内地方性知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国内人类学界已经认识到地方社区是大社会中的“地方世界”,但在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中尚少有这种意识。将地方性知识等同于传统,运用二元论范式将之与科学知识相比较,揭示其在处理与地方生态环境关系中的优势,是最为常见的策略。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忽略了地方性知识是在特定历史与社会情境中演进的事实;其二,存在一种脱离历史与当代情境的研究趋势,导致未对地方性知识在何种程度上或是如何在当代发挥维系人与生态环境平衡的功能做深入探讨。这也可能会强化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对立,并无助于地方性知识的去魅和走向公众视野。
其次,生态上的“高贵野蛮人”神话的各种形式正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地方性知识有从“非科学”倒向“科学”之趋势,以“拯救者”的形象被用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批判之中。事实上,这正是地方性知识很难被吸纳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项目之中的重要原因,无形中削弱了地方性知识在当代知识话语和社会发展中的价值。迈向实践领域的地方性知识研究将更有利于揭示知识的本真,也更有利于探索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的糅合之路,为将之运用到地方“科学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中创造机遇。
最后,国内地方性知识的研究尚少涉及知识的限度、产权与权利,以及知识与全球和地方政治之关系的探讨。这说明:一方面国内地方性知识研究的潜力巨大,大有可为;另一方面,我们仍需充分吸纳西方生态人类学在该领域的新进展,以拓宽研究视野和推进研究的深入。
Reflections on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the new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LUO Yi
(Center for Studies of Moderniz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Groups of Xinjiang,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Xinjiang 830054,China)
In recent 20 years,the studies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Western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have experienced dramatic transformations in three aspects:the marginalization and rediscovering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the subversion of the myth of the ecologically“noble savage”and the practice-based research orientation,and the reflections on its limitations and power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 and regional politic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nd recent progress in the studies of indigenous knowledge,analyz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reflections on indigenous knowledge,and expounds the inspirations for the domestic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ndigenous knowledge;reflections;ecological anthropology
王德明]
C912.4
A
1000-5110(2015)05-0021-09
罗 意,男,重庆长寿人,新疆师范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生态人类学与游牧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