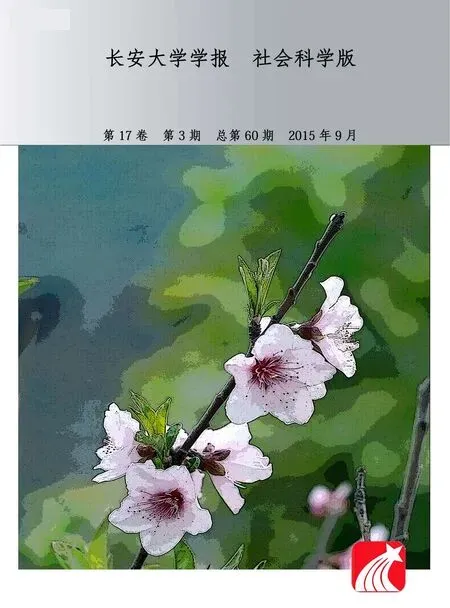《WTO协定》国内解释主体
——兼论条约解释中的翻译问题
冯寿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44)
《WTO协定》国内解释主体
——兼论条约解释中的翻译问题
冯寿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44)
国际法体系的日益丰富使得条约解释问题日趋复杂。在国际争端裁决机构和国内法院的适用条约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条约用语含义、条约间关系的解释问题以及条约解释主体、解释的效力等问题。中国尚缺乏明确的条约国内法解释的程序保障。在WTO中与国内立法有关的事项被认为是事实问题,由于存在着与翻译有关的某些不确定性,对事实的确定会受到限制。对于中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中的条约解释条款应予以修订,以明确条约在中国国内的解释主体、解释程序以及条约翻译等相关问题。
《WTO协定》;条约解释;解释主体;条约翻译
国际社会的“水平型”特征决定了作为国际法主要渊源的条约的制定、修订、解释、适用、效力、位阶等方面都与国内法的相关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一国缔结条约不仅会涉及诸如缔约能力、缔约权、全权证书、谈判、签署、批准、登记与保存、公布,还会涉及条约的国内、国外解释问题。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国际法的规则鲜少能够获得精确表达”[1]。国际法在国际争端裁决机构和国内法院的适用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对条约用语含义、条约间关系的解释以及条约解释主体、解释的效力等问题。以国际法院、WTO争端解决机构等主要国际争端裁决机构而言,《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VCLT)第31、32条的习惯国际法地位赋予了上述机构适用相关解释规则的义务,上述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法体系化与碎片化之间的矛盾,兼顾了条约解释的“同时性原则”和“演进解释”原则。国际法体系的日益丰富使得条约解释问题日趋复杂。“对条约解释规则的恰当适用需要正确的程序和对达致正确解释的最佳保障。”[2]对于条约在中国的解释程序,国内法尚欠缺明确的制度保障。
国内涉及条约解释的机构主要是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对于条约,由最高立法机关、最高司法机构所作出的解释有不同法律意义。目前,国内法对条约在中国解释的主体、方法(即按照解释国内法的方法还是根据VCLT第31、32条)、解释效力规定的缺失,直接涉及条约在中国的效力问题,并制约着条约能否有效实施以及条约与国内法的协调程度。
《缔结条约程序法》仅在第13条规定了不同文字文本在涉及条约解释中的作准问题,这涉及VCLT第33条相关规定,但并无任何条款规定,体现VCLT第31条(解释之通则)、第32条(解释之补充资料),对条约在中国国内法中的地位、条约国内解释主体、条约解释效力等规定皆付之阙如。“垂直型”国家的主权性与“水平型”国际社会国家间主权平等性决定了条约解释主体、方法、效力、程序等方面与国内立法解释相关方面间存在显著差异。从法理看,法律的制定者有权解释该法律,但国内法的国内解释之影响并非完全局限于国内,尤其是对于条约的国内解释问题的研究,仍然存在诸多难题。比如,条约的国内解释之国际法意义如何?条约的国内解释在国内法、国际法上的效力如何?深入研究条约的解释主体、背景、过程等问题,以及条约国内解释间冲突的解决、条约国内解释的模糊,对完善《缔结条约程序法》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定,明确条约的国内法位阶、条约解释主体、解释方法、解释效力,通过条约国内解释来善意履行中国条约义务以维护中国的国际信誉,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仅从立法者和司法者的局限性、法律本身的局限性角度说明法律解释的意义或价值尚不充分,“特别是还需要从法律解释在法制整体中的位置的角度来观察问题,才能完整地认知并进而完整地实现法律解释的意义和价值。”[3]可以认为,对《WTO协定》的国内解释主体问题的研究,既涉及中国相关国内法的完善,又存在国际法意义。
一、《WTO协定》中国国内解释主体不明的国内法原因
“对《WTO协定》的直接、间接理解都会受一国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制度以及该国文化、历史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影响。”[4]实施《WTO协定》的国内立法是在国内层面解释WTO协定的关键因素之一,尤其是起草该立法的方式和在该立法起草过程中解释WTO协定的方式[4]。因此,国内法中包括条约解释主体在内的相关规定会对条约的国内解释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国内法对条约解释主体的规定仍存诸多缺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对于条约的国内解释问题,《缔结条约程序法》存在一些局限,相关原因主要包括《宪法》规定的缺失、《缔结条约程序法》本身存在的关于缔约权限及制约机制方面规定的不足以及条约的国内解释与其他国内法解释在主体、效力和方法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等。“解释WTO协定在国内法律制度中实施的立法和相关的国内贸易立法的规定是国内层面上解释WTO协定的关键因素之一,特别是对翻译的授权和部门、解释的方法以及与WTO协定有关的WTO法理被接受到国内体系的方式和影响解释的方式。”[4]此外,管理和实施《WTO协定》的政府部门的相关措施和行为也属上述关键因素。
对于条约在中国国内法的地位问题,中国《宪法》和宪法性文件尚未予以明确说明,从而令条约在中国的适用方式和解释主体缺乏根本法规范基础。同时,鉴于全球化背景,中国处理涉外纠纷必定会涉及条约义务的履行、适用和解释的实践需要问题,由此中国一些部门法和司法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减少根本法规定缺失所带来的困惑。一种方式是在民事、行政法律中规定可以直接适用条约,例如,《民法通则》第142.2条。
根据国际条约法理论,国际组织、国际法院和法庭以及国内法制中的条约解释者通常被涵盖在条约解释主体范围之内,这与国家为条约缔约方情形有所不同。在国家作为条约缔约方时,条约解释者事实上是指“政府、政府法律顾问和官员、国家立法机关、律师和非政府机构。”[5]法律解释制度是同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度等制度并行的一种法定制度,是国家法制整体中一种专门制度。法律解释在国家法制中不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而且还是一个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方面,是关乎法制全局的一种制度。只有那些法定的正式解释或有效解释,才是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3]。
由于中国《宪法》对条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问题未予规定,由此导致学界对该问题存在不同解答。相关问题是,“国际法位阶比照论”是否存在合理性?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条约制定/批准/核准部门是否与相关缔约权限成一一对应关系?不同位阶法律制定者之间在法规的制定和解释方面是否存在联系?最高司法机关在条约的国内解释方面的实践情况怎样?实施WTO诸协定的国内立法是在国内层面上解释WTO诸协定的关键因素之一,尤其是起草该立法的方式和在该起草过程中解释WTO诸协定的方式[4]。所谓“国内法位阶比照论”是指有些学者把中国立法中规定的中国国内法的位阶拿来比照国际条约在中国的效力地位的推论。他们把国内法的制定机关和条约的批准机关相比照,把立法权限和缔约权限、缔约名义相比照,推断出条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顺序为:(1)宪法;(2)全国人大决定批准的条约、法律;(3)国务院核准的条约、行政法规;(4)无须决定批准或者核准的条约、部门规章[6]。赵建文认为该观点不成立,并给出了下列主要理由:(1)“国内法位阶比照论”不符合国际法的基本理论;(2)无论哪个国家机关行使缔约权,都是代表国家缔结条约;(3)无论国家以什么名义缔结条约,都是代表国家缔结条约;(4)无论国家以什么名义缔结条约,缔约权都是统一行使的;(5)无论国家以什么名义缔结条约,缔约代表的权限都是国家统一授予的[6]。笔者认为,《缔结条约程序法》规定的有权对外缔结条约的机构所缔结/批准/核准的条约,根据VCLT的相关规定,确实对中国都有拘束力,是代表国家缔结的条约。根据VCLT第2.1条甲项规定,条约可以采取其他特定名称,但VCLT并未明确不同的条约名称在法律意义上是否存在差异。从条约法律效力角度而言,这些诸多不同的条约名称并不影响其对缔约方的拘束力。“条约的效力不取决于它的名称。因此,国际条约不论采取什么名称,都具有国际法上的法律效力。”[7]从条约的其他缔约方角度看,不同国家的国内法在缔约程序、条约与国内法关系、条约在国内的实施方式、缔约权限的配置及制约等方面常存在不同规定,但其他缔约方关心的是所订条约能否被善意遵守,只要符合VCLT的规定,并不在意其他国家国内法对享有缔约权的机构作如何规定。可以说,不论中国《缔结条约程序法》规定由哪一个机构或个人来行使缔约权,从其他缔约方的角度来看,这并没有什么不同,中国在该条约下的权利、义务/责任并不受到影响,因为中国的缔约权是统一行使的。
二、国内解释主体
不同名称的条约在条约法中并不存在任何不同。从国内法层面看,不同国家的国内法对条约的国内解释问题的规定往往存在不同的国内法效果或意义,该问题包括缔约程序、缔约权限、条约形式/名称、条约的国内解释主体等事项的规定。根据中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不同的缔约/批准/审查权限由不同的机构或个人所享有。从条约对中国的效力角度来说,由中国的哪个国家机构/个人依据中国法律来签订/缔结/批准/核准条约,并非其他缔约方需要特别关注的事项,因为他们都是代表中国来谈判、缔结条约的。但从中国国内法层面来说,《缔结条约程序法》的相关条款,意味着条约缔结、解释权力在不同国内机构间的配置。条约解释的主体、解释的效力会影响到条约解释的分类。李浩培曾据此分别界定了官方解释和有权解释的含义:“官方解释是条约当事国或其授权的国家机关所作出的对于条约的解释。……必须条约当事国全体同意的解释才是有权解释。……有权解释是指一个条约的全体缔约国对该条约的解释,所以如果该条约是双边的,应是缔约双方对它的解释,如果是多边的,应是该多边条约的全体缔约国,毫无例外,对它作出的解释。国际司法或仲裁机关根据当事国共同同意而作出的解释,也是有权解释。”[8]“国家(National)解释和国内(Domestic)解释过程都会与WTO争端解决过程和《WTO协定》的实施间相互影响。一旦缔结了国际协定,就必须在国际层面对之进行解释并涉及到国内立法,并以该方式实施。由于同样原因,为得到实施,必须在国内层面解释国际协定。”[4]因此,《WTO协定》的解释涉及国内解释主体和翻译问题。
目前,ISO/IEC17025:2005[11]以及 GB/T 27025-2008[12]中均要求检测实验室具有评价测量不确定度的程序,能够对检测项目的不确定度作出正确评估,满足客户及检测工作的要求。测量不确定度在实验室数据比对、方法确认、标准设备校准、量值溯源以及实验室质量控制与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根据 JJF1059.1-2012[13]、CNAL /AG06:2003[14]技术规范的要求,对HPLC-ICP-MS技术测定牛黄解毒片中砷元素形态的不确定度进行了分析,以期为这方面研究提供参考。
(一)条约的国内解释与立法活动
国家通过宪法规定对条约的实施主要有两个方法:直接适用和转化。后者是指国内立法机关直接援用条约原文或将其转变成立法条款而赋予条约以国内法效力。与国内立法有关的事项在WTO中被认为是事实问题,对事实的确定会受制于与翻译有关的某些不确定性。
条约的国内解释往往须遵守关于法律解释的国内法原则和规则。在直接适用条约的一些国家,在同意成为条约缔约国时向立法机构或其他机构提交的材料中常包括对条约义务的解释性备忘录或其他指南,在源于对条约含义分歧而对条约的解释过程中,有时会提及该指南。“因此,解释履行WTO承诺的国内立法之目的解释方法可能不一定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层面上对WTO义务的严格解释相一致。为了在国内解释中既不出现对WTO义务的扩大解释,也不出现与国际承诺不一致的解释,需要使国内对WTO层面上解释WTO诸协定的方法的认识保持一致。”[4]
在WTO争端中,国内有权解释成为案件事实。因此,国内立法机关应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做好条约国内解释工作。如果成员域内法规定被其他成员视为不符WTO协定,就可能涉诉,如2000年“加拿大—药品专利保护案”(WT/DS114/R)中,欧共体对《加拿大专利法》第55.2条的合TRIPS性提出申诉。条约国内解释应与缔约方在约文中体现的共同意图一致,对条约任意、非善意甚至扭曲的解释是对“有约必守原则”的违反[9]。“并不存在普遍可适用的制度,每个国家的(条约国内解释)程序受其宪法和法律制度的支配。尽管如此,单边解释必须诚实反映缔约方间协定下义务。国内法中的缺陷并不构成缔约方违反条约义务的抗辩。”[2]VCLT第26、27条对此有明确规定。在确定国内法与《WTO协定》相符性方面,“印度专利案”的上诉机构认为,为此目的的国内法律是一个事实问题:“在国际公法中,国际裁决机构可能会以几种方式来看待国内法。国内法可起到对事实的证据作用,并提供国家实践的证据。尽管如此,国内法也可构成与国际义务相符或不相符的证据。” 因此,作为中国法定条约解释主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转化方式解释条约时,其所制定的国内法是对条约的国内理解和解释,具有一定国际法意义。
(二)条约的国内解释与政府措施
尽管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都会涉及条约解释,但政府最经常会涉及条约解释,因为政府是条约谈判的主要机构。尽管通常会受到最高权力机关的制约,但是处理对外各领域的国际关系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条约的谈判、缔结和实施中,政府及其官员都必须要解释条约。不同宪法安排下政府实施条约的方法存在差异。条约往往需要借助国内法措施来有效实施,因此,国内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在履行各自职能时都会涉及条约解释[2]。
作为条约的国内解释之表现形式的国内行政法,对条约的理解/解释是准确性与模糊性并存。产生该模糊性或错误理解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的利益导向,也会与条约的国内翻译和解释难题有关。当然,国内行政机关对条约的解释与实施并非总是界限如此清晰。中国政府在WTO中作为申诉方/被申诉方/第三方涉诉,相关权利主张往往体现了在国内层面上对条约的解释和理解——无论是通过国内行政法形式,还是通过在争端解决过程中对条约含义或国内法合法性的解释与论证。“申诉方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启动反映了一缔约方对《WTO协定》解释的看法是如何相异于另一方的看法;当条约的一缔约方作为被告参与了争端,则反映了一成员方对被规定在其国内法中的《WTO协定》的最初解释;通常作为第三方参与争端的成员往往会涉及对《WTO协定》解释过程的参与,该国国内对诸体系问题的关注[4]。WTO成员以不同身份(申诉方、被申诉方、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往往会从追求胜诉的策略性目的解释《WTO协定》和本国国内法。可以说,国家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对同一条约条款用语的含义的理解/解释会发生变化。
(三)国内司法机构的条约解释
由于不同国内司法机构对条约的直接/间接适用的结果并非仅有国内法意义,国内不同司法机构的相关判决可能被作为证据适用于WTO争端程序中,因此,探讨国内司法机构的条约解释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法院对条约的适用会涉及条约国内解释主体问题,且国内外的(准)司法机构在解释条约时的考量和要求存在差异,其解释的效力也存在差异。对国内法院作出的不同、存在冲突的条约解释,国际争端裁决机构会面临选择问题。“1916年美国反倾销法案”的专家组提及国际法院做法,并引用了“巴西贷款案”[2]。由此可从诸多渠道确定条约在一国国内的解释问题。“关于在国内体系中如何解释WTO诸协定和这些协定应该被怎样解释的真正的国内观点可以从下列一系列来源得以被发现,这些来源包括:1.在加入谈判或多边谈判期间作出的声明或采取的立场;2.作为当事方或第三方在WTO中的诉讼期间采取的立场;3.在WTO的不同机构中采取的主张;4.对违反《WTO协定》的指控的官方回应;5.在贸易政策审查机制中,成员方自己以及作为对其他成员审核的回应而作出的声明;6.关于国内贸易政策和实践的官方声明;7.国内的对外贸易机制。影响上述观点形成的因素包括一般性的经济导向和国内历史和政治背景。”[4]这需要在国内法律框架下来理解国内措施。然而,在国内措施中对WTO协定中术语的使用并不能保证这些术语的含义是相同的。此外,孤立地看待国内措施,而不考虑它是如何在国内制度中被解释和实施,这违反了《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和程序的谅解》第11条规定的专家组应客观评估案件事实。因此,必须根据其历史、文化、法律和经济背景来考虑国内措施,正如国内法院通常会考虑该背景一样, 条约的国内解释与国际解释间存在内在的关联性。
三、国际(准)司法机构的相关实践
条约解释是争端裁决机构准确适用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环节。尽管包括WTO、ICJ在内的国际(准)司法机构的判例理论上并无普遍的约束力,但鉴于其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力,其许多判例早已超越个案的影响和意义。对于条约解释争端,作为缔约方的国家间可直接协商解决,也可经其共同同意的第三方裁决。
在大多数国内制度中,并不能直接适用《WTO协定》,使得国内解释具有WTO的法理基础。包括《WTO协定》在内的条约中规定的各种例外在一定条件下为条约的国内解释提供了自由,尤其在条约对某些具体问题没有作出具体、明确规定的时候,更是如此,且易导致争端。DSU第3.2条仅规定了解释《WTO协定》应遵循的规则,第9条仅规定成员方有“寻求对一适用协定规定的权威性解释的权利”,都未明确有权解释的主体范围。
在国际层面上,尽管尚无系统的结构性方法来适用VCLT中的条约解释规则,但国际法院、WTO争端解决机构等作出的许多判例已揭示了特定解释要素的价值。
WTO成员方对《WTO协定》的国内解释反映了其对相关协定条款的理解,是对协定中模糊条款、漏洞的澄清与填补,是形成“嗣后惯例”的国家一致性行为的组成部分。如果成员方的域内法规定被其他成员视为对WTO协定下义务的不符,就可能涉诉,例如,“中国稀土案”2014年专家组报告涉及中国的《进出口关税条例》、《2012年关税实施方案》(海关总署公告2011年第77号)等法规;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申诉方和被申诉方都会竭力论证本方诉求的合法性,其中就包括了本方对相关条约/协定条款的解释以及对国际(准)司法机构判例的援引;WTO专家组/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中往往会对争端各方对相关条约条款含义的解释之分析论证进行评析,并得出自己对该条款含义的理解和解析;如果WTO的裁决生效,被指控国内法违反WTO协定下义务的成员方就需要修改/完善其域内法的相关规定,使之与其条约义务一致。条约的国内解释应与条约的缔约方在约文中体现的共同意图一致,对条约的任意的、非善意的甚至扭曲的解释是对“有约必守原则”的违反。“并不存在普遍可适用的制度,每个国家的(条约国内解释)程序受其宪法和和法律制度的支配。尽管如此,单边的解释必须诚实地反映了缔约方之间的协定下义务。国内法中的缺陷并不构成缔约方违反条约义务的抗辩。”[2]VCLT第26、27条对此有明确规定。
对《WTO协定》的有权解释问题,该协定第9.2条规定:“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对本协议和多边贸易协议具有专属的解释权。”“这表明解释条约的权力不会隐含着或者不经意地存在别处。此外,DSB通过专家组报告,与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解释条约,两者是不同的。例如,DSU第3条第9款规定:本谅解的规定不影响成员根据《WTO协定》的决策程序寻求对协定条款进行权威解释的权利。上诉机构还指出,《国际法院规约》第59条也有类似规定:‘法院之裁判除对于当事国及本案外,无拘束力。’但这并没有妨碍该法院发展出一套先例,并且这些先例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引用’和‘遵循’除了名义上的区别之外,事实上是很难区分的。事实上,WTO是‘遵循先例’的。在‘日本酒精饮料案II’中,在论及GATT专家组报告的效力时,上诉机构认为,GATT缔约方全体通过了专家组报告,并不意味着该报告对相关规定就构成了最终解释(definitive interpretation)。WTO成立之后,情况尤为如此。”[9]
四、翻译与条约的国内解释
VCLT第33条规定了“以两种以上文字认证之条约之解释”,但该条仅与国际协定有关。《WTO协定》第16条规定:“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各有一文本,每个文本均有同等效力。”这似乎间接规定了WTO的3种工作语言——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这在“韩国商船案”的专家组报告(WT/DS273/R, para 24)中得到了证实。DSU也并未就应当如何解决对国内翻译中存在的冲突问题提供指导措施。DSU第13条规定了专家组“寻求信息的权利”, 国内法律/措施作为事实问题,与之相关的翻译问题当然可借助于语言专家了,专家组当然会自主决定是否采取所指定的(语言)专家的意见。对此,“日本胶卷案”的专家组似乎已发展出处理国内措施的正确翻译所存在的意见分歧的程序(WT/DS44/R, para 1.9)。
在国际争端中,对条约用语或WTO成员方国内措施的翻译方面的分歧,与其说是翻译学问题,不如说是该翻译或解释涉及能否为当事方的诉求提供支持的问题。因此,对翻译存在的分歧之实质很可能就是条约解释方面的分歧。例如,在“巴西影响干可可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中,“曾提及在专家组与诸当事方首次见面的第二天,巴西向专家组提交了一份两页的文件,载明了对‘Interministerial Ordinance No.11 和 DTIC Opinion 006/95’翻译的矫正。巴西表明最初译本并不能恰当反映出葡萄牙语言的本义。菲律宾认为专家组在较晚日期接受经修正的译本对菲律宾不公平。” “当事方对国内措施的正确翻译存在不同看法所引发的解释问题,已有不同WTO案例。这些问题的大多数似乎已发生在专家组层面,这可能是因为,在WTO中,涉及国内措施的问题通常是事实问题,而仅能向上诉机构就法律问题提起上诉。如果国内法院能引用WTO诸协定,则翻译方面的差异在理论上说也可能会在国内层面发生。这些差异大多会与翻译成国内语言有关或与实施《WTO协定》的国内立法有关。从比较视角研究已出现的任何差异的形式和这些差异如何被消除,非常有价值。尽管如此,该活动会面临语言技能的挑战,需要这些技能来积累数据和比较研究。”[4]
在对条约的翻译、国内司法机构对条约的解读、国内立法对条约的转化、在国内层面上对国际法的解释以及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中,可发现对包括《WTO协定》在内的国际法的解释。“正如国内贸易立法影响国际贸易一样,翻译国内贸易立法涉及对《WTO协定》的实施。”[4]缔约方对条约的国内实施不仅是通过国内立法方式的实施,还通过将条约翻译成本国官方语言方式来实施。翻译条约的过程也是解释条约的过程。将条约翻译为并非WTO等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的文种或将国内法翻译为外文,其背景都是对该条约的理解和国内法律制度中对国际条约义务的通常理解。要达到对条约内容的适当理解,除须具备良好的语言水平,还需其他相关材料促成对条约的恰当理解,这些材料可能包括条约的谈判历史、草案及修订情况、国际争端裁决机构的相关判例、学界研究成果等。“在该方面,国内官方的翻译是相关的。尽管如此,在国际层面上,该翻译文本并不会改变或取代一WTO成员的义务。”[4]这是因为条约是所有缔约国意志的协调,在整体上体现了其共同意思,单方或部分缔约国对条约的解释一般来说对其他缔约国无法律效力。一些条约本身会明确规定条约解释的有权机构。
除了在信息透明、准确方面有重要作用外,翻译工作在信息收集方面,以及对政府决策和执行部门而言都有积极作用:“如果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在日本和中国未被分别翻译成日语和中文以供其政府机构使用,则这些机构对WTO诸协定的认知将是不全面的。”[4]鉴于翻译在条约解释和国际诉讼中的重要性,“大多数WTO法理都指向了解释的差异,表达翻译方面的差异,本质上是《WTO协定》背景下的国内措施解释方面的差异。”[4]翻译意味着对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精通,条约翻译意味着对公共英语和专业英语的高水平掌握;否则,在条约的谈判、缔结、实施、国内解释中,会因语言水平而产生问题。“中国入世谈判经历了15年多,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签订的一些文件中确实存在不少谈判者自己都不一定弄清楚其确切含义的措辞。……有些则可能受到语言的影响。”[4]
在包括WTO体系在内的国际法层面,可能会因翻译产生许多涉及国内立法的规范冲突问题。第一,如果对国内措施的翻译与成员方提供的与其自己的国内法翻译不同,该新翻译会产生自动修订国内立法的结果吗?当裁决涉及国内措施与WTO法相符性背景下对《WTO协定》的解释时,这与一WTO专家组/上诉机构的裁决在国内体系中的地位问题不同。如果根据该新译本,国内立法并未被修订,则该成员并未遵守其WTO义务。而且,该译本的修订在其国内法律制度中的地位通常依赖于其关于国际义务的国内宪法。第二,如果成员以WTO工作语言翻译其自己的立法与其国内立法不同时,情形会怎样?在该情形下,在WTO层面上,是该成员自己介绍对其立法的变更;在国内法律制度层面,这两个立法版本哪一个优先?作为国内法事项,这必须依赖于该国内宪法。作为国际法事项,该情形或许相当于错误(misrepresentation)。如果该译本与WTO一致,且该成员在其国内制度中继续使用未被翻译的文本,可能就违反了其WTO义务[4]。该译本的结果是对国内立法的实质性变更。在“韩国影响政府采购措施案”中,韩国将其1989年版本的《政府组织法》第2.3条的标题“Subordinate linear organizations of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ve organs”翻译成修订了原文的“Subsidiary organs of central administrative agencies”。专家组认为这两个短语含义不同,并认为对韩文原文的翻译可能增加了该问题的某种模糊性。
五、结语
法律解释与制定、修改法律不同,因此,有必要划清法律解释同法律制定、修改间界限。否则,法律解释“使立法的严肃性受损害。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同法律修改和补充混同起来,就直接侵犯了立法权,堕入违法以至违宪的境地。”[3]国家法律还应明确国务院及其部委的法律解释权限、程序及效力:“《立法法》虽然是规定国家的立法制度,但也需要确立‘各制定机关对其制定的法规性文件的解释是立法解释,立法解释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规性文件具有同等效力。’严格将司法解释限制在‘个案’上,其他解释权力可以由两高提出议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进行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限于其个案的范围。行政解释只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有约束力,不能对司法机关产生约束力。司法解释不能侵越立法权。建立与《立法法》、《监督法》规定相一致的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制度。”[10]“最高人民法院不时地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有关部委等联合发布司法解释,进一步损害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11]目前,尚不清楚上述机构的条约解释间存在冲突的解决途径。“行政机关的解释可以对法院适用条约具有参考价值,也可以具有决定性意义。”[12]应当修订《缔结条约程序法》中的条约解释条款,明确条约的国内解释主体、程序、条约翻译等问题。
[1] 郑斌.国际法院与法庭适用的一般法律原则[M].韩秀丽, 蔡从燕, 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2] Richard K Garadiner.Treaty interpreta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3] 周旺生.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J].现代法学,2003(2):3-10.
[4] Asif H Q.Interpreting WTO agreement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5] Johnstone I.Treaty interpretation: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J].Michigan JIL,1991(12):371-390.
[6] 赵建文.国际条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J].法学研究,2010(6):190-206.
[7] 徐杰.论条约的概念及其法律特征[J].外交学院学报,1996(4):50-56.
[8] 李浩培.条约法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9] 杨国华.事实上的遵循先例[EB/OL].(2014-03-28)[2014-04-09].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 ArticleID=82306&Type=mod.
[10] 汪全胜.司法解释正当性的困境及出路[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3):90-95.
[11] 魏胜强.司法解释的错位与回归——以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为切入点[J].法律科学,2010(3):56-65.
[12] 李鸣.应从立法上考虑条约在我国的效力问题[J].中外法学,2006(3):351-360.
Subject of the domestic interpretation oftheWTOAgreement——discussion on the translation in treaty interpretation
FENG Shou-b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Jiangsu, China)
As a result of the increasing sophist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system, the treaty interpret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In the applicable treaty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adjudication institutions and domestic courts, the issu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eaty’s meaning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eaties, as well as the subject and the effect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are inevitably involved. The domestic legislation lacks procedural guarantee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Matters related to domestic legislation in WTO is considered as the matter of fact. The determination of facts will be restricted due to some uncertainty related to translation. The items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in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ontheProcedureoftheConclusionofTreatiesshould be revised to determine the treaty domestic interpretation subject, procedure, treaty translation and the relevant problems.
theWTOAgreement; treaty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subject; treaty translation
2014-11-19
中国法学会项目(CLS201187)
冯寿波(1965-),男,江苏东海人,副教授,法学博士。
D996.1
A
1671-6248(2015)03-007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