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良:一个人的反垃圾战争
符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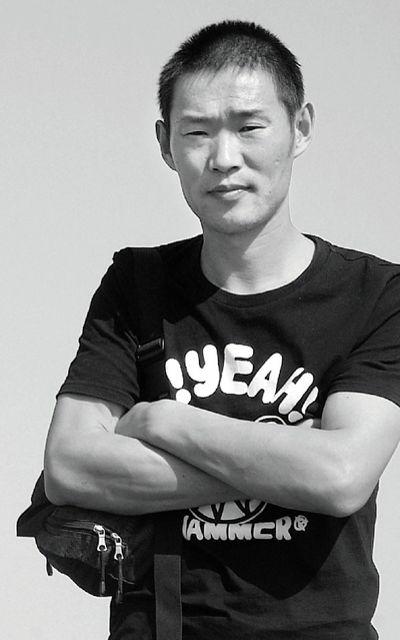
王久良。图/受访者提供
2014年的最后一天,38岁的纪录片导演王久良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航班。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他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研究一个很宏大的课题:“美国塑料垃圾的全球出口与回收”。
这是一次追根溯源的旅程。继2010年的《垃圾围城》系列报道之后,一直在国内与垃圾打交道的王久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从世界各地漂洋过海而来的“洋垃圾”,和那些源源不断向中国输送“洋垃圾”的发达国家。这一次,他想弄清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这些垃圾产生的根源;或者更直接点儿说——“美国的垃圾是如何到中国来的?”
同时,他带去了自己的最新作品,历时三年拍摄的纪录片《塑料王国》。他说想把片子放给美国人看,让他们看看自己所产生的垃圾给地球另一端的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镜头下繁荣中国的另一面
《塑料王国》的英文片名是《Plastic China》,这是王久良精心设计的双关语。其中“Plastic”一词,既指废旧塑料本身,也暗含了“外表繁荣、实质脆弱”的意思。类似于经过“plastic surgery”(整容手术)后展现出来的外表,光鲜精致,却并不自然、真实。
拍摄这部片子的想法起源于2011年他的一次美国之行。当时,王久良去参观加州的一所垃圾回收中心,在那里,他见到了一辆辆满载着塑料垃圾的集装箱货车。工作人员向他随手一指:“看,那是要运往你们中国的。”
这让王久良心生疑惑:为什么美国人自己不回收利用这些塑料垃圾而是要卖给中国?运到中国之后它们又将被怎样处理?带着好奇与不解,他想到拍一部纪录片,追踪这些“洋垃圾”在中国的故事。
三年间,王久良走访了华北、华南、华东十几个集中回收处理进口废旧塑料的基地,深入到这个产业的每一个环节,记录下了这些“洋垃圾”在中国的“重生之路”和一个又一个因此被裹挟的命运。
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商品制造国,同时也是最大的废旧塑料进口国。多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市场对塑料的需求一直在同步增加。而作为石油提炼的下游化工产品,塑料原料的价格随着近年来国际原油的不断涨价也在持续攀升。在这样的情况下,因其成本低廉、利润可观的特点,进口国外的废旧塑料进行加工再利用,成为了国内原料市场的大趋势。
在加州伯克利市的垃圾回收中心,负责人对王久良说:“中国的市场实在是太好了,中国的买主能出别人两倍以上的价钱。”
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旺盛的市场需求促使中国废旧塑料的进口量持续猛增。世界上70%的塑料垃圾都被运到了中国。2010年后更是如此,海关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自此连续三年,中国每年的废旧塑料进口量都超过800万吨。而这,还仅仅只是官方的数字。
而这样的市场需求背后,是遍布全国各地的一个个家庭式废旧塑料加工作坊。分拣、水洗、粉碎、造粒……“洋垃圾”在这些“土作坊”里获得了重生,人们因此获利。但原始粗放的加工模式,还带来了不可扭转的环境污染和严重的健康威胁。
在王久良的镜头中,几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工人们坐在堆积如山的垃圾堆里,完全依靠手工将不同种类的塑料分拣出来。说的是只有废旧塑料,其实“垃圾里什么都有”,破衣烂衫、臭鱼烂虾……
工厂外,清洗塑料用的水直接灌入了附近的河流,粉红的、黑黄的、或是泛着泡沫的废水,侵蚀了庄稼、毒死了鱼虾。周边的居民再不敢喝地下水,尽管已经过得很艰难,每个月他们也要挤出十几块钱去买干净的水喝。村里许多岁数不大的人也得了癌症,大家再问的是,“还有谁没得癌?”
在露天的野垃圾场,在农田、水塘边,无法加工再利用的垃圾被直接焚烧,滚滚黑烟铺天盖地……
这是一个繁荣的中国、一个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残酷却又真实的另一面。
用影像为一个社会问题留下“证据”
从2008年开始关注垃圾,王久良的名字就再也没和这两个字分开过。
这并非他最初的设想。本来,他是一个自由摄影师,他还差点成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
他第一次在“艺术圈”崭露头角是在2007年的中国安吉高校影像大展上。当时,还在中国传媒大学摄影专业读大四的王久良,因为一组名为《往生》的图片作品吸引了艺术评论家、著名策展人鲍昆的注意。作品以中国传统的殡葬文化、民间鬼神信仰为主题,其中展现出的思考和文化底蕴让鲍昆觉得,这和其他许多无病呻吟的作品很不一样:“有聊斋的感觉。一看就是有根基的,有生命的经验。”
鲍昆托人找到王久良,得知王即将毕业,鲍昆建议,“你不要找工作了,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家坯子,你就做艺术吧!”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因担心职场的氛围会把这个学生身上的禀赋磨掉,错过艺术创作的黄金时间,他建议王久良,先专心做两年艺术,“你的生活我来给你解决”。
不工作就没有稳定的收入,专心做艺术也不见得就能“做出来”,可这条看不到未来的路却正合王久良的意。他是一个乡野间长大的山东农村孩子,骨子里就带着几分生猛和比常人更多的固执。
1996年他高中毕业,本来考上了省内的一所大学,但他觉得“那不是我要的”,不到一个学期就退学了。索性开始闯荡社会。他开过摄影工作室,办过美术培训班,卖过手机也卖过菜,各种行当折腾了一圈,最后决定要学摄影。
有了目标,在离开学校5年之后,他又回去参加高考,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学校。读了一年又退学了。直到2003年,王久良第三次参加高考,以27岁的“高龄”走进中国传媒大学。
对他来说,认定了的事情,就全身心地去做去争取,他受不了“凑合”。
毕业后,在鲍昆的指导下,他开始了现代艺术的创作,在《往生》的基础上又继续创作了几个同题的作品,并在北京798艺术区的一家画廊里办了展览。
出于中国文化中对死亡的忌讳,这些作品并没有达到师徒二人预期的反响。鲍昆调整思路,让王久良尝试关注一些与现实更切合的艺术题材,比如环境和垃圾。
起初的灵感来源于鲍昆早年在德国参观垃圾处理设施的一段经历。在他看来,和那些现代化的垃圾处理设施相对应的,是大型仓储式超市中成箱售卖的食品和生活用品。在一个消费主义达到极致的环境中,从食品到垃圾的过程,正是消费品的生死循环。
而对于在乡下的坟地里拍摄《鬼神信仰》的王久良而言,遍布田间地头的农药包装袋是他眼里的垃圾。回到北京后,他开始追踪起了垃圾。
不知道哪里有垃圾场,他就每天骑着摩托一路跟在垃圾车后面。也没有钱,拍纪录片用的摄像机都是借来的。
自2008年8月起,在两年的时间里,王久良探访了北京周边460多座垃圾场,行程15000公里,拍摄了四五千张照片和超过60小时的纪录片素材。除此之外,他还借助“谷歌地球”,在地图上标出了每一个垃圾场的具体位置。
现实令所有人震惊:光鲜的首都北京竟被大大小小的垃圾场紧密地环绕着。
眼看着地图上的标记越来越多,他拿着胶片去找了鲍昆。他对导师说:“我突然觉得,艺术不艺术一点儿也不重要了。”
“商品社会消费主义”的主题也不重要了。听了徒弟的话,一贯主张艺术不能脱离现实的鲍昆,激动得“眼泪都差点儿掉下来”。
于是,垃圾场成为了新的主题。王久良给作品起名为《垃圾围城》。
2009年12月,凭借《垃圾围城》,王久良在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上获得“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
王久良火了。他说,这是他用影像为一个社会问题留下“证据”。
鲍昆还希望王久良能做得更多。在他看来,《垃圾围城》只是把一个表面上容易为人们所看到的现象展现了出来,而垃圾处理的背后还有更多深层的东西,“需要有社会责任感、有艺术感知、又掌握一定话语权的人来探索”。
他对王久良说:“不要再做艺术家的梦了,你完全可以走这条路,也可以获得成功。”
但这一次王久良没有听话。
他想继续扩大《垃圾围城》的影响和知名度。2010年6月,在王久良的坚持下,《垃圾围城》的全部摄影作品和同名纪录片移师北京宋庄美术馆。在这个带着某种象征意味的地方,他从野垃圾场拉回了四大卡车过期的、长条包装的速溶咖啡。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垃圾场的工人、附近的村民和宋庄的艺术家们一起,将这些包装袋整整齐齐地铺满了美术馆四周的小广场。放眼望去,红橙黄绿,色彩斑斓。
拍个片子“跟做贼一样”
《垃圾围城》摄影作品获奖后,引起了多方的关注。新华社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报道,北京市的有关部门也专门约见了王久良。此外,市政府还出台了文件,宣布直接投资100亿元的专项资金,拟在2015年以前新建、改建40余座垃圾处理设施,彻底治理北京周边的垃圾场。
一些媒体也先后向王久良发出邀请,给他提供摄影记者的职位。这曾经是他向往的职业,但他犹豫再三,一一婉拒了。他担心因为身份和时间的限制,无法“相对自由地表达”。
《垃圾围城》带来的改变让王久良看到了个人行动的价值,也开始对社会、对垃圾、对这个充斥着物欲和消费主义的时代有了更多自己的思考,之后也就有了《塑料王国》。
开始拍摄《垃圾围城》的时候,没什么收入来源,又刚结了婚,经费总是王久良最头疼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次和鲍昆交流拍摄进程,“每封邮件都是说钱”。刚开始,鲍昆常自掏腰包塞些钱给他,或是留下几张购物卡,时间长了,就开始动员艺术圈的朋友们帮忙。照相机、胶卷、笔记本电脑、内存卡、办展览的宣传页、扫描照片的费用,都是大家赞助的。
他深切感受到那种四处筹钱的窘迫,所以《塑料王国》一开始,他就决心要换一个模式:商业合作。
他先找来大学的同班同学、泰岳文化的创始人岳冠廷。岳冠廷答应公司作为制片方,他看中了《塑料王国》的想法,更看重王久良这个人。岳冠廷当即给王久良投了第一笔几十万元的启动资金,此后又协助他组了一支4人的工作团队:除他以外,还有一个摄像师、一个外联和一个来自纽约大学的实习助理。
这是一个非常顺利的开端,但之后的进程却并没有因此顺利起来。
第一个困难依然是资金。按照计划,团队将在一年内完成全部的拍摄和剪辑。但从前期调研开始,他们就不断地遭到一些利益相关方的干扰和阻挠。在2012年5月正式开机之后更是如此,拍摄进行得一直不顺利。很快,钱花得差不多了,东西却没拍到多少。
“找钱”,又一次摆在王久良面前。他找过东方良友影视传媒,找过CNEX(华人新世代华人影像项目),为德国的电视台拍过片子,片子也被范立欣带着去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拿到一点儿钱就拍上一阵子,没钱了就又去找。就这样拍拍停停的,支撑了28个月完成拍摄。
回想起那段日子,王久良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停拍两个月,但项目一天都没停下,写文案、联系合作方,恨不得“做梦的时候脑子都在想”。
“我第一不是天才,也不是什么特别出色的人,唯一还算是好的品质就是能坚持,我经常说,要挺住。”王久良这样形容自己。
但也常觉得要挺不住了。
除了资金,他还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如何对付人。
拍摄《垃圾围城》时,他的画面以场景为主,没有太多机会跟垃圾场的人接触,也很少涉及他们的利益,即使有人出面阻止,大不了拍完就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塑料王国》却不一样。要记录人的故事,就需要深入到产业内部,需要每时每刻和里面的人打交道。而在这个有着太多灰色地带的隐秘行当里,这样的拍摄就是“揭黑”“曝光”。
在最初的几个月,没有一家塑料厂愿意让王久良他们拍摄。如何进入工厂成为了每天最难解的难题。好不容易有同意和他们接触的,往往在一两次之后就会受到威胁,在夏天被断水断电,从此也就再没了音信。
有一次,他们刚在当地租了房子,房东就被人威胁,不得不把他们赶走,房东直接把铺盖行李都扔出了门外。
还有一次,他们到河北的一处塑料回收基地做调研,下车才半个小时,当地政府的车就直接开到了他们面前……
为了防止人多目标大,拍摄团队从刚开始的四个人减成两个,慢慢的,最后只剩下了王久良一人。整个2013年,他又回到了之前单枪匹马的日子,一个人一台车一部机器,穿梭在一个个废旧塑料的加工基地里。
“说实话,每天都在害怕,每天都在躲人,连走路都躲着走。”在那些日子里,王久良被地痞流氓围堵过,也被人打过,很多时候,他都要一边拍摄一边四处张望,“差不多跟做贼一样”。为了阻止他的工作,某地政府甚至派人去了他的老家,又到北京找了他的亲友,软硬兼施希望他能离开当地,他表面上答应了,但没过多久就又转了回去。
采访中,王久良并不愿对《中国新闻周刊》提起那些经历,他用一句话总结:“我觉得不重要。”
“他认准的事情,别人劝他可能用处不太大。正是他的这种执拗,能让他把这事儿做完。按照常人的思维,中间可能会放弃,但是他不会。”岳冠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污染,而是人心”
在没能进入那些塑料加工作坊之前,车间里传来的机器的轰鸣声总让王久良有种神秘感。都说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这个资源回收再利用的产业有多么美好,可在王久良看来,一旦你真正踏进去了,一个神话就打破了。
要回收废旧塑料,第一道工序是分拣,一个小小的玩具上可能就有三种塑料,机器没法分,只能靠人鉴别完拧下来。分好类之后要用清洁剂对废旧塑料进行清洗,这是最费水的一步,一家工厂一个小时可能就要抽取50吨地下水。清洗过的塑料被放入粉碎机磨成粉末,然后再进行熔化、造粒或是拉丝。
对于严格遵照环保标准的大企业来说,整个工序下来,人力物力的消耗太高,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并不划算,因而在众多发达国家,回收废旧塑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就给中国成千上万的小作坊提供了“机会”。
在《塑料王国》中,王久良记录下在堆满各种垃圾、臭气熏天、苍蝇遍布的车间里,一个工人的孩子因为病菌感染而患上了黄水疮,大大小小的脓疮长得满头满脸;另一个孩子,拿着一只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废弃针管,毫无戒备地塞进嘴里滋水玩。而他们的父母正在一旁分拣、处理着那些印有各国文字的“洋垃圾”,没有时间和精力管他们,也并不在乎。
一个女工每天不间断地分拣塑料垃圾,每个月收入七八百块钱。她干了20多年,手指的每一个关节都是肿大变形的。
“其实俺也不愿意干,这东西又脏又有污染,俺自己也知道,对俺自己也不好,但是俺为了生存,没办法。”
“空气,空气不好,水,水不好。什么好?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钱好。”
跟拍久了,王久良说,他常常感到很分裂。
一方面,长时间的接触,他和塑料厂的业主、工人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早已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感情;可另一方面,他又实在没办法喜欢上他们。他同情他们的境遇,理解他们的无奈,却还是没办法认同他们的选择。
“明明知道是污染,为什么还要做这个?”这是王久良一直不能释怀的问题。
这个问题他问了他们许多人,问来问去无非就是两种答案。要么是说没有污染,再问就是“不知道”;要么,“他们知道的比你还详细。”
可是,知道了还是要做,不然该怎么办呢?
他试图给他们讲道理,可对方往往会说:“水泥厂有污染么?化工厂有污染么?都有污染。所以这是正常的,是不可避免的。”关于环境、健康、子孙后代的大概念,就被他们轻而易举地,用一种看似无比正常、合理的逻辑化解掉了。
就这样,大大小小的利益相关者们用虚假的繁荣应对着来自外界的审视与追问,竭尽全力地维护着这个庞大的产业。而那些贫穷的、生活在底层又缺少选择余地的人们,为了已被层层盘剥后剩下的一点点微薄利润,心甘情愿地牺牲掉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健康甚至是生命。
“其实他们也很分裂。他们也是受害者,蝼蚁一般。”王久良说。
“走到下面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污染,而是人心。”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污染的河水、刺鼻的气味,时间长了他都习惯了,可那些麻木的、懦弱的、犬儒的、短视的员工,却总是让他无法平静。那一个个人的命运,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存故事,每时每刻都在触动着他。“不是震撼,是震颤。”
他拍摄的一个主人公是一个彝族的小女孩,从7岁起就随父母打工。她的父母告诉王久良,“等我们赚到钱了就送她读书”,可以一晃四年过去,小女孩还是没有上学。
他还见过一个三四岁小男孩,寒冷的冬天光着脚在车间里玩,因为穷,他的父母都舍不得给他买一双鞋。他想起了自己差不多大的女儿,他把孩子的脚放在自己的本子上描了个大小,当天拍摄结束后就给他买了三双鞋。
“社会远比自己想象的凶险”,王久良说,接触得越多,了解得越深,他反而越来越脆弱了。但他自诩为“乐观的悲观主义者”,虽然个人的力量不一定能改变什么,但他还是想做点儿事儿,想看看除去那些虚无缥缈的社会责任感、公共利益,“到底能不能真正地改变一点儿人的命运?”
《塑料王国》的完整版还在后期制作的过程中,预计今年6月完成。王久良觉得,相比之前的《垃圾围城》,《塑料王国》所能带来的改变可能要难得多。而在了解那么多现实之后,他深知对一个国家而言,在短时间实现内部的改变是多么艰难。
2013年2月,全国各地海关启动了一次为期10个月的“绿篱行动”,旨在加强对进口固体废物的监管,打击“洋垃圾”走私入关。仅在最初的五个月,就拦截了超过68000吨塑料垃圾。这一举措一度引起国外众多垃圾处理企业的恐慌,有媒体甚至写道:“中国的绿篱行动让我们在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上所做的努力全都成为了徒劳,因为现在绝大部分的废旧塑料只能进入填埋场了。”
但在王久良看来,这些还远远不够。可反讽的是,迄今为止,反垃圾行动成就最高的却仍是这部《塑料王国》,接下来王久良表示,主要精力将放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和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