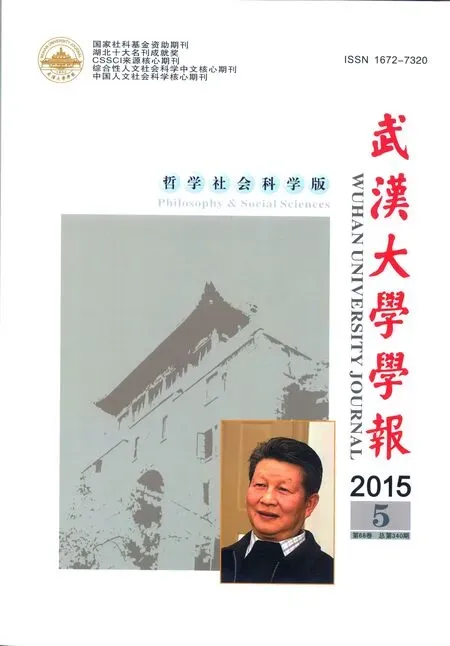政治情境中的“华夷之辨”——秦汉以后“华夷之辨”的历史语境与意义生成
张星久

政治情境中的“华夷之辨”
——秦汉以后“华夷之辨”的历史语境与意义生成
张星久
摘要:在儒家“华夷之辨”的经典话语中,固然以强调华夏文化的先进性和主导性为核心,但“华”“夷”文化的高下之分又必然表现为区域分布上的内外之别以及因语言、生活、风俗习惯不同而形成的族群之分,几个层次的含义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秦汉以后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实际上存在着对上述经典话语的四种具体表达形态和意义类型。政治斗争情境,特别是当时统治者的合法化策略实际上主宰了“华夷之辨”的意义生成与知识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精神活动的普遍规律,印证了将政治思想本身视为政治行动的观点。但是精神活动过分实用化、功利化,亦步亦趋地紧跟政治现实,又容易造成思想和知识生产上的短期行为,不利于一个民族精神上的成长和政治文明进步。
关键词:“华夷之辨”; 儒家经典; 历史语境; 政治情境
所谓“华夷之辨”或“夷夏之辨”,是指中国思想传统中有关如何辨别“华夏”与“夷狄”、进而如何处理两者关系的讨论和认识。它实际上涉及到当时中国人处理中外文化关系乃至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同时“用夏变夷”、“严夷夏之防”也是儒家对士大夫提出的一项重要文化使命和道德实践原则。因此,这一问题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乃至对当时整个东亚世界国际政治秩序格局无疑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以往的研究中,比较集中讨论了“华夷之辨”思想的内涵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等问题,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多资料的便利和观点上的启发。在这些研究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华夷之辨”的三个方面的标准或三层基本含义中,“华”、“夷”之间的种族之分、居住区域上的内外之别相对比较次要,而文化标准亦即是否认同、实行华夏礼乐文化,才是辨别“华”、“夷”更根本、更重要的标准。从大的方向上看,这样的研究结论当然是没有疑义的,但也存在着对文化标准强调得有失分寸、过度解释的问题。似乎为了彰显中国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某些论著往往过分地、孤立地强调是否认同中国文化的所谓文化标准,而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回避“华夷之辨”中的其他标准(如族群之分以及居住分布地域上的内外之别)。从这种研究取向出发,一些论著对儒家经典中的“华夷之辨”思想的基本含义不是从整体、从内在有机联系方面准确把握,而是割裂甚至互相对立起来,使本来清楚的问题弄得十分混乱,甚至被解释出矛盾之处;在讨论各个历史时期的“夷夏之辨”时,也往往抽掉古人讨论问题的前提和具体的语言环境,对文献记载进行断章取义,孤立、夸大地强调文化标准,造成对历史问题的曲解;更有人把古人“华夷之辨”思想撕裂为三,归纳出“华夷之辨”发展三阶段,即从血缘标准阶段发展到地缘标准阶段,再从地缘标准阶段发展到文化标准阶段。这些问题不仅造成对历史事实的误读,也容易助长过分功利、实用的学风。鉴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儒家经典中的“华夷之辨”思想从整体上加以认真梳理,在此基础上把各个历史时期发生的“夷夏之辨”放到当时的具体条件、语言环境等历史语境中,重新理解其在真实历史中的含义,归纳出不同的演变类型,并尝试探讨各种“华夷之辨”话语的生成演变机制以及文化意义。
一、 儒家经典中的“夷夏之辨”
综合已有的研究,揆之个人对有关记载的理解,中国思想传统中所谓“夷夏之辨”或“华夷之辨”,从直接的含义上看,首先强调的是华夏民族(“诸夏”)与少数民族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同,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族群上的区分,主张二者之间应该存在内与外、中心与边缘的相对固定的区分,其中华夏民族居天下之“中”,四夷居周边,形成空间分布上的一种等级秩序。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人关于“天下”或世界秩序观的一种反映。在古代中国人关于世界的认识中,“天下”是由“中国”和“四夷”构成的。如《诗经·民劳》里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尚书·仲虺之诰》里的“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等等,都反映了这种认识。虽然对具体含义存在理解上的差异,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所谓“中国”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中央之国,大致上是指以京师为核心的关中至河洛一带。“中国”和“四夷”说法本身就含有中心与边缘的方位上的意义。从历史上看,这一地区是最早的“诸夏”民族聚居区,也是文化上相对先进的“华夏”或“中华”农耕文明的核心区域,与此对应的是居于外围的少数民族,他们在生活习惯、语言风俗、分布地域上都与华夏民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正是基于各民族自然形成的这种居住与分布格局,形成了“内诸夏外夷狄”的观念。另外《尚书·禹贡》中又有古人“五服制”的记载,指的是上古以至西周时期各地分五等向中央王朝提供差役、履行臣属义务(服),即按照距离京师的远近、以距离王畿五百里为一个等次,由近及远分别提供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等五种差役义务。按照历代注释家的一般理解,前面四种义务要求分别是指:为王室“治田”、“出谷税”(甸)、作为斥侯而保卫王室(侯)、安服王者政教(绥)、接受天子的文教约束(要),最后一种“荒服”则主要是针对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而言,因其“政教荒忽”,则只能“因其故俗而治之”,而没有差役方面的具体要求(《尚书正义·禹贡》)。《禹贡》虽然一般被认为是成书于战国时期,但就其“五服制”的思想内容看,实际上是前述《诗经·民劳》、《尚书·仲虺之诰》中的华夷秩序观的具体化、系统化表述。也正是在这一思想与文化背景下,在孔子删定的《春秋》这部经典中,“尊王攘夷”、“内诸夏外夷狄”就成了后世儒者公认的“春秋大义”之一。《礼记·王制》也认为,“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也是强调“中国”与“戎夷”在风俗习惯、居住和生活区域方面不可推移的区别。
从更深层次上看,儒家经典中的“夷夏之辨”更主要的还是强调“华夏”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与先进性,彰显其与其他少数民族在文化、礼仪上的优劣高下之分。故《春秋》使用“华夏”来形容地处中原的“诸夏”,以显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而夷狄则被认为贪婪无亲、不识礼仪,乃至蔑视为“禽兽”、“豺狼”*如《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称“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襄公四年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闵公元年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在《论语》中,孔子更明确提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论语·八佾》),意谓“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而礼义不废”(《论语·八佾》)。
既然强调华夏文化的中心地位与文明程度上的先进性,则“用夏变夷”、维护华夏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反对在文化上“以夷乱华”,自然也是“夷夏之辨”中的应有之义。如孔子称赞管仲是一个仁者,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就是因为管仲维护了中国的礼仪文化,没有他,中国就可能沦为君不君、臣不臣的“夷狄之区”。另外史载鲁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时,齐国官员“请奏四方之乐”而齐景公又允准,这种“以夷乱华”的行为,被孔子斥为“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史记·孔子世家》)。而孟子也是基于坚持华夏文化先进性、主导性的原则,针对许行一派学说的流行,明确提出“用夏变夷”的主张。当时楚国人许行宣扬“神农之言”,主张所有人都要亲自参加农业生产,“与民并耕而食”,竟然受到一些人追捧,甚至有的儒者也“尽弃其学”。在孟子看来,“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许行的思想明显违背人类社会分工协作的发展趋势,而一些儒者竟然也被其迷惑,追随这“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简直就是“变于夷”、从文明倒退到野蛮。所以他援引《诗经·鲁颂》“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之义,主张效法周公,打击“戎狄”的侵扰,并提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的主张(《孟子·滕文公上》)。
当然,儒家的“用夏变夷”并不是刻意地、超越时代条件地用华夏文化去改造、同化其他民族的文化,更没有依靠暴力征服去输出本民族文化之义。从思想整体上看,儒家一贯倡导仁政或王道政治,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孟子》一书就对王道思想阐述颇详。孔子更明确指出,对于远方或四方之人,要通过修德、怀柔的方式感召其归顺,如所谓“柔远人,怀诸侯”(《中庸·第二十章》),所谓“柔远人则四方归之”(《中庸·第二十章》),以及“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等等。可见,主张在与其他民族和平的、正常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显示华夏礼乐制度、伦理观念的先进性和感染作用,乃是儒家“变夷”思想的要义所在。
概言之,儒家经典中的“华夷之辨”实际上是与当时中国人的天下秩序观相联系的,这种由“华夷之辨”所体现的秩序观包括以下基本含义:(一)其核心是强调“华夏”与“夷狄”在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分,突出华夏文化上的中心地位与主导地位;(二)其最起码的要求是,防止“夷狄”对于“诸夏”文化的侵扰,强调“诸夏”与“夷狄”在居住地域上的内外之别,突出“诸夏”的世界(天下)中心地位,并强调“诸夏”与其他族群的区别,彰显华夏文化的礼仪风俗之美;(三)其最理想、最符合人类文明进步趋势的状态是“用夏变夷”,即:在与其他民族正常的、渐进的文化交流中,展示自己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发挥其引导和辐射作用。换句话说,在通常意义上,“华夷之辨”的地域标准、血缘与种族标准、文化标准三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用夏变夷”、其他民族及其成员接受、同化于华夏文化的情况下,地域上的内外之别、血缘种族上的族群之分才会淡化或自动消失。
近年有论者提出“华夷之辨”的三个演变阶段说,即认为清代以前的“华夷之辨”经历了从血缘标准阶段到地缘标准阶段,最后发展到以文化标准衡量“华”“夷”的阶段。这一划分固然整齐好看,却把文化标准从血缘标准、地缘标准中割裂出来,摆在“华夷之辨”的最后、最高发展阶段,似乎在强调血缘标准、地缘标准的阶段,就是不讲文化标准,这就有生拉硬拽之嫌,明显曲解了古人“华夷之辨”的基本含义。如上所论,在由儒家经典所代表的古人“华夷之辨”思想中,只有在“华”“夷”关系的理想状态和终极发展态势下,即:只有在实现了“用夏变夷”,在其他民族及其成员接受、同化于华夏文化的情况下,“华”“夷”之间的地域分布之别、血缘族群之分才会淡化会自动消失,才会存在只就文化标准进行“华夷之辨”的可能;而在现实中的大多数情况下,“华”“夷”地域之别、血缘族群之分与文化高下之辨往往是结合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在古人心目中,之所以如此严格区分与其他少数民族在地域分布上的内外之别,就是因为他们和汉民族之间存在文化上和族群上的差别。所以提到“中国”、“诸夏”就是“礼仪之盛”、“服章之美”,提到“夷狄”就是贪婪无亲、不识礼仪。上引《礼记·王制》中的一段话,也明明把中国和“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分布方位与风俗习惯、饮食衣服、语言不通相提并论,这是“三阶段”论者自己都在引用的。难道讲风俗习惯、饮食衣服不同,讲语言不通不是在讲文化标准,怎么能把这种“华夷之辨”单单归结为地缘或血缘的一种标准?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还将看到,在秦汉以后的“华夷之辨”中也不存在这种单线式的三个演变阶段,即使有些朝代确实有人主张以是否认同、代表中国文化作为“华夷之辨”的标准,也是事出有因,并不表明就一定是进步、开明的。
另外还有两条材料,常常被一些论者拿来说明孔孟的华夷思想很“开放”,或被证明是孔孟的“自相矛盾”之处。一是《论语·子罕》的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意思是孔子曾想到九夷之地居住,有人不理解孔子为什么要到那么不开化的地方去,孔子回答说,君子住在那里,还会鄙陋吗?如果结合前面对儒家“夷夏之辨”思想的梳理,这句话其实不难理解。它无非说明,孔子对自己所承载的“道”、对华夏文化非常自信,认为即使居于“九夷之地”,也可通过绽放华夏文化的光彩,展示君子身上的文明力量,去影响环境,去“用夏变夷”。一个地方是否蛮荒、鄙陋,端在于何人所居,“夷狄”居之则为“陋”,君子居之则“何陋之有”。这和孔子的一贯思想,和前述儒家的“华夷之辨”原本一脉相通,既无自相矛盾,也与“开明”无关。
另一条记载是孟子对舜和周文王的一段议论,说舜与周文王都是夷狄出身,最后都成了中国的圣人——“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放在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看,孟子在这里也无非是说,从发展趋势和最终结局看,华夏文化因其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定能不断地从中心向周边传播,引领和同化“夷狄”,使之渐进于中华礼乐之教,成为华夏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分子。但这不等于说,孟子可以不顾时间、空间条件,超越当时“华”“夷”在文化上、分布地域上存在明显差别的事实,笼统地强调天下一家、内外无别。从文化发展的趋势和理想目标而言,孟子坚信“夷狄”最终可进于诸夏、天下终将大同,但不要忘记,为了捍卫华夏文化的主导地位,孟子恰恰又主张效法周公,打击“戎狄”对“诸夏”文化的侵扰!因此,不能把这段话和儒家思想的整体割裂开来,然后妄断孟子的立场有什么模糊、松动甚至“开明”之处。
以上我们梳理了先秦儒家有关“华夷之辨”的基本主张。这些基本主张奠定了中国历史上“华”“夷”秩序论的基本话语体系和经典表达,可谓“华夷之辨”的理论类型。至于后世发生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则是孔孟这些儒门圣人所不及见的。在“中国居内以制四夷、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朱元璋语)这一似乎是天造地设的内外区分格局被打破之后,“华夷之辨”的原则如何践行?这是摆在后世儒家士大夫面前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二、 历史语境中的“华夷之辨”
秦汉以后的有关华夷秩序的讨论,一方面是在前述儒家“华夷之辨”理论的框架内展开的,但同时也因为各个时期民族关系的具体情势、参与话语再生产的个人处境等方面差异而有不同的侧重和取向,从而形成具有不同时代内涵的表达和实践形态。
大体而言,秦汉以后的“华夷之辨”主要有以下四种表达形态或意义类型。
第一种形态为,强调中国与“四夷”内外有别、互不侵扰。主要发生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内外分布秩序基本维持、同时汉族政权又不断受到外部侵扰的时期,如汉代。这种情势下的夷夏之辨大体沿袭了先秦儒家的思路,同时更加强调汉族与少数民族应该遵守双方之间自然形成的疆界,反对“夷狄”对汉民族居住区域的侵扰。
汉朝人关于“夷夏”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如何处理与匈奴的关系问题。匈奴自先秦以来即为患于当时中国的北边,汉初更发展成为严重威胁中原汉族政权的劲敌。汉高祖七年,刘邦亲率大军迎击匈奴,竟陷白豋七日之围,几遭不测。此后双方时和时战,文帝时匈奴前锋甚至直逼至长安城外200里。面对匈奴这个最具威胁性的挑战者,汉朝人对“夷夏”问题的认识与思考,无疑会更趋理性和务实。从士大夫到皇帝,他们不得不接受“夷狄”“不能臣”、“不能制”、不服圣王教化的事实。武帝时大儒董仲舒就认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汉书·匈奴传赞》)。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朝廷令公卿议定礼仪,太子太傅、经学家萧望之认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汉书·萧望之传》),而汉宣帝也采纳其建议,下诏“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汉书·萧望之传》)。另外哀帝时扬雄也上书说,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汉书·匈奴传》)。
既然匈奴如此不堪教化,华夷之间的文化差距如此之大,则承认双方之间天然形成的疆域界限以及各自的管辖权,尽量地维持边境的和平,使双方相安无事,就成为当时“夷夏之辨”的重点。在具体的应对策略上,则是一方面主张遵守双方的和亲之约,互不侵犯,同时随时准备反击匈奴对汉地的侵扰。如汉文帝前三年夏,匈奴右贤王侵犯河南之地,于是文帝下诏谴责说,原本“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无侵害边境”,现在右贤王竟然“将众居河南地”,“捕杀吏卒”,是破坏约定的行为。文帝后二年,又派遣使者重申与匈奴之约:“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內冠带之室朕亦制之。”(《汉书·匈奴传》)为了边境的和平,汉朝常常忍受屈辱,不得不对匈奴“卑下而承事之”,但即使如此,匈奴还是“数寇边境”,于是汉武帝时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反击,基本缓解了威胁汉帝国的匈奴之患。对于这种认识和处理匈奴问题的方式,史家班固在《汉书·匈奴传赞》中进一步总结为:“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第二种形态是,在“夷狄”认同华夏文化、“慕仁义、行礼乐”的情况下,对其采取“王者无外”的态度,主张打破种族界限,从是否认同中国文化来判断其是否为“华”、“夷”。这种观念主要出现在与“夷狄”冲突中取得胜利的唐代。唐太宗曾说过一句被广为流传的话,即所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条)。唐代后期还有进士陈黯、程晏分别撰写了《华心》和《内夷檄》,认为“华夷之辨”在乎是否“行合乎礼仪”(《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七),“慕中华之仁义忠信”(《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一)。许多人据此证明唐朝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的开明,更有论者由此断言唐代“以文化不以种族”来区别华、夷,但他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唐朝人上述说法的具体背景。首先,唐太宗是在贞观二十一年对群臣说这番话的,斯时唐朝已经通过几次大规模战争击溃了东西突厥,在当时的华、夷冲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他即位初期(贞观三年)谈起父亲被迫称臣于突厥的屈辱,唐太宗说的却是:“国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诡而臣之,朕常痛心病首,思一刷耻于天下。”(《新唐书·突厥传上》)可见,唐太宗“爱之如一”的表白除了显示出盛唐帝国的自信之外,显然还有对于已归化的突厥等少数民族的怀柔之意。其次,上述陈黯、程晏两人有关华夷关系的议论,其实也是在少数民族不断归化、融合于汉文化的大背景下,针对具体事由而发的。宣宗时陈黯写《华心》一文,强调“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七)。《全唐文》记载其说这番话的直接起因是,当时一个叫李彦升的大食人拟参加科举考试,却因其“夷人”身份而受到质疑,陈黯反对这种僵化的华夷观念,才提出以上观点加以反驳。昭宗时进士程晏写《内夷檄》,其直接原因虽然史无可考,但其内容中就有所谓“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一),显然也是针对“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认同了汉文化而已经内向的那部分“四夷”而言的。综观整个唐朝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态度,首先仍然是立足于对外来侵扰的武力征服,维护边疆稳定和政权安全,在取得主动权的前提下,对于归降内迁的民族从生活、生产方面给予妥善安抚,并尊重其风俗习惯。至于对那些认同华夏文化甚至已经汉化的夷人给予同样的社会、政治地位,不过是对传统的“用夏变夷”思想的具体运用。因此,不能抽离具体的语境,把唐朝人针对具体问题而提出的观点过度解释为一般的原则,甚至概括出一种新的辨别“华”、“夷”的标准。
第三种形态则主要针对像北魏、金、元这类进入中原同时又发生某种程度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主张以是否认同、代表中国文化来体现“华夷之辨”,进而判断一个政权是否代表文化正统,而不再拘泥于华夷之间疆域、种族的界限,隋唐之际的王通、金元之际的郝经、许衡等即其代表。王通将实施汉化的北魏拓跋氏政权奉为正统,认为“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中说·述史》)。郝经作为协助忽必烈推行汉法的重要人物,认为“中国而既亡矣,岂必中国之人而后善治哉,……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何有于中国于夷”(《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十九),进而明确提出“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十七)。而作为元朝儒家领军人物的许衡,曾向元世祖忽必烈建议,“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元史·许衡传》),并实际参与了元代许多重要汉法的设计与推行,这种举动本身就被认为是“居夷变夷”(许衡,2009:338),“用夏变夷”(许衡,2009:339)。特别是许衡还曾写诗明志云:“直须眼孔大如轮,照得前途远更真;光景百年都是我,华夷千载亦皆人”(许衡,2009:265),明确表达了捍卫华夏文化的信念以及以儒家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华夷一家思想。
王通为隋唐鼎革之际民间大儒,郝经、许衡则是“居夷之地”的儒家知识分子,三人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况各有不同。他们之所以放弃传统“华夷之辨”的种族、地域意识,而特别推重汉法、中国之道,是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夷狄”征服汉地已成为既成事实,而伴随着每一次暴力征服,往往是大规模的血腥杀戮和对中国文化的浩劫,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就是接受中国既亡、“夷狄居中国之地”的残酷现实,促使“夷狄”建立起码的礼乐秩序,以儒家“仁民爱物”精神收束统治者残忍好杀之心,减少政治中的残暴与血腥,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使“天地有奉,生民有庇”。他们的这些看法以及政治动向,其实是和儒家的基本理念以及儒家对士君子的道德要求一脉相承的。儒家以“仁”为最高的道德要求与政治原则,其具体表现为施仁政、行王道,立君为民、民惟邦本、仁民爱物。而一个君子就应该以仁为己任,利济苍生,成己成物,甚至越是风雨如晦、世道艰难,越需要以松柏傲霜、舍我其谁、杀身成仁的精神勇猛入世,以一己之身去承载、证成儒家之道。王通立志于几百年“五胡乱华”的魏晋之后重振儒家道统,“续命河汾”,郝经、许衡“居夷”而“用夏变夷”*《许衡集·卷十二·像赞》引后学王九思赞:“盖愿学孔子者,公之志;美而且大者公之造;用夏变夷者,公之心。”同书卷十四《先儒议论》引胶东邓中和诗“仕非为禄屡辞禄,道在居夷能变夷”。,推动统治者力行汉法,以“挽回元气,春我诸华”(《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郝公行状》),特别是许衡明知自己的努力“势有甚难者”,甚至是“足蹑虎狼尾,手撩虺蛇头”(许衡,2009:256),却仍要勉为其难,正是儒家那种仁为己任、民惟邦本、人能弘道精神的体现。
其他像金代翰林学士赵秉文曾撰《蜀汉正名论》一文,也认为能够“采用中国之礼”、“有公天下之心”就是中国,就应该称之为汉;金末元初的杨奂也反对“以世系土地为之重”,主张“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也”,只要行王道即可以称中国正统,也大体上和郝经属于同样的情形(赵永春,2009:1-12)。对于像赵秉文这样的汉族儒士来说,他所生活的金国早已高度汉化,他本人的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并不输于南宋士大夫,其主张以是否有“公天下之心”、是否能“行中国之礼”作为辨别华夷的标准,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四种“华夷之辨”则相反,其重点恰恰就在于“以世系土地为之重”,绝不承认“夷狄”统治中国,混淆华、夷之间在居住疆域上的内外之别,认为任何“夷狄”入主中国,都是造成文化上野蛮倒退的“以夷乱华”行为,因而坚决主张“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并将这种“华夷大防”观念提到《春秋》大义、圣王大法的高度。这种观点主要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北方“夷狄”政权对峙的南朝各政权,宋、辽、金、元对峙状况下的宋朝一方,以及通过反元而建立起来的明朝。如西晋的江统曾写下著名的《徙戎论》,坚持“内诸夏外夷狄”、“戎晋不杂”的立场,强烈主张将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迁回其故地;南朝沈约修《宋书》,则专设《索虏传》以指北魏拓跋政权(汪高鑫,2010:48-53);而南宋遗民郑思肖撰《心史》,更毫不含糊地认为,即使像北魏拓跋氏采用中国的礼乐文物,也是“夷狄行中国事,古今天下之不详,莫大于是”,和人臣篡位一样都是“僭”,是“僭行中国之事以乱大伦,是衣裳牛马而曰人也,实为夷狄之大妖”,应属“天理必诛”(《心史·古今正统大论》)。而明朝本来就是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下,通过反抗民族压迫进行政治动员而建立起来的,故君臣上下有关“夷夏大防”的声浪尤高。比如在著名的朱元璋《谕中原檄》中,开宗明义就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认为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违背了以华制夷的天然秩序,使“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谕中原檄》据说出自开国儒臣宋濂之手,而宋濂的弟子方孝孺作《释统》、《后正统论》,自谓此文深得其师赞同,也是旗帜鲜明地认为“夷狄”和“篡臣”“贼后”一样,均不得视为正统(方孝孺,2013:66-76)。尤其在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那里,在主张“夷夏大防”方面最为决绝,由于亲身经历亡国之痛,眼见“内夏外夷”格局似乎又一次翻转,更把“华夷之辨”视为“天下大防”(王夫之,1975:372),直斥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是“沐猴之冠,优俳之戏而矣”(王夫之,1975:471),甚至对于许衡在元朝传播儒家礼乐文化的努力,他也认为是“以圣人之道为沐猴之冠”(王夫之,1975:882)。
以上是历史上“华夷之辨”的四种表达形态(见表1)。第一种(汉代)和第四种(明代为代表)形态都是从种族、文化和分布地域等各方面强调“夷夏”之间的区别,进而突出“夷夏之防”的思想,虽然激烈程度或有不同,但都可归为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华夷之辨”;而第二、第三种(唐太宗、王通以及金、元时期的许衡、郝经等代表)则试图淡化“夷夏”之间在种族与地域上的界限,而偏重于从文化、文明程度上辨别“夷夏”,因而又可以归类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夷夏之辨”。

表1 “华夷之辨”的四种历史表达形态
三、 作为政治行动的“华夷之辨”:知识生产与意义生成机制
可见,虽然先秦儒家奠定了华夷之辨的理论类型,确立了讨论问题的基本原则与思想框架,从而界定了后世华夷之辨的展开范围或可能的方向,但这毕竟属于“能指”,这些话语在现实中实际“所指”的含义是什么,想要重点表达什么问题,则主要取决于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语境,即取决于当时民族冲突关系的具体情势,以及统治合法性建构的需要。表面上看,似乎有许多人都秉持共同的文化标准,即都在根据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化为标准来判断“夷”与“夏”、野蛮与文明,似乎都符合传统的“用夏变夷”原则,实际上讨论问题的前提却各有不同,因而在相似的话语体系下所表达的意义也不相同。比如对于唐朝而言,由于在华“夷”关系中占有相对主动地位,针对那些归降内迁的民族,以及那些认同华夏文化甚至已经汉化的“夷人”主张“爱之如一”、不问种族而看文化标准,自然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各民族的和睦相处。而对于像王通、许衡这类儒家知识分子而言,他们避开种族问题而强调从文化、文明程度判断统治正当性,则主要是因为“夷狄居中国”已成既成事实,当务之急是促使“夷狄”的统治者采用汉人的“礼乐文物”,减少政治中的残暴与血腥,为百姓也为人类的文明赢得一线生机。汉代“夷夏之辨”则是在匈奴不断进攻的现实压力下展开的,故侧重于强调华“夷”之间生活环境、风俗文化方面的悬殊和不相融性,以及视“夷狄”为“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主张与匈奴互不侵扰、维持现状,其“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借以维护“中国”在空间区位和文化上的中心地位。而对于明朝的开国者而言,最好的政治动员方式莫过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旗号,通过它很容易唤起和强化对蒙古“夷狄”统治者的敌忾意识,凸显汉人所代表的华夏文化、实际上是明朝统治者的正统地位,加上蒙古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确实又在一般民众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从而为明朝统治者的合法性谋划提供了方便,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容易形成激烈的民族情绪和整体式的“严夷夏之防”思想。而王夫之强调夷夏之间的峻防,也与他作为明朝遗民、又亲身参与抗清斗争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所以,在真实的“夷夏之辨”历史中,并不存在那种直线递进的所谓“三个演变阶段”,不存在没有前提条件的、孤立抽象的所谓文化标准;也不能简单笼统地认为,避开种族、地域问题而专就文化、文明程度展开“华夷之辨”,就是开明、包容,而强调“华”“夷”之间的种族、地域之别就一定是狭隘、封闭。在很多情况下,种族、地域、文化三种标准事实上是无法分开的,特别在面临“夷狄”入侵或“夷狄居中国”的情势下,对华夏文化的捍卫首先就表现为对固有土地家园的捍卫,表现为坚决反对“夷狄居中国治天下”。
说到底,各个时期“华夷之辨”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最终还是取决于当时的民族关系、政治斗争的情势,还是服从于当时统治者的合法化策略需要,而不存在一些人所理解的不断发展进步过程。各族统治者通过对“华夷之辨”的元典内涵进行选择性表达,如通过对于其中某一部分或强调、或遮蔽、或默许、或鼓励,实现有利于其统治合法性的建构。而那些儒者只能在国家权力规定的话语空间中,以有利于统治者合法性的方式进行华夷之辨的话语表达与实践,从而最终达成了双方在合法性建构中的共谋,适应了统治者的合法性构建,政治斗争主宰了话语实践、知识的维持与再生产。比如从表1就可以看出这样一种明显的对应关系:当少数民族“居中国治天下”的时候,其统治者往往会有意强调文化意义上的“夷夏之辨”,而淡化、回避种族、地域因素;当中国之内存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情况时,特别存在像明朝与元朝之间那种剧烈的合法性竞争关系情况下,汉族政权下的统治者及其士大夫则倾向于采取完整意义上的夷夏之辨,从文化、种族、地域等全方位排斥“夷狄居中国”的正当性。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王通、唐太宗、郝经、许衡等人主张文化标准看待“夷夏之辨”就是开明、进步的,而方孝孺、王夫之等人反抗民族侵略的“严夷夏之防”就是狭隘、落后的。而根据刘浦江教授最近的研究,朱元璋《谕中原檄》中的激烈民族情绪其实也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一旦时过境迁,朱元璋甚至有时还对元朝流落出感念之情,说“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还把元世祖和唐太宗、宋太祖一起入祀历代帝王庙,实际上等于承认其正统地位(刘浦江,2014:79-100)。
这种“华夷之辨”的意义生成与话语演变特点,对于认识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都具有典范意义。它实际上反映了传统中国思想和知识生成过程中的一个通病:太过强调理论和学术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太过强调理论服务于现实,在学术和现实政治之间、在理论研究和对策设计之间缺少必要的距离和张力,至今依然如此。尽管中国思想传统中也存在一定的“道”与“势”、“道统”与“政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张星久,1996:72-77;张星久,2006:773-778),但是整体上看这种独立性远不如西方政教分离传统中那么明显。尤其涉及到“华夷之辨”这样的现实性、政治性极强的问题,更是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特别是直接服务于统治集团之间的合法化竞争,使其在很大意义上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这种思想(知识)活动与政治现实之间的无缝隙式关系,势必造成思想和知识生产上的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导致思想短促、思维短路,不大会进行延伸思考,不大顾及观点的逻辑后果与潜在风险。比如,当我们说王通、李世民、许衡、郝经这些人所持的文化标准是有不同背景、条件和不同含义时,其实是我们今人对这些人讨论“夷夏之辨”的语境进行研究的结果,他们本身并没有向人们明言这些背景和前提条件,更没有进一步思考这种文化标准是否适用于其他的朝代。因为,只有当人们把诸如“夷夏之辨”的问题当成一个相对超脱的知识问题,或当成一个需要系统思考的理论问题来对待时,才会将思考延伸到这些问题。而从那种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无缝隙思维习惯出发,则一切从现实需要立论,而不太顾及所谓思想的背景、前提条件、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问题。但是这种没有明确界定条件、适用范围的文化标准,却容易造成后人的误读,容易使人误以为是普遍适用的标准,是离开具体条件的开明、包容思想。而一旦这样理解问题,则在逻辑上这种文化标准就可以运用于任何时代的“夷夏之辨”,不管它是唐代、金代、元代还是汉代、宋代。而一旦真要把这种避开疆域、种族问题的文化标准用到汉朝、宋朝,就不免让人产生这样的困惑与混乱:既然“光景百年都是我,华夷千载亦皆人”,既然“夷狄”迟早会认同中华文化,则汉朝对匈奴,宋朝对女真、蒙古入侵者的抵抗还有什么意义,匈奴、女真乃至蒙古这些“夷狄”的南侵岂不有了正当的理由?
而对于像王夫之这些对“华夷之辨”持最严厉立场的人来说,也会面临同样的诘难。他严厉斥责王通、许衡等人的言行是助长“夷狄”的“沐猴而冠”,是和违反君臣大义一样的叛逆行为,但他也没有明确告诉人们,在“夷狄居中国”已是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一个儒家士大夫究竟应该怎么做才更符合先师孔子的精神,他除了像许衡那样之外还有怎样更好的选择?是一死了之,还是效法老庄,消极避世、归老林泉?而王通、郝经、许衡这些人当时所面临的问题,譬如在“中国既亡”、代表中国文化的汉族政权不复存在而百姓又生活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下,儒家士君子该如何进退自处,如何与“夷狄”政权、特别是已经汉化的“夷狄”政权打交道等等,实在是儒家在道德实践中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王夫之作为王通、许衡等人最为严厉的批判者,却没有与之发生多少观点上的正面交集与回应,没有给出更有说服力、可行性的论证!
所以,在这种知识和观念生产机制下展开的“华夷之辨”,看起来众声喧哗,却没有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千百年来似乎都在进行着低水平的重复,表达的仍是一些碎片化乃至泡沫化的意见,而无法形成具有层次结构的、逻辑自洽的系统思想和相对客观化的知识积累,以增进整个民族的思想深度和智慧。伴随着这种近乎自说自话式的“华夷之辨”,事实却是,任何在中原建立政权的王朝,都可以从中找到证明其正统性的理由,从而陷入无是无非、成王败寇的逻辑,引发“千古兴亡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无常感与道德虚无主义。
四、 结论
总之,从“华夷之辨”的理论形态看,其核心是华夷文化先进与落后之分,强调华夏文化先进性、主导性,但又必然表现为地域分布上的内外之别,以及见之语言、生活、风俗习惯不同而形成的族群之分,同时也含有发挥华夏文化的引领辐射作用、实现“用夏变夷”的含义。几个层次的含义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既不能割裂开来,也不能简单地归约为文化标准。从秦汉以后对“华夷之辨”的历史表达即实践形态看,可以分为四个衍生形态,并归结为两大类型:一是整体意义上的“华夷之辨”,偏重从种族、文化和分布地域等各方面突出“夷夏”之别,强调“夷夏之防”,主要发生在汉朝、西晋、南朝以及明朝;一为文化意义上的“夷夏之辨”,突出文化、文明程度因素而淡化“夷夏”之间种族与地域界限,主要出现在“夷狄”内附,在华、夷冲突中占优势的唐朝,以及像北魏、金、元等“居中国”之地又发生某种程度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
之所以出现这些不同的历史表达形态,主要是由当时的民族关系、政治斗争情势,特别是合法化策略所决定的。为了建构统治合法性,各族统治者会对“华夷之辨”的经典理论进行选择性表达,而儒家士大夫们也只能在权力设定的话语空间中,以有利于统治者合法化的方式进行“华夷之辨”的话语实践,政治斗争因而主宰了“华夷之辨”的意义生成与知识生产。所以,不存在没有前提条件的抽象文化标准,也不存在所谓血缘标准→地缘标准→文化标准三阶段直线演进的过程,各个王朝具体采取什么“夷夏之辨”标准,主要取决于与当时民族关系以及政权合法性建构的具体情势,和朝代先后顺序、文明演进程度没有直接关联。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避开种族、地域问题而专就文化、文明程度展开“华夷之辨”,就是开明、包容,反之就是狭隘、封闭。
这种政治斗争主导下的“华夷之辨”观念与知识生成机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精神活动的普遍规律。昆廷·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就是从“以言行事”预设出发,将政治思想视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但是精神活动毕竟不同于直接的政治行动,精神活动过分实用化、功利化,恰恰又是中国思想传统的通病。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看,一个民族精神活动的理论化、超越化程度,以及相关的抽象思辨能力、批判反思能力,至少也是衡量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尺之一。历史上有很多当时看来毫无用处甚至是有害的理论探讨,却带来了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和影响深远的思想革命。而思想活动亦步亦趋地紧跟政治现实,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思想和知识生产上的机会主义、短期行为,恰恰不利于一个民族精神上的成长和政治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1]班固(1962).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2]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1988).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金元别集(影印本)(9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3]董诰(2013).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
[4]方孝孺(2013).方孝孺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5]何晏注、邢昺疏(1990).论语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6]孔颖达(1990).春秋左传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7]孔颖达(2008).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8]孔颖达(2007).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9]刘浦江(2007).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中国史研究,3.
[10] 欧阳修等(1975).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
[11] 饶宗颐(1996).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2] 司马光(2011).资治通鉴.长沙:岳麓书社.
[13] 司马迁(2008).史记.长沙:岳麓书社.
[14] 宋濂等(1976).元史.北京:中华书局.
[15] 唐玄宗注、邢昺疏(1990).孝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6] 王夫之(1975).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
[17] 汪高鑫(1987).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史学集刊,6.
[18] 许衡(2009).许衡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 张沛(2011).中说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 张星久(1996).儒家思想与中国君主专制的内在冲突.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21] 张星久(2006).帝制中国的两种基本“公”“私”观及其制度表现——一个从制度回溯观念的尝试.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
[22] 赵永春(2009).试论金人的“中国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
[23] 朱熹(1983).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作者地址:张星久,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xj00zhang@hotmail.com。
■责任编辑:叶娟丽
The Distinction of “Hua” & “Yi” under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t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Meaning Generation after Qin and Han Dynasties
ZhangXingjiu(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e Confucian classical discourses,the distinction of “Hua” “Yi” within several layers of meaning,is to emphasize the advancement and the dominanc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s the core,but also inevitably show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inside and outside,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thnic group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languages,ways of life,customs and habits.In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after Qin and Han Dynasties,the distinction of “Hua” “Yi” actually had four specific expression forms and meaning types.Political struggle situations,especially the strategies of legalization of the rulers,actually dominated the meaning generation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the distinction of “Hua” “Yi”.This partly reflected the universal law of mental activities and confirmed Quentin Skinner’s view that political thought itself is political action.However,excessive practice and utility of mental activities,as well as closely following the political reality,may easily cause short-term behaviors in thought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also be not conducive to the growth of spirit and the advancement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of a nation.
Key words:the Distinction of “Hua” & “Yi”; Confucian classical; historical context; political situation
基金项目:■湖北省政府委托项目(115-140817)
DOI:10.14086/j.cnki.wujss.2015.0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