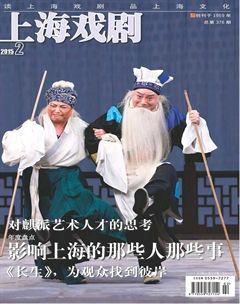但愿那月落重生灯再红
刘轩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伴随着袅袅笛声,2014年12月的第二个周末,北京天桥剧场也透出三春暖意,“大师版”《牡丹亭》在此处热热闹闹地上演了。这可以说是一场真正没有“小角色”的演出,不仅剧中男女主角由当今顶尖的昆曲表演泰斗共同演绎。其他配角的扮演者也都是重量级艺术家,如“闺塾”中扮演春香的魏春荣,“离魂”中扮演杜母的王维艰,“道觋”中扮演石道姑的刘异龙,“冥判”中扮演判官的侯少奎等。全剧由十四出经典折子戏串成,分为上下两本。作为“2014全国昆曲传承汇报演出”的开端,这也被视为一场颇具“典范”意义的演出,值得评说处甚多。但在我看来,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仍然是那个看起来老旧的话题:即如何运用“死”的程式表现“活”的人物的问题,也即昆曲界常说的“活”的传承问题。
昆曲作为我们民族艺术的精华,近代以来几经沉浮,存续至今,此次参演的大师们多曾受教于“传字辈”老师,一招一式,本于一脉,而他们经过自己多年的舞台实践,从自身理解和条件出发,即使是同一个人物,也往往展现出迥异的风采,例如,这次杜丽娘由沈世华、华文漪、梁谷音、王奉梅、张继青、张洵澎、杨春霞七位闺门旦艺术家分扮,沈世华纤弱文秀,华文漪华美端丽,梁谷音个性十足,王奉梅端庄雅致,张继青大气朴素,张洵澎娇俏灵动,杨春霞清新内敛,但不论哪一种风格都能在观众中获得拥趸。在不断强调昆曲正宗的今天,这实在是一个有趣且令人深思的现象。细思想起来,无非就是“合情理”三个字,动静皆从人物起,归于情境中。
以王奉梅的“写真”为例。这是一出比“寻梦”更为难演的“冷戏”,不仅曲词文雅,唱段繁多,而且由于是表现杜丽娘在屋内作画的场景,在身段动作和舞台调度上也不可能像“寻梦”那样大开大合,王老师在20世纪90年代初左右曾得姚传芗亲授此戏,在恪守昆曲程式规范的同时,她从揣摩人物内心情感逻辑出发,适当地加入了一些富有生活情味和情感逻辑的“小动作”,丰富了舞台表现手段,既抓住观众,又恰切地传达杜丽娘此时孤凄落寞的心境。例如,表现杜丽娘看到自己不多时“瘦到九分九”的悲哀和吃惊,其他闺门旦演员一般是作照镜科,继而作猛然一惊状,以手捂镜,低头做悲叹介。而王奉梅此处着力突出了“照镜子”,前后一共照了三次,第一次是春香把镜子拿起来,离杜丽娘还有一段距离远观,王奉梅的杜丽娘在这第一照之后并没有马上立起,而是手托腮微微一愣,面部表情是有些迷茫和怀疑,这巧妙地传达出杜丽娘近日为梦中之情所困,无心理妆已久的背景;第二次是顺着第一次的情感逻辑进行,因为第一次远观效果令人难以置信,所以要再仔细看看,便招手叫春香把镜子拿近前来,而此时春香则做不情愿状,配合渐强的音乐伴奏,整个舞台节奏开始加强,观众的注意力也随之集中到杜丽娘身上,第二次照是全折的第一次情感小高潮,杜丽娘离开座位冲到台前仔细照镜,继而一惊,顺势往后一退,跌坐在座位上,把镜子捂在胸前,表达出杜丽娘看到容颜消瘦后的震惊,经过短暂的停顿后,她又慢慢拿起镜子边看边无奈地摇头,这是第三照。经过这一系列细腻入微的表现,观众明明白白地体会到了杜丽娘此时容颜消瘦的状况和悲戚心情,为下面的描画真容做了非常充分的情感铺垫。
另外,虽然《牡丹亭》是传奇经典之作,但是王奉梅的“写真”出于舞台表现和人物刻画需要,对原作进行了一点小小的改动,即在描容之前,配合【普天乐】的曲牌,增加了一小段“整装”的表演,在我看来这真是神来之笔:首先,这一段表演使得杜丽娘大家闺秀的身份更加鲜明,与“游园”之理妆形成呼应;其次,【普天乐】四句唱在其他版本的表演中,多为杜丽娘对着观众演唱,在这种情况下其中“不因他福分难消,可甚的红颜易老”两句中的“他”难免有指代不明之感,而王奉梅在对镜整装的同时面对镜中人唱这两句曲词,杜丽娘自伤自怜的情绪就自然而然地感染了全场观众,也使得配合这四句唱词的程式动作有了更为明确的内在情感逻辑。
七旦同台,纤瘦浓淡各不同,但都从某种角度传达出了彼时彼刻杜丽娘的闺秀神韵。同样地,四位巾生表演艺术家岳美缇、石小梅、汪世瑜、蔡正仁在舞台上或如春风拂面三分暖,或如壁立梅花沁骨寒,或顽皮或宽厚,也都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岭南才子柳梦梅的书生心性。
“拾画叫画”可谓柳梦梅的本传,是塑造他“情痴而幻”性格特征的关键折子。其中,“拾画”又被称为“男版‘游园”,同之前杜丽娘的“游园”相呼应。周传瑛老前辈曾用“静、雅、甜”来归纳“拾画叫画”中柳梦梅的表演,在我看来,“叫画”中的柳生或许是甜蜜的,但“拾画”中似乎“清峻”些更为妥当,它的情感基调应该是笼罩着淡淡的伤感,而不应过分欢快。
石小梅老师的柳梦梅一出场,并没有像一般出场一样“亮靴底”,而是以幅度较小的台步一步一顿地从上场门走到台口,定睛环视四周,开唱【金珑璁】——一般演员出场,尤其是独角戏,为了在一开始就抓住观众,都讲究亮相,或是身段,或是绝活,或是嗓音,但是在这里,石小梅的头两句唱“惊春谁似我,客途中都不问其他”,却故意放轻了声音缓缓吟出,结合出场特别的台步,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柳梦梅大病初愈的情境。所谓表演一切从人物出发,不光是善于做加法,也要善于做减法,不符合特定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表演,即使再有亮点,也坚决弃之不用。总体看来,石小梅的“拾画”表演与寻常演法相比,节奏略慢了一些,身段动作幅度也较小,例如【颜子乐】中“苍苔滑擦”一句,常见的表现方法是演员双手拎褶子,原地走两个趟步,一只脚在原地向前方和侧边做几下点地,最后做一个滑步。而石小梅老师在表现这一句时放弃了最后的滑步,用左右脚向前方轮番做了三次点地,每次均以脚尖、脚掌和脚跟依次点地三下,最后“擦”字一个小趔趄,向前一小步站稳,一手拎褶子,眼望地面投一只水袖,仿佛在埋怨苍苔为什么这样滑,把柳梦梅表现得既谨慎又有孩子气的天真,令人莞尔。【颜子乐】一曲末尾,柳梦梅看到满园寒花绕砌、荒草成窠,更添惆怅,石小梅唱此句时在“草”字上用了一个腔,观众听来犹似叹息一般,同时在身段上,她没有采用大的调度,只是拎褶子,跑一个小圆场,唱至“窠”站定,放下褶子,却更加逼真地表现出在茂盛的荒草地中穿行的情景。同为生行表演大师的蔡正仁老师曾说:“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演员,在台上动作非常多,这是很容易的;而动作越是少,难度越高。”石小梅的身段表演幅度和动作的复杂程度都不大,但难得都在情境中,如同素描一般,寥寥几笔,一个萧索的园林和一个满怀闲愁的士子便活泼泼立在观众眼前了。
作为一场具有“垂范”意义的演出更为可贵的是,除经典的折子之外,一些过场戏也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道觋”即是如此。上海昆剧团的文丑表演艺术家刘异龙把这出戏演得精彩火爆,甚至掀起了上本的一个小高潮。他扮演的石道姑一出场,并没有立刻走到舞台中央开始插科打诨,而是在九龙口面向半空中有一个停顿,做欣赏科,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当大家正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时,只见他伸手一捞,一朵小花出现在指尖,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用俗话说,这一下就把场子炒热了。这个魔术的运用不仅提升了舞台表演效果,同时也突出了石道姑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爱美,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有了这一层铺垫,之后石道姑愿意担着砍头之罪帮助柳梦梅开棺并一路庇护二人就更好理解了。
凭心而论,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客观因素,大师们在嗓音、气息和扮相上与其艺术巅峰时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演出仍然能使观众身临其境、如痴如醉,尤其是扮演杜丽娘、柳梦梅和春香的几位艺术家,以年迈之躯出演花季少男少女,却能给人传神之感。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于扮演对象心理状态和情感逻辑做了细致深入地体悟,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了解人物,而是把这种对人物的体验与自身对生活和生命的体验结合在一起。正如王奉梅老师讲她演戏的体会时所言,一个演员要演好一个角色,必须投入到人物和规定的情境中去,深入挖掘人物的心理状态。这是对固有的程式化动作做生活化的理解和领悟,并且能够和自己已有的人生经验、情感经历融合在一起,把由模仿得来的程式动作变成自己由内心发出的肢体语言——观众在观赏这种表演时,即使是耳熟能详的老戏码,同样能获得新鲜深刻的感受和触动。窃以为,所谓“大师”,绝不仅仅在于他们从事艺术时间久,能演的戏多,更在于他们能够真正从人物和情节需求出发,融程式于人物之中,一点小动作不管是恪守规范还是锐意创新,都能从人物逻辑的角度解释出道理来——戏之好坏,本没有绝对的圭臬,但看合理不合理,这也是“典范”的意义之所在。也只有合理地传达具有普适性的情感,昆曲之灯才能如再世为人的杜丽娘一般,永远光彩照人。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在读博士生)